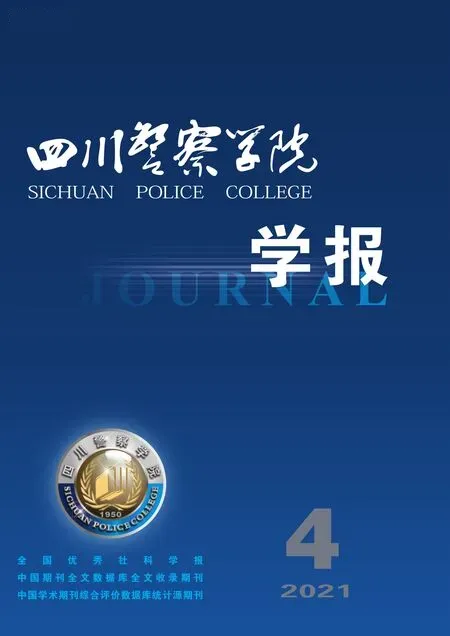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研究
趙何佚璽
(四川大學 四川成都 610207)
2016 年11 月兩高三部聯合發布《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的工作辦法》(以下簡稱《試點辦法》)標志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實踐中的落地[1]。但這并非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舞臺初現,為解決我國案多人少的矛盾,實現案件分流,早在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問題的重大決定》中黨中央就確定了“完善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藍圖。由此可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產生是“大勢所趨”。誠然,作為一種緩解案多人少矛盾,提高司法效率的手段,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效益是有目共睹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我國從試點至今已運行整整四個年頭,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推行,其帶來效益的同時也顯現出不少弊端。正如辯訴交易所揭示的道理,效率的提升往往伴隨著權利的讓渡,一味倡導程序加速或許面臨著權利保障不足的尷尬局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架盡管不同于辯訴交易,但其效率價值優先的內涵恐怕同樣難逃辯訴交易中被害人權利保障被弱視的結局,慶幸的是,這種隱患早在制度創設之初就引起了改革家以及理論者的警覺。權利保障視角下,這些擔憂多瞄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卻鮮有問及被害人,從《試點辦法》的出臺到2018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再到2019年10月24日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從制度的變遷中均能尋覓到“重被告、輕被害”的改革基調。因此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中,被害人權利保障已然被置于邊緣化的地位,面臨著挑戰“定紛止爭”這種傳統訴訟理念的局面。被害人作為在刑事案件中是被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對象,其盡管在訴訟中具有訴訟參與人的身份,但仍然不能相較于以國家力量為支撐的檢察機關。無論辯訴交易還是認罪認罰從寬,作為一種以認罪協商為基礎的恢復性司法,不能僅以受損害的國家秩序為修復對象,同樣重要的是直接受侵害的被害人,其應該被置于恢復性司法的首要地位[2]。因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過程中,從多角度對被害人權利構建保障體系甚為重要。但是,在權利構建的同時還應該注意到實際可操作性,即對被害人權利保障之提議并非就直言要將其權利上升到同被告人同等的高度才算完善,值得注意的是效率價值為何會與程序價值相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背景是我國案多人少的矛盾,目的是實現程序簡化,提升效率。效率價值相較于程序價值而言,效率價值契合于我國的司法現狀。從這個角度出發,如果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過多強調被害人權利保障,或許會導致效率難以提升,制度的愿望落空等結局。因此,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中,被害人的權利需要保障,因為這是契合訴訟目的之需要,同時也要警惕這種權利保障的呼聲成為制度發展的阻礙,尋找到讓這二者價值雙贏或者雙雙妥協的平衡點是至關重要的。
一、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現狀及問題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初具形態到如今體系完備已經歷整整四個年頭,其間司法實務界和理論界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討論也從未間斷,并且這些理論的爭鋒還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是,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研究卻鮮有人問津,既有的研究成果尚處于《刑事訴訟法》修正前后的時期,不具備時效的前沿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新的變化難以用舊的研究來總結,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現狀和制度創設之初相比已是今非昔比,無論從理論、司法實踐、還是制度上,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都有了新的發展。因此,在新語境下對現狀進行梳理并發現問題是研究的大前提。
(一)被害人權利保障現狀:形式完備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試點至今的四年中,實體制度的變遷伴隨著學界理論的呼聲大致完成了兩次跨越。第一次是從《試點辦法》到刑訴修正案的正式確立,第二次是2019 年10 月24 日兩高三部《指導意見》的出臺。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相關規定隨著制度的變遷同樣在發生變化。《試點辦法》第29 條規定主要是對認罪認罰從寬的程序事項作出了規定,其中有四條涉及“被害人”的相關規定,可見于《試點辦法》第3 條,第7 條和14 條以及第17 條中。第3 條規定了“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要重視被害人權益的保障”。第7條規定了“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應該將是否和解,被害人是否諒解作為量刑參考,同時還應當聽取訴訟代理人以及被害人在案件中發表的意見”。第14 條規定了“案件中對于被害人涉案財物的返還問題”。第17 條規定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將被害人與被告人沒有達成調解或和解協議的作為不適用速裁程序的類型”。解讀《試點辦法》對被害人的規定可以看出實際上涉及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只有第3條和第7條,第14條和第17條中關于被害人的規定僅僅是程序性規定[3]127。《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實現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法律銜接,實現了從試點到正式運行的跨越。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多處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定,例如:第15 條就首先規定了認罪認罰從寬的概念,其余的規定多集中在提起公訴部分。《刑事訴訟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權利的保障可見于第173 條,其中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應該聽取……訴訟代理人和被害人在規定事項上發表的意見……”;2019年10月24日兩高三部發布的《指導意見》中,第五部分對被害人權益保障做了更全面專門的規定。主要有三點,“第一,辦理認罪認罰的案件時,應當聽取訴訟代理人和被害人對案件發表的意見;第二,辦案機關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要積極促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被害人一方進行賠償損失以及賠禮道歉,積極取得被害人一方諒解;第三,被害人一方若反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并非一律有效。”可以看出,從《試點辦法》到《指導意見》,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制度實現了由模糊到具體、由缺乏到完備的構建。
在認罪認罰從寬的推行中理論界的呼聲同樣也是見仁見智,絡繹不絕。盡管此語境下權利保障的關注多向被告一方傾斜,但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研究同樣存在多種看法。最高檢陳國慶副檢察長認為“在推行認罪認罰從寬的過程中應當重視被害人一方的意見,要將這種認罪協商和被害人一方的同意掛鉤,評價標準就是看被害人一方是否收到被告方在精神以及物質方面的賠償并對被告方進行諒解。”[4]陳衛東教授則認為“推行認罪認罰從寬要注意效率價值和權利保障的沖突,效率優先的制度底蘊要防范權利保障語態下被害人一方主觀變化導致影響協商進程,因此不宜對被害人賦予過多權利從而使其對案件協商進程產生影響。”[5]劉少軍教授認為“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要構建認罪與認罰從寬不同的話語體系,認罪協商中被害人應當具備更多的話語權,而認罰從寬程序中為了不影響協商進程,被害人只能具備輔助地位。”[3]137-138何靜副教授認為“在推行認罪認罰從寬的過程中推動被害人方權利保障體系的構建不僅監督公權力的行使還可以彰顯當事人的主體地位,然而遺憾的是現行制度中對其權利保障的規定是缺乏的。因此在被害人權利保障的語境中可以考慮構建‘知情權’‘參與權’‘獲得賠償權’‘救濟權’。”[6]從上述理論觀點可以得知,在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爭鳴主要體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要不要保障”,二是“如何保障”。“要不要保障”問題的爭論焦點體現為認罪認罰從寬的效率價值與程序價值之沖突,過于倡導被害人權利保障恐會導致被害人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濫用權利,導致訴訟效率降低背離改革初衷。“如何保障”問題的爭論焦點中,學界觀點多認為認罪認罰不能犧牲被害人應有的權利保障,應當提升被害人在新語境下的權利保障使其具備話語權。具體來看就是賦予其在程序中的“救濟權”“提出異議發表意見權”“知情權”“法律幫助權”。
(二)被害人權利保障隱患:實質缺乏
通過制度和理論現狀的梳理大致可以發現幾點問題,一是制度上對被害人權利保障的關注不夠,其二是理論呼吁的滯后,沒有起到引導制度變遷的作用。從《試點辦法》的規定來看,總共有29條,僅有四條和被害人有關,其中和被害人權利保障相關的僅有第3 條和第7 條。第3 條統領性的指出了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過程中要保障被害人權利。第7 條則是被害人權利保障的具體展開,可以看出第7條實際上是第3條的具化和展開[7],29個條文中僅有兩條涉及被害人權利保障,因此可以看出試點之初制度的創設并未過多考慮被害人權利保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三年所沉淀的司法實踐經驗通過《指導意見》有所體現,盡管對于被害人權利保障有了專項規定,但仍然顯露出保障不足的缺陷。例如:《指導意見》第16條規定的“聽取意見權”可以看作是《試點辦法》第7條的復述;第17條前半段規定的“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對于認罪認罰的嫌疑人、被告要積極促進當事人自愿達成和解”,實際上是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必然要求,應有之義;而第17條后半段規定的“公檢法在認罪認罰過程中應當充分聽取被害方意見”又和第16 條規定有所重復。《指導意見》中具有新意的當數第18條的規定,第18條規定了被害方異議的處理程序,可以說是對理論爭鳴的一種回應,但具體制度安排卻同樣又暴露出對被害人權利保障體系構建的欲言又止,例如第一句話就規定了“被害人一方不同意對被告方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并不影響從寬制度的適用”,這意味著新語境之下被害人仍然沒有話語權,其無論是否同意都不影響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綜上所述,盡管表面上看起來《試點辦法》和《指導意見》對被害人權利保障的規定更多,實際上卻呈現出保障不足的尷尬局面。
理論研究上存在關注不足、制約不足的問題。關注不足首先體現在研究成果的數量上,目前為止在知網能檢索到的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專業性論文數量有限,且多集中在試點前后時期。其次是沒有時效前沿性,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正式納入刑訴法以及《指導意見》的出臺,被害人權利保障有了一些專門規定,例如此前學者所倡導的知情權、提出異議權、發表意見權等基礎性權利均已在制度中予以明確。而制約不足主要體現在《指導意見》出臺前學者們所呼吁的“救濟權”“法律幫助權”等實質性權利并未得到制度關照[8],從而表現出理論呼吁無關于制度痛癢的現象。
制度和理論的發展最終和司法實踐相關聯,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現狀和理論現狀所呈現出的保障不足的問題也得到司法實踐的印證。有調查數據表明,在149 個認罪認罰的并且有被害人的試點案例中,僅有58.39%的被害人獲得了被告人的積極賠償并作出諒解,并且在取得諒解的案例中85.49%是被判處拘役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況[9]。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是被害人權利保障不均衡,輕罪案件的被害人更容易同被告達成和解,而重罪案件被害人基于和被告的緊張關系反而較少在認罪認罰程序中得到修復和彌補;其二是仍有41.61%的被害人沒有得到被告方的積極賠償。不難看出,無論理論還是制度上抑或刑事司法實踐中,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已然被邊緣化,權利保障岌岌可危。
二、權利保障不足之成因探析
被害人權利保障缺乏的問題無論是制度改革之前還是之后都一直存在。但是,此前按部就班式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對被害人保障所具有的缺陷在認罪認罰從寬中暴露的更加明顯。因而可以說,認罪認罰從寬觸動了被害人權利保障問題的短板,拉燃了被害人權利保障不足這種隱患的導火索。總結其原因不外乎有三方面,一是我國刑事司法所獨有的重被告輕被害人的司法慣性,二是認罪認罰從寬效率優先的制度原理要排斥程序加速的阻礙,三是理論呼聲底氣不足,沒有博得制度關照。
(一)“輕重有別”的刑事司法慣性使然
司法實踐中“重被告、輕被害”的觀念是造成被害人權利保障缺乏的首要因素。其權利保障的缺乏并非是認罪認罰從寬這項制度的獨有缺陷。拋開自訴案件不談,刑事案件由檢察機關行使審查權和起訴權并代表國家追訴犯罪。這種模式使檢察機關和被告形成了對抗格局,而有強大國家后盾的檢察機關和弱小的被告人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制度和理論應更多地朝向如何構建一個權利平等的舞臺,對被告的權利進行全方位關照,這種對被告的關照在刑訴法的變遷中反映得明明白白。例如辯護權、非法證據排除、庭審實質化等制度的改革都是朝著如何構建控辯平等的格局發展。對被告方權利保障的過多關注必然導致程序利好偏重一方,顧此失彼。檢察機關履行追訴職能代表了被害人和國家利益雙重主體之訴求,易言之,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應受到的關照面臨被國家公共利益這一主體擠占的局面[10]。不難看出,作為侵害行為直接對象的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應該得到的權利保障被削弱了兩次,一是控辯平等格局之下對被告人權利的傾斜削弱了對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照顧,二是檢察院所承擔的代表國家的公訴職能擠占了被害人應得的權利保障。由此可見,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行之前,我國被害人權利保障已然成了短板,這和我國的訴訟構造是息息相關的。在制度的影響下,對被害人的忽視更是演變為一種司法慣性,例如在近年來所頻繁出現的冤假錯案,媒體和理論的關注點多集中于如何提高被告人權利保障,卻很少有焦點關注到被害方,這也就是念斌案中兩名被害人的母親最終只能以披麻戴孝靜坐法院的方式為逝者討公道的原因[11]。盡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種克服案多人少矛盾的有力手段,但并未觸及制度的結構安排,即便是認罪認罰的情況下案件同樣遵循三道刑事程序,法庭上同樣表現為控辯兩方對抗。既然結構未變那么“重被告、輕被害”的司法慣性就同樣要波及到這種新的制度安排,易言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缺失其原因之一是來自于訴訟結構本身所附隨的重被告輕被害的司法慣性。
(二)效率優先的制度原理使然
認罪認罰從寬效率優先的制度原理是導致刑事被害人“權難得”的重要因素。《指導意見》開篇中就對其制度的意義做了解釋性規定,“適用……推動刑事案件簡繁分流、化解社會矛盾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看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基點著力于實現案件的簡繁分流,背景是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所存在的“案多人少”的這種凸顯矛盾。不難看出,效率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所追求的價值之一,這種效率價值論目前也達成了理論界的共識。例如:秦宗文教授認為“認罪認罰從寬本質上就是程序加速,其目的就是實現我國案多人少背景下的案件快速處理。”[12]林喜芬教授認為“速裁程序作為認罪認罰從寬的一種經驗基礎,其背景就是普通訴訟程序過于繁瑣,擠占了司法資源,以及簡易程序不簡,導致案件積久難決。”[13]汪建成教授認為“刑事訴訟裁程序作為制度改革的載體應該將提升司法效率作為唯一的價值選擇而不是賦予其他價值訴求。”[14]。不難看出,在認罪認罰的這項制度試點之初,理論界已然就“效率優先”達成了共識。然而對效率價值的追求與權利保障具有先天張力,過于強調當事人權利保障可能會導致對效率價值的追求難以實現。同樣,在此項制度中,效率優先的指導原則必將導致那些阻礙效率的因素難以生存。效率是量和時間的比值,此項制度中效率優先就意味著快速的處理案件,此語境下若過于提倡被害人權利保障則會使程序停滯不前,難以達到效率。或許有觀點認為,認罪認罰從寬語境下賦予被害人權利保障并不會對司法效率產生太多影響,在此制度中的協商并讓被害方加入既能體現刑事司法正當性,同樣也更有利于效率的提升。筆者認為,這樣的設想當然存在,但也并非絕對存在。對于輕罪案件,訴訟兩方的矛盾更容易達成和解,被告人一方可以通過積極賠償被告人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諒解,這樣即修復了損傷的社會關系,提升了案件處理效率,也修復了被害人所受的損害,對各方來講都是皆大歡喜;而在重罪案件中,被告和被害之間矛盾深重,想要達成和解諒解十分困難,司法實踐中存在許多被害人“漫天要價”的情況,雙方僵持難斷,造成案件累計,久拖難決。因此,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效率為目標的語境下,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勢必要讓渡于對效率的追求。
(三)理論呼吁未得到制度關照
理論關照缺失是造成新制語境下權利缺乏保障的又一因素。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至今的四年時間中,在理論界不斷爭鳴與交鋒并將討論推向頂峰的過程中,并未有太多的焦點關注到躲在隱秘角落的被害人。時至今日,筆者在中國知網上檢索到的關于“認罪認罰從寬、被害人權利保障”主題的專門性文章仍然寥寥無幾,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就更是屈指可數,總體上呈現出研究不足、時效滯后的局面。或許有觀點會認為這種缺乏關注是由于不少學者已然認識到認罪認罰從寬中對效率價值的追求注定與權利保障必將背道而馳,因此在這種新語態之下討論舊頑疾等于是“提了也沒用,索性不提”。但筆者認為這種考慮卻有失偏頗,一方面是理論的呼吁是否可采并不能決定理論研究的要式性,是否可采是立法者的選擇。二方面是盡管權利保障和效率價值相背逆,但學者們對于被告人權利保障卻是津津樂道。概言之,與其說是擔憂新制度之下被害人一方權利體系構建的可行性,倒不如說是在新制度之下過多的熱點吸引了過多的關注而忽略了被害人權利保障這個現實問題。在制度試點之初就有不少學者對被害人權利保障格局的構建貢獻了十分具化的意見,例如刑訴訟程序中適用認罪認罰從寬這項制度應該征得被害人一方的同意,其享有在辦案過程中發表意見的權利[15],其還應具有“知情權”“獲得法律幫助權”“救濟權”等權利。但理論的呼聲雖然得到了制度的回應但卻沒有博得制度的青睞,制度的回應在于通過理論的吶喊,最終《指導意見》中對其權利保障有了專門性規定,但遺憾之處是這種制度回應太少,僅僅具有形式上的保障,不具備實質可操作性。《指導意見》第16、17條之中,明確規定“被害人有提出意見的權利,同時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是否從寬應該聽取被害人一方的意見”,這可以看成是對理論界其權利保障呼吁中的“意見權”“知情權”的制度回應。第18 條中規定的“被害方異議的處理”可以看成是對被害人提出異議權的制度回應,對于“獲得法律幫助權”“救濟權”等至關重要的權利卻只字未提;《指導意見》第3 條規定中同樣也表現出了矛盾之處,例如在前兩條中規定了被害人的“意見權”,但在第17條中卻規定“被害方不同意對被告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的并不影響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這種“即肯定又否定,先肯定后否定”的制度設計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實踐中會導致制度形同虛設、缺乏可操作性的現象。理論的呼聲沒有得到制度的關照,這既是被害人權保障的理論現狀,也是被害人權利保障不足的原因。既然在理論和制度的雙軌上對被害一方的關照都力不從心,那么在新制度的司法實踐中被害方的權利保障便更加沒有操作方案與保護依據。
三、新語境下權利保障的現實意義
認罪認罰從寬的改革背景之下疏于對被害方權利保護的討論實際上也表現為一種對司法實踐隱患的擔憂,擔憂其權利的高調倡導恐阻礙制度發展的進程。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權利保障和效率雖然表現出一定的張力,但這并非意味著對效率的追求就可以罔顧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相反,在這種改革的新語境之下強化其權利話語體系在順應法律原則、銜接制度規定、解決潛在隱患方面有重要意義。
(一)人權保障的應有之義
《刑事訴訟法》第2 條便規定了“保障人權”是基本任務,這種權利保障的原則不論用何種解釋方法都不能認為其僅僅只是保障刑事被告一方的權利,而應該保障訴訟各方的權利。簡單地講,被害一方作為訴訟參與人其權利保障是刑訴法的基本原則,而制度的改革創新不能以犧牲原則為代價,易言之,人權保障的基本觀念必須延伸到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然而,這種權利保障原則到了新的制度中卻轉變了話風,更多的關注投向了被告方權利體系的構建,而被害一方的權利保障則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正當化權益面臨著被侵犯的危險。例如在制度中的認罪環節是否存在統一的對嫌疑人和被告人悔罪與否的判斷標準?司法實踐中存在不少為了換取認罪認罰從寬的適用而虛假認罪的情況,在辦案機關面前認罪,在被害人面前卻不認罪。因此若在認罪階段忽略了被害人的權利保障,那么后續的從寬處罰就不具備正當化依據,和制度設置的初衷背道而馳;在認罰階段,《指導意見》中對認罰從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都做了具體說明,即“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要接受偵查機關處罰和檢察機關的量刑意見并且要簽署具結書”。無論檢察機關的意見還是偵查機關的處罰決定抑或法院的處理結果,其作出的依據之一便是被告人的悔罪態度,而悔罪態度的衡量不僅看是否認罪還要看是否對被害人進行精神和物質賠償,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諒解。然而在《指導意見》第16 條中卻規定“被告人未能退賠退贓,賠償損失,和被告人達成和解諒解的,從寬應酌減”,可以看出被告方是否積極主動賠償損失,是否積極取得諒解達成和解并不是衡量是否從寬之絕對條件;同樣的,《指導意見》第8條規定從寬包括實體從寬和程序從簡,質言之,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真誠悔罪,那從寬的依據從何而來?綜上,新語境下,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缺失存在于刑事程序的各個階段,這種權利保障的缺失讓認罪認罰從寬這項制度丟失了正當化理由,對被告人從實體和程序上給予優惠都沒有依據,背離了刑訴法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16]。因此,只有在新語境下落實其權利的保障體系和原則才能使這項制度在司法實踐中運行流暢。
(二)制度邏輯的必然要求
認罪認罰新語境下全方位構建被害方權利的保障格局對化解制度矛盾,使其銜接一體具有重要意義。新制度的出現對我國既存的刑事和解制度帶來了沖擊,兩種方案在運行邏輯上表現出矛盾。其和刑事和解作為我國自生自發的本土化的理論成果具有相同性質,刑事和解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認罪認罰從寬。從適用范圍上看,《指導意見》第5條規定“認罪認罰從寬沒有適用罪名和判處刑罰的限制,適用于所有罪名”。《刑事訴訟法》第288條規定“刑事和解制度僅適用于刑法分則第四、第五章中規定的并且刑期在三年以下的情況,以及除瀆職罪外判處七年以下過失犯罪案件”,不難看出,前者是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以及理論中探索出來的積極成果。從二者適用條件的對比來看,適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真誠悔罪,并且通過積極賠償以及賠禮道歉的方式取得諒解及達成和解”,可見諒解和同意是適用刑事和解這項制度的前提條件,否則不能適用刑事和解。認罪認罰從寬中適用條件僅僅只是“承認其罪,認可其刑”,同時結合《指導意見》第18條可以看出被害人是否同意僅僅只是酌定參考因素,并非決定因素。因此,兩種制度就表現出矛盾,即“輕罪案件的刑事和解都需要被害人同意,而重罪案件的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卻無足輕重”,普通程序中其權利保障已然不足的情況下在制度變化的新語境中無異于雪上加霜。在新語境之下化解老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正視這種矛盾并且在制度中對其權利保障給予更多關照,使其在訴訟中享有的權利在形式和實質上都能和刑事和解制度銜接。
(三)防范風險的有力手段
恢復性司法的理念作為一種世界潮流,在我國同樣也得到了推崇,例如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提倡讓被害人參與到訴訟程序中和被告進行對話,最終達成和解諒解,一定程度上讓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中得到了滿足,所受到的傷害也通過對話交流得到了修復。恢復性司法重在恢復,被告與被害兩方的溝通對話,讓被害人在訴訟中能夠表達意見和提出要求,通過溝通對話這個過程修復被害人在侵害過程中所受傷害。作為一種我國司法實踐中自生自發的一種智慧結晶,刑事和解為何要讓被害人參與其中,其背后原理值得深思。正如陳瑞華教授所言“訴訟參與人如果在案件中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張,不能在訴訟中提出證據為自己的觀點辯解爭論,那么將會失去對司法所要求的公平正義的信賴,造成這種后果的因素便是對其權利的忽視”[17]。不難看出,若在刑事案件處理過程中忽視其權利保護,那么必然將對其造成“雙重傷害”,一重傷害來源于被告,二重傷害來源于公檢法等官方機構。這種忽視被害人所造成的多重傷害會造成兩方面的后果,其一是,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作為直接侵害的對象,本應具有主導性的話語權,這種權利的剝奪將會導致被害人和被告之間的矛盾被推向高潮,恐造成社會矛盾。其二是,被害人在訴訟中得不到的權利將會通過其他途徑爭取,例如司法實踐中被害人更多通過申訴這種方式喊冤,即浪費了司法資源也違背了效率優先的初衷。筆者在國家統計局的網站上查詢了最新的檢察機關處理申訴案件的數據[18],如表1所示,在刑罰執行中和刑罰執行完畢后均有被害人申訴的情況,受案分別是2632件和1143 件,立案復查的數量分別是1078 件和442 件。由此可以提煉出兩個結論,一是司法實踐中刑事被害人申訴的情況十分普遍,二是被害人的申訴最終有一半得到了立案復查。從上述高申訴量可以推論出,在被害人權利保障缺失的語境下提升其權利話語體系是十分重要的。認罪認罰從寬作為一種刑事案件簡化處理的制度探索仍然難以脫離刑事訴訟程序和原則的規制[19],如前所述,和刑事和解制度比起來其對被害人權利保障方面的安排更缺乏,不難推論出“新的制度語境之下被害人的這種矛盾可能會讓這種結果愈演愈烈”。因此,在這項制度中對被害人權利給予全方位保障是防范社會風險和司法隱患的有力手段。

表1 2018年人民檢察院處理申訴案件情況(單位:件)
四、新語境下被害人權利保護的路徑
“被害人權利保護有三方面的內容:首先是被害人保護論,即在訴訟程序中保護被害人受到‘二次傷害’;第二是被害人介入論,讓被害人介入到刑事程序,在訴訟中具有話語權;第三是被害人的救濟,即被害人從被告以及國家獲得賠償補償以彌補損傷”[20]。認罪認罰從寬作為一種案件快處的司法應對方案,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同樣應該從這三方面進行構建。從試點期間學界形成的理論觀點來看,對其權利的保障也進行了全方位的提議,比如要保障其具備“知情權”“意見權”“異議權”“獲得法律幫助權”“救濟權”等基本權利。時隔四年,從《指導意見》第16條“聽取意見”以及第18條“被害方異議的處理”可以看出試點之初學者們所提出的賦予被害人“知情權”“發表意見權”和“提出異議權”三種權利都得到了正面回應,但這種制度安排僅僅只保障了被害人參與,但和被害人保護以及被害人救濟有關的“獲得法律幫助權”以及“救濟權”卻只字未提,若被害人沒有權利獲得法律幫助以及救濟,那么也很難保證被害人能真正的參與到訴訟程序中。結合現狀,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還需要從法律幫助權和救濟權兩方面著手。
(一)獲得法律幫助權
被害人權利保障缺乏的現狀在法律幫助方面表現尤為突出。《指導意見》第四章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第10 條至第12 條規定對如何保障更是進行了詳細說明,比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法律援助中心要安排值班律師專門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務[21],并且對值班律師如何進行法律幫助都進行了事無巨細的規定。然而在《指導意見》第五章節被害人權利保障中并未看到有同樣的福利,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的法律幫助權并未得到特殊關照。如前所述,認罪認罰從寬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不足實際上也體現出了立法者的擔憂,對被害人的關照恐造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難以推行,這種矛盾關系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被告和被害的對立關系,其二是會與查明真相發生沖突。結合新形勢下所出臺的《指導意見》,筆者認為,對被害人構建法律幫助權并不會對認罪認罰從寬造成阻礙,相反有助于效率提升。首先,被害人對刑事程序的阻礙大體表現為兩方面,其一是“漫天要價”造成被告人難以承受最終未達成和解,其二是被害人執意要求從嚴處理被告,不接受和解。然而《指導意見》第18條中規定了“被害方不同意對認罪認罰的被告從寬處理的不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被害方賠償請求明顯不合理,不影響被告的認罪認罰從寬”,可以看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方想通過“漫天要價”和執意處罰被告的偏執來阻礙訴訟進程的意圖注定不會實現。其次,盡管認罪認罰從寬是基于效率優先,但它并不能以犧牲程序正義為代價。作為一種處理刑事案件的制度,必須要體現出被害人的話語體系。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種類是多樣的,這種多樣表現為“傷害程度多樣”“被害人經濟條件多樣”“被害人知識水平多樣”等,很多刑事案件被害人面臨著“沒錢治療救命”“不知自己有何權利”“不知自己如何參與案件”“不知如何協商”,正是因為如此之多的無奈,被害人才走上不斷申訴上訪的道路。在認罪認罰從寬中賦予被害人法律幫助權可以讓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了解自己的權利,通過律師表達自己的訴求,與被告就救治費用等方面進行溝通,積極協商并及時得到賠償。由此看來,無論用哪種程序制度來處理刑事案件,被害人作為直接受害對象必須要從訴訟中得到修復和補償,因此那種效率優先的政策同樣也繞不開修復被害人所受損傷的必然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不聞不問留下隱患還不如直接引入律師幫助權,讓被害人在認罪認罰從寬中得到形式和實質上的幫助,這相反是提高了訴訟效率。當然對被害人的法律幫助權并非意味著要提高到與被告人辯護權比肩的高度,具體操作辦法上,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指導意見》中對被告人辯護權保障的規定[22],在被害人權利保障中新增“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有義務保障被害人獲得法律幫助”,同時也應當明確,這種法律幫助僅限于為被害人提供程序上的法律銜接,讓其更快融入認罪認罰從寬這種程序中來。當然,具體如何進行制度安排還需要決策者統籌兼顧,全盤考慮。
(二)獲得救濟權
“無救濟則無權利,權利的有效行使需要依靠救濟制度的保駕護航。”[23]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獲得救濟的權利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上的救濟,二是權利上的救濟。刑事案件中難以排除被害人被告人雙方都沒有錢的情況,而被害人的救助具有緊迫性,因此對被害人的經濟救濟從制度上進行保障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可以使得被害人所受的傷害得到及時的止損,二方面可以使被害人感受到在刑事程序中檢察院是真正代表自己在履行對犯罪行為的追訴職能,真正在維護自己的權益。當然對刑事被害人給予經濟上的救助早有規定,例如早在2015 年中央政法委、財政部會同公安部、司法部、最高檢、最高院制定了《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其中就規定了“國家補償原則”。在2020 年10 月15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張軍檢察長作了“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24],其中指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至今“對33040 名被害人發放司法救助金4.89 億元”,可以看認罪認罰從寬中國家在對被害人經濟上的救濟是十分重視的,并且給予了較大的投入。筆者認為,對被害人的經濟救濟還略顯不足,報告中指出僅2019 年1 月至8 月就辦結了1416417 件案子,短短八個月時間就能取得如此高的成效,可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效用是明顯的,但如此之多的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僅有33040 名被害人得到了救濟,救濟率僅僅只有2.3%左右,若以近幾年來辦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總數為基數,則救濟率更低。盡管《指導意見》對被害人的“知情權”“意見權”“異議權”都給予了安排,但這些權利若沒有救濟制度對其進行保障就形同虛設。比如在《指導意見》第18 條中規定了被害人的“異議權”,但緊接著又規定了被害人的異議并不影響對被告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排除被害人無理由、無根據的異議,若被害人的正當異議沒有得到認可并且沒有救濟的途徑,那么為何要賦予其“異議權”?可見條文出現了自相矛盾的局面。
由此可見,在被害人權利保障體系略顯疏漏的情況下,賦予其救濟權是意義重大的,這種救濟包含了經濟的救濟以及權利的救濟。在具體操作上,筆者認為,對被害人經濟上的救濟應該從制度上進行明確,盡管目前司法實踐中對被害人有經濟救濟,但若不從制度上進行安排,將會導致對被害人的經濟救濟不具有指向性;在權利的救濟上,同樣要從制度上進行安排,或許有觀點認為“對被害人權利規定了救濟權可能會造成無休止的救濟,以至于認罪認罰從寬這項制度難以擁有效率優先的優勢”,筆者認為,不能用制度的不足來否定制度的價值,認罪認罰從寬中對被害人權利的救濟給予安排的確會存在阻礙效率優先這種價值的醞釀,但這種缺陷并非是不可抑制的,比如在《指導意見》第18條中就規定了“被害方請求明顯不合理,一般不影響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寬”,因此對于那種毫無根據的異議,辦案人員完全可以按照標準進行判斷。
五、結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試點至今已近四年,其間,討論這種制度的理論交鋒不勝枚舉,但這種你來我往的交鋒卻忽略掉了被害人這個直接受害對象。無論在理論還是制度上,對被害人權利保障的研究都寥寥無幾,其原因或許在于效率優先與權利保障的先天張力,亦或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一直被忽視的司法傳統,但隨著權利保障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恢復性司法世界潮流的前進,這些統統將越來越不能成為阻礙被害人權利保障的論據。盡管《指導意見》對被害人權利保障作了專章回應,明確了“知情權”“意見權”“異議權”,但“獲得法律幫助權”“獲得救濟權”這種實質性的權利卻并未給予制度安排,這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精神是不相契合的。筆者建言,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要進行全方位的完善,基本路徑是從“法律幫助權”和“救濟權”兩方面著手,讓被害人在認罪認罰從寬這種效率從快的視角之下仍然能夠體會到程序的正義。唯有如此,才能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效率優先的價值目標提升到極致,才能讓制度中已有的被害人權利保障規定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