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意引誘型誘惑偵查裁判規(guī)則實(shí)證研究
畢清
(福建師范大學(xué) 福建福州 350108)
實(shí)踐中對(duì)于那些具有常習(xí)性、隱秘性高而取證困難的特定犯罪,偵查機(jī)關(guān)有時(shí)會(huì)以“特情人員”隱匿身份使用所謂的“陷阱”或“提供機(jī)會(huì)條件”等方式抓獲犯罪嫌疑人,這類偵查手段在理論上被稱為誘惑偵查,并根據(jù)被誘惑對(duì)象此前是否具有犯罪傾向劃分為“機(jī)會(huì)提供型”和“犯意引誘型”。2018 年《刑事訴訟法》第153 條規(guī)定將誘惑偵查納入法治化軌道。對(duì)此,理論界普遍認(rèn)為該153 條的但書條款部分表明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禁止實(shí)施犯意引誘型的誘惑偵查手段,但并未從整體上否定誘惑偵查手段的合法性①。據(jù)此,本文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展開進(jìn)一步分析。
“犯意引誘”一詞通常被認(rèn)為來源于日本,目前學(xué)界對(duì)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duì)犯意引誘的界定,如對(duì)“犯意引誘”“數(shù)量引誘”與“誘惑偵查”等相關(guān)概念的區(qū)別[1]。當(dāng)然也有關(guān)注到“犯意引誘”的證明等問題,例如,臺(tái)灣地區(qū)林鈺雄教授認(rèn)為,被告人客觀上是否具有犯罪的犯罪嫌疑、主觀上是否具有犯罪的意圖、被告人最終的犯罪意圖是否超越了引誘的界限、警察引誘的方式和強(qiáng)度是否對(duì)被告造成了促使其犯罪的壓力是認(rèn)定警察的引誘行為是否屬于犯意引誘的四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2]。針對(duì)同一問題,不同學(xué)者的認(rèn)識(shí)存在差異:艾明認(rèn)為對(duì)于“犯意引誘”的認(rèn)定上,不僅要審查被引誘者,還應(yīng)當(dāng)審查偵查機(jī)關(guān)行為的合法性[3];田宏杰則認(rèn)為被引誘者必須存在重大犯罪嫌疑是啟動(dòng)正當(dāng)?shù)恼T惑偵查的前提,以引誘行為本身不能與犯罪意圖或行為有因果關(guān)系為界限[4]116-126。就犯意引誘的法律后果而言,翟金鵬教授則認(rèn)為若被告并無初始犯意,被引誘行為一般不會(huì)產(chǎn)生客觀危害結(jié)果,故沒有犯意的被引誘者不應(yīng)當(dāng)被追究刑事責(zé)任[5]。由此可見,學(xué)界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研究主要是從理論方面入手,以合法的誘惑偵查為切入點(diǎn)對(duì)犯意引誘進(jìn)行考察,反映出了學(xué)界較少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進(jìn)行獨(dú)立觀察,缺少了相關(guān)裁判規(guī)則的實(shí)證研究。
從司法實(shí)踐的角度來看,“不得誘使他人犯罪”是單純不得引誘犯罪人產(chǎn)生犯意,還是需要從整體上判斷偵查機(jī)關(guān)的行為形態(tài)以及手段是否妥當(dāng),法律上既無明確標(biāo)準(zhǔn),實(shí)務(wù)中對(duì)相關(guān)案件的處理也較為混亂。為此,本文擬通過實(shí)證研究的方法,對(duì)法院裁判過程中在認(rèn)定是否存在犯罪引誘問題上的論理進(jìn)行歸納總結(jié),繼而提煉出中國刑事司法實(shí)踐對(duì)犯意引誘所持的標(biāo)準(zhǔn)與規(guī)則。
一、法律法規(guī)文本中的“犯意引誘”
為了打擊毒品犯罪、集團(tuán)犯罪等具有高隱蔽性、高程度組織化犯罪行為,偵查機(jī)關(guān)在偵查活動(dòng)中多采取了隱匿身份、誘使被偵查對(duì)象落入圈套等手段,這些特殊手段大大打擊了此類特殊犯罪行為,相應(yīng)的也產(chǎn)生了一些問題。為了規(guī)范由此涉及的問題,相關(guān)司法機(jī)關(guān)陸續(xù)出臺(tái)了一些規(guī)范文件。
(一)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
在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偵查手段中的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主要依據(jù)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實(shí)踐中,偵查機(jī)關(guān)在毒品案件偵查中多采取誘惑偵查的手段,但是無論是司法實(shí)踐還是理論界都對(duì)誘惑偵查到底是國家追訴犯罪還是制造犯罪產(chǎn)生了極大的爭論。作為傳統(tǒng)偵查手段的補(bǔ)充與輔助,“采取一定誘惑手段”“提供條件或制造機(jī)會(huì)刺激犯罪發(fā)生”將誘惑偵查②[4]116-12中偵查機(jī)關(guān)是促使犯罪人犯意暴露還是使犯罪人產(chǎn)生犯意的問題,特情人員受到公安機(jī)關(guān)支配再去尋找賣家的行為是機(jī)會(huì)提供型犯罪還是犯意誘發(fā)型犯罪的問題拋了出來。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將犯意引誘定義為行為人本沒有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jìn)而實(shí)施毒品犯罪③。對(duì)“持毒待售”“準(zhǔn)備實(shí)施大宗毒品犯罪”采取特情貼靠、接洽破獲的案件則認(rèn)為不存在犯罪引誘。對(duì)于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會(huì)議紀(jì)要》規(guī)定應(yīng)根據(jù)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從輕處罰。除此之外,《會(huì)議紀(jì)要》還對(duì)“機(jī)會(huì)提供”“犯意引誘”“數(shù)量引誘”和“雙套引誘”進(jìn)行了識(shí)別④。
(二)《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
2018 年《刑事訴訟法》對(duì)辯護(hù)、證據(jù)、偵查等進(jìn)行了大范圍修改,對(duì)偵查工作影響重大而深遠(yuǎn),為了保證公安機(jī)關(guān)正確貫徹執(zhí)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公安部對(duì)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進(jìn)行了相應(yīng)的規(guī)定。相對(duì)于2018 年《刑事訴訟法》的153 條,2020 年修改后的《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271條⑤肯定了部分誘惑偵查手段的存在,但排除了“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合法性,并且比《刑事訴訟法》153條但書“不得誘使他人犯罪”更進(jìn)一步明定“誘使他人犯罪”是不得采取各種方式“促使他人產(chǎn)生犯罪意圖”,其與2008 年《會(huì)議紀(jì)要》對(duì)“犯意引誘”的定義相符。第273 條⑥規(guī)定合法的誘惑偵查與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肯定了合法誘惑偵查收集的證據(jù)的合法性,但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收集的證據(jù)是否合法未做規(guī)定。
另外,厘清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與控制下交付的適用情形,須識(shí)別誘惑偵查與控制下交付。根據(jù)《聯(lián)合國禁止非法販運(yùn)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相關(guān)條款⑦,控制下交付系法定偵查措施之一,由此取得的證據(jù)并無合法性及量刑的影響。控制下交付與誘惑偵查最顯著的區(qū)別是,誘惑偵查中偵查機(jī)關(guān)在案件中并非僅僅是知情者或監(jiān)控者,而是有直接介入案情之中,促使犯罪嫌疑人實(shí)施犯罪。由于部分特情偵查會(huì)誘發(fā)行為人的犯意即偵查手段超過誘惑偵查的合理范圍,故會(huì)對(duì)定罪量刑產(chǎn)生影響。
(三)“地方性”規(guī)范中的“犯意引誘”
1.四川省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關(guān)于販賣毒品案件有關(guān)犯罪預(yù)備問題的意見》。2001 年四川省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針對(duì)四川省毒品犯罪案件中禁毒偵查部門在運(yùn)用誘惑偵查手段時(shí)存在的問題聯(lián)合制定了《關(guān)于販賣毒品案件有關(guān)犯罪預(yù)備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意見》肯定了公安機(jī)關(guān)可以使用合法的誘惑偵查手段,同時(shí)第6 條規(guī)定“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中,嚴(yán)禁引誘犯罪”。結(jié)合該《意見》第1條和第2條的規(guī)定,使用誘惑偵查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有犯罪預(yù)備行為即“為販賣毒品準(zhǔn)備工具、制造條件”⑧,這是四川公檢法認(rèn)定毒品案件誘惑偵查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犯意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若符合上述條件之一,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此采取誘惑偵查手段,則就不應(yīng)認(rèn)定為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其偵查行為是合法的誘惑偵查行為。
2.廣東省高級(jí)人民法院《關(guān)于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指導(dǎo)意見》。為進(jìn)一步依法嚴(yán)厲打擊毒品犯罪活動(dòng),準(zhǔn)確執(zhí)行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廣東省高級(jí)人民法院根據(jù)廣東省各級(jí)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經(jīng)驗(yàn)以及2002年的實(shí)際情況,對(duì)毒品犯罪案件審判實(shí)踐中亟須解決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相關(guān)意見。其中對(duì)于特情介入的問題,該意見認(rèn)為在以下兩種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屬于犯意引誘,應(yīng)從輕處罰:(1)確有證據(jù)證明被告無犯意;(2)特情主動(dòng)提出、多次要求等手段引誘。但是存在以下幾種情形,不宜認(rèn)定為“犯意引誘”或“數(shù)量引誘”:(1)特情雖主動(dòng)提出,但被告人對(duì)此一拍即合;(2)被告人積極實(shí)施毒品犯罪行為。
并且對(duì)于特情介入的案件中不能確定屬于引誘,但難以排除引誘因素的,《意見》規(guī)定可以根據(jù)案件具體情況酌情考慮,不宜對(duì)被告適用死刑的量刑標(biāo)準(zhǔn)。
3.遼寧省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關(guān)于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dǎo)意見》。遼寧省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結(jié)合本省毒品犯罪案件實(shí)際情況,對(duì)辦理毒品案件中涉及的特情引誘問題提出相關(guān)意見。首先,對(duì)存在犯意引誘與數(shù)量引誘的案件的量刑作了區(qū)分:對(duì)于具有犯意引誘的被告人,應(yīng)從輕處罰,且無論毒品數(shù)量多大,都不能判處死立執(zhí);而具有數(shù)量引誘的被告人在從輕處罰時(shí),若毒品數(shù)量標(biāo)準(zhǔn)超過死刑標(biāo)準(zhǔn),一般情況下也不能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其次,針對(duì)間接受特情引誘的被告人,該意見規(guī)定應(yīng)對(duì)被告從輕處罰,且在達(dá)到死刑數(shù)量標(biāo)準(zhǔn)時(shí),一般不應(yīng)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另外對(duì)于是否存在特情引誘不明確的案件,偵查機(jī)關(guān)不予說明或案情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存在特情引誘情況的案件,量刑時(shí)應(yīng)予以考慮,審慎使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最后,對(duì)非特情引誘情況作了認(rèn)定,意見規(guī)定只要非特情引誘人,受偵查機(jī)關(guān)支配,所起的作用和特情一樣,那么仍然應(yīng)該在量刑上對(duì)被告人給予考慮。
二、審判實(shí)踐中的犯意引誘
(一)研究樣本情況
在“無訟案例”法律信息數(shù)據(jù)庫中以“犯意引誘”為關(guān)鍵詞,檢索判決書全文中出現(xiàn)“犯意引誘”此詞的刑事判決書為7008 篇⑨,其中販賣毒品案件為5986 篇。以“誘惑偵查”為關(guān)鍵詞,檢索判決書全文中出現(xiàn)“誘惑偵查”此詞的刑事判決書為325 篇,其中販賣毒品案件為230 篇。以“犯意誘發(fā)”為關(guān)鍵詞,檢索判決書全文中出現(xiàn)“犯意誘發(fā)”此詞的刑事判決書為25篇,其中販賣毒品案件為10篇。由于本文需研究實(shí)務(wù)中法院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情節(jié)案件的處理方式,因此筆者將隨機(jī)提取含有“犯意引誘”和“誘惑偵查”兩詞的刑事判決書300份作為樣本進(jìn)行分析比較。
從上述數(shù)據(jù)可知,在含有“犯意引誘”和“誘惑偵查”的案件中,由于主要是依靠關(guān)鍵詞檢索,可能存在一篇判決書中關(guān)鍵詞重復(fù)或者幾個(gè)關(guān)鍵詞都存在的情形,只能避免顯示案件是否構(gòu)成犯意引誘具有很大的爭議,故筆者將對(duì)這300份案件以“案件類型”“辯方抗辯理由”“公訴方提起公訴的理由”“法院裁判情況”“法院判斷標(biāo)準(zhǔn)”等方面進(jìn)行具體分析:
就案件類型而言,300 份案件中,涉及毒品類犯罪的案件有264 份,涉及非法買賣、持有、制造槍支、彈藥案件有13份,涉及敲詐勒索罪的案件有5份,涉及非法經(jīng)營罪的案件有3份,涉及盜竊罪的案件有3份。
(二)樣本所涉及的控辯審三方情況
就辯方提起的抗辯理由而言,300 份案件中除36 份案件未提及相關(guān)關(guān)鍵詞,其余案件都有提及“犯意引誘”“誘惑偵查”等詞匯。其中,以“犯意引誘”作為抗辯理由的案件有93 份,以“誘惑偵查”作為抗辯理由的案件有111份,提及存在“特情引誘”現(xiàn)象的判決書有35篇,辯護(hù)人認(rèn)為存在數(shù)量引誘現(xiàn)象的案件有43篇,辯護(hù)人提及其余類似詞匯的案件46份。值得注意的是,一個(gè)案件可能存在辯護(hù)人同時(shí)主張存在“犯意引誘”“誘惑偵查”和“數(shù)量引誘”,例如在300份案件中,“犯意引誘”和“誘惑偵查”兩詞同時(shí)出現(xiàn)的判決書有12 篇,“犯意引誘”與“數(shù)量引誘”同時(shí)提及的判決書有32篇。這種現(xiàn)象表明辯方自身對(duì)抗辯理由的提出就是混淆的,并不能準(zhǔn)確的定義誘惑偵查手段與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關(guān)系。
就公訴方提起公訴的理由而言,除了對(duì)被告人以相關(guān)罪名提起公訴外,公訴人也會(huì)判斷是否存在“犯意引誘”或“特情引誘”情節(jié)以提起量刑建議。在300 份案件中,以“犯意引誘”和“誘惑偵查”作為量刑情節(jié)的案件有6 件,以“數(shù)量引誘”作為量刑情節(jié)的案件有2 件,反駁辯護(hù)人提及的存在“特情引誘”和“誘惑偵查”情節(jié)的案件有4 件,其余案件均未提及誘惑偵查手段及其相關(guān)的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在司法實(shí)踐中檢方甚少對(duì)偵查機(jī)關(guān)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進(jìn)行判斷認(rèn)定,檢方對(duì)此類案件多是不提及不判斷的態(tài)度,從側(cè)面反映出,實(shí)務(wù)中對(duì)涉及犯意引誘相關(guān)問題的證明責(zé)任并未完全由控方承擔(dān)。
從法院裁判情況來看,300 份案件中法院明確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50 份,否定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存在的案件占多數(shù),達(dá)251份(其中一份為同案兩被告不同認(rèn)定),故可知審判實(shí)務(wù)中法院對(duì)辯護(hù)人及其被告提出的具有“犯意引誘”等偵查手段的意見,多是采取否定結(jié)果。
三、犯意引誘存否的裁判類型
(一)肯定存在犯意引誘的裁判情形
1.明確肯定存在犯意引誘。明確肯定存在犯意引誘,即法院正面認(rèn)定偵查機(jī)關(guān)的行為屬于犯意引誘。在50份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的案件中,法院在裁判文書中明確表明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有38份,例如重慶市第二中級(jí)人民法院審理的何某販賣毒品一案,法院認(rèn)為“何某本沒有實(shí)施販賣毒品的主觀意圖,而是在公安特情人員謝某的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從而實(shí)施販賣毒品犯罪,故本案存在犯意引誘,依法應(yīng)當(dāng)從輕處罰。”⑩在實(shí)際判決中,法院援引相關(guān)事實(shí)及證據(jù)認(rèn)定偵查機(jī)關(guān)的行為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多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先查獲毒品,再利用被查獲的毒民為特情人員接洽販毒者佯稱購毒,公安機(jī)關(guān)在約定地點(diǎn)當(dāng)場抓捕販毒者這類情形。由此從側(cè)面表明法院在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的判斷因素中,“特情人員主動(dòng)求購”是尤為重要,具體又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
(1)法院根據(jù)單獨(dú)的線人主動(dòng)求購即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例如,安徽省無為縣人民法院審理的邰某某聚眾斗毆、販賣毒品一案中,人民法院認(rèn)為“被告人邰某某在起訴書指控的第3起販賣毒品犯罪中,因誘惑偵查被公安機(jī)關(guān)查獲,同時(shí)因犯意引誘使得該宗冰毒自交易一開始即不可能完成,系犯罪未遂,均依法從輕處罰。”?此案中法院就依據(jù)單一的特情人員主動(dòng)求購的事實(shí)判定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
(2)法院根據(jù)偵查機(jī)關(guān)布控+特情主動(dòng)求購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例如衡陽市中級(jí)人民法院審理的江某某販賣毒品一案。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指“被告人江某某的毒品犯罪行為系特情引誘,屬犯意引誘。”?此案中公安機(jī)關(guān)抓獲匡某某后,以匡某某作為偵查手段的延伸,匡某某在控制中主動(dòng)與被告人聯(lián)系誘使被告人販賣毒品,偵查機(jī)關(guān)并對(duì)此展開一系列布控。法院依據(jù)此案件事實(shí)和證據(jù)判定匡某某屬于偵查機(jī)關(guān)的特情人員,其行為屬于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行為,認(rèn)定該情節(jié)屬于犯意誘發(fā)型偵查手段。
(3)法院根據(jù)偵查機(jī)關(guān)控制+特情主動(dòng)求購+毒資或所販毒品為公安機(jī)關(guān)或特情人員安排提供此三因素判定偵查手段存在犯意引誘。例如武漢市硚口區(qū)人民法院審理的何昌偉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一案中?,特情人員王某某主動(dòng)與被告人何昌偉電話聯(lián)系購買毒品事宜,且王某某購買毒品的200 元毒資由公安機(jī)關(guān)提供,之后被告人何昌偉在約定地點(diǎn)將毒品交付給王某某時(shí)當(dāng)場被公安機(jī)關(guān)抓獲。又如姚敏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一案中?,法院經(jīng)審理查明特情人員李某在向姚敏電話聯(lián)系要求購毒的經(jīng)過中,姚敏表明其“手中沒有毒品,且沒有錢拿不到毒品”,而李某卻主動(dòng)向姚敏匯入購買毒品的毒資。這兩個(gè)案件法院最終都判定偵查機(jī)關(guān)存在犯意引誘,故可知,特情人員或偵查人員在行為上的主動(dòng)界限是判斷是否存在犯意引誘重要因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38 份判決書中有10 份案件法院只是單純表明采納辯護(hù)人或被告人的意見,并未采用相關(guān)案件事實(shí)和證據(jù)說理是如何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的,或者法院闡述理由簡略,甚至存在未引用相關(guān)事實(shí)和證據(jù)來說明被告人為何是在特情介入引誘下形成犯意,又是如何認(rèn)為被告人之前沒有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的現(xiàn)象,缺乏文書說理。
2.反面印證存在犯意引誘。除了上述法院在裁判文書中明確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38 份案件外,其余12 份案件,法院在文書中均采用了“不排除存在犯意引誘情形,依法從輕”的表達(dá)。此種方式表明,法官雖未在判決書中直接明確肯定犯意引誘的存在,但從判決書的的言語表達(dá)中可以反面印證出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手段超過合法限度。如在豆虎東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罪一審判決書中,法院在判定公安機(jī)關(guān)在偵查過程中的偵查手段是否合法時(shí),法官認(rèn)為“本案中,證明被告人豆虎東持有毒品待售的證據(jù)不足,特情人員介入后,不排除特情引誘情形即犯意引誘情形的存在。”?又如潛江市人民法院審理的楊放新販賣毒品案?,對(duì)于辯護(hù)人提出的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行為超出誘惑偵查的合法范圍的辯護(hù)詞,法官在結(jié)合案件事實(shí)和證據(jù)后認(rèn)為“不能排除存在犯意引誘”,最后法院都對(duì)被告人的量刑予以了從輕,雖然未直接在判決書中明確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但依據(jù)存疑時(shí)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采取了“不排除犯意引誘情形存在”的表達(dá)方式,對(duì)被告人量刑上予以了從輕,反面印證了偵查機(jī)關(guān)在偵查過程中采取了犯意引誘型的偵查手段。
(二)否定存在犯意引誘的裁判情形
司法實(shí)踐中,法院在判決文書中表明不存在犯意引誘時(shí),要么認(rèn)定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行為屬于誘惑偵查中的機(jī)會(huì)提供型,要么直接否定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目前學(xué)界認(rèn)為判斷是否屬于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應(yīng)從“犯罪人表現(xiàn)”“引誘力度”“引誘的危險(xiǎn)性”出發(fā),而在實(shí)際的判決中,法官考量的因素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被告人已持有犯罪的主觀意圖,主要表現(xiàn)為“主動(dòng)電聯(lián)”或“主觀上積極主動(dòng)”(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31%)。如張某某販賣毒品案中?,辯護(hù)人提出公訴機(jī)關(guān)指控的第三起犯罪事實(shí)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意見,法院認(rèn)為“雖然是公安人員運(yùn)用特情破獲,但當(dāng)時(shí)張某某主觀是積極主動(dòng)的,且毒品交易完畢后張某某又實(shí)施了販賣毒品的犯罪,綜合全案事實(shí)足以說明張某某已持有毒品販賣的主觀意圖。”判斷被告人是否已有犯罪意圖,是一個(gè)綜合判斷因素,需要法官綜合全面的評(píng)價(jià)行為人的主觀態(tài)度及其行為。多數(shù)案件中,法院主要從犯罪人在行為前、被引誘時(shí)、行為后的表現(xiàn)著手,判斷被引誘者在各個(gè)階段的主觀態(tài)度是否積極主動(dòng)。
2.被告人在接到買家購買信息后在較短時(shí)間內(nèi)就準(zhǔn)備好毒品或犯罪物品,表明此前被告人即具有毒品交易傾向或犯罪傾向(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9%)。在這里“較短時(shí)間”是法官進(jìn)行審查判斷的最重要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之一,而多長時(shí)間是“較短時(shí)間”?在吳義總販賣毒品案中,對(duì)于吳義總在當(dāng)天短短30 分鐘后就準(zhǔn)備好毒品并到達(dá)交易地點(diǎn)進(jìn)行交易這一事實(shí),法官認(rèn)為“被告人吳義總的行為表明其案發(fā)前就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和行為,發(fā)生本案并非是特情誘惑促成的,且特情僅僅要求購買90元毒品,并非引誘實(shí)施大量毒品犯罪,故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誘及數(shù)量引誘的情形。”?又如楊某販賣毒品案中?,楊某短時(shí)間就與特情達(dá)成交易。
由此可知,“短短時(shí)間”主要表現(xiàn)為被告人與特情之間求購與達(dá)成交易的時(shí)間長短,應(yīng)以正常一般人對(duì)短時(shí)間的判斷為標(biāo)準(zhǔn)。其實(shí)此種判斷因素也是從側(cè)面在考量被告人行為、態(tài)度的積極性,被告人的行為往往表現(xiàn)為“隨即交易”“一拍即合”“立即答應(yīng)”“短短時(shí)間交易完成”等狀態(tài),其態(tài)度總體上呈現(xiàn)積極性。
3.被告人在實(shí)施本起犯罪前已經(jīng)實(shí)施過同類型犯罪行為(在251 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13%)。如孔龍輝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二審中?,法官的主要理由是孔龍輝在實(shí)施本起犯罪之前已實(shí)施過兩次售賣毒品的行為,說明孔龍輝主觀上已經(jīng)具備犯意并已著手實(shí)施了犯意,故偵查機(jī)關(guān)在偵查過程中僅是提供了一種有利于其犯罪實(shí)施的特定條件和機(jī)會(huì),不存在誘發(fā)無罪者犯罪的問題。又如但文潔、但元平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毒品一案21可以看出,犯罪人之前是否有過同類型的犯罪行為是法官判斷行為人在案發(fā)前是否已具有犯罪主觀意圖的重要依據(jù)。
4.法院認(rèn)為案件中并不存在“特情人員”或“線人”,偵查機(jī)關(guān)是依據(jù)相關(guān)“舉報(bào)”或“線索”抓獲被告人,故案件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在251 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12%)。此種裁判理由具有特殊性,在裁判文書中多表述為“本案是同案關(guān)系人某某為了立功,在警察控制下主動(dòng)聯(lián)系上家進(jìn)行的毒品交易,并無特情參與,不存在特情引誘的情況。”22或“本案系公安機(jī)關(guān)根據(jù)舉報(bào)人舉報(bào)后布控將被告人抓獲歸案。”23這類型的考量因素,模糊了案件中“特情人員”“線人”的性質(zhì),否定了“特情人員”作為公安機(jī)關(guān)偵查手段延伸的存在。
5.被告人案發(fā)前已持有毒品或犯罪物品待售,偵查機(jī)關(guān)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意引誘(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11%),如文紅安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一案24。對(duì)于行為人在案發(fā)前已持有毒品待售這一因素,根據(jù)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規(guī)定,對(duì)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證據(jù)證明已準(zhǔn)備實(shí)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誘,應(yīng)當(dāng)依法處理。實(shí)踐中法官也主要依據(jù)此規(guī)定裁判案件。
實(shí)務(wù)中,若案件中存在“犯罪前已出售過毒品”+“已持有待售毒品”或者“犯罪前已有吸食毒品的行為”+“已具備出售大宗毒品的能力”幾種情形的結(jié)合,裁判法官會(huì)當(dāng)然認(rèn)為偵查行為不構(gòu)成犯意引誘。例如毛某一案中,對(duì)于辯護(hù)人提出的販賣毒品行為系犯意引誘的辯護(hù)意見,法院認(rèn)為“被告人毛某持毒待售,并有出售記錄,其主觀上具有販毒故意,客觀上實(shí)施了販毒行為,不存在犯意引誘。”25
6.不構(gòu)成犯意引誘,但構(gòu)成數(shù)量引誘(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4%)。吉地拉鬼、雷保民販賣毒品案、林以保、王君祥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案等,法院都認(rèn)為不存在犯意引誘,但構(gòu)成數(shù)量引誘,應(yīng)當(dāng)依法從輕處罰。
7.無證據(jù)證實(shí)偵查機(jī)關(guān)具有犯罪引誘的行為(在251 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9%)。如陳俊非法持有毒品一案中26,對(duì)于是否存在犯意引誘這一爭論,法院以無證據(jù)證明駁回了辯護(hù)人的意見。這種無相關(guān)證據(jù)證明存在或者不存在犯意引誘的情形,法院直接裁判為不存在犯意引誘情形做法,與上文所言反面印證存在犯意引誘情形的做法是相互矛盾的。并且這里的“無證據(jù)”是指的辯護(hù)人沒有證據(jù)還是公訴人沒有證據(jù)?誰對(duì)此負(fù)有舉證責(zé)任?在王玉全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案中,法官認(rèn)為公訴機(jī)關(guān)提交的證據(jù)中沒有證據(jù)證明朱某系特情人員,且存在犯意引誘的事實(shí),否定了辯護(hù)人的辯護(hù)意見,可以看出本案是公訴機(jī)關(guān)承擔(dān)了證明是否存在犯意引誘的舉證責(zé)任。
可是在多數(shù)案件中,這里的“無證據(jù)”是指辯方及被告沒有提供相應(yīng)證據(jù)證明偵查機(jī)關(guān)偵查行為存在犯意引誘的主張,如蘇某、鄧某非法制造、買賣、運(yùn)輸、郵寄、儲(chǔ)存槍支、彈藥、爆炸物案。是否存在犯意引誘的舉證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由誰承擔(dān)?這個(gè)問題值得考究。
8.未對(duì)辯護(hù)人或被告人提出的犯意引誘的辯護(hù)意見進(jìn)行說理,只是單純的進(jìn)行了否定(在251份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中占比11%)。如陳某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罪一案中27,法院對(duì)于辯護(hù)人提出的偵查機(jī)關(guān)存在誘惑偵查情節(jié)的意見,以“毒品犯罪在司法實(shí)踐中需要采取特情介入的偵查方式,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誘情形”為由,不予采納。
從前述被告人有無同類型犯罪前科、是否“持有待售毒品”、是否有主觀積極的行為或態(tài)度等來看,這些因素都是法院在判斷犯罪人是否已持有犯罪意圖上進(jìn)行的細(xì)分,它們都可以成為判斷被告人是否已有固定犯罪的主觀意圖或行為的綜合判斷因素。從上述案件的觀察可看出,目前法官在判斷是否具有“犯意”時(shí),主要聚焦在被引誘對(duì)象即被告人的行為表現(xiàn)上,對(duì)于偵查機(jī)關(guān)在偵查中采取的引誘事項(xiàng)是否具有危險(xiǎn)性、其行為是否超過“引誘力度”等并未進(jìn)行過多審查,這與理論上所存在的爭議是不同的。前述判斷因素中看似可與“引誘力度”掛鉤的是法院對(duì)于“數(shù)量引誘”的認(rèn)定。但是“數(shù)量引誘”是屬于合法的機(jī)會(huì)提供型偵查手段,與“犯意引誘”是兩個(gè)并行的概念,其并不能作為判斷是否具有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因素。因此,實(shí)務(wù)中對(duì)于“引誘力度”“引誘事項(xiàng)的危險(xiǎn)性”的審查是缺少的,法院應(yīng)當(dāng)對(duì)此二者引起重視。
四、存在犯意引誘的裁判結(jié)果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不得誘使他人犯罪”,明令禁止偵查機(jī)關(guān)在偵查過程中采用引發(fā)他人犯意的偵查手段。法官在確認(rèn)偵查機(jī)關(guān)采用了犯意引誘型的偵查手段時(shí)又將如何處理,實(shí)務(wù)中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將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所獲取的證據(jù)作為非法證據(jù)予以排除
在300份案件中,共有24份案件中的被告人及其辯護(hù)人在審判中主張以犯意引誘偵查手段收集的證據(jù)為非法證據(jù),應(yīng)通過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予以排除,如果排除此證據(jù)無法達(dá)到定罪標(biāo)準(zhǔn),法院應(yīng)當(dāng)作出無罪判決。但是此種主張法院甚少采納,既存在不采納犯意引誘和排除非法證據(jù)的情形,又存在采納犯意引誘的主張,但不采納非法證據(jù)排除的情形。如徐明、康山夫販賣毒品罪一案中對(duì)于辯護(hù)人認(rèn)為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手段不合法,存在犯意誘發(fā)的情節(jié),其收集的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依法予以排除的主張,法院并未采納。盡管有《刑事訴訟法》第52條有關(guān)于“嚴(yán)禁以引誘方法收集證據(jù)”的規(guī)定,但由于《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的規(guī)定28,故實(shí)務(wù)中法院多數(shù)的做法就如浙江舟山普陀區(qū)法院審理的高從芳販賣毒品案一樣29,甚少有適用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情形。
(二)將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作為被告人除罪的理由
這一觀點(diǎn)認(rèn)為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具有欺騙性、引誘性,偵查行為作為國家打擊犯罪的手段實(shí)際上卻促使了犯罪發(fā)生,損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權(quán)益,不利于公平正義的實(shí)現(xiàn),故對(duì)于被采用犯意引誘偵查手段的被告人,應(yīng)當(dāng)運(yùn)用個(gè)人排除刑罰事由,宣告無罪。此理論界的觀點(diǎn),除了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法院有判決外30,目前大陸地區(qū)尚無此種判決。雖然法院無此判決,但實(shí)踐中卻有被告人及其辯護(hù)人將此作為除罪的理由。例如在300份案件中,有8份案件中的被告人及其辯護(hù)人主張“犯罪事實(shí)系犯意引誘不應(yīng)認(rèn)定為犯罪”,但是在這8 份案件中,法院都沒有采納辯護(hù)人及其被告人的意見,而是對(duì)構(gòu)成犯意引誘情形的被告人量刑上予以了從輕。
(三)將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作為對(duì)被告人從輕量刑的情節(jié)
案件中若存在犯意誘發(fā)型偵查情節(jié),理論界的一種觀點(diǎn)是將此作為被告人的量刑情節(jié),在刑罰上對(duì)其從輕或減輕處罰。司法實(shí)踐中,法院多依據(jù)2008年的《會(huì)議紀(jì)要》的規(guī)定對(duì)被告人依法從輕處罰。
在判決書中還存在一種情形即法院認(rèn)為“雖不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但因特情介入,犯罪行為處在公安機(jī)關(guān)的控制之下,沒有流入社會(huì),應(yīng)對(duì)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此種觀點(diǎn)是將特情介入+偵查機(jī)關(guān)控制相結(jié)合,認(rèn)為被告人販賣的毒品或犯罪物品不可能流向社會(huì),不可能給社會(huì)造成危害,將此作為量刑情節(jié)對(duì)被告人予以酌情從輕處罰。在此種情形下,法院已經(jīng)明確否定了犯意引誘偵查手段的存在,若又因合法的誘惑偵查或特情介入對(duì)犯罪人予以酌情從輕處罰,此種做法是否合理?2008年的《會(huì)議紀(jì)要》在第六章“特情介入案件的處理問題”最后一條的規(guī)定31和遼寧省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指導(dǎo)意見》對(duì)間接引誘的規(guī)定,似乎上述情形法官的做法是合理的。但是無論是何種情況予以量刑從輕,目前存在的一個(gè)問題是,這些規(guī)范性文件并不是立法機(jī)關(guān)制定的正式的法律文件,在其適用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問題。
除此之外,對(duì)于有可能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的案件,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是定既遂還是未遂,在實(shí)踐中也是一個(gè)爭議很大的問題。在300份案件中,有29份案件的辯護(hù)人及其被告人都提出了存在犯意引誘,犯罪未遂的辯護(hù)意見。在曹文輝走私、販賣、運(yùn)輸、制造毒品案中,一審法院采納了辯護(hù)人的意見,認(rèn)為案件中存在犯意引誘的情節(jié),應(yīng)根據(jù)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的原則從輕處罰;鑒于曹文輝在犯罪過程中被抓,系犯罪未遂,比照既遂犯減輕了處罰。檢察院在二審中予以抗訴,主張案件不存在犯意引誘,其行為已既遂,原審判認(rèn)定販賣毒品未遂,系適用法律錯(cuò)誤。在之后的審判中,二審法院否定了案件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并認(rèn)為曹文輝已經(jīng)實(shí)際著手實(shí)施犯罪,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屬犯罪未遂,最后以因特情介入,毒品未流入社會(huì),社會(huì)危害性較小對(duì)曹文輝酌情從輕處罰。
對(duì)于存在犯意引誘情節(jié)下,法院對(duì)該犯罪行為是定既遂還是未遂,筆者在3份判決書中發(fā)現(xiàn)法官對(duì)此作出了未遂裁判,其余判決書均否定了辯護(hù)人關(guān)于未遂的意見。如邰某某聚眾斗毆、販賣毒品案32。
對(duì)于認(rèn)定既遂的法院的裁判理由多為如“在犯意引誘不成立的前提下,吉地拉鬼已將毒品帶入雙方的交易現(xiàn)場,故應(yīng)視為犯罪既遂”33“販賣毒品的行為已進(jìn)入交易環(huán)節(jié),根據(jù)相關(guān)規(guī)定性”“對(duì)于犯罪未遂問題,通過但文潔與特情人員之間毒品交易成功,應(yīng)認(rèn)定為犯罪既遂”。雖然販賣毒品罪只要完成了毒品交付的就是既遂(非法藥物類犯罪,行為人只要完成了任何一個(gè)危險(xiǎn)品的流通,就成立犯罪既遂),但由于審判實(shí)務(wù)中大多數(shù)毒品案件被告人被抓獲時(shí)正處于買賣交易狀態(tài)完成時(shí)或待完成時(shí),若單純的認(rèn)為“販賣”是購買和出賣兩個(gè)行為,這樣就會(huì)導(dǎo)致偵查機(jī)關(guān)控制被引誘者是否構(gòu)成既遂或未遂的問題,即偵查人員是否允許毒品在現(xiàn)場交易將直接關(guān)系到犯罪的既遂、未遂的問題。因此,筆者認(rèn)為行為人以販賣毒品目的實(shí)施了購買毒品行為或?qū)⒊钟械亩酒穾У脚c買方約定的地點(diǎn)交易的,應(yīng)按既遂處理。在運(yùn)用特情介入的案件中,行為人犯意形成在前,特情介入在后并且只是為行為人販賣毒品提供一個(gè)機(jī)會(huì)和交易對(duì)象,則對(duì)此種情形,應(yīng)按照行為人本來的意思和行為處理,若被告人已經(jīng)實(shí)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應(yīng)認(rèn)定為既遂。若行為人犯意是特情介入后產(chǎn)生的,且特情人員誘使了行為人實(shí)施了犯罪行為,其犯罪行為其實(shí)是無法構(gòu)成既遂的。
目前,我國實(shí)務(wù)中對(duì)已認(rèn)定為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案件,最終的裁判結(jié)果都是采取2008 年《會(huì)議紀(jì)要》的做法,對(duì)被告人的量刑予以了從輕。但是筆者結(jié)合目前的實(shí)務(wù)案例分析認(rèn)為,確定存在犯意引誘的法律效果方面,宜采認(rèn)定被告人無罪的觀點(diǎn)。
首先,根據(jù)刑法體系與理論,若該犯罪行為的產(chǎn)生是偵查機(jī)關(guān)使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引誘、挑唆、違法制造的,那么犯罪人的行為就應(yīng)屬于個(gè)人排除刑罰的事由,且沒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其次,“犯意引誘型”偵查行為也嚴(yán)重侵犯了被告的權(quán)利,違背了刑法應(yīng)有的人權(quán)保障以及社會(huì)保護(hù)機(jī)能,違背了刑罰的預(yù)防目的,故明確否定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才能使刑法的預(yù)防理論達(dá)到效果。
并且,實(shí)務(wù)中法官并不是僅對(duì)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情形的被告人量刑上予以了從輕,在有些僅僅存在特情介入、未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的案件的被告人也予以了從輕,理由是“鑒于特情介入,毒品未流入社會(huì),未造成實(shí)際危害,酌情從輕。”正如其所言的“毒品未流入社會(huì),未造成實(shí)際危害”,那么犯罪行為的產(chǎn)生是由于偵查機(jī)關(guān)使用引誘手段挑唆、違法制造的,且被告人在該具體案件中也并未對(duì)社會(huì)造成實(shí)際危害,那為何還要對(duì)其予以量刑呢?故筆者認(rèn)為,在被引誘者刑事責(zé)任方面,若法官判決明確認(rèn)定存在犯意引誘情形,被引誘行為一般不會(huì)產(chǎn)生客觀危害結(jié)果,那么沒有犯意的被引誘者就不應(yīng)當(dāng)追究刑事責(zé)任。
另外,對(duì)于實(shí)施引誘的公務(wù)人員或特情人員是否構(gòu)成其所引誘或幫助犯罪的共犯,法律上并沒有相關(guān)規(guī)定,實(shí)務(wù)中法院也沒有相關(guān)判決。若認(rèn)為需要對(duì)相關(guān)的偵查人員及相關(guān)特情人員的行為予以定性,則可以刑法上的未遂教唆形態(tài)進(jìn)行分析討論,若采共犯獨(dú)立說,則不可罰;若采共犯從屬說,則仍具有可罰性。若構(gòu)成犯罪,可對(duì)其追究相應(yīng)的刑事責(zé)任。
五、犯意引誘型偵查的規(guī)制路徑
(一)以立法定義犯意引誘
目前我國司法實(shí)踐中處理存在誘惑偵查的案件主要依據(jù)的是最高法院印發(fā)的2008年《會(huì)議紀(jì)要》,雖《刑事訴訟法》第153 條規(guī)定了“不得引誘他人犯罪”,但始終未明確提出認(rèn)定犯意引誘的規(guī)則,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同樣沒有對(duì)如何認(rèn)定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作出解釋,這也導(dǎo)致了在審判中法院對(duì)于犯意引誘的認(rèn)定無法可依,僅依據(jù)2008 年《會(huì)議紀(jì)要》對(duì)犯意引誘的認(rèn)定以及對(duì)相關(guān)法律后果作出的規(guī)定,法院在審理可能存在犯意引誘的案件時(shí),容易對(duì)犯意引誘與誘惑偵查等概念混淆。
在前文中的概念辨析中可知誘惑偵查是當(dāng)前偵查機(jī)關(guān)偵查犯罪普遍使用的一種偵查手段,存在著幾種情形。日本學(xué)者田口守一認(rèn)為“誘惑偵查是指偵查人員或民間偵查合作者促使第三人犯罪,將其逮捕,分為機(jī)會(huì)提供型和犯意誘發(fā)型兩類。”[6]日本學(xué)界為了區(qū)分合法的誘惑偵查和非法的誘惑偵查而對(duì)誘惑偵查進(jìn)行了“兩分法”,在審判實(shí)務(wù)中更是基于“兩分法”將誘惑偵查中合法的情形定義為“機(jī)會(huì)提供型”,非法的情形則為“犯意引誘型”[7]。2004 年7 月12 日,日本最高法院首次針對(duì)誘惑偵查的合法性要件作出的判決34與過去二分說的觀點(diǎn)相比較而言,明顯更傾向采納實(shí)質(zhì)的觀點(diǎn),即將誘惑偵查的案件分為三個(gè)類型35,由此可知,日本實(shí)務(wù)中的重要判例將“犯意引誘型”36定義為合法誘惑偵查的相反面,該犯意引誘概念清晰且有相關(guān)解釋和法律規(guī)定。
反觀我國,由于主要依據(jù)最高法院印發(fā)的《會(huì)議紀(jì)要》,因此審判實(shí)務(wù)中就存在著辯護(hù)人或者被告人,更甚至公訴機(jī)關(guān)和法院對(duì)于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概念界定不清。如辯護(hù)人采用“誘惑偵查”“數(shù)量引誘”等屬于合法偵查行為的概念來作為存在“引誘犯罪”的抗辯理由,并且控辯雙方對(duì)此展開一系列辯論,真正需要認(rèn)定審查的“犯意引誘”反而被忽略了,這就導(dǎo)致實(shí)務(wù)中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不一,司法機(jī)關(guān)對(duì)此類案件的態(tài)度模糊不清。
(二)以立法確定犯意引誘的判斷基準(zhǔn)
犯意引誘定義的模糊一方面也導(dǎo)致了我國審判實(shí)務(wù)中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認(rèn)定態(tài)度的模糊、混亂,并未形成如日本、美國、歐洲人權(quán)法院一樣清晰的認(rèn)定條件,所以在實(shí)務(wù)中無論是公訴人還是法院在否定存在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情節(jié)時(shí)所援引的理由都不一樣。由于受《會(huì)議紀(jì)要》對(duì)“犯意引誘”的定義,司法機(jī)關(guān)在認(rèn)定偵查機(jī)關(guān)的行為是否屬于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時(shí),將重點(diǎn)放在了偵查機(jī)關(guān)的行為是否引起犯罪人的“犯意”上。結(jié)合上文的實(shí)務(wù)分析也可以清晰看出,目前司法機(jī)關(guān)對(duì)此的審查主要集中在犯罪人的行為和主觀表現(xiàn)上,缺乏對(duì)偵查機(jī)關(guān)本身行為限度的關(guān)注。
犯罪人的行為和主觀表現(xiàn)的審查也存在單一性問題。例如在前文中,法院有單純依據(jù)被引誘者之前存在同類型犯罪行為就認(rèn)定被誘惑人已持有固定犯罪的主觀意圖。這存在一定偏頗。筆者認(rèn)為即使被引誘者之前實(shí)施了同類型犯罪行為,也并不能肯定被引誘者對(duì)此次犯罪已存在犯意。被引誘者并不是意味著必須是沒有犯罪的人,而是要求被引誘者在該具體案件中,被引誘之前沒有犯意,法官重點(diǎn)在于審查該具體案件中犯罪人的“犯意”何時(shí)產(chǎn)生,這是對(duì)該具體案件中行為人主觀和客觀的綜合判斷。例如以美國的Jacobson v.United States 案37為例,法院最后判決被告主張的“引誘犯罪”的抗辯成立,主要觀點(diǎn)就是Jacobson是不警惕的無辜者,即被告的犯意是由偵查人員的引誘行為引起的,被告人在被引誘前沒有犯意。若被告人之前具有犯意,則偵查人員的行為僅僅是對(duì)不警惕的罪犯提供了不尋常的誘因或條件。從此案就可以看出,不能單純以被引誘者之前存在同類型犯罪行為就認(rèn)定被誘惑者已持有固定犯罪的主觀意圖。
實(shí)務(wù)中,目前我國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認(rèn)定缺乏對(duì)偵查機(jī)關(guān)本身行為合法性的審查。結(jié)合2018 年《刑事訴訟法》第153 條但書“不得誘使他人犯罪”,對(duì)公安機(jī)關(guān)采取的“隱匿身份偵查措施”進(jìn)行的限制來看,《刑事訴訟法》對(duì)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偵查活動(dòng)進(jìn)行了自我限制,強(qiáng)調(diào)了偵查行為的合法限度。因此在新修后的刑事訴訟法的背景下,法官再在實(shí)務(wù)中單純依據(jù)《會(huì)議紀(jì)要》的規(guī)定,青睞主觀審查的標(biāo)準(zhǔn)就有點(diǎn)不合時(shí)宜。畢竟“主觀基準(zhǔn)會(huì)促使犯罪挑唆問題的面向從警方行為的妥當(dāng)性過度轉(zhuǎn)移到行為人品格性向及前科的審查使刑法從行為罪責(zé)淪落為人格罪責(zé)。”[8]因此筆者認(rèn)為可以立法,明定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實(shí)務(wù)可采取將“主觀審查說”和“客觀審查說”相結(jié)合的混合審查模式判定犯意引誘相關(guān)問題。
一要注重審視被引誘者的主觀層面。在主觀審查方面,要落實(shí)在該具體案件中,對(duì)被引誘者行為和主觀進(jìn)行審查。可以參考美國的主觀審查基準(zhǔn),判斷被告人在被引誘前是否具有犯意。第一,考量被引誘者之前是否具有類似的犯罪行為,若有,則需考察實(shí)施該類似犯罪行為的次數(shù)和與此次被引誘犯罪行為的間隔時(shí)間。第二,審查被告人被引誘之后的行為態(tài)度,這里可以參考2001年四川省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聯(lián)合制定的《關(guān)于販賣毒品案件有關(guān)犯罪預(yù)備問題的意見》的做法,即以被引誘者之前是否實(shí)施了犯罪預(yù)備的行為來具體判斷被引誘者的“犯意”是何時(shí)形成。若被引誘者為該犯罪行為主動(dòng)準(zhǔn)備了工具、制造了條件,則該被引誘者在主觀和行為上是積極主動(dòng)的,就可認(rèn)定在該誘惑偵查中被引誘者之前就具有犯意。另外,還應(yīng)將被引誘者在實(shí)施犯罪過程中是否可以主動(dòng)放棄犯罪納入考察因素。第三,將被告人實(shí)施犯罪的能力,如有無金錢購買毒品或犯罪工具、有無時(shí)間實(shí)施犯罪行為等納入判定因素。除此之外再行考量被告人的公共評(píng)價(jià)和被告人的后續(xù)行為及言論等因素。
二要重點(diǎn)考察偵查行為的合法界限。在客觀審查方面,需要對(duì)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行為是否超出合法限度進(jìn)行判斷。第一,需要判斷偵查機(jī)關(guān)采取此種偵查方式有無必要,該被引誘者是否已經(jīng)具有犯罪嫌疑。若偵查機(jī)關(guān)針對(duì)被引誘者及其涉嫌的事實(shí)已經(jīng)先行展開了一定的調(diào)查程序,但該調(diào)查程序無法取得偵查效果,那么此時(shí)采取特情介入的手段就是適宜的。第二,需要審查“特情”“臥底”“線人”的行為是否屬于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行為。在前述實(shí)務(wù)分析中,可以看出有些案件控方和法官否定了“特情”“臥底”“線人”是偵查機(jī)關(guān)偵查行為的延伸的。誘惑偵查的行使主體在我國現(xiàn)行的偵查體制下是法定以及特定的,且除非有必要是不得采取誘惑偵查措施的,故可以明確的知道其實(shí)施主體只能是偵查機(jī)關(guān),而具體執(zhí)行的人員可以不限于偵查人員還包括偵查機(jī)關(guān)所支配的人即偵查協(xié)助者。司法實(shí)踐中偵查協(xié)助者參與誘惑偵查也確實(shí)占據(jù)了相當(dāng)大的比例,“特情”“臥底”“線人”就是作為偵查協(xié)助者參與到偵查過程之中的。雖然有些案件中法官認(rèn)為“特情”“臥底”“線人”是同案犯,是為了立功參與案件,并在判決的結(jié)果中認(rèn)定為其構(gòu)成立功,但是也不可否認(rèn)“特情”“臥底”“線人”是作為偵查協(xié)助者參與到該案件中的,其行為就是偵查機(jī)關(guān)行為的延伸,所以法官就應(yīng)該考察其行為的引誘次數(shù)、引誘力度、危險(xiǎn)性和合法界限。第三,要審查偵查機(jī)關(guān)實(shí)施誘惑偵查的方式和強(qiáng)度,超過了手段的正當(dāng)性和強(qiáng)度,就構(gòu)成了非法的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3]193-202。刑事偵查的目的是為了查明事實(shí)和保障人權(quán),這意味著偵查機(jī)關(guān)的職責(zé)是發(fā)現(xiàn)犯罪且打擊犯罪而不是主動(dòng)制造犯罪,這也是誘惑偵查的應(yīng)有之意即偵查機(jī)關(guān)不能因?qū)嵤┱T惑偵查而制造犯罪,不能使無犯意的人產(chǎn)生犯意,否則就失去了偵查權(quán)所應(yīng)有的正當(dāng)性。在具體案件中,法官應(yīng)從誘餌的刺激性、引誘的次數(shù)、誘惑時(shí)間的長短、犯罪利益的誘惑性、偵查人員涉案程度等入手,審視偵查機(jī)關(guān)在案件偵查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三)明確不存在犯意引誘的證明責(zé)任應(yīng)由控方承擔(dān)
實(shí)務(wù)中在對(duì)犯意引誘型偵查手段進(jìn)行認(rèn)定的過程中,存在著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的混亂的問題。從有些案件可以看出,法官傾向于將證明責(zé)任科以控方,控方若不能提供有力證據(jù)有效證明不存在犯意引誘情形時(shí),法官最后會(huì)采取存疑時(shí)有利于被害人原則,反面認(rèn)定不存在犯意引誘情形。從有些案件的裁判理由來看,法官又傾向于將證明責(zé)任科以辯方,若辯方不能提供有力證據(jù)有效證明存在犯意引誘情形,則將承擔(dān)不利的后果。這種混亂的情形導(dǎo)致同類型的案件最后有不同的裁判結(jié)果。
筆者認(rèn)為,犯意引誘的證明責(zé)任由控方承擔(dān)比較妥當(dāng)。原因有二:一是從我國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第51條規(guī)定來看,雖然犯意引誘存在與否的問題嚴(yán)格意義上屬于量刑問題,但人民檢察院承擔(dān)的有罪證明責(zé)任并不意味著檢察院只能提供被告人有罪的證據(jù),人民檢察院也可以基于客觀公正的原則,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無罪或罪輕、罪重的證據(jù)都提交給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根據(jù)全案證據(jù)綜合判斷被告人是否有罪、無罪、罪輕或罪重;二是控方是國家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其更易接近和查找證據(jù)證明偵查機(jī)關(guān)的偵查人員或特情是何時(shí)接觸被引誘者,控方也更易就被引誘者在偵查人員第一次與其接觸前被告人是否已具有犯罪意向舉證,證明偵查人員行為是否逾越且超過合理懷疑的程度。
[注釋]:
①這些研究主要有:翟金鵬,簡遠(yuǎn)亞的《機(jī)會(huì)提供型誘惑偵查行為非犯罪化問題研究》,載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 年第28 卷第156 期,第109-114 頁;萬毅的《論誘惑偵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51 條釋評(píng)》,載于《甘肅社會(huì)科學(xué)》2012年第199期,第164-168頁。
②誘惑偵查是指國家偵查機(jī)關(guān)為了偵破某些重特大疑難案件,由偵查人員或其協(xié)助者隱蔽身份,采取一定的誘惑手段,提供條件或制造機(jī)會(huì)刺激犯罪發(fā)生,借此抓獲犯罪嫌疑人。
③詳見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第六章內(nèi)容。
④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認(rèn)為:“①機(jī)會(huì)提供,即對(duì)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證據(jù)證明已準(zhǔn)備實(shí)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誘,應(yīng)當(dāng)依法處理。②犯意引誘,即行為人本沒有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jìn)而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對(duì)因“犯意引誘”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據(jù)罪刑相適應(yīng)原則,應(yīng)當(dāng)依法從輕處罰,無論涉案毒品數(shù)量多大,都不應(yīng)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③雙套引誘,即行為人在特情既為其安排上線又提供下線的雙重引誘下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處刑時(shí)可予以更大幅度的從寬處罰或者依法免予刑事處罰。④數(shù)量引誘,即行為人本來只有實(shí)施數(shù)量較小的毒品犯罪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shí)施了數(shù)量較大甚至達(dá)到實(shí)際掌握的死刑標(biāo)準(zhǔn)的毒品犯罪的行為。”
⑤《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271 條規(guī)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shí)候,經(jīng)縣級(jí)以上公安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人決定,可以由偵查機(jī)關(guān)或者公安機(jī)關(guān)指定的其他人員隱匿身份實(shí)施偵查。隱匿身份實(shí)施偵查時(shí),不得使用促使他人產(chǎn)生犯罪意圖的方式誘使他人犯罪。”
⑥《公安機(jī)關(guān)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273條規(guī)定:“公安機(jī)關(guān)依照本節(jié)規(guī)定實(shí)施隱匿身份偵查和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
⑦《聯(lián)合國禁止非法販運(yùn)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規(guī)定:“控制下交付是指在當(dāng)局知情及監(jiān)控下,允許貨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其他毒品或替代物繼續(xù)進(jìn)行運(yùn)送與交易,以此來查明涉及該毒品犯罪的人員,包括幕后指揮者和操作者。”
⑧四川公檢法三機(jī)關(guān)《關(guān)于販賣毒品案件有關(guān)犯罪預(yù)備問題的意見》:“犯罪嫌疑人有犯罪預(yù)備行為指:一是為販賣毒品樣品在四川省境內(nèi)主動(dòng)尋找毒品賣主;二是協(xié)定毒品樣品在四川省境內(nèi)主動(dòng)尋找買主;三是為販賣毒品,有商談毒品種類、價(jià)格、數(shù)量、質(zhì)量、交付時(shí)間、地點(diǎn)、方式、出示毒品樣品、預(yù)付、收取定金、準(zhǔn)備運(yùn)輸工具等情形的;四是其他為販賣毒品準(zhǔn)備工具、制造條件的行為。”
⑨數(shù)據(jù)來源于“無訟案例信息數(shù)據(jù)庫”,https://www.itslaw.com/home,案件搜索結(jié)果截止于2020年2月8日。
⑩資料來源于《(2014)渝二中法刑終字第00002號(hào)判決書》。
?《(2015)無刑初字第00133 號(hào)判決書》寫道:“檢察院在指控邰某某的第三起販毒事實(shí)中,張某作為線人主動(dòng)與被告人邰某某電話聯(lián)系購買毒品事宜,被告人邰某某在約定地點(diǎn)準(zhǔn)備交付毒品時(shí)當(dāng)場被張某帶領(lǐng)來的公安機(jī)關(guān)抓獲。”
?《(2015)衡中法刑二終字第285 號(hào)判決書》寫道:“本案中,匡某某因吸毒被抓獲后,為立功愿意配合公安機(jī)關(guān)抓獲販毒人員。經(jīng)過公安機(jī)關(guān)布控后,匡某某主動(dòng)電聯(lián)江某某佯稱購毒,并約定毒品交易時(shí)間、地點(diǎn),江某某同意交易。后江某某按約攜帶毒品偕其妻開車至毒品交易地點(diǎn),將毒品交給匡某某時(shí),被事先埋伏的公安人員當(dāng)場抓獲,并當(dāng)場繳獲毒品。”
?《(2017)鄂0104刑初435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院認(rèn)為本案存在犯意引誘,依法可對(duì)被告人何昌偉酌情從輕處罰。”
?《(2014)婁中刑一初字第33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院認(rèn)為本案沒有證據(jù)證明被告人姚敏曾經(jīng)有販賣過毒品的事實(shí),也沒有證據(jù)證明被告人姚敏事前有販賣毒品的犯意,本案存在犯意引誘和數(shù)量引誘。”
?《(2017)甘12刑初8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官認(rèn)為特情引誘分為犯意引誘和數(shù)量引誘。犯意引誘指的是公安特情人員對(duì)沒有犯罪故意的人進(jìn)行引誘并使其產(chǎn)生犯罪行為,持有毒品待售的,即便特情人員介入,也不構(gòu)成犯意引誘。”
?《(2014)鄂潛江刑初字第00145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官認(rèn)為本案中,賈某某雖交代其之前販賣的毒品來源于被告人楊放新,但被告人楊放新對(duì)此予以否認(rèn),再無證據(jù)予以證實(shí),且在公安機(jī)關(guān)安排賈某某聯(lián)系被告人楊放新購買毒品之前,沒有證據(jù)證明被告人楊放新持有毒品待售或者已準(zhǔn)備實(shí)施大宗毒品犯罪。”
?資料來源于《(2014)額刑初字第21號(hào)判決書》。
?《(2015)湛開法刑初字第97 號(hào)判決書》寫道:“本案的案件事實(shí)為2014 年10 月21 日22 時(shí)許,公安機(jī)關(guān)的特情人員“梁三”(化名)了解到被告人吳義總有販賣毒品行為,主動(dòng)電聯(lián)吳義總購買毒品,并對(duì)數(shù)量、價(jià)格、交易地點(diǎn)進(jìn)行了約定,吳義總表示同意。約30分鐘后,吳義總到達(dá)交易地點(diǎn)被公安民警抓獲。”
?《(2017)粵03刑終329號(hào)裁定書》寫道:“特情人員11日23時(shí)求購毒品,上訴人與特情12日1時(shí)許即達(dá)成交易,短短時(shí)間,雙方就毒品交易價(jià)格、地點(diǎn)、約定時(shí)間一拍即合,因此本案不存在犯意引誘。”
?資料來源于《(2018)閩0723刑初84號(hào)判決書》。
21《(2018)皖12刑初77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院認(rèn)為但文潔案發(fā)前曾兩次因犯販賣毒品最被判處刑罰,在該起毒品交易中就毒品數(shù)量、價(jià)格中起積極主動(dòng)作用,因此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但文潔的偵查行為并不存在犯意引誘問題。”
22資料來源于《(2013)綿刑初字第28號(hào)判決書》。
23資料來源于《(2017)浙0382刑初637號(hào)判決書》。
24《(2016)滬0110 刑初375 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院根據(jù)相關(guān)證據(jù)認(rèn)為文紅安在與特情人員聯(lián)系前已經(jīng)持有毒品待售,且在特情人員向其購買冰毒時(shí),未予絲毫拒絕就于特情人員進(jìn)行了交易,因此文安紅實(shí)施販毒行為并非他人引誘的結(jié)果。”
25資料來源于《(2015)紹柯刑初字第67號(hào)判決書》。
26《(2018)鄂01刑初112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院認(rèn)為辯護(hù)人提交的視聽資料截圖形式要件缺失,證據(jù)形式不合法,亦不能證實(shí)照片中的男子與案件事實(shí)存在關(guān)聯(lián);該組照片交由江夏區(qū)公安分局刑事偵查大隊(duì)禁毒中隊(duì)民警辨認(rèn),中隊(duì)民警均表示該組照片中無本案線索中涉及的“特情”人員;同時(shí)××物業(yè)服務(wù)中心××、公安機(jī)關(guān)、陳俊的辯護(hù)人均出具情況說明證實(shí),未調(diào)取到證實(shí)存在犯意引誘的相關(guān)證據(jù)。綜上,現(xiàn)有證據(jù)不能證實(shí)本案部分毒品存在犯意引誘。故該辯護(hù)意見與證據(jù)、事實(shí)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納。”
27資料來源于《(2015)臺(tái)椒刑初字第942號(hào)判決書》。
28《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規(guī)定:“依照本節(jié)規(guī)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jù)使用。”
29《(2015)舟普刑初字第179 號(hào)判決書》寫道:“本案的證據(jù)是由特情偵查獲取的證據(jù),來源形式合法,可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jù),在事實(shí)認(rèn)定上不得以非法證據(jù)為由排除適用。”
30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最高法院臺(tái)上字”第5000號(hào)判決文書》寫道:“若行為人原本無販賣毒品營利之意思,因調(diào)查犯罪人員之引誘或教唆始起意販毒,即屬陷害教唆,不能認(rèn)已成立販賣毒品罪。”
31 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huì)紀(jì)要》認(rèn)為:“對(duì)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實(shí)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原則依法處理。”
32《(2015)無刑初字第00133 號(hào)判決書》寫道:“法院認(rèn)為被告人邰某某在起訴書中指控的第三起販賣毒品犯罪中,因誘惑偵查被公安機(jī)關(guān)查獲,同時(shí)因“犯意引誘”使得該宗冰毒自交易一開始即不可能完成,系犯罪未遂。”
33資料來源于《(2013)三刑初字第00029號(hào)判決書》。
34《〈刑集〉第58卷5號(hào)》第333頁寫道:“該判決認(rèn)為在沒有直接被害人之藥物犯罪等之偵查案件,僅以通常的偵查方法查獲該項(xiàng)犯罪有困難之情形,將可疑為一有機(jī)會(huì)即實(shí)行犯罪之意思者作為對(duì)象,實(shí)施誘惑偵查,應(yīng)解釋為是基于刑訴法第107 條1 項(xiàng)所定的任意偵查,而予以容許。”
35日本將誘惑偵查分為三種,即依比例原則實(shí)施“以無直接被害人之藥物犯罪等之偵查案件”,必要性原則實(shí)施“僅限于依通常的偵查方法查獲該項(xiàng)犯罪有困難之情形”,而對(duì)象之被誘惑人已具有犯意而有實(shí)行犯罪之嫌疑者為限,作為任意偵查合法性的三個(gè)檢驗(yàn)標(biāo)準(zhǔn)。
36日本學(xué)者認(rèn)為犯意引誘的非法性在于對(duì)象案件的范圍不限于“無直接被害人”的毒品犯罪等,且沒有高度實(shí)施誘惑偵查的必要性,且被誘惑的對(duì)象無犯意而沒有實(shí)行犯罪的嫌疑。
37基本案情為:警方因Jacobson 曾在成人書店以郵寄方式購買過含有男童及少男裸照的雜志,實(shí)施過同類型的犯罪行為,就鎖定Jacobson為偵查目標(biāo),并長時(shí)間誘使其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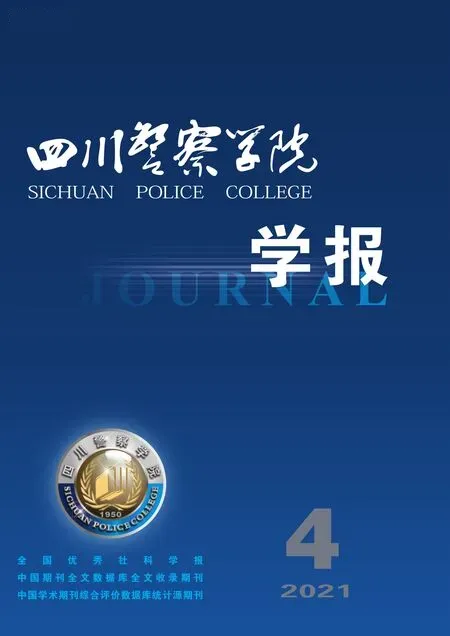 四川警察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1年4期
四川警察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1年4期
- 四川警察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基于學(xué)習(xí)進(jìn)階的翻轉(zhuǎn)課堂在公安院校物理學(xué)課程教學(xué)中的運(yùn)用
——以“力矩轉(zhuǎn)動(dòng)定律”為例 - 家暴案中受虐婦女殺夫行為之防御性緊急避險(xiǎn)的適用
- 認(rèn)罪認(rèn)罰從寬制度中被害人權(quán)利保障研究
- 法經(jīng)濟(jì)學(xué)視域下人臉識(shí)別技術(shù)應(yīng)用的法律規(guī)制
- 信息網(wǎng)絡(luò)安全管理義務(wù)的立法現(xiàn)狀、批判與匡正:從涂爾干社會(huì)分工論觀瞻
- 刑事裁判思維形式化傾向的類型與風(fēng)險(xiǎn)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