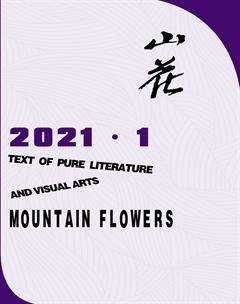梁山泊的雙重寓意(外一篇)?
李慶西

拙著《水滸十講》(文匯出版社2020年8月初版)出版時,正是上海書展,我兩次被拉到現場與讀者交流。我試圖簡潔地描述自己對《水滸傳》這部小說的基本解讀方案,講述中卻感到頭緒紛亂,譬如說到造反、招安與忠君互為因果的悖論關系,又不得不回頭解釋江湖法則與儒家倫理綱常,因為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有關聯。
本來“十講”是從不同角度辨析小說主旨,即席發言時我并沒有想好如何整合到一個思路中。過后重新梳理水滸敘事演化和意象表達,想來想去,梁山泊這個山寨實體正是聚焦多重敘述關系的一個集合,作為解讀的切入路徑或有方便之處。“十講”中有一篇專講水滸地理學,已約略涉及梁山泊的設意,可是如果要藉此說明小說的命旨,還不能僅據地理意義作出解釋,因為這不單純是一支江湖武裝盤踞之處,更是一個納入某種構想的江湖社會。因而,本文擬于“十講”之外,以梁山泊這個敘述主體為路徑,再辨宋江等人“上山”與“下山”之義,并討論《水滸傳》的敘事特色。
一
首先要說,梁山泊在水滸敘事中是一個虛構的存在,不能視如歷史上赤眉、綠林、瓦崗一類。當然,宋江確有其人,只是跟小說描述的情況大相徑庭。按史書記載,宋江并非以梁山泊為根據地,他這個武裝團伙一向慣用沖州過府的流寇式作戰方式。如《宋史·張叔夜傳》謂“宋江起河溯,轉略十郡”,《侯蒙傳》又稱“(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而至宣和三年,如《徽宗紀》所云:“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綜合上述史料,可知宋江這伙人是從河溯(又作河朔,泛指黃河以北)轉略齊魏,從今之山東半島運動到河南安陽一帶,繼而又遞次南下淮陽軍(今江蘇邳州、宿遷)和楚州(今江蘇淮安至鹽城)、海州(今江蘇連云港一帶)等地,最后是在海州被圍剿和招安。可見,宋江的造反跟梁山泊這個地方本無瓜葛。
在早期水滸敘事中,梁山泊好漢并不在梁山泊,而是在太行山。如元刊《大宋宣和遺事》,有孫立等人救出楊志往太行山落草的情節。再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所載龔開(圣與)《宋江三十六人贊并序》,在盧俊義、燕青、張橫、戴宗、穆橫五人贊語中都出現“太行”字樣,亦表明宋江最初的地盤是在太行山一帶。《水滸傳》第十六回敘說楊志押生辰綱過黃泥岡,已在濟州鄆城縣地界,梁山泊左近,而書中形容行路艱難,竟有“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此是太行山”之語。此處出現太行山字樣,應是小說家采擷宋人說話文本沒有處理干凈。查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太行山距離梁山泊幾乎千里之遙。
然而,《宣和遺事》不但提到太行山,亦有宋江奔梁山濼(泊)尋晁蓋的關目,而且還將兩地捏合到一處,說是晁蓋等人劫了生辰綱,與楊志等十二人結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為寇”云云。在水滸敘事中,這是梁山泊最早的出處。《宣和遺事》大抵拼湊宋人說話情節成書,太行山與梁山泊雜然并置,或是魯迅所謂“鈔撮舊籍”的痕跡。宋人說話已有講述水滸的風氣,是不爭的事實,如宋末羅燁《醉翁談錄》著錄《石頭孫立》《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數種,都是與水滸有關的名目,可惜那些話本無一存世。
元雜劇水滸戲亦是早于小說的水滸敘事。元劇存目之水滸戲有二三十種,傅惜華等人所編《水滸戲曲集》收錄有文本流傳的六種,即《黑旋風雙獻功》(高文秀)、《燕青博魚》(李文蔚)、《黑旋風負荊》(康進之)、《還牢末》(李致遠)、《爭報恩》(無名氏)、《黃花峪》(無名氏);另外還收錄明初朱有燉二種,即《黑旋風仗義疏財》《豹子和尚自還俗》,以及標以“元明間無名氏作”雜劇四種,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鬧銅臺》《王矮虎大鬧東平府》《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考慮到朱有燉和元明間無名氏雜劇與《水滸傳》成書時間較為接近,姑且視如小說之前的文本。這十二種劇目中,宋江的山寨概稱梁山泊,太行山一說已廢棄。雖然雜劇仍持三十六人之說,卻以“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描述梁山人馬,這應該是小說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來由。
需要指出,《宣和遺事》、龔氏贊序以及元劇水滸戲這些文本,不但早于小說《水滸傳》,亦早于《宋史》成書時間。《宋史》修于元末,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告竣,完全有可能采擷之前問世的各種文本。但修史者不取梁山泊之說,稱宋江“起于河溯”, 應該另有所據。這說法雖然含混,卻暗合早期太行山的傳說。
小說《水滸傳》將聚義之地定于梁山泊,乃延續元劇水滸戲的路數,亦可追溯到《宣和遺事》的記載。由此亦可見,將宋江等人安置于梁山泊,明顯是移花接木的文學手法。事實上,整部《水滸傳》并無多少史實依據(梁山一百零八人僅宋江一人見于正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將之列入“講史”一類,并不妥切。
二
當然,作為地理名稱的梁山泊并非文學虛構,這是真實的歷史地名。這片水域,古代名曰大野澤(又作巨野澤),在今山東巨野、梁山、東平諸縣之間。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元和郡縣圖志》稱其“東西百里,南北三百里”。據此可知,元劇和小說里說是“八百里梁山水泊”,并非夸張之語(“八百里”是古人詩詞楹聯中形容湖面遼闊之常用語)。但因常受黃河改道影響,梁山泊水體盈縮甚巨,五代時曾部分淤涸,而北宋真宗、神宗時兩度因黃河決流又使湖面大增。據譚其驤地圖第六冊(宋遼金時期),北宋末年的梁山泊是一個足有八百平方公里的腰形湖泊。當時梁山泊正是湖水豐盈時期,是長江以北(北宋境內)最大的湖泊。可是僅僅過了七八十年,在金代地圖上,梁山泊便只剩下原先三分之一的水面。到了元代,梁山泊就變成了一片面積不大的沼澤。小說《水滸傳》成書時,梁山泊這片水域干脆就不存在了,只是并不影響小說家拿水泊梁山大做文章。
從譚其驤地圖上看,梁山位于湖澤北端,宋時在壽張縣境內(今屬梁山縣)。《方輿紀要》介紹說梁山原名良山,因西漢梁孝王常游獵于此而更名。其謂“山周二十余里”(即方圓不足2×3公里),實在是很小的一座山。又謂:“宋政和中,盜宋江等保據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顧氏竟以水滸敘事為信史,可見學人以小說為“講史”亦由來已久。
《宋史》未將宋江與梁山泊扯到一起,但也說到梁山泊確有盜匪,幾處文字分別見于蒲宗孟、許幾、任諒諸傳。蒲宗孟是神宗時人,熙寧間曾為鄆州知府;許幾、任諒大率與宋江同時代,一為鄆州知府,一為提點京東刑獄。這三人曾為梁山泊周邊州府官員,各傳舉述他們針對轄區內梁山泊(濼)的治盜事略,有謂“梁山濼多盜”“梁山濼漁者習為盜”云云。從神宗熙寧年間到徽宗政和、宣和年間,實有半個多世紀,梁山泊一直匪患不絕。但據各傳所述,梁山泊盜匪主要是當地漁戶,藉行舟之便做些劫掠的勾當。這等小打小鬧與小說描述的梁山泊武裝有天壤之別,他們根本不可能跟官府作正面抗衡。
盡管《宋史》敘述的梁山泊與宋江等人毫無關系,但是水滸敘事偏偏傍上了這處匪患之地。繼《宣和遺事》將梁山泊(濼)寫入之后,元劇和小說都將此作為敘事的核心地點。
水滸文學敘事中為什么要將山寨從太行山移至梁山泊?為什么要讓宋江改變流寇式作戰方式,偏在水泊梁山建立根據地?這是解讀《水滸傳》敘事意圖之關鍵。
作為嘯聚山林的根據地,雄偉嵯峨的太行山顯然具有更為理想的地理條件,相形之下,梁山不過是一抔土丘。或許,水泊是一個重要因素,宋江手下有張順、李俊和阮氏兄弟等一干水上健兒,挪至水泊梁山則便于小說敷衍精彩的水戰。但這不是一個絕對的理由,因為元劇水滸戲里宋江等已在梁山泊安營扎寨,而存世的十二種早期水滸戲里并沒有水上作戰的關目。不言而喻,梁山泊的地理意義不能僅從其軍事活動和生存角度去理解。水泊梁山打開了文學想象的空間,自然有著更重要的承載。
其實,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梁山泊的地理位置。從譚其驤地圖上看,梁山泊與東京開封府的直線距離不到兩百公里。兩地之間如此接近,這絕對是一個超現實的大膽構想。許多水滸研究者竟沒有意識到,何以將一支強大的江湖武裝擺在距離東京不遠的地方。這豈不是朝廷的肘腋之患?《三國演義》說關羽在樊城水淹七軍,探馬飛報許都,曹操慌亂之中便有遷都之議。樊城到許昌,比梁山泊到東京還遠出一大截(如今高速公路也有三百五十公里)。《三國演義》是講史,是寫實,旬日可達的距離足以讓敵方極度不安。但《水滸傳》玩的是象征和隱喻,自有某種春秋大義,實不以寫實主義考量軍事問題。所以,不管這一切是否可能,硬是將一個想象的存在擺到了你面前。
將強大的梁山泊與廟堂之下的東京作近距離并置,無疑是一種形成對照的思路:一邊是“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一邊是綱維弛廢的大宋朝廷,分明彰顯盜亦有道的救贖之義,不啻更新了“山高皇帝遠”的江湖法則。江湖匪遠,廟堂不高,小說第八十回梁山泊擊潰十路節度使進剿,忠義堂筵席上出現了燕青與高俅廝撲爭交的一幕,這是將綠林與官家置于同一平臺的政治隱喻。以競技替代干戈,從對抗走向對話,儼然營造了一種和解與合作的氣氛。
三
小說里,梁山泊最早出現于林沖敘事——火燒草料場后,柴進讓他去梁山泊投奔王倫。那時候山上只是王倫、杜遷、宋萬三個頭領(還當算上酒店的朱貴),底下七八百嘍啰,以打家劫舍為務。至晁蓋、吳用等人上山,梁山泊已初具與官軍正面對抗的實力。當然,山寨真正強大是宋江上山之后,宋江從江州和黃山門帶過來的好漢就有二十余人,這時梁山泊的座次已排到四十位了。此前魯智深、楊志、武松已在二龍山落草,孔明、孔亮據有白虎山,李忠、周通占桃花山為王,后來三山聚義打青州,一同歸了梁山泊。之后大鬧華山,又有少華山史進、朱武一伙加入。就敘事形態而言,梁山泊的逐步壯大是一個遞次匯入的過程,故前人有謂“百川歸海”。
筆者在“十講”第二講中專門提出,《水滸傳》包含“小水滸”和“大水滸”兩層敘事內容。具體說來,“小水滸”是表現個體冤情和反抗的個人敘事,其中包括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江湖行徑。小說是由若干“小水滸”敘事分別導入,這是它的結構方式,書中前三分之一篇幅分別敘述王進、史進、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和宋江等人蒙受冤屈,或逃避或反抗的經歷。其間插入晁蓋、吳用等人智劫生辰綱而上山聚義之事,形成梁山泊和其他幾處山寨割據態勢。在宋江上山之前,所有這些反抗和劫掠,都沒有什么政治目標,“小水滸”敘事特點是不作政治倫理層面上的考量,從個人復仇到投名入伙,只是沿循江湖道義和生存法則。宋江入伙后改變了江湖常態,將散落各處的好漢勾連到一起,終而使枝枝蔓蔓的個人敘事逐漸匯聚于“大水滸”的敘事主干。“大水滸”的目標是將江湖道義融入王權體制,讓朝廷承認反抗的合法性,也讓山寨弟兄們承認王權乃天道,這是一種政治妥協的安排。
宋江作為鄆城縣一名刀筆小吏,原非江湖人士,卻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譽,可見其心念蒼生已久。但宋江從來就不是異端分子,而是信奉王道與禮治。按小說敘事邏輯,那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公平與正義(而不是一般所謂“階級矛盾”),是謂“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容與堂本李贄評語),實是體制失衡。宋江不需要從理論上明辨儒家倫理綱常的設計缺陷,眼前的事實告訴他,仁義忠恕的圣人教諭已不能整肅綱紀,而扶危濟困的江湖道義卻行之有效。所以,他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圣人之道納入江湖規則,如何在王權體制內重建倫理秩序。
小說第四十二回,宋江還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書,是全書一大關目。宋江上山之初,藉此提出“替天行道”和“輔國安民”的方針實是十分重要。其時梁山泊已從半隱秘狀態的江湖社會變身為公然割據一方的軍政實體,單憑行俠仗義的江湖倫理已難以統轄人心,山寨既已做大做強,就不能沒有一個超越個體命運的大目標。當然,這個大目標并非將造反進行到底。造反是為了伸張正義,但正義不能永遠表現為叛逆姿態。宋江希冀在王權框架內改革弊政,這就需要跟朝廷合作,所以后邊有了招安的故事。反抗 / 妥協 / 救贖,這恰是《水滸傳》的正反合之題。我在“十講”第三講中寫道:
《水滸傳》無疑是將民間造反上升為具有意識形態內容的政治行為,因為反抗的理由就是這種想象的合理性——他們遠比那些廟堂之士更具仁義之心,遠比帝國官僚體制更切合儒家政治倫理,遠比主流社會更趨光明。所以,他們有了“替天行道”的責任與使命,亦漸而革除了某些黑社會屬性的江湖陋習(如劫掠平民,擄獲婦人等)
相比這番“強盜從良”的敘事,山寨之外卻是十分不堪,整個體制已黑社會化。小說生動地展示了一條自上而下的黑色鎖鏈——在朝是蔡京、童貫、高俅,地方上是張都監、蔡九知府、劉知寨之類,還有高廉(高俅的叔伯兄弟)的小舅子殷天錫,衙門里為虎作倀有陸虞侯、黃文炳諸輩,鄉閭惡霸乃西門慶、鄭屠、蔣門神、毛太公,最底層的是潑皮牛二。
四
從另一方面看,正是與官府對峙的現實處境,使梁山泊構筑了自身的理想化圖景。小說刻意將梁山泊描述成一個和諧有序的團體,竟很少涉及山寨內部矛盾,這本身帶有很大的假定性,即假定不會發生內部訌爭和分裂之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幾點:
一、梁山泊匯聚二龍山、白虎山、桃花山、少華山、清風山、枯樹山、芒碭山等各個山頭的好漢,還有大批招降的中高級軍官,卻從未發生山頭派系訌爭。
二、梁山一百零八人經歷大小戰事無數,沒有陣前倒戈或是暗中叛變者,沒有敵對勢力滲入(整部小說未有針對梁山泊的離間和策反),亦可印證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三、更重要的是領導層未見窩里斗。宋江與晁蓋、盧俊義,心性、旨趣并非一致,但宋江不論作為二把手還是一把手,與前后兩位搭檔從未產生齟齬,更不消說有何公開化分歧。
其實,宋江和晁蓋的關系很微妙,小說的處理方式亦頗特別。晁蓋去世之前,宋江并不公然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這是盡量不使二人因方針政策產生矛盾的敘事策略。九天玄女授天書之際,對宋江專門叮囑道:“只可與天機星(吳用)同觀,其他皆不可見”。這是神道設教的手法,使宋江獲神諭之助,讓晁蓋成了局外人。
凡此種種,自然皆非寫實主義。不妨對照《三國演義》,蜀漢一方同樣被賦予忠勇節義的理想色彩,卻不像梁山泊這樣鐵板一塊。關羽鄙視黃忠欲與馬超爭鋒,荊州危急之際劉封則拒援關羽;而叛變內斗亦皆有之,先有孟達投魏,傅士仁、糜芳投吳,后有魏延與楊儀死掐,黃皓讒害姜維……相比之下,梁山泊可謂一方凈土。一種想象的純凈。一個龐大的江湖組織被描述得如此和衷共濟、步調一致,自是凸顯山寨的凝聚力,表明江湖道義足以維系人心。不過,這種烏托邦想象并非全是小說家的無根之說,而是演繹古代圣賢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這種古老的政治傳統,因而魯迅評價《水滸傳》亦作“國政弛廢,轉思草澤”之論(《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五篇)。
作為以理則和邏輯推衍的寓言敘事,梁山泊大體亦是一種神話構成。小說第七十一回,梁山好漢排座次后,便有一篇贊語,稱道梁山泊的好處——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杰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并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仆,爭斗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刀槍,或奔馳,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
這番描述簡直就超越了古代先賢構想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經典中,“大同”只是一個理論概念,而《水滸傳》則在某種程度上勾勒了一幅趨近完美理想的具體圖景。從帝子神孫到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通常以為其中必然有著互為主體的階級鄙視鏈,但《水滸傳》恰恰相反——不僅將這些人組合成一個和諧的團體,而且“隨才器使”,各盡所能。難怪梁啟超認為“此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小說叢話》),而近代南社作家黃人、王鐘麒則從中看到了“平等”和“社會主義”(參見《水滸十講》第三講)。他們的認知大抵來自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所描繪的那種社群形式和群己關系。
英國人托馬斯·莫爾所著《烏托邦》被認為是最早建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學作品,該書出版于一五一六年,那是中國明朝正德年間,而《水滸傳》成書時間則在元末明初,比莫爾那本空想的游記要早一個多世紀。而且,《水滸傳》的寫法是附會于實際的歷史背景,固然不是真正意義的“講史小說”,卻也不似莫爾那種憑空結撰。這個中國式的烏托邦嵌入了現實語境,有其改造現實的針對性。
當然,這是一個建立在舊制度框架內的烏托邦,可謂儒家禮治思想的極度發揮(具有某種創造性或曰變異性思路),只是這種想象依然囿于某種根本局限。但不管怎么說,梁山泊讓江湖社會大行禮治之道,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認知——這個山寨烏托邦建構無疑包含超越時代的前瞻意識,反映了《水滸傳》成書年代的讀書人在“鐵屋子”里尋求新思維的努力。可惜,后來的研究者們大多未意識到這一點。
五
不能說梁山內部矛盾毫無顯現,正是招安這樁大事使梁山好漢一度產生分歧。第七十一回石碣天書之后,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大鬧菊花會,嚷嚷招安“冷了弟兄們的心”。而且,他們不認為梁山的道義能改造滿朝奸邪,正如魯智深所說,“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殺怎得干凈?”第七十五回,太尉陳宗善來洽談招安時,阮小七偷換御酒,李逵怒扯詔書,存心將這事情攪黃。事后吳用勸慰宋江,“哥哥,你休執迷!招安須自有日,如何怪眾弟兄們發怒?”看來吳用的態度比較曖昧,他不反對招安,卻也并不積極推進。
反過來看,李逵是幾度嚷嚷殺去東京,要將宋大哥推上皇帝寶座,可這改朝換代的主張在山寨里幾乎沒人呼應。在弟兄們眼里,梁山泊便是自己的理想國,他們似乎滿足于“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山寨平均主義。按說這是“小水滸”敘事的最佳結局,但這仍是一種懸置狀態。金圣嘆“腰斬”水滸,試圖讓故事定格于此,但他忽略了整合一百零八人自是一個新的敘事起點。如果梁山泊只是一個被帝國勢力隔離的烏托邦,它會是怎樣一種存在?“強盜”既做不成“英雄”,而“英雄”亦將繼續打家劫舍。
其實,他們并未真正獲得自由。他們不曾意識到,從某種意義上說,江湖本身亦是牢獄。因為與整個社會相隔離,梁山泊只是一個封閉的烏托邦,日常亦猶似扃禁的牢城(如林沖之于滄州,武松之于孟州,宋江之于江州)。我在“十講”第四講考辨宋代刑獄制度,對牢城與梁山泊的隱喻關系略作闡述——前者大率如福柯所稱“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而梁山泊這種“隔離區”在廣義上亦納入了“規訓社會”,乃至擴展到一種無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視主義”機制(參見《規訓與懲罰》第三部分第三章)。所以,盡管李逵反對招安,卻是最能感受到山寨的幽扃,他一有機會就往山下跑(參看《水滸十講》第六講)。宋江決意去東京賞燈之際,那種躁動明顯流露內心重返社會的渴念。他一再申明“權居水泊,專等招安”,不僅是對朝廷官員表明心跡,亦真正是將此作為回歸社會的救贖之路。
不可忽略的是,小說里一再出現牢獄的隱喻。宋江等一百零八人原是鎮于龍虎山伏魔殿石穴中的“魔君”,開篇第一回就有交代,后來梁山泊聚義亦是這個隱喻的延伸。當忠義堂下掘出石碣天書,這些天罡地煞早已分定次序。這個寓言帶有“原罪”的意味,小說家顯然意識到了“小水滸”的反抗敘事對于王權制度的破壞力——第七十二回中,柴進潛入宮苑,在睿思殿屏風后看到御書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國家被我們擾害,因此時常記心,寫在這里。”他割下“山東宋江”四字帶回來給宋江看,相對嗟嘆不已。
由于宋江的威望和感召力,反對招安的聲音并未持久發酵,梁山泊終究是步調一致。宋江既然領受“替天行道”的法旨,明確“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的政治倫理關系,便決意將梁山眾人引入“去邪歸正”的軌轍。然而,謀求招安實是一個艱難過程。從第七十二回到第八十一回,宋江東京賞燈,太尉陳宗善梁山之行,又屢屢大敗官軍以及捉放高俅,都是敘述招安的關目。整個過程曲曲折折,內外皆有阻力。最后是燕青潛入東京直達天聽,終于討得赦罪詔書。
六
將反抗之路歸結于禮治之道,這是尋找出路的思想,宋江盡管歸順心切,其真正意愿自然不是謀官求爵,而是讓江湖與體制相融合,說到底是要打破反抗與殺戮無限循環的歷史怪圈。前引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贊語,最后還有一句“休言嘯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廟”,即點明了小說敘事意圖——梁山泊只是從山林到廊廟的中轉站,一個過渡性烏托邦。在容與堂百回本中,這整段贊語文字頗有出入,最后兩句是“休言嘯聚山林,真可圖王伯業”(“伯”通霸,王伯業即王霸業)。休言之下,便是一番慨嘆,明明可自成王霸之業,卻不以改朝換代為目的。這是贊詡宋江深明大義,還是替梁山泊感到惋惜?這是小說頗有深意的地方。
魯迅評論招安一事,有一點似可商榷,他在一篇雜文中批評說:“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其實,小說寫得很明白,其時梁山泊已是兩贏童貫、三敗高俅,軍事上占有壓倒性優勢;招安根本不是迫于“大軍一到”的壓力,反倒是梁山泊倒逼朝廷接納自己。小說里特別強調宋江的主動意愿,這一點不容忽視。
當然,招安的結局并不好,梁山泊絲毫未能改造體制,甚至都不能融入其中。招安之后,宋江率眾進入“輔國安民”的敘事,小說后三分之一篇幅主要是“征四寇”,即出征遼國和討伐田虎、王慶、方臘。這幾個部分大多敘述潦草,歷來為人詬病(但其中也有不俗之筆,如瓊英與張清的“宿世因緣”,還有王慶身世各節)。然而,作為一部悲劇性的大作品,這些恰恰又是不可或缺的敘事過程,最后的悲劇氣氛直是躍然紙上。征方臘歸來,梁山眾將十損其八,回到東京只剩二十七人,最后宋江、盧俊義等人又死于御賜毒酒毒膳。為王前驅,落得這般下場,說是“狡兔死,走狗烹”未免太損,而事實確是如此不堪。再看滿朝奸佞,依然作威作福,一切都回到了原點。招安以后的情形不遑細述,讀到魯智深聞潮而寂,獨臂武松六和出家,直是令人凄涼無已。燕青遁去之日,盧俊義還指望衣錦還鄉,“圖個封妻蔭子”,他對燕青說,“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燕青卻道,“只恐主人此去,定無結果。”燕青實是高人,最后果然是一個顛覆性結局。
“征四寇”雖說都是攘外安內的大事件,卻依然是脫離史實的憑空結撰。唯有討方臘之事史書約略提及,《宋史·侯蒙傳》謂:(侯)蒙上書言:“今青溪盜起,不若赦(宋)江,使討方臘以自贖。”但侯氏的建言并未被朝廷采納。《宋史》記述方臘起事始末,概見《宦官三·童貫傳》,剿滅方臘的是童貫、譚稹率領的禁軍與秦晉廂兵,宋江未參與其事。小說家慣于附會歷史,卻以完全的虛構手段保持敘事自由。用梁山泊人馬討剿方臘,自是瓜皮搭李樹,藉以將梁山泊的烏托邦推向反面烏托邦。
有一點相當耐人尋味:招安之后,樞密院計議要拆散梁山泊人馬,正遇遼國來犯,在太尉宿元景干預下,朝廷讓宋江帶著自己的隊伍前往征剿。因而以后幾次出征,梁山泊亦一直保持自己的建制,仍是宋江和盧俊義為正副先鋒(統帥)。小說家這個刻意安排,使得離開了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人變成了一個流動的梁山泊,繼續演繹戰場上的優勝記略。
流動的梁山泊以南征北戰的軍事勝利完成了“去邪歸正”的救贖之義,同時走向了命運的反面。縱觀整部作品,仍是一個“反抗-絕望”的敘事模式。走出山林草澤的梁山泊,穿過廊廟下的陰影,終于墜入命運的深淵。
宋江死后葬于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那是個四面俱水的地方。但蓼兒洼不是在梁山泊么?當初柴進讓林沖去投王倫,介紹說“……地名是梁山泊,方圓八百余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晁蓋等人撤往梁山泊時,阮小七在蘆葦叢里唱“打魚一世蓼兒洼……”書里沒有說明怎么會有兩個蓼兒洼,但不妨視作一個流動的意象,起于彼,終于此,彼此竟是一處。“魔君”也好,冤魂也好,終而神聚不散。
七
一直未想通的問題是,魯迅為何將《水滸傳》歸入“講史小說”?應該說,這部小說是將寓言編織在一個具有歷史維度的框架中,只是給人感覺具有“講史”性質而已。如前所述,梁山泊人物唯獨宋江一人見于《宋史》記載,書中所有故事情節均無史實依托。但小說家以時間、空間,以及某些人物和事件作為歷史標識,似乎給人造成一種敘史風格的印象。如,宋徽宗和高俅、蔡京、童貫等當朝奸佞確是真實人物;各處城鎮和政區亦盡量采用實有的歷史地名(雖然錯訛不少);至于北宋末年與遼國的戰爭以及方臘起事,則是當時真實事件。不過,這些只是小說家藉以假托歷史的背景元素,使得敘述看上去似有某種寫實特點。
“講史小說”源自宋代說話的一個分支,它與通常所說的“歷史小說”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宋代文獻中關于說話家數有不同分類,但“講史”是一個公認的名目,吳自牧《夢粱錄》有較為詳備的釋義,即:“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征戰之事。”(卷二十“小說講經史”條)可見“講史”乃直接依托歷史敘事,是將歷史敘事通俗化的一種文學手段。這種說話家數后來就成了一種小說路數,魯迅討論“講史小說”,所舉《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東周列國志》等皆屬此類,直到近世尚有蔡東藩所著歷朝通俗演義。
但《水滸傳》恰恰不應被攬入講史之屬。這是一部假托歷史的寓言小說,或者說就是一部帶有寓言性質的歷史小說。它既非講史,亦非寫實,既是烏托邦小說,也是反烏托邦小說。可以說是一體兩面:一方面它表現以江湖道義融合古代圣賢的大同理想,重建禮治之道的文學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推演出一個悲涼而無奈的結局,事實上在它敘述的歷史語境中,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整部作品通過“小水滸”與“大水滸”參差交互的復雜敘事,最終完成了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的自我解構。
語詞三國
錢鍾書《談藝錄·七六》引《隨園詩話》“世有口頭俗句,皆出名士集中”一條,是謂詩家語亦成民間俗語,所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之類,凡十余例。錢氏辨其詩例來源,又厘正若干舛誤,旨在溯本求源。至于是否詩家采擷俗語入詩,自亦無以反向考證。其實,這種語義擴散現象不獨在詩一方,在小說戲曲等敘事作品中更是大量存在,如《三國演義》和三國戲衍生的種種譬語廋詞(包括成語、俗語、歇后語等)就是一種特殊的語詞現象。
由小說戲曲導出的口頭俗語,緣自三國人物故事的最多。如說到呂布,既有“三姓家奴”的惡謚,又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的贊詡。說到關羽,從“千里走單騎”“單刀赴會”“刮骨療毒”“水淹七軍”到“大意失荊州”“敗走麥城”,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諸葛亮是“舌戰群儒”“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出師未捷身先死”……至于曹操,你馬上就能想到“說曹操,曹操到”,更有 “挾天子以令諸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乃至“天不滅曹”等種種說法。這些或是采自文本本身,或是在傳播過程中生成的語詞和典故,這里姑且稱之為“傳述性語詞”,因為這些東西經常出現在人們口語或文字表達中。
從這種語言現象來看,在公眾傳播層面上,三國的影響因子遠甚于其他古典名著。譬如,水滸盡管也是家喻戶曉,但它生成的譬語廋詞卻并不多,像“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或是“李逵遇上李鬼”這種俗語,你能舉述十個算你厲害。《紅樓夢》有“假作真時真亦假”,有“東風壓倒西風”,有“劉姥姥進大觀園”,有“大有大的難處”,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可是搜搜刮刮也找不出太多。
《三國演義》開篇便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看似村儒俗論,卻是概括天下大勢的周期律。小說家比史家更懂得國人的接受心理,以循環論解釋歷史總有希望所在,風水輪流轉,自是超越現實的一種預期,絕對不是福山那種終結論。當然,這類語詞并非一概出自三國文本,如“天不滅曹”,作為惡人難除的譬語,實是由接受層面生成。曹操屢屢絕處逢生,捉放曹前后已是三度逃生,戰濮陽從呂布眼皮子底下溜走,宛城之厄有典韋舍身護衛,華容道幸而遇上念舊的關羽,潼關潰敗則是割須棄袍又躲過一劫。曹操不死,自是劫數未盡,劫數亦自被認為是一種規律。赤壁一戰,諸葛亮料定曹操兵敗必走華容道,偏讓與曹操有舊誼的關羽去把守那兒,劉備擔心關羽真的會放走曹操,而諸葛亮夜觀星象,明知“操賊未合身亡”,是故意給關羽留了這份人情。這不同于民諺“好人不長命,惡人活千年”的無奈之嘆,“天不滅曹”好像大有玄意,藉天命所示,透出超然于紛紜之局的智慧特點。
在語詞建構的三國劇情中,“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以說是事關大局的一句臺詞。曹操能夠結束董卓死后的北方亂局,一個重要因素是將獻帝攥在自己手里。其實,車駕流落之初,袁紹的謀士沮授已看到這步棋,《后漢書·袁紹傳》記述他給袁紹出主意:“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但袁紹另外兩個謀士郭圖、淳于瓊則反對迎駕,認為漢室陵遲,迎天子已無意義。袁紹不出手,結果讓曹操抓到了這張好牌。作為民間語匯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既是挾制諸侯的霸凌手段,也帶有四兩撥千斤那種機巧喻意(捏住了獻帝等于掌握了某個樞紐)。
顯然,三國敘事的智慧性更多表現為謀略特點,因而這類語詞生成亦多。如劉備為麻痹曹操,故意在許昌下處種菜,以為“韜晦之計”。這里所用“韜晦”一語,并非小說自創,《舊唐書·宣宗記》:“歷太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群居游處,未嘗有言。”但毫無疑問,正是《三國演義》使它成為“傳述性語詞”。一些原本表示小說情節的語詞,如“蔣干盜書”“借東風”“空城計”之類,在民間傳述中成為一種謀略性譬語。另外,如“劉備摔孩子”“周瑜打黃蓋”之類,亦是接受層面生成的譬語廋詞,但這種表達心計與謀略的歇后語在傳述中則難免偏離其本義,“周瑜打黃蓋”是要誘騙曹操,歇后之義卻是雙方愿打愿挨的默契。
說到智謀,人們愛拿諸葛亮說事兒,圍繞這位謀略大師的譬語層出不窮,從“初出茅廬”“錦囊妙計”“ 諸葛亮吊孝”到“諸葛一生唯謹慎”,再到“事后諸葛亮”,再到“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實際上是對諸葛亮的過度消費。三國的智謀人物不唯諸葛一人,可是有關智謀的語詞偏是集中在他身上。為何不以司馬懿取譬?當然,這跟三國故事的敘事立場有關,從《三國志平話》到元劇三國戲,再到《三國演義》,諸葛亮一向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良形象。杜甫詩中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更是平添一種悲劇色彩。但同樣作為謀略大師的司馬懿,卻因為是人們不喜歡的反派人物,就被褫奪了智者的身份。
在三國“傳述性語詞”中,跟司馬懿相關的語匯很少,“得隴望蜀”算是一條。小說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漢中,司馬懿建言火速進兵西川,趁劉備立足未穩一舉拿下益州。曹操不聽,還挖苦說:“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不過,作為成語的“得隴望蜀”,并非出自《三國演義》,原本是漢光武帝自嘲之語。東漢大將岑彭征討隗囂、公孫述時,在隴西合圍西城、上邽二城,《后漢書·岑彭傳》謂:“(光武帝)勑(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光武之言,乃指示岑彭下一步征伐目標,捎帶作自我解嘲。唐人編纂《晉書》時將此語挪到司馬懿頭上,則是將其作為嘲謔對象。《晉書·宣帝紀》謂:“(司馬懿)從討張魯,言于魏武(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顯然,小說此節據《宣帝紀》復制而來。
在三國文學敘事中,司馬氏父子既是蜀漢的敵人,又背負篡魏的罵名,所以民間又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歇后語。其實,此語亦出自史書記載。《魏志·三少帝紀》記高貴鄉公率宮人討司馬昭被殺,“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句下,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在后人傳述中,“司馬昭之心”便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的意思。
從司馬懿父子擅政到司馬炎代魏,民間的說法就是篡魏。史家或許不認為司馬氏的操作缺乏合法性——周公居攝,堯舜禪位,古已有之;至于代魏還是篡魏,這種政治倫理問題自有道學家小說家去究詰。其實,更多的關懷在于大眾傳述,罵完曹氏篡漢,接著再罵司馬氏篡魏。民間的政治正確以忠恪和道義為準則,容易將歷史過程約化為好人與壞人的政治。
“漢賊不兩立”歷來是申明政治倫理的熱詞,這原是諸葛亮傳述劉備的說法,出自《后出師表》:“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演義》既以劉備和蜀漢為承祧漢室的合法繼承人,亦大體貫穿“漢賊不兩立”的敘事立場。在黃巾作亂背景下,小說從劉關張“桃園結義”進入故事,無疑體現了這種意圖。異姓結契所包含的忠誠和道義,由此成為政治社團的倫理要則。詞語傳述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等等,都是將劉關張休戚與共的兄弟關系作為人格至高境界。還有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則是表白絕對忠誠的政治操守。
當然,漢末三國的政治關系并非黑白分明,涉及的政治倫理問題亦有其復雜之處。如關羽“降漢不降曹”,如徐庶“身在曹營心在漢”(另有“徐庶進曹營—— 一言不發”的歇后語),則是以曲折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忠恪。倘若以“漢賊不兩立”的決絕立場劃線站隊,哪怕是暫時寄身曹營也未嘗不是一種失節。然而,有趣的是,劉備本人亦曾是曹操的座上賓(所謂“勉從虎穴暫趨身”),曹操還跟他“煮酒論英雄”,暢言天下大勢來著。其實,漢末三國之際仍是顧炎武所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那種局面,亂局之中大家都奉行適者生存的機會主義,而劉備恰恰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他投靠曹操之前,曾依附于袁紹、呂布,之后又傍上劉表,赤壁之戰與孫權結盟,最后竟鳩占鵲巢奪了劉璋的地盤。按說劉備不大可能要求別人都是一副寧折不彎的氣節。
所謂“漢賊不兩立”,很可能是藉《后出師表》假傳先帝遺旨。魏蜀吳相繼建國后,“士無定主”的局面漸已改變。諸葛亮以延續漢祚為立國之由,用政治正義的悲情話語建構國家意識形態,并借助持續的伐魏戰爭凝聚人心(參見拙文《代漢·祀漢·去漢》,刊于《書城》2020年7月號)。所以,自諸葛亮主政之后,蜀漢幾乎沒有出現過內訌和反叛者。雖說諸葛亮死后有魏延嘩變,但魏延之叛實是與楊儀水火不容,并非真有異心(參見拙文《魏延之叛》,刊于《讀書》2016年第4期)。當然,諸葛亮歷來不喜歡此人,稱之腦后有“反骨”——這也是源自《三國演義》的一個著名譬語。早在關羽取長沙時,魏延城頭起義,諸葛亮卻認為此人不可留——“云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斬之以絕禍根。”(第五十三回)這個日后得到應驗的推測,自是小說家的安排,本意乃表現諸葛亮如何料事如神。但這種過度強調隊伍純潔性的政治倫理意識,亦確契合當日意識形態之變化。“反骨”一語,在諸葛亮尚有以形貌取人的一面,而在后人傳述中已完全抽象為某種性格特點。現在人們說某人有“反骨”,實不在腦后,而是指其內心的桀驁不馴。
三國譬語廋詞里邊,最具隱喻意味的似乎是“雞肋”一說。曹操與劉備爭漢中,屯兵日久,進退兩難。夏侯惇來稟請夜間口令,曹操正就餐,見碗中有雞肋,隨口便說“雞肋,雞肋”。 此物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主簿楊修即由此推斷曹操將要撤兵,便吩咐手下收拾行囊。曹操忌恨楊修太聰明,便以擾亂軍心為由將他斬了(第七十二回)。楊修“雞肋”之解,原見《魏志·武帝紀》及《陳思王傳》裴注引《九州春秋》《典略》。關于楊修之死,諸史說法不一。《典略》稱曹操殺楊修是因為“漏泄言教,交關諸侯”;《后漢書·楊修傳》說是因袁術外甥的緣故,“慮為后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則謂楊修與曹植“飲醉共載”,又謗訕曹彰,惹怒了曹操,故收殺之。楊修不算重要人物,后人記憶中主要就是這份“雞肋”之解。
國人常說的“望梅止渴”“樂不思蜀”等成語,大抵也從是小說里得知。小說第二十一回,曹操告訴劉備:“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邊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這個“望梅止渴”故事原出《世說新語·假譎》,小說很巧妙地插入“煮酒論英雄”一節。至于“樂不思蜀”,說的是后主劉禪降魏后已不思舊國,其實是小說借用《漢晉春秋》記事,在第一百十九回。《蜀志·后主傳》“后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句下,裴注引習鑿齒曰:“司馬文王與禪(劉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小說幾乎完全復制了這一段,句中司馬文王就是司馬昭。
源自史乘的三國語詞還有“煮豆燃萁”“吳下阿蒙”“生子當如孫仲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等等。前兩條分別見于《世說新語·文學》和《吳志·呂蒙傳》裴注引《江表傳》。“生子”條是曹操贊詡孫權的話,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須口不克,見孫權“舟船器杖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此見《吳志·吳主傳》裴注引《吳歷》。“寧飲”一條見《吳志·陸凱傳》:孫皓甘露元年將都城從建業遷到武昌,全賴揚州百姓“泝流供給”,民間苦患不堪。陸凱上疏直陳徙都之弊,引用當時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孫皓未必肯納諫,但物流供給如此困難,終究撐不下去,第二年就將都城遷回了建業。
除了這類采自史籍的典故,更多由三國敘事帶出的傳述性語詞,是直接從故事中概括而來,如“一時瑜亮”(又有“既生瑜,何生亮”),如“大意失荊州”,如“揮淚斬馬謖”等等。這些語詞不像“望梅止渴”那種插入性文本片斷,而是受眾記憶梳理的敘事情節,藉以傳述某種理則。甚至有些并無理則可言,僅僅是某種特點的描述,也成了民間口頭語,如“寶刀不老”,小說第七十回:“忠(黃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卻不老。”;如“赤膊上陣”,是第五十九回許褚大戰馬超的場面;還有“扶不起的阿斗”,實是讀者對后主劉禪印象的準確概括。
有趣的是,有不少取譬三國人物的語詞跟三國故事毫無關涉,亦非某種創造性誤讀,如“事后諸葛亮”“關公門前耍大刀”一類,只是將三國人物作為類型符號,代入某種被嘲謔的行為現象。尤其拿張飛說事兒的歇后語,竟有一大堆:“張飛繡花——粗中有細”“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張飛吃秤砣——鐵了心”“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碟”……這些民間謔語描述的張飛,只是作為某種人物特征的借代,完全是生活層面的意義生成,根本與文本無關。不知為什么,這些諧謔語還都找上了張飛。從網上又查到這些——
張飛賣秤砣——人強貨硬
張飛賣豆腐——人硬貨不硬
張飛賣肉——一刀切
張飛擺屠案——兇神惡煞
張飛扔雞毛——有勁難使
張飛請客——不領情不行
張飛翻臉——吹胡子瞪眼
張飛耍杠子——輕而易舉
張飛嗑瓜子——不夠塞牙縫的
……
在三國人物中,按說張飛并不是最具性格意義的角色,曹操、劉備、關羽、諸葛亮、孫權、周瑜、司馬懿,甚至呂布,性格都比他有層次,但人們偏就找上他了。這一點亦頗奇怪。你可以說這些都是好事者胡亂編造,可是為什么偏拿張飛說事兒?脫離了三國語境,粗糙而率性的張飛愈發被塑造成一種卡通化的呆萌形象。
以人物而論,三國傳述性詞語分布極不均衡,與曹操、關羽、諸葛亮有關的最多(涉及張飛的多已脫離三國敘事,此姑不論),劉備、呂布、周瑜等次之。奇怪的是,有些重要人物居然并不是詞語取譬的對象。譬如,前期的袁紹,后期的姜維,好像找不出一條與他們有關的譬語廋詞。袁紹志大而顢頇,姜維則是忍辱負重的悲劇人物,這兩人都有故事,按說都可以從中抽繹生動的詞語,卻是沒人理會。詞語的生成與傳述好像另有一種法則,或者干脆并無規律可循,反正不是文學的套路。
從小說敘事時間來看,傳述性詞語大多由前八十回導出,后四十回較少產生讓人口口相傳的語詞。其實,就故事而言,《三國演義》后三分之一不算太遜。魯迅評論《水滸傳》時說過“一部大書,結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但《三國演義》有其特殊性,它是根據史傳撰述的“講史小說”,其敘事梗概大體以史實為脈絡,各方勢力消長是一個客觀過程,這不同于一般小說家之結撰。但為什么后四十回產生的傳述性詞語比較少呢?想來大概有這樣兩個原因——
首先,最受人關注的三國人物大多集中于小說前三分之二。魏蜀建國前后,曹操、劉備相繼崩殂,之前呂布等各路豪強盡皆出局,當年赤壁之戰時荊州和東吳人物多數已去;到諸葛亮獨撐大局之際,五虎大將只剩下年邁的趙子龍。三國后期故事雖然情節不算差,但人物實在不如前邊的有趣,就連諸葛亮也失去了當年“舌戰群儒”俎樽折沖的風邁。
其次,小說后邊這一截與讀者心理預期嚴重不符,諸葛亮“六出祁山”,姜維“九伐中原”,雖說打得司馬懿父子滿地找牙,到頭來卻是一部蜀漢消亡史。受眾喜歡嘲謔東吳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寧愿嘮叨“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劉備的江山——哭出來的”,卻不喜歡“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凄慘局面。不管怎么說,蜀漢之亡顯然不是受眾“喜聞樂見”的戲碼(在傳統戲曲中,三國后期劇目大概只是《失空斬》《鐵籠山》等寥寥幾出)。
跟史家和小說家的敘事不同,本文討論的三國詞語,原則上是受眾的二度創作,即便采自史著和小說原話,也是傳述者重新表達的歷史經驗,或是不同時代公眾經驗意向的疊加。這些作為俗語和成語被人們反復講誦的壓縮文本,在比附現實的同時,以“事后諸葛亮”式的判斷,顯示了某種所謂“理解的歷史性”。
老話說“看三國掉淚——替古人擔憂”,是指初涉文本的閱讀體驗,而世人嘴里傳述的語詞三國已是老道的經驗之談。嘲謔的語態中,未免帶有堪破世情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