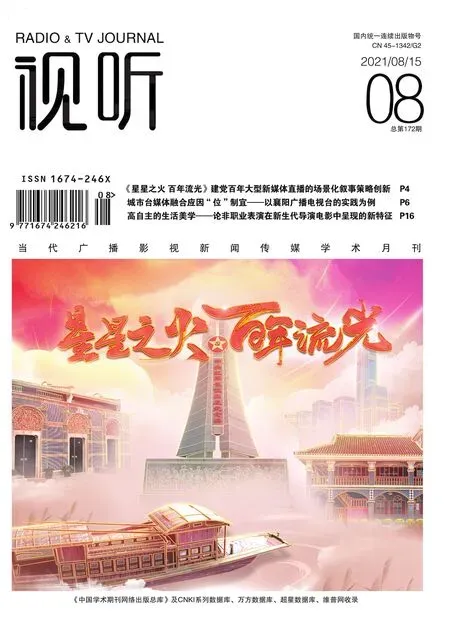榮光與缺失:試論戛納電影節的“無意識性別失衡”
許修純
作為電影交流與推廣、融資與發行的平臺,各大電影節在近百年電影發展史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優秀的中國電影人紛紛走上國際A類電影節的領獎臺,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上的聲譽與地位得以逐步提升,中國電影打開國際市場也成為可能。而在一眾國際A類電影節中,戛納電影節被公認為是目前世界上“學術性最強、權威性最高、規模最大的國際電影節”①,因此,入圍戛納電影節乃至獲獎,也是作為一個電影人的至高榮譽。
然而,2018年,在戛納電影節上,82位女性電影人走上紅毯集體抗議:自第一屆戛納電影節成立以來,作品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女性導演僅82名,而同期入圍的男性導演卻多達1688名②。作為最富盛名的電影展會之一,公平性是基礎,想必戛納組委會不會容忍刻意而為之的“性別偏見”。造成男女比例如此懸殊的主要原因,極有可能是評委們根據電影節的政治、商業、文化功能評定時導致的“無意識性別失衡”。本文通過分析戛納電影節自創立以來的運作背景及目的,結合近十年來以女性為主導的電影入圍主競賽單元的情況,分析女性導演較難入圍的原因,嘗試探究戛納電影節評委們甄選入圍影片的潛在規律。
一、繼往開來,十年一覽
追溯戛納電影節的起源,其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和當時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抗衡。20世紀30年代,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由法西斯主義控制,在希特勒的壓力下,陪審團甚至不能按照自身的自由意志決定獲獎者名單,使得這個世界上第一個電影節完全淪為納粹宣揚意識形態的工具。為了對抗法西斯的囂張氣焰,也為了給當時的電影藝術家們提供一個“避難所”,主張“藝術將不再受政治操縱”③的戛納電影節誕生了。這一歷史淵源為戛納電影節重視藝術性奠定了基礎。
就早期的戛納電影節而言,由于選址在氣候宜人、風光明媚,適合旅行度假的戛納小鎮,該電影節起初往往被視作“旅游節”。英國學者露西·馬茲登(Lucy Mazdon)曾對電影與旅游業之間的關系展開討論,并將“電影觀眾”描述為“正在體驗文化流通新動力的熱情的旅行者”④,意味著戛納電影節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和觀眾,并積極地為它的觀眾提供新穎的觀影體驗,不僅是地域上的,更是文化上的。
戛納電影節的另一個關鍵發展時期是在19世紀末期,隨著電視這一媒介形式逐漸發展和普及,電影節的影像得以在國際上廣泛傳播。如今,戛納電影節仍然在努力借助各種國際新興的媒介形式引起公眾的關注。例如通過每年標志性的“紅地毯臺階”儀式制造輿論并使之在各大互聯網社交平臺廣泛傳播,將戛納電影節打造成為傳播法國電影聲望的中心,同時又促進了各種形式的國際交流,呈現出當代電影和電影業的發展趨勢。
戛納電影節創立70多年來,已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盛會,設有多個類別、多重獎項。最引人矚目的類別當屬“主競賽單元”(長片),每年僅有約20部長片入圍這一競賽單元,競選戛納電影節最出名的獎項——金棕櫚獎。雖然戛納電影節享有很高的聲譽,但也受到不少批評,尤其是“少有女性主導的電影入圍主競賽單元”這一現象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過去十年中的統計數據表明,由女性導演創作的影片在主競賽單元中所占的比例一直相對較低。
2019年以前,每年以女性導演為主導的影片入圍的最多有4部(2011年和2019年),最少的時候沒有女性導演的作品入圍(2010年和2012年),2013年入圍的女性導演作品僅1部,2014-2016年每年各有2部,2017-2018年每年各有3部。在這些女性電影人中,河瀨直美(日本)、麥溫(法國)、愛麗絲·洛爾瓦徹(意大利)、琳恩·拉姆塞(英國,蘇格蘭)的作品多次入圍,已然是戛納的“老朋友”。到2020年,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選流程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整體入圍影片數量相比往年直接翻一倍,光是女性電影人參與創作,入圍的作品就達到了13部之多。這一數據的變化一方面預示著越來越多女性電影人投身到電影產業中,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這一年主競賽單元里新增的兩個板塊“New Comers”(首次入圍)和“First Features”(新長片電影),使這些還不夠有名氣的女性電影人有機會通過戛納這個平臺向全世界影迷展示自己的作品。
二、品質為王,多元發展
戛納電影節之所以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還有一個原因是“歷屆評委會的主席都由不同國家的文化名人輪流擔任”⑤,縱然每屆主席的審美意趣不盡相同,但是評委們對服務于該電影節的宗旨和履行其主要職責的使命在他們評選影片的決策過程中是統一的。通過以上對于戛納電影節歷史背景的分析,結合數據情況,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造成戛納評選流程中“無意識性別失衡”的主要因素。
(一)藝術追求與國際聲望
一覽近十年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的女性導演作品,不難發現熟悉的名字反復出現。即便是僅入圍一次的女性導演(除 2020 年“New Comers”“First Features”等新板塊外),她們以往的作品也曾在其他國際A類電影節被提名或者已獲不少獎項。法國是“作者電影”理論的故鄉,似乎戛納電影節的評委們本身也更青睞那些已經具備一定名氣和藝術風格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稱為“Auteur”的導演。這一規則在入圍的男性導演身上同樣適用。僅看2019年入圍的21部影片,除了由女性導演瑪緹·迪歐普執導的《大西洋》是首次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其他20位導演幾乎都是戛納電影節的“入圍常客”。或許是評委們出于對保持戛納電影節的聲望及對貫徹藝術性的追求的考量,在他們的潛意識里更傾向于選擇知名導演的優秀作品以保證入圍影片的質量。然而,這樣的選片模式勢必會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在全球電影行業中,知名男性導演的數量本身就多于女性導演。如果大量男性導演因其在各大電影節積累的名氣而使其作品更容易入選,主競賽單元將沒有足夠的空間接納由新興的女性導演主導的作品。
(二)附屬市場與多元文化
從電影節經濟作用的角度來看,入圍影片的名額分配也具有一定的規則。最初被認為是旅游勝地的戛納,在“國際電影論壇”身份的加持下,現如今已經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7000多名電影愛好者。世界各地的文化意識形態、先進的電影創作技巧在這里得以廣泛交流,藝術電影國際生產與發行的閉環也在這里形成。再次以2019年入圍的21部影片為例,我們可以明確觀察到評委們對于制片地區多樣性的追求:有6名導演來自于法國,4名導演來自于美國,其余入圍的導演分別來自于巴西、西班牙、韓國、意大利、巴勒斯坦、羅馬尼亞、比利時、奧地利、加拿大、中國和英國。縱觀近十年入圍的影片,制片地區的多樣性都得以保證。然而,這一規則對維持戛納電影節的性別平等卻不見得有利。據外媒報道,縱使近年來好萊塢女性導演的影響力得到顯著提升,在2020年好萊塢TOP 100高票房電影中,由女性執導的影片也僅僅是占到了16%⑥。像美國好萊塢這樣被認為在全球電影業中扮演領導角色的電影中心,女性導演的比例仍相對較低,在其他少數族裔國家里女性導演占比則更少。在保證其他少數族裔國家的影片入選時,女性導演的作品入圍可能性更小。
(三)招賢納士與“作者”養成
最后一個因素似乎是一把雙刃劍。從戛納電影節歷年來的評選結果可以推斷出:組委會一直致力于發現新的電影人才并希望將他們培養為“電影大師”,甚至會給這些導演的作品更多入圍的機會和關注度。尤其是日本女性導演河瀨直美,在2010年至2020年期間獲得了4次提名。河瀨直美具有與戛納電影節期望履行的職能與目的相符的雙重特質,一方面在于她的文化身份,在她的電影中,她可視化了她認為代表日本文化及其人民的元素;另一方面則在于她的女性身份,她呈現出了女性視角的審美感受。表面上看,這種規則是支持了女性導演,但實際上這又是一種隱形的限制,這與評委們的審美意趣有關。作為女性電影創作者,河瀨直美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數女性導演的創作風格:例如體裁方面,她的電影通常是講家人和身邊朋友的故事;主題方面傾向于制作愛情片和浪漫劇情電影。出于對入圍影片主題和題材多樣性的考量,當河瀨直美幸運地成為被選擇的那一個,絕大多數類似創作風格的女性導演的作品被主競賽單元排除在外。
三、結語
隨著2020年戛納電影節賽制的調整,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女性導演數量大幅提升,長期以來備受譴責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似乎終有改善的趨勢。當戛納電影節愿意給女性導演更多機會時,如何抓住機會是所有女性電影人需要思考的問題。戛納電影節歷年來入圍的女性導演人數較少的根本原因還是全球電影界女性導演影響力的缺乏,當戛納評委們考慮兼顧入圍影片藝術性與文化多元性時,女性導演的力量還不夠突出;再加上由大多數女性導演執導的電影難以突破既定的類型和主題,被匯聚在戛納電影節由男性為主導的各類電影大師的作品的光芒所掩蓋。中國電影人應更好地了解戛納電影節,創作出更多優秀的電影,并通過戛納電影節的平臺走向世界。
注釋:
①⑤賈磊磊.競技場·角斗場·名利場——戛納國際電影節縱覽Cannes[J].國際人才交流,1994(02):30-32.
②82位女電影人手挽手走戛納紅毯 抗議行業中性別不平等現象[EB/OL].搜狐網,2018-05-13.https://www.sohu.com/a/231430980_656058.
③戛納電影節歷史[EB/OL].戛納電影節官網.https://www.festival-cannes.com/zh/73-editions/history.
④Mazdon,L.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as transnational space[J].Post Script,2006,25(2),19-30.
⑥好萊塢女性導演影響力顯著提高,數量創紀錄,但占比仍未超20%[EB/OL].搜狐網,2021-01-03.https://www.sohu.com/a/442176145_223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