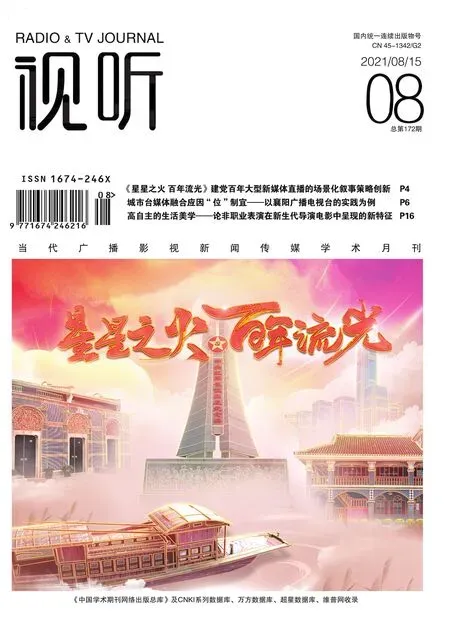全民笑聲的響起與消失
——國產情景喜劇興衰背后的文化傳播邏輯
薛瀟悅
從1993年英達執導的《我愛我家》問世至今,情景喜劇在中國已經走過了將近30年。在中國電視劇的發展史上,情景喜劇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類別。但與情景喜劇的發源地美國相比,中國情景喜劇的歷史較短暫,但其中不乏有很多內容豐富、形式大膽、思想深刻的作品贏得了廣大觀眾的認可,在一代人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最近幾年,情景喜劇的發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本文通過梳理情景喜劇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探討國產情景喜劇興起和衰落的原因。
一、國產情景喜劇的興衰歷程
(一)情景喜劇的引入與本土化
在中國,情景喜劇這種藝術形式屬于舶來品,其發源地在美國。進入中國之前,情景喜劇在美國已經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題材涉及非常廣泛。有戲仿20世紀60年代間諜文化的《精明神探》,也有政治諷刺劇《那才是我的布什》等,題材表現內容從種族歧視、兩性關系、勞資矛盾、死亡到科幻、警察與罪犯直至戰爭,幾乎無所不包。美國的情景喜劇經典作品《成長的煩惱》和《老友記》,對中國的《家有兒女》和《武林外傳》等產生了直接影響。國產情景喜劇首先得益于“現代室內劇”這一電視劇形式。1990年50集家庭倫理劇《渴望》播出,引發了廣泛關注,開創了現代室內劇的形式,同時把電視劇的關注焦點轉向非英雄化的平民形象。1991年趙寶剛執導的《編輯部的故事》問世,具備了情景喜劇的雛形。這部劇中講述的故事幾乎都取材于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熱點話題,比如當時的小保姆進城熱、詩歌黃金時代、瓊瑤劇、臺灣老兵返鄉省親、迪斯科等都在劇中得到了反映,通過編輯部里的6個人串聯起整個社會的眾生相,展現人間百態。但“情景喜劇”的概念重點在“情景”二字,要求場景相對固定且集中于室內,由于編輯部的故事有大量外景,所以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情景喜劇。
據“國產情景喜劇之父”英達自述,他在美國攻讀碩士期間參觀了美國情景喜劇《考斯比節目》的拍攝,很感興趣,把他們方方面面的工作過程都進行研究后,決心把這一劇種引入國內,回國后執導了中國首部真正意義上的情景喜劇——《我愛我家》。《我愛我家》誕生于1993年,由梁左、王朔擔任編劇,這是國產情景喜劇的開山之作。英達曾直言中國的情景喜劇是在模仿美國情景喜劇的道路上一步步走過來的:“現在我在國內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造,國內很多人認為英達是一個有很多創造能力的人,能夠發明出很多新的東西,腦子里有很多想法,其實我沒有。我的很多東西都是在把美國現成的成果轉化為中國的東西,只不過我轉化得相對巧妙一些。”英達在引入情景喜劇時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做了本土化的處理:這部劇從20世紀90年代的一個北京家庭切入,通過展現家庭成員、街坊鄰里、親朋好友的日常生活狀態,融入了世界杯、股票、卡拉OK等當時的諸多流行元素,以一個普通的市井家庭折射出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整個社會的眾生相。國產情景喜劇的大幕由此拉開。
《我愛我家》獲得成功后,國內陸續出現了多部情景喜劇:根植于北方文化的《候車大廳》《閑人馬大姐》《東北一家人》、反映上海風情的《老娘舅》、帶有明顯廣東地方特色的《外來媳婦本地郎》等,影響力雖然不及《我愛我家》,但整體上也獲得了觀眾的認可。
(二)新世紀國產情景喜劇的多元化
進入新世紀,國產情景喜劇在內容上不再局限于家庭生活和市井風情,形式上也更加大膽。尚敬執導的《炊事班的故事》《衛生隊的故事》等,首次把軍旅題材與情景喜劇的形式結合起來,塑造了與人們的傳統認知迥異的軍營生活。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軍隊里的生活是刻板嚴肅的,處處彰顯著保家衛國的豪情壯志。而尚敬導演的軍旅情景喜劇則把目光轉向軍人的日常生活,并融入幽默詼諧的元素,讓鐵骨錚錚的軍營里多了幾分溫情。
2005年林叢執導的《家有兒女》把家庭教育的問題引入了情景喜劇,母親劉梅的形象反映出中國絕大多數家長在子女的教育過程中存在的不當之處,同時設置了父親夏東海這一理想化的形象作為示范,講述道理的同時使問題在輕松的氛圍中得以解決,寓教于樂。在21世紀初期,傳統的控制式教育的方式仍然是家庭教育的主流,《家有兒女》所倡導的平等、尊重、開導、疏通的理念使人眼前一亮,引發了全民關于教育問題的新思考,被稱為中國版《成長的煩惱》。《家有兒女》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下,當時的中國家庭以獨生子女居多,《家有兒女》中三個孩子引發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是中國傳統家庭氛圍的回歸。劇中重組家庭的設定是中國社會進入新世紀以后離婚率普遍升高的產物,折射出了社會轉型期中國家庭形態的變化。
2006年尚敬執導的古裝情景喜劇《武林外傳》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武俠世界:名震江湖的盜圣其實是個膽小如鼠的跑堂,五岳盟主只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關中大俠也不過是老實迂腐的酸秀才,神秘的“江湖”其實就是人們身處其中的現代社會。每一集的結尾都會借劇中角色的臺詞陳述一個道理,傳遞一種正向的價值觀,這種寓教于樂的方式對當代人價值觀的構建有重要的啟迪。《武林外傳》帶有強烈的后現代主義特質:顛覆傳統、解構經典,讓每個小人物定義自己的“江湖”,沒有刀光劍影,沒有打打殺殺,只有與現代社會相似的日常生活場景;讓古代人物開口說出現代語言,這也是該劇的大量笑料所在,表現了消費時代的世態人心和種種弊端,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劇中各種方言的大量使用也拉近了觀眾和人物的心理距離,引發了當年的收視狂潮。
(三)巔峰過后:國產情景喜劇的困境
此后幾年情景喜劇的創作主要是此前作品的續集,如《家有兒女3》《家有兒女4》《炊事班的故事3》《馬大姐新傳》等。2009年的原創情景喜劇《愛情公寓》是互聯網時代下情景喜劇的一次新嘗試,不僅語言笑料大量運用當時流行的網絡段子,播出方式上也采用了電視播出和網絡點播結合的模式,吸引了不少年輕觀眾。2010年以后情景喜劇的創作陷入了低迷,除《愛情公寓》的續集外,網劇《屌絲男士》《極品女士》等原創作品雖然受到了一定關注,但劇作整體質量不高,只是單純搞笑逗樂而弱化了社會意義。
二、社會轉型期制造的群體笑聲
(一)社會轉型與價值觀的變化
國產情景喜劇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產物。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國民生活方式、心態和價值觀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國策,社會轉型的大幕悄然拉開。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狀態,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精神娛樂的需求隨之而來。加上改革開放后國外的文化元素涌入國內,沖擊著國人的價值觀,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曾經被主流文化提倡的思想理念。這樣的社會環境成了國產情景喜劇得以成長的土壤。
(二)罐裝笑聲與價值觀的解構
大多數情景喜劇都會在劇中設置虛擬的觀眾笑聲,這也是情景喜劇標志化的形式特征,意在引導屏幕前的觀眾發笑。這種群體性笑聲的出現與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人為設置的笑聲是當時文化引進的標志,這一時期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化背后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人們對舊的價值觀產生了懷疑,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形成,情景喜劇就充當了群體性社會規訓的角色,用人造笑聲提醒觀眾“這種行為是搞笑的”。
虛擬的情景笑聲也叫“罐裝笑聲”,即提前錄制好觀眾的笑聲,根據情節需要在適當的位置插入笑聲音軌。由于最初的情景喜劇是在舞臺上現場演出,觀眾可以在觀看時給出即時的反饋。電視出現以后,情景喜劇開始采用影棚錄制的方式,現場觀眾的笑聲就被人為設置的虛擬笑聲取代了。罐裝笑聲為電視屏幕前的觀眾營造了一種劇院的現場性,也在引導著家庭成員集體發笑。《我愛我家》就插入了觀眾的笑聲、拍攝花絮和觀眾在現場觀看演出的情景,起到了一種“仿劇場”的“間離效果”。“間離效果”在《武林外傳》中的處理則表現為導演、攝像機、手機等現代設備直接出現在劇中,其作用與罐裝笑聲類似,都對屏幕前的觀眾產生著示范作用,引導觀眾發出笑聲,間接參與意義生產過程。
除此之外,罐裝笑聲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意義。情景喜劇以調侃、戲謔的方式解構著主流價值觀,笑聲就是一種反抗性的力量。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寬松的政治環境改變了人們的心態,也改變了中國的文化格局。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將近30年的時間里,緊張的政治氣氛壓抑著人們的心理。改革開放后人們緊繃的神經得到了放松,希望以輕松的心態走向新生活。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越來越重視精神娛樂方面的需求,在官方意識形態主導的主流文化和知識分子主導的精英文化之外,出現了“大眾文化”這一根植于民間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沖擊著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重心。罐裝笑聲通過引導觀眾,反抗、消解著曾經廣受推崇的主流價值觀。
(三)社會思潮的變化在創作中的表現
政策上的寬松使文藝作品的創作也逐漸趨于多元化,創作相對自由。文藝不再作為政治的傳聲筒出現而具有了獨立的價值,其藝術性、娛樂性與政治性相脫離,表現內容也從以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轉變為世俗社會中的普通人。“中國電視劇的創作開始從中國社會的經濟巨變、普通百姓的現實境遇和民間文化的世俗精神出發,感受普通人的價值觀在大時代下合理性的自然演變。1990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長篇電視劇《渴望》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它引領了世俗生活的審美轉向。”《渴望》的出現為后續室內劇的創作打下了基礎。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國門大開,國外的社會思潮促使人們反思階級斗爭,反思曾經被奉為正統的主流價值觀,于是有了《編輯部的故事》中一系列反傳統的人物形象:余得利油嘴滑舌甚至帶有一些江湖習氣;劉書友膽小怕事,代表了傳統知識分子軟弱的一面;戈玲是一名心高氣傲的文藝女青年,被列為“不靠譜青年”;牛大姐三觀極正、滿口馬克思主義經典,卻因思想守舊而總受擠兌;李冬寶是雜志社里最有想法的人,卻也帶著些冷幽默的喜感……這些形象顛覆了過去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認知,主流價值觀里的褒揚、謳歌被當成了笑料,這種諷刺、戲謔的手法,對社會主流話語的嘲笑和解構,符合改革開放初期相對自由包容的社會環境下人們渴望放下包袱、掙脫束縛的心理狀態,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具備了情景喜劇的特征。
《我愛我家》中,有一個特別的人物形象也被顛覆:退休老局長傅明,總是習慣性地愛打官腔卻難有作為,和晚輩相比,他顯然是個落伍的人。這一形象的塑造與《編輯部的故事》中牛大姐的形象如出一轍,二者都迥異于傳統認知中的國家干部形象,消解著主導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鼓書藝人何平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賈志國都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但何平充滿了舊式藝人左右逢源的習氣,也常常鬧出不少笑話;賈志國也有普通市民那種斤斤計較的勁頭,代表了那個時代工薪階層的形象,他們的身上帶有明顯的社會轉型期的時代印記。
三、笑聲漸遠:國產情景喜劇的沒落
2009年《愛情公寓》播出,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但此后再沒有能引起反響的作品出現,國產情景喜劇走向衰落。這在文化產業高度發達的今天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思。
新的社會環境下,社會群體的多元化引起了價值觀的多元化,曾經被奉為正統的主流價值觀已經在笑聲中被解構,情景喜劇也就失去了其攻擊的目標,全民發笑的動機消失了。情景喜劇在中國的興起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轉型期,這一時期國民對傳統價值觀產生了懷疑,但新的價值觀尚未形成,情景喜劇的顛覆性、解構性恰好迎合了受眾的心理需求。在當時相對單純的社會結構下,人們的生活經歷、心理狀態大致相似,情景喜劇中人為設置的笑聲引導著人們群體笑聲的形成,這種笑聲本身就是一種反體制的力量。而近些年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引發了經濟、文化結構新的變化,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群體的多元化和價值觀的多元化,情景喜劇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后逐漸完成了解構主流價值觀的任務,在價值觀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下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近幾年沒有能引起全社會廣泛關注的情景喜劇出現,而針對小部分人群的特定類型的喜劇,如《鄉村愛情》等則填補了人們對喜劇的心理需求。
網絡和電影的興起分流了大量電視觀眾,電視媒體的全民宣泄功能、全民建構功能降低。網絡的飛速發展拓展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其娛樂需求可以隨時隨地通過網絡得到滿足,隨處可見的網絡段子也加大了原創情景喜劇的創作難度;加上新世紀后電影體制的產業化改革使得電影業逐漸興旺,一掃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低迷狀態,近幾年喜劇電影作為喜劇界的一支新生力量異軍突起,投資人從收益的角度考慮,也更傾向于大制作的電影產業,相比之下,小成本的情景喜劇就受到了市場的冷落。相當一部分觀眾從電視轉向網絡和電影,曾經的電視尤其是情景喜劇群體性社會規訓的功能就減弱了。
美國的情景喜劇題材廣泛,而中國的情景喜劇出于種種限制,題材選擇范圍相對狹窄,大多數局限于家庭、職場,給觀眾留下“換湯不換藥”的印象。《我愛我家》問世以后,絕大多數國產情景喜劇都難以跳出家庭的范圍,導致內容的同質化現象嚴重。近幾年依托網絡環境而生的《屌絲男士》《極品女士》等作品,創作者向市場經濟低頭妥協,一味追求點擊率和商業回報,迎合受眾的低級趣味,導致情景喜劇失去了應有的文化內涵,向膚淺、低俗的方向發展。此外,網絡情景喜劇受播放平臺的限制,不再是家庭成員集中觀看,也沒有群體性的受眾,全民發笑的“情景”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