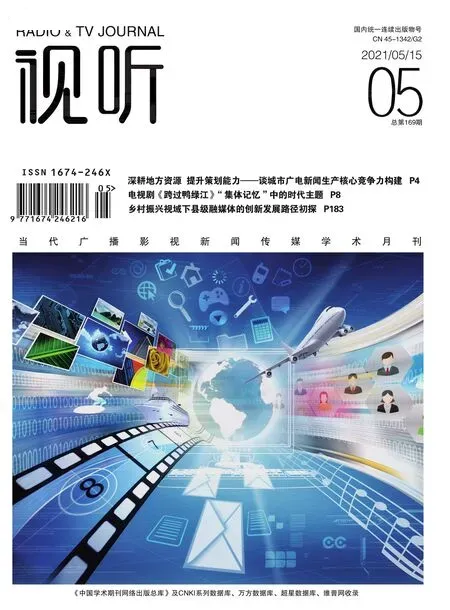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阿麗塔:戰斗天使》:空間區隔與冷戰顯影
□ 董星光
電影《阿麗塔:戰斗天使》是由科幻電影大師詹姆斯·卡梅隆編劇及監制,鬼才導演羅伯特·羅德里格茲執導的科幻動作視效巨制。《阿麗塔:戰斗天使》改編自日本動漫《銃夢》第一部中前兩本的內容,是一幅混雜了朋克、機械、星際、熱血等元素的格斗漫畫。漫畫中的加里作為一個全身機械的改造人在尋找記憶的過程中建立自我,經歷了襁褓、初戀、覺醒等人生過程,在自我建構過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進而探究著什么是本我的深層哲學命題。影片監制卡梅隆作為一位成功的電影藝術家,以敏感的政治嗅覺從諸多劇本中選擇日本動漫《銃夢》進行改編,其意識形態的指涉與美日的當下政治形勢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同構關系。
一、空間的對立
縱觀歷史,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會給全球穩定和地緣格局帶來影響。而大國間的爭霸與興衰更替,無不受地緣法則的支配。影片中,地緣政治理論得到了橫向的指涉,鋼鐵城與撒冷的二元關系體現了美日關系從依附到對立的微妙調整。木城雪戶的原作《銃夢》創作于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與整個日本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原作的整體基調十分陰郁,對于廢墟城與天空之城的對立,作者花大篇幅進行描寫,折射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尷尬處境,即“非正常國家”狀態。
改編后的影片中,鋼鐵城與撒冷城之間的二元對立實際上可以看作日本與美國的冷戰博弈前奏。正如影片中,天墜之戰后,只有撒冷城保存了下來,在戰爭中毫發無損。大戰后,緊密相連的兩座城也斷絕了全方位的聯系,而且致使鋼鐵城淪為大戰之后的難民集中營。鋼鐵城的每個人都成為撒冷城的奴隸,把努力工作的成果輸送給撒冷,換來的卻是廢棄的金屬垃圾。天墜之戰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格局的重塑,美國(撒冷)成為了最大受益國,而日本(鋼鐵城)因在二戰中失敗則受到諸多條約限制,雖有理想抱負,試圖完成獨立自主,躋身上流,但又面臨強制性規則所限的悲慘處境。美國曾經出于冷戰需要對身處亞洲的日本進行了扶持,同時利用美日聯合,牽制中國與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后半葉,伴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有擺脫美國控制的企圖。美國為了自身利益,對日本的態度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利用自己在世界上的主導權,對日本進行了打壓。在影片中,撒冷城被稱作是比魔法更厲害的工業科技,我們不難由此聯想到美國曾經通過科技贏得冷戰、獲得全球霸權的歷史,這種冷戰思維至今仍然得到延續,并施加到其他潛在的大國對立局勢之中。這樣一種地緣政治邏輯在影片中隱蔽地表達出來。
二、地緣政治與冷戰寓言
影片中的諸多邏輯隱喻了日本對于理想信念的自我懷疑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例如影片中人們對鋼鐵城本土的摒棄和對撒冷城域外的向往。從地理位置上來講,日本生存于一個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中蘇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左右夾縫中,同時受到了東西多重文化的雜糅影響。影片中鋼鐵城形形色色的人群,如農民、牧師、醫生、機械人等,實際上意味著日本多重文化的事實顯影。影片中的鋼鐵城處處籠罩在灰色的陰霾之中,畸變的人類肢體、冰冷的情感交流、膨脹的金錢欲望成為鋼鐵城真實的寫照。這種頹廢、破敗、滄桑感映射了日本二戰后荒誕的社會現實以及自身在世界范圍內的焦慮與自我懷疑。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不同國家的綜合國力差距加大。在冷戰中美國最大的威脅國蘇聯解體后,只剩美國一個超級大國。當美蘇冷戰結束,這時的美日關系轉型為影片中撒冷與鋼鐵城的二元關系。影片中,雨果提到,鋼鐵城不允許居民持槍,有槍是死罪,因為持槍會對撒冷城造成威脅;依德醫生提到,下面的人為撒冷工作。由此可見,雖然撒冷城與鋼鐵城分屬兩城,但是主導權掌握在科技更為進步、實力更為雄厚的撒冷城手中,鋼鐵城一直以來都受到撒冷的壓制,僅僅是撒冷城的附庸。同時,鋼鐵城諸多的規則都由撒冷城制定,甚至鋼鐵城的居民把去撒冷城視為自己的夢想及自我救贖的方式,例如影片中的雨果、依蓮等人。鋼鐵城諸多利益的紛爭都因為人類自我對于回撒冷城這一病態欲望的功利訴求。如果說鋼鐵城所代表的日本是一個被資本捆綁、人們喜歡弱肉強食的地域范圍,那么影片以一個全知的視角批判與揭露的恰恰是撒冷城相比于鋼鐵城更為殘酷與病態的社會事實。這實際上代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相對于日本,美國冷戰欲望的膨脹。
三、文本改編的兩難
日漫的文本經過好萊塢工業化的包裝,無疑把作品打造成一部美日“混血”意味的影片。但是在這樣一部作品的改編中,明顯地透露出美日兩國意識形態的沖突與文化抉擇的兩難。
首先,文本涉及到的所指關系體現著美日兩國意識形態的沖突與對立。因為當這部作品被改編為好萊塢電影時,這種劇作邏輯與空間架構的照搬與嵌套會顯得極為拘謹。因此,改編的難度在于美國恰恰是原作中所包含的焦慮、惶恐、危機與彷徨的現實之源。文本改編后的影片所折射的意識形態沖突并沒有很好地稀釋在大的人性之美中。影片在北美市場的失敗意味著這種改編并沒有規避好意識形態的沖突問題,制片方試圖在亞洲市場突圍,但最終也沒能挽救票房慘淡的遺憾。
其次,在改編時,處理文化通約性這一問題具有一定的難度。影片試圖遵循好萊塢工業化體制對文本的慣常處理策略,通過愛情、親情、友誼等全球所共通的話題來彌合本土與海外文本之間的文化沖突,但事實上,木城雪戶的原作《銃夢》所書寫的廢墟城的末日氛圍、女主人公的身份危機以及工業科技與人類情感的關系等諸多命題都是日本在自我歷史發展中面臨的原生問題,好萊塢執意拿來改編注定沒有日本那種生命經驗與文化體驗。影片雖然塑造的是后人類時代的商業圖景,但是對于人類欲望本能的關照都是當下話題。此外,導演試圖通過人類情感的注入平衡機械城的冰冷,增加一定的溫情。但是,日本作為大戰中創傷的親歷者,原作文本中潛在的那種不安、彷徨、無奈、感傷的情緒與日本長期以來形成的物哀美學傳統注定不會輕易地被些許罐裝的情感所稀釋。例如,影片中阿麗塔的男友死亡,人們在廢鐵城信仰喪失,最后也并沒有一個人找到理想的燈塔,仍然過著困頓、無望的生活。
總之,編劇對于兩個空間的書寫總體上都持有否定態度,鋼鐵城固然是文明崩塌、秩序待建的,而撒冷城也絕非一個人類前進理想的終點。影片地域區隔所體現的地緣政治以及當下緊張的美日關系所顯現的冷戰前奏,沖破了意識形態縫合體系所塵封的審美感性,為重新讀解美日關系呈現了藝術領域的自我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