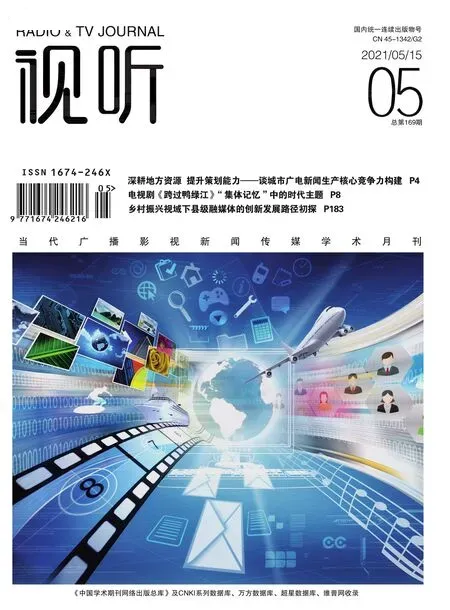淺析藝術作品的三層次——以電影《暖》為例
□ 孫雨菡
藝術作品作為藝術家經過自身審美創作過程創造出的成果,從藝術分析的角度可概括為外在形式與內在內容的相統一。從藝術作品的層次構成來看,可分為藝術語言、藝術形象、藝術意蘊三個層次。“關于這一點,我國魏晉時期的王弼在他的《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由此可知,王弼數百年前早已從文學作品中界定了言、象、意三層次的關系,三者間各有差別,但又相互影響。被稱為人類創造的“第七藝術”的電影更是秉承著藝術作品有機統一的整體性原則,由表及里地進行實踐性創作。霍建起導演的電影《暖》通過講述主人公暖、林井河以及啞巴三人各自跌宕起伏的生活經歷,表達了對命運無常的感嘆。《暖》是電影藝術的典型作品,本文從藝術語言、藝術形象、藝術意蘊三個方面對影片進行評析,有助于觀眾更好地了解藝術作品的內涵及價值。
一、多維度融合,豐富藝術語言
藝術語言作為藝術作品的物質化表現手段,是藝術成果的外部形式。電影語言具有豐富的藝術性,生動展現出了創作者的審美構思,具有明顯的個人美學特征。正是因為藝術語言兼具豐富性與差異性,所以電影可以帶給受眾不同的藝術感受。藝術語言在電影《暖》中可以視為最明顯的外在表現形式,導演主要通過鏡頭語言、色彩以及聲音等方式來表露。
(一)電影鏡頭語言的個性運用
1.長鏡頭突出紀實感受。長鏡頭的使用秉持了客觀記錄的特點,在時間不間斷的情況下表現現實生活的真實性。影片《暖》中,導演以林井河回鄉的長鏡頭開篇,在有限的畫面空間中巧妙展現了家鄉的風景全貌。在井河去暖家的路途中,導演用固定長鏡頭拍攝,井河由遠至近向鏡頭走來,展現出了內心的忐忑,觀眾也代入自身情感,對接下來劇情的發展充滿期待。結尾處運動長鏡頭跟隨井河游走在蘆葦中,長鏡頭跟隨步伐節奏,配合井河的獨白,將井河的內心情緒外化表現,讓觀眾更好地感受到人物情緒的變化起伏,同時點明了影片主題,得到了思想意義上的延伸。
2.空鏡頭呈現“留白”美。鏡頭語言作為影視作品的“自述”,恰當地使用空鏡頭能契合觀眾的期待視野。影片中的空鏡頭與中國繪畫中“留白”的作用不謀而合,除了展示環境、加強氛圍的作用外,開頭處的空鏡頭還發揮了場景轉換的作用,與聲音結合自然銜接了下一刻故事的發生,為后續井河與暖的重逢埋下伏筆。在影片中,導演更多地將空鏡頭作為回憶與現實兩個時空的過渡點,保障影片的節奏。影片中的空鏡頭對于景物的刻畫,展現出鄉村特有的恬靜,情與景相互交融,審美回味無窮。在影片后半段,導演選取長達20多秒的空鏡頭,用空蕩的秋千寓意暖命運的轉折。
(二)冷暖色調交替
色彩作為重要的電影修辭語言,不僅能營造電影意境,而且能體現出時代特色或心境變化。電影《暖》中,通過冷暖色調的強烈對比,凸顯人物角色,引起觀眾的注意,起到對故事的推動作用。冷暖色調正好對應回憶與現實雙時空,從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回憶中的場景大多是金色的陽光、豐收的麥田以及主人公臉上洋溢的溫暖青春的笑容。暖對未來的期望、井河對愛情的向往、啞巴對暖的默默保護,美好的溫情讓這份回憶愈加珍貴和溫暖。相反,導演用冷色調突顯了現實的沉重與傷感。淅淅瀝瀝的雨水、青灰的石板路,像是一幅水墨畫充斥著悲傷與孤單。現實中的冷色調也早已預示了井河的心境,導演沒有刻意營造煽情,而是通過兩種色調的對比把評判權留給觀眾,借助回憶與現實雙時空敘事的方式,將人物情感一點點地展現在觀眾面前,讓人們了解到井河和暖兩人心理狀態的變化,增強了情節的流動性,發揮了觀照現實、反思當下的作用。
(三)聲音元素的選擇性運用
獨白在《暖》中多次表現為井河對自己內心活動的第一視角的主觀陳述。開篇介紹自己的回鄉原因,引出往事回憶,觀眾感受到強烈的敘述感。而后在路上的獨白將井河對未知的緊張描述得真實直白,成功外化內心世界。后期井河在獨白中承認自己已經被現實環境改變,將暖的感情視為一份負擔,流露出自己真實的想法。隨著影片中獨白的引導,展現不同階段人物情感的轉折點,引發觀眾共鳴。此外,《暖》的音樂指導是著名作曲家三寶老師,他選取了極具特色的民族樂器蕭為影片增色。悠揚空靈的蕭聲與井河的獨白對應,讓情緒得以宣泄的同時又充斥著憂傷,奠定了影片感傷的基調,成為電影的魅力源泉。
二、象征意象,隱喻藝術形象
藝術形象作為藝術家通過藝術語言創作出來的成果,被稱為藝術作品的核心。在電影創作中藝術形象更多的是以綜合形象為代表,其中涵蓋了視覺形象、聽覺形象等。藝術形象的塑造成果是創作者個性化思考的結果,給受眾以審美體驗。影片《暖》中,導演對藝術形象的創新呈現可謂是影片的一大亮點,象征意象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完成隱喻的表達。
(一)暖——搖擺的秋千
影片中導演以過程化的手法展現了暖的女性形象,更直觀地對人物進行剖析。青春時期的暖是老家中的佼佼者,對愛情和未來充滿了向往和好奇,所以被小武生深深吸引,為愛苦等但以失敗告終。后來她和井河在秋千上看到了北京,那是她憧憬的地方,也再一次因為承諾開始了等待,但意外的降臨讓兩人漸行漸遠,最終暖嫁給了同村的啞巴。三段愛情經歷就像暖蕩起的秋千,秋千上的她給予自己短暫的飛翔,秋千一上一下對應了暖的人生,既有高處的風景讓她充滿期待,又有下落時的慣性注定要回到起點,似乎是無法脫離的命運安排。身為理想主義者的暖一直是等待者,把太多希望和未來寄托在別人身上,卻沒能明白秋千只有自己把握的時候才是最穩妥的。霍建起導演用秋千暗示了暖的命運變化,貫穿全片,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最終暖的醒悟也讓她收獲了平等的愛情和屬于自己的幸福。
(二)林井河——彌補的雨傘
十年未返鄉的林井河回到這里更多的是回憶與懺悔。十年前暖是他的夢想,因為暖的影響立志考上大學,完成了自己社會階層的改變,但也被現實改變。失信的承諾讓他備受折磨,導演將塑造林井河這個人物的重點放在了對他內心矛盾沖突的刻畫上。導演安排了送雨傘的情節,通過道具表現出井河內心渴望進行補償。傘下遲來的道歉更像是井河對自己長達十年的心事尋找一份答案,而暖拒收雨傘更像是對往事的告別,現在的她真正明白好與適合之間的取舍。影片結尾,旋轉的雨傘代表了家鄉外面精彩的世界,井河將傘送給了暖的孩子,他明白女兒是暖新生活的象征,傘的贈送在這里更像是一份傳遞的承諾。這不僅僅是井河對自己過去錯誤行為的彌補,更是女兒所代表的新生活的開始,依舊對未來充滿憧憬與希望。
(三)啞巴——“沉默”的鴨子
影片中,啞巴雖是配角但導演對于該角色的設置讓觀眾耳目一新。啞巴喜歡暖的方式是通過欺負來引起她的注意,在沒人時去搖晃秋千釋放自己的情感。送鴨蛋、背山路,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守護著暖。撕信可以解讀為他對井河行為的憤怒以及對暖的心疼。沉默的啞巴在片中經常獨自趕著一群鴨子,導演用鴨子的意象讓藝術形象得到充分表達,啞巴對暖的愛像影片中鴨子的叫聲簡單卻真實。盡管啞巴現實中無法對暖做出任何承諾,但是相比小武生和井河,他卻是那個真正用行動履行承諾的男人,這樣的設置具有諷刺意味。影片結尾,他將暖和女兒交給井河,示意讓其帶走,樸實直接的想法更是詮釋了他的善良。
三、人文關懷,彰顯藝術意蘊
藝術意蘊是藝術作品中存在的深層次的精神內涵,是隱蔽在藝術生命體內的靈魂。成功的藝術作品應該包含哲理、精神思想的傳達,需要欣賞者們去理解和探索。《暖》的導演霍建起兼具第五代和第六代導演的創作風格,對傳統有著深刻的體會,同時又將目光投入到小人物的表現上,這正是其形成獨特的藝術意蘊的主要原因。
(一)追憶青春情感意向
霍建起導演在電影創作中關注的是身邊普通人的不平凡的存在,他尊重每一個角色,平等的角度讓觀眾被影片中真摯的情感所感動。《暖》中人物命運走向的設置耐人尋味,含蓄而又委婉的敘事魅力滲透出濃郁的傷感情懷。導演將故事安排到鄉村,遠離城市的喧囂,構建精神家園,讓觀眾隨影片的進展回望過去無憂的日子,重拾美好情感。《暖》中樂觀的生活態度展現了影片主題,與導演追求的美學風格相吻合。
(二)儒家思想哲理表達
霍建起導演的作品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林井河沒有忘卻初心,重返家鄉幫助老師處理麻煩,與暖相遇時沒有選擇視而不見,而是去家中看望,盡其所能彌補過錯。儒家思想中的“仁義”在井河身上顯現,塑造了內心矛盾、形象立體的人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之一,影片中面對井河的道歉,暖說:“你越不回來就越忘不了。”這時的暖早已不再活在幻想之中,而是學會了與現實握手言和,腳踏實地地珍惜現在的生活,將過去作為美好的回憶放在心底。暖身上表現出儒家文化中的“信、忠、孝、悌”的女性美德。從作品中不難看出,導演受儒家思想影響,將觀眾對真善美的渴望變成現實中美好的愿望,喚起人們的向往,是對儒家優良傳統道德的一種贊揚。
(三)人文關懷精神傳遞
想要打造一部好的藝術作品,需要從自己的文化出發。藝術作品中蘊藏的文化涵義和人文精神能夠展現出較高的文化品格和藝術魅力。霍建起導演的作品充滿深刻的人文關懷,盡管暖悲慘的遭遇改變了她的命運,但影片的最后她也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幸福,感悟到生活的真諦,實現心靈上的解放。粗魯的啞巴在影片最后得到升華,讓觀眾看到了他內心的美好,使影片主題的表達更加強烈。當女兒說“爸說讓叔帶我和我媽走”的時候,真善美的人性之光閃耀。觀眾從中看到了生命本質的美好和淳樸,井河最后獨白的自我反思傳達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殘酷的故事內核被導演巧妙地化解成對于青春的追憶。從《白狗秋千架》到電影《暖》的改編,導演摒棄了部分內容,改造了結局,以情感人,營造希望,讓觀眾的情緒得以安放,也可看作是導演對觀眾的一份美好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