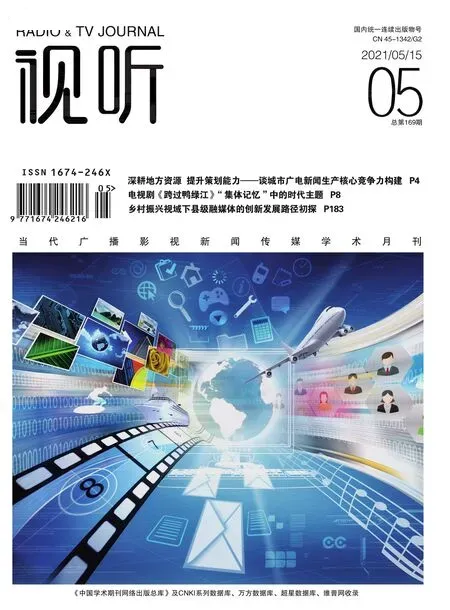方言對城市影像的想象表達與文化再現——以武漢方言電影為例
□ 魏媛媛
方言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與城市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土地孕育了方言,方言的使用與表達代表著地域文化。武漢地處中部,城鄉氣質濃厚,關于武漢的城市影像多是游離在大都市繁華之外的,以一種簡樸、繁亂的氣息呈現在觀眾眼前。武漢話往往會給人一種潑辣爽快、雷厲風行的感覺,使得以武漢為背景的城市電影能呈現出強烈的真實感和濃郁的江湖氣息。武漢方言電影幾近真實地展現了在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下城市底層人物的歷史陣痛,從小人物的視角折射出社會傳統迷失、人性善變、物欲橫流的市井生活。
一、地域文化的再現與真實感的營造
方言是影片在地性的表現形式之一,極其逼真地呈現了那些散發著泥土氣息的地域質感,彌補了電影畫面中無法企及的城市景觀和生活文化,增強了城市影像的真實空間塑造能力。武漢方言電影能讓觀眾感受到武漢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的城鄉變化和經濟高速發展下形成的浮躁的社會環境。
武漢方言電影集中展現了城市的市井文化和時代變遷下小人物的命運。方言是一個城市市民的縮影與寫照,是一個時代最真實的體現。王超的《江城夏日》選用武漢籍演員田原扮演主角李艷紅。李艷紅的爸爸李啟明曾是一個城市文化人,卻被下放農村,當他重返武漢時看到的是一個陌生的地方。物欲橫流的現代都市、五光十色的夜總會、魚龍混雜的筒子樓,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增加了城市的高度和物質的縱橫,但也讓女兒成為陪酒女,兒子因偷盜而喪命。在方言電影中,武漢話成為一種標簽,代表了底層人們的草根文化,是一種現實狀態提煉出來的在地化表達。《萬箭穿心》里李寶莉與閨蜜聊天時形容李寶莉的新家在風水上是萬箭穿心,李寶莉立刻反駁道:“么叫萬箭穿心,我就不信這個邪,奶奶小寶都得我罩著,我越是要說這是萬丈光芒!”《萬箭穿心》電影的英文譯名就是“Feng Shui”,風水文化在思想還沒完全開放的城市里仍保留著一席位置,在武漢影響頗深,這是傳統文化留下的時代印記。《萬箭穿心》真實地還原了當年漢正街商品市場的人來人往、車水馬龍,是武漢城市嬗變過程中所裹挾著的市井文化生活的展現。
而刁亦男的《南方車站的聚會》則試圖以一種寫實的手法表現現實和夢之間的美學影像。雖然刁亦男延續了《白日焰火》中抹去現實城市景觀特征的表現手法,但是導演將拍攝地設置在武漢,選用非武漢籍演員要求他們學習武漢話,并大量采用武漢本地的群演,讓觀眾認為這個南方車站就在武漢。主角劉愛愛與周澤農在輕軌下初次見面時,劉愛愛的一聲“拐子”就把故事帶入了武漢的下雨天中。周澤農所屬的團伙在內部相互爭奪地盤時談到的興業街、解放路、宏基路和勝利街都是武漢真實存在的道路,影片在看似高度真實的圖景中又超越了現有真實的城市環境。在演員的對話中仍然能聽到武漢特有的俚語,例如“不服周”“你盒我”“差火”等,能讓觀眾感受到城市特有的煙火氣息。那些嘈雜的集市、垃圾成堆的筒子樓以及市民跳舞的廣場都是武漢城中村景觀的真實再現。這些視聽語言是在還原導演刁亦男的社會洞察,而那些指向被時間遺忘的社會空間則使影片更富有社會性。
與普通話相比,方言更具有本土特色,能夠作為觀眾辨別地域文化的聲音符號,構成地域文化的一種標準樣式。方言影片不僅僅把目光鎖定在燈紅酒綠的摩登都市,更是聚焦了中國在高速發展進程中凸顯出來的社會現實問題,反映了當下劇烈變革中的城市面貌與人的狀態,展現了中國地域的多元文化。
二、底層邊緣人物敘事與女性形象塑造
方言電影能夠充分地展現邊緣化群體的底層生活,審視飛速發展中的社會問題,力圖讓觀眾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底層民眾的無盡苦難。武漢方言電影中的女性形象仿佛天生就帶著武漢人俠肝義膽、粗糙火爆的性格特點,她們或與外部世界的傳統觀念抗爭,或與自身人性的枷鎖反抗。影片中的武漢女性雖有著悲劇性的命運,但從不妥協,可歌可敬。
《萬箭穿心》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武漢。李寶莉老公馬學武因升職而分到了新房,但這新居卻沒有給李寶莉帶來幸福,反而導致了她未來幾十年的悲劇人生。馬學武向李寶莉提出離婚,李寶莉忍痛舉報老公嫖娼,導致馬學武跳江自殺。李寶莉不得不做一名“扁擔”掙錢養家,然而她的辛勞卻沒有換來兒子小寶的理解。雖然李寶莉是城里人,但文化水平不高,一輩子都在漢正街做工,所以她嘴邊總掛著“狗日的”“婊子養的”“老子”等臟話。方言中的粗話和臟話有著普通話不可比擬的地道和丑陋,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最真實的體現。武漢戶口的李寶莉下嫁給了農村人馬學武,在這段婚姻中男性弱勢、女性強勢構成了兩性關系的不平衡狀態。《萬箭穿心》中的李寶莉是武漢女性的真實再現,不僅在于她說話時的語音語調,更在于她用武漢話表達情緒時顯露出來的堅韌勇敢、不愿服輸的生活態度。影片對女性的弱者形象進行了一次有力的顛覆,真實立體地表現了生存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鮮活人物。
《南方車站的聚會》作為暴力美學的作品,無疑是男性視角的敘事模式,片中的男性把力量和欲望進行階級和利益的劃分。但當劉愛愛出現后,影片塑造的江湖氣息就逐漸消失,開始慢慢走進被掩蓋的真相之中。劉愛愛陪泳的這份工作是她迫于生存的無奈選擇,她擔任了楊淑俊舉報周澤農行蹤以獲取30萬獎金的中介人身份。大部分的時間劉愛愛聽從周澤農和華華的吩咐安排,在幾方勢力的斗爭下她不得已出賣了周澤農,但最后劉愛愛決定拋棄利益,完成了心靈上的自我救贖。她的思維轉變使得她從忍辱負重的被動轉化為大義凜然的主動行為,始終保持著自身人性的善良。
有抵抗、掙扎的女性必然就會有妥協者。《江城夏日》的李艷紅為了尋找哥哥,重新回到父親的故鄉武漢,卻被物欲橫流的都市所籠罩,成為一名夜總會的小姐并且懷上了老板的兒子。當從父親嘴里聽到哥哥去了深圳,李艷紅說:“聽說深圳離香港比較近……”在她的眼里城市永遠都是一個美好的夢,不論她現在從事什么樣的工作、擁有什么樣的生活,李艷紅仍向往幸福的生活。李艷紅力圖擺脫命運的桎梏,所以她選擇回到武漢,卻又向新的生活狀態妥協,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以獲得周邊人的接納和認可。
武漢曾被稱作中國最大的城中村,城鎮發展規劃結構性失調。當城市文化建設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時,這些底層女性會成為被邊緣化的群體,在社會中舉步維艱,但她們卻活得認真、勇敢又火辣。演員運用方言表演真實地展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期鮮活、獨立、立體的女性形象,并從女性視角去尋求其生存困境的緣由,挖掘她們身上的閃光點,探索女性的生命意義。
三、“陌生化效果”與異鄉人的身份認同
“陌生化”這一基本理論是俄國形式主義典型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表達藝術的技巧在于讓人們熟知的對象帶給觀眾不一樣的感受,而這種不一樣的感受則需借助語言這一文化加以修飾,通過語言的變形與表達,使枯燥的文字變得富有美感、耐人尋味。方言在語音語調以及詞匯用法上都與普通話有所區別,讓觀眾感到新奇并自動融入劇情之中。
《失孤》的開頭部分聚焦在武漢的輪渡上。雷澤寬趴在摩托車上睡覺,有武漢市民看到了他車身上的尋人啟事,兩人非常熱心地為雷澤寬提供建議,在此過程中兩人卻爭吵起來,隨后發生了打架事件。這場戲里,雷澤寬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從武漢人的對話中展現了武漢人的熱情與火爆的性格。雷澤寬從安徽出發,途經湖北,前往福建,他只是一個過客。方言的出現造成了異鄉人與本地人鮮明的身份差異與行為隔閡,這種隔閡來自于雷澤寬在尋子旅途上與不同人物進行溝通而產生的異同,從而造成了疏離感。不同方言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地域文化之間的沖突,而這種語言矛盾造成了人物之間的身份間離。在多種語言、文化共生的人文環境中,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是難以避免的,矛盾和沖突也會時常發生。在電影《人在囧途》中,這種沖突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王寶強扮演的牛耿是河北農民工,而徐崢扮演的李成功則是說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的商業精英,兩人以語言為基礎構成了身份對立。另一方面,兩人在去往長沙的旅途中途經武漢農村,村民對兩人乘坐的大巴車群起而攻之,幸虧牛耿化解危機并得到了意外幫助。影片在這一部分采用了講方言的演員,既能表現武漢農民的火爆性格與外地人初次進入該地的戲劇沖突,又能體現在事件處理后武漢農民的熱情好客,這正是異鄉人帶來的不同文化在碰撞交流后產生的戲劇沖突與效果。
短暫的停留使人物感受的身份認同問題是稍縱即逝的,而當異鄉人長期居住在武漢這個漂泊的城市則會更加迷失自我。《頤和園》中,余虹孤身一人來到武漢,她游蕩在舞廳、咖啡館,尋找到了與她相似的唐老師,然而余虹和唐老師只有肉體上的碰觸,卻沒能彼此相愛。余虹在武漢生活的這些日子里,總能聽到辦公室里同事用武漢話議論她的孕吐,出車禍后醫生護士們也用方言問她的家人朋友在何處。武漢的人事物都在告訴余虹她不屬于這個城市,她始終是這個城市的過客,單純的小吳、已婚的唐老師都無法填補她對愛情的渴望。武漢在《頤和園》中占據著重要的篇幅,影片將余虹兩段愛情故事同時安排在了武漢。城市的復雜性正如影片中呈現的那樣,不缺乏文化,但也有平庸世俗的一面,如余虹一樣的異鄉人是無法融入武漢的,他們生活在一種繁榮燦爛的表象之中,而真實的內心卻在漂泊中迷失。
方言帶來的地域文化是陌生化的效果展現,可以展示武漢的文化特點和人民的性格特征。武漢方言電影中的身份認同,還與影片中所表達的人物生存狀態息息相關,是他們內心世界最真實的告白。
四、結語
武漢方言電影有著較為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影片中的人物既保留了對城鎮生活的眷戀,又感受著現代化都市迎面而來的沖擊,在這樣一個充滿矛盾與沖突的空間里,有太多可以被發掘的人事物。在這些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敢愛敢恨、敢爭敢退的李寶莉,忍辱負重、自我救贖的劉愛愛,空虛敏感、不甘平庸的李艷紅,還有迷茫在路上的李成功、牛耿、雷澤寬和余虹。方言是他們不變的腔調與符號,武漢是他們流浪的驛站與見證者,每個平凡個體的掙扎與苦楚、辛酸與溫暖,都被展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