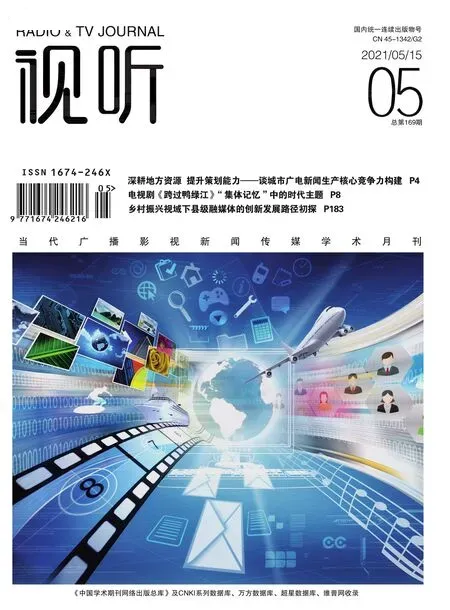淺析新世紀國產戰爭題材影片中的女性形象
□ 卜健洲
據不完全統計,新世紀國產戰爭片近七百部,其中大部分影片都有著女性角色的身影。國產戰爭片中的女性形象不斷豐富,逐漸脫離男權主導下的棄婦、怨婦的單一塑造,她們成為具有勇氣智慧,努力實現個人價值、社會價值的獨立個體,進一步完成了女性的自我陳述。
一、女性形象分析
(一)平民形象
上世紀的戰爭片往往把平民女性塑成堅守傳統美德的家庭女性,富有理想主義色彩。她們辛勤勞作、教育兒女、贍養老人,默默等待出征的丈夫,處于正面戰爭的語境之外。如《高山下的花環》(1985)中,梁三喜的妻子韓玉秀通情達理、任勞任怨,成為影片中隱忍的代名詞。只有在夜深人靜,偷偷到丈夫的墳前時,她所克制的悲傷才能得以宣泄。
進入新世紀,國產戰爭電影對平民女性形象進行了更多客觀深入的塑造,使女性平民角色更富有現實性,增強了平民女性自我陳述的能力,展現出更多的敘事表意可能性。《南京!南京!》(2009)中,在日軍侵略南京的初期,唐太太沉迷于娛樂消遣,完全不顧戰火紛飛的環境與丈夫的警示,體現了愚昧的“小民意識”。而隨著戰火的蔓延,她的生活也被戰爭完全破壞,面對著親人的不斷犧牲,嬌弱的她只能默默流淚承受一切,無力反抗。影片通過展現這一普通女性生活脫軌的過程,表現了戰爭的殘酷無情以及對“小民意識”的批判。影片《明月幾時有》(2017)通過“表姐”婚禮這一場景,對戰爭背景下的平民女性形象進行了多元的探討。“表姐”一家家境相對殷實,但是即便如此,“表姨”也著急將“表姐”嫁出去,這是源自于女性之社會屬性的匱乏,而戰爭下社會失序的狀態又放大了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安全感。此外,許鞍華導演也突出了“表姨”這一人物對傳統習俗的重視、對家族親人的耐心。不過,這些習俗其實是在父權控制之下整個文化系統對女性的禁錮與約束。導演透過這一角度突出了女性之間的生命情感交錯,表達了對女性的憐惜,也用冷靜的態度表達了對父權社會的質疑。
(二)軍人形象
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國產戰爭片中,女性軍人形象的女性特質往往處于失語的狀態,成為部隊之中的當代“花木蘭”。在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1961)中,女主角吳瓊花的女性意識被自然消解,她成為戴著男性面具的“鋼鐵女戰士”。導演主動淡化了片中人物性別的二元對立,取而代之的是對政治、階級立場差異的突出強化。但女性在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的同時,也喪失了自我的性別特質。女性不得不隱藏自己的生理屬性和個性觀念,唯有如此才能融入到男性氣質占絕對優勢的軍人群體中。這是在父權社會的壓迫下女性意識的特殊形態。
步入21世紀,許多電影都力圖讓女性軍人角色表現更為豐富的性別特質。例如在《紅海行動》(2018)中,佟莉是蛟龍戰隊中唯一的女性,影片不僅展現了其作為機槍手英勇的作戰表現,還通過其與隊友石頭的動人情愫表現了佟莉作為女戰士的另一側面。在《戰狼》(2015)中,龍小云作為全片唯一的女性形象,不再處于完全附屬的失語狀態,也并非被表現為必須隱去原有性征的“花木蘭”式的女性形象,而是被塑造成了男主人公“冷鋒”的良師,她對冷鋒的肯定使得后者有機會進入戰狼中隊而非被軍隊開除,成為電影敘事中關鍵的一環,這是影片對女性塑造的積極之處。不過,《戰狼》實際上更多突出了龍小云作為“女性”的這一性別特質,并非她作為軍人的這一職業屬性、社會屬性。龍小云對于影片敘事的推動、對冷鋒這一人物的幫助,也是建立在冷鋒對她的原始征服沖動之上的。故此,性感威嚴、機智聰敏很大程度上成為浮在龍小云身上的標簽,使影片對于龍小云這一人物的建構帶有扁平色彩。
(三)臥底形象
在上世紀的革命經典影片中,敵方臥底形象往往被限定為女性,她們具有冷艷外表、蛇蝎心腸,利用放蕩野性的女色來勾引我方的男性戰士,成為父權社會下一種被妖魔化的欲望載體。而我方的臥底則以男性偵察員為主,他們歷經種種考驗,最終成長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例如在《冰山上的來客》(1961)中,巴里古兒兼具美貌和智慧,她是敵方安排進我方組織內部的間諜。影片對巴里古兒的塑造過于程式化、臉譜化,她成為一個淺顯直白的“壞人”,并悄無聲息地被其所忠于的政治陣營殺害。可以說,在電影內外,巴里古兒都是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她始終漂浮在劇情之外,成為可以被隨意抹去的臉譜化人物。
新世紀以來,對上世紀的“反特片”進行了一系列創新,一定程度上剔除了政治語境下性別臉譜化的濾鏡,開始嘗試意識形態的軟性表達,對以往分明的二元對立進行了部分隱性處理。在《風聲》(2009)中,李寧玉雖身為汪偽政府情報科高級科長,但卻具有善良單純的品質,對愛情有著敏感的執念。影片有意識地淡化了李寧玉與我方地下工作者顧曉夢的政治營壘對立,并且渲染了二人的姐妹之情。而當顧曉夢向李寧玉坦白并要求揭發自己的時候,李寧玉的那句“別人怎么樣我不管,我要你活著”也讓二人的政治立場在這一段落中完全消隱,淡化了意識形態敘事色彩,貼近了觀眾的生活,隱性表達了當代主旋律精神。
二、塑造手法的創新表現
(一)多重身份的交錯:多元背景下對人性的挖掘
在新世紀的戰爭片中,影片賦予了人物多重的身份,探討人性在復雜境況中的變化。在電影《紫日》(2001)中,影片細致地展現了秋葉子作為“學生”“少女”“軍國主義軍人”的不同側面。秋葉子是一名在日軍投降前夕應“一億玉碎計劃”進入部隊的女學生,她和數萬同齡學生共同接受“軍事訓練”,而訓練的本質是給學生們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在蘇聯紅軍的突擊中,秋葉子與日軍大隊伍失散,在林區中與中國農民楊玉福和蘇聯女軍醫娜佳相遇并發生了一段動人的故事。
影片極富層次地展現了秋葉子的思想蛻變與掙扎。秋葉子從最初對軍國主義的堅持,逐漸轉變為對國家意志的反思,這一轉變不僅僅是由于被楊玉福救下而產生的感激之情,還是因為處在大興安嶺如此近似于烏托邦的環境下,三人的政治立場、國籍歸屬都被自然消解了。而當三人走出復雜的林區再次回到日軍的扎營地,則意味著烏托邦的逝去,他們又重新回到了戰爭的語境之下。于是,當秋葉子聽到了日軍投降的廣播時,她又將槍對準了楊、娜二人。透過秋葉子這一形象,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軍國主義思想的破碎崩塌,也是個體心中對自我情感價值的追尋。
(二)樸素情感的回歸:個體價值對傳統的解構
新世紀以來的國產戰爭影片相比于革命經典影片,在人物塑造層面更多地強調個人情感的表達,同時也有著對傳統的解構。影片《明月幾時有》中的方母一角具有濃重的市井氣息也有著閃光點。一方面,方母為人市儈利己,面對落難的沈氏夫妻,不顧茅盾在中國抗戰文學領域的重要地位,對其一家錙銖必較,眼看留租無望,還將用來討好沈氏的糕點找借口端走。但是另一方面,方母也有著最為樸素的個人情感:面對日軍在夜晚對平民百姓的侵略、對女性的蹂躪,她憤怒地表達厭惡之情;當女兒方蘭加入抗日隊伍進行地下宣傳工作,她反對的原因之一是認為女兒太過柔弱,自己死不重要,一定不要連累革命的隊友。就是這樣一個生活極其精明甚至吝嗇、沒有宏大家國抱負的方母,在面臨生命威脅之時,抱著對女性的憐憫、與革命志士的共情,堅持守住了秘密,保住了阿四的生命。
許鞍華對“女性英雄”的塑造,并非強行將民族大義、家國興亡安置在女性身上,也不是將強壯、硬朗這些男性特質標簽直接貼在女性角色身上,而是將樸素的個人情感作為角色的行為動機,對“英雄豪杰”這一形象進行大膽解構:“英雄豪杰”并非代表著身體的絕對強壯、精神的絕對純潔高尚。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不僅是在性別語境下保留了女性陳述,也是對傳統的主旋律電影敘事表達進行的創新。
(三)敘述視角的轉變:消費熱潮中男性凝視的“復辟”
在十七年經典電影中,由于意識形態的影響,導演往往刻意淡化由男性欲望視角出發的女性呈現方式,逐漸抹去女性被男性注視的欲望目光與鏡頭表達,并且將相同的革命信仰當作二人的連接要素,將兩性間的情愫隱性化,即以“革命戰友情誼”代替“兩性個體愛情”。而在七十年代后,由于受西方經典電影敘事機制的影響,女性被男性注視的欲望視角再次復辟。進入新世紀,一方面隨著消費主義的盛行、市場經濟的發展,“娛樂至死”的理念在觀眾中廣泛傳播,因此催生出了《舉起手來》(2003)等一系列以極強娛樂性取代戰爭殘酷色彩的影片。另一方面,社會的男性霸權地位也在進一步加強,女性成為被男性凝視的欲望對象,女性的身體也在銀幕中成為被消費的欲望符號。
以女性戰士遭受刑罰的段落為例,不同時期的影像表達具有鮮明的傾向差異。在《永不消逝的電波》(1958)中,李俠與何蘭芳被日軍逮捕后,作為女性的何蘭芳是刑罰旁觀者,她被迫來觀看李俠遭受敵人的非人折磨,她處在刑罰的直接語境之外。在《烈火中永生》(1965)中,江姐的身體雖然直接遭受了敵人的虐待,但是影片有意識地隱去了江姐受刑的具體畫面,暗示著種種酷刑是共產主義者的煉金石,影片所要強調的是對共產主義戰士的贊美與歌頌。而在影片《風聲》中,當地下抗日成員顧曉夢決定犧牲自我后,被迫騎到一根帶刺的麻繩上被男性士兵來回拖拽,鏡頭突出表現了滿是鮮血的麻繩以及無比痛苦的顧曉夢。這一幕充斥著赤裸裸的性別暴力,也是一處以女性受辱而滿足男性欲望的銀幕奇觀。
當下,中國社會對男女權利關系的關注度日益高漲。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媒介,國產電影對于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尤其在當下男性話語仍占主導的戰爭片領域,國產戰爭電影要怎樣建構性別權利的圖景,如何均衡觀賞性、藝術性以及思想性之間的交互關系,是需要電影人繼續探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