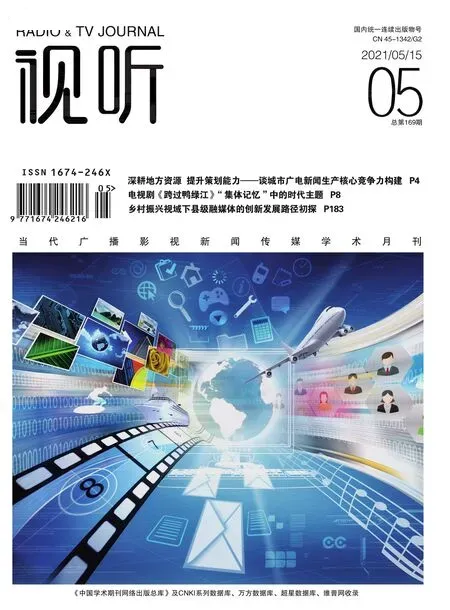女性價值悖論:新媒體傳播中的“她”
□ 李淳永
性別主流化不斷推進、傳播技術飛速發展使得性別傳播上升為社會關注的重點議題。女性群體成為傳播格局的新主體,通過媒體平臺構建著全新的性別傳播話語體系,親身打造并詮釋了“她”文化與“她”價值。“她”,雖然引起了更多的媒體關注,但也在符號化與符號解讀過程中被有意無意地誤讀,從而產生有關女性價值的悖論。
一、價值悖論的媒介體現
(一)商業廣告對女性的物化
2020年1月初,全棉時代發布了一則反轉廣告:一年輕女子在深夜獨自步行回家,遭遇黑衣男子的尾隨。女子為擺脫跟蹤,急中生智拿出全棉時代濕巾卸妝,最后還原成一副男性面孔嚇跑尾隨者。廣告一經發布便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波。雖然廣告方在致歉聲明中宣稱視頻的出發點是追求創意效果,突出強調產品的清潔功能,絕無對女性的冒犯之意,但此般避重就輕的說辭不能為公眾所接受。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曾指出,“女人只是被改頭換面、轉移再販賣的眾多商品中的一個品種”,她認為在社會中確有物化女性的風險。全棉時代的這則“創意”反轉廣告無疑擊中了女性群體的痛點。一方面是生理弱勢不敵潛在犯罪危險。該廣告反以戲謔滑稽先行,讓廣告的盈利目標走在道德、法律和生命安全之前。女性群體遭遇的不幸境況被商家消費,淪為泛盈利化生產線里被標價的消費品。另一方面,該廣告傳達了一種更為扭曲的、遍在的價值觀:對女性的人身侵犯取決于女性的樣貌,樣貌出眾的女性更容易被尾隨。而一旦女性卸妝成素顏的模樣,就沒有了剩余的價值。將美貌與女性價值畫上等號,物化女性的傾向顯而易見。
在新媒體環境之下,網民的話語權和主動權大大增強,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與網民對重要議題的關注相互呼應,使得以受眾為議程設置主體的逆向模式的產生,即按照個人議程、公眾議程和媒體議程的順序依次進行。全棉時代事件發酵之后,“全棉時代廣告被指侮辱女性”話題迅速登上微博熱搜。網友的反對聲音形成公眾輿論,反向影響了多家自媒體、微博大V的議程設置,體現一種“溢散效果”。隨后,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婦女報、光明日報、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主流媒體相繼發文產生共鳴效應,強烈譴責該廣告及其道歉態度,要求樹立尊重女性的先進價值觀念、端正企業的性別文化意識。
(二)新聞報道中的隱性歧視
新聞的生產與傳播離不開具有意義的象征符,通過符號提示一定的社會文化意義。語言符號作為人類基本的符號體系和意義載體,能夠最直觀地、完整地傳播特定的意涵。無論是英文單詞還是中文詞匯,往往蘊藏著習焉不察的隱性歧視①,直接表現為對職業與身份概念的標簽化呈現。
在男權制度支配的傳統型社會,女性經歷了漫長的以男權話語為中心的權力體系構建過程,在社會分工與角色扮演時經常處于附屬、被支配的地位,鮮少被關注其更加豐富的社會價值。從漢字“媽”“姨”“姑”“婆”“奶”“姥”“姐”“妹”以及“婚”“嫁”“娶”中可以看出,古早女性的社會角色主要與家庭密切相關。由來已久的以男性為核心、以女性為邊緣的社會分工規范,無形中熔鑄著女性價值與家常倫理之間的綁縛鏈條,而構建了一種職場性別壁壘與性別鴻溝。
如在百度引擎上搜索“女企業家”的詞條,最終顯示約有31,300,000個相關結果,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標題為“又美貌又有才”“最美的女企業家”“面相分析女企業家”“38歲未嫁”等,這些帶有隱晦歧視性質的主題看似是對女性企業家才貌兩全的褒獎贊賞,實則是一種善意型的價值偏見。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首次提出“刻板成見”的概念,意指人們對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觀念②。同時,大眾傳媒并不是鏡子式地對客觀事物的直接再現,而是通過有選擇的陳述突出強調某種意識形態、反映文化規范。當媒體在職業“企業家”前冠以性別“女”的限定,就在無意之中加深了職場的性別成見,使傳播對象將全部關注焦點投向與主流規范定義相悖的內容,從而陷入性別認知的怪圈。
新聞報道若以事業有成的女性作為采訪對象,則往往通過強化女性的家庭關系而弱化所承擔公務行為的方式達到吸引眼球的目的③。在一篇題目為《董明珠的硬核人生》的報道中,媒體稱“丈夫的去世,作為她人生的轉折點”而模糊了董明珠本身所具備的剛毅、要強、上進的品質,刻意制造婚姻不幸與事業成就之間的因果關聯。將“其實董明珠很有做賢妻良母的潛質,只不過生活沒有給她那樣的選擇”置于報道的結尾,再次回歸了傳統社會的性別觀念。帶有此類偏向的新聞傳播不勝枚舉,盡管報道以“硬核”的框架來定性企業家董明珠的傳奇履歷,但仍未脫離男權文化的藩籬,反而在更深的程度上默認和強化了舊有的社會性別定位。正如從事媒介性別研究的權威學者劉伯紅所述,女性形象被大眾傳媒一如既往地展現為賢妻良母④,囿于男權對女性的角色期待當中。
(三)女性對自我價值認知存在矛盾
一致連貫的自我認同是女性傳播自我價值的首要前提與動力來源。這種認同機制需要通過作為媒介的身體與外部世界和實踐情境發生關聯得以形成。社交化的傳播平臺提供了更宏觀的實踐空間和“表演”舞臺。公、私領域之間不再界限分明,個人身體作為視覺符號亦可通過圖像視頻等手段得到呈現,而女性群體往往在身材的話題上面臨著更為嚴苛的價值規訓。女演員熱依扎就曾因身著黃色吊帶引發網友熱議,原因是“表露不完美的身材可恥、影響市容”;對比之下,鋼琴家郎朗的妻子吉娜因孕期仍保持完美的身材而頻登微博熱搜、受到畸形審美驅動的推崇與贊揚。
在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協同制定的趨同化主流審美標準之下,女性既是身材空間規訓的行動主體,為創造完美的視覺符號凝望著他人和自己,不斷通過改造身形提高自我認同。同時,女性又是具有批判意識的思想主體,借助社交媒體發起Anti-Body Shaming的全球傳播活動,鼓勵女性大膽摒除被強行賦予的、異形化的女性價值觀。
對于來自他者和自我的身材審視,積極趨附或果敢拒絕的兩種態度體現出女性對自我價值認知的悖論。高標準甚至反生理規律的體態校正,看似是女性追求審美觀和價值觀的主體意識的增強,實則能夠折射出關于女性價值的社會結構張力和對媒介主導營造的“擬態環境”對女性價值的扁平化、單一化誤讀,導致女性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不合理的價值設定。
二、價值悖論的產生原因
(一)新媒體市場化的運營模式
伴隨網絡信息技術和傳播事業的快速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重塑了新聞傳播格局。首先,多元化的網絡傳播平臺為公民賦予了更多的媒介接近權,更為企業自身走媒體化道路融合提供條件⑤。海量信息呈爆炸式增長,為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高額的盈利目標,部分企業崇尚“流量為王”的運營理念,通過制造低俗趣味的內容以迎合市場需求、搶奪流量紅利。在唯流量論的基礎上,“黑紅也是紅”的企業反向營銷模式順勢而生。
其次,傳媒業積極順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趨勢,面向市場化運營方向前進。抖音平臺作為時下短視頻領域的領頭羊,以“輕松幽默”“荒誕滑稽”為主要的媒介調性。抖音所具備的媒介技術使用戶可以通過夸張的表現方式、設置富于戲劇性與懸疑感的情節來創造獨特的擬態環境,增強用戶的代入感,因此為廣告方提供了“劇情廣告”的思路。無論是京東金融“誘導農民工借貸”的廣告,還是全棉時代“侮辱女性”的反轉廣告,都通過讓人不快的歧視、偏見性內容刻意制造沖突,將傳播平臺另一端的用戶視作為“創意”買單的消費者,扭曲了“受眾即市場”的傳媒活動觀。
此外,傳播技術取得長足進步等客觀條件使得如今大量自媒體占據信息傳播場域的主導地位,新聞生產呈現去專業化和情感化表達的特點,沿用并更新了上世紀60年代興起的新新聞主義手法。在新聞生產方面,當前新聞內容呈現幾何級增長、可選取的信息材料過于泛濫,為了輔助深度報道與特稿內容、起到快速打動人心的作用,自媒體更加看重情感張力,把新新聞主義作為撰寫新聞的慣常手法⑥。而在新聞接收方面,由于碎片化的時間管理與閱讀模式形成,傳播對象無法集中于深刻的思辨而更傾向于接受直白、動人的敘事性文本,反過來推動了自媒體新新聞主義的發展。
但是,新新聞主義者對文學手法和情感性表述的過度追求會導致某種不實聯想的產生。在標題為《女科學家顏寧:以智慧定義美麗》的新聞報道描述“顯微鏡前的顏寧,如同一個天真、純粹的小女孩”“如同城堡的樓宇外…就像到了哈利·波特魔法學校的大廳一樣”,不自覺將爛漫感性、樂于憧憬等媒介塑造的女性形象作為新聞點,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科學家顏寧的專業能力。
(二)傳統社會定義性別規范
社會性別理論認為,社會性別是以性別規范和社會角色為基礎的文化建構,這個過程是動態且連續的。文化符號、歷史傳統繼承并鞏固了男性霸權規定的女性客體地位,將“容貌姣好”“身材苗條”“照顧家庭”“尊崇男性”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價值體現。基于社會心理學家米德的觀點,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受到社會評價和社會期待的“客我”影響,長久以來,女性群體按照上述的規范要求自己、采取行動。
在新媒體時代,關于女性價值的悖論愈發激化。劉伯紅表示,男權文化孕育的媒介模式反過來會造成無意識的性別歧視⑦。盡管互聯網技術帶來了低門檻的準入機制和更加多樣的社會化媒體平臺,但是從整體上看,女性的媒介素養有限且容易產生激進情緒,難以有效地通過媒體合理展現女性的真正價值或左右充斥著價值悖論的媒體議程。
三、化解價值悖論的策略
(一)提高女性的媒介使用素養
福柯將話語賦予了社會學意義,他認為話語“是由權勢提供的,有什么樣的權勢就有什么樣的話語”⑧。兩性平等意識雖然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但男性依然占領著話語權與表達權的上風地位。為此,女性群體需要樹立并提高女性價值傳播意識,善于針對具有性別偏向的報道理性發聲、革除女性價值污名化和妖魔化的風氣。同時,女性要不斷提升媒介素養,警惕男性話語主導意見氣候的媒介環境,為女性價值正名。
(二)樹立正確的女性傳播意識
媒體在進行傳播活動時要秉持公正平等的性別觀。樹立先進的性別傳播意識是規避隱性歧視的重要前提。無論是廣告還是新聞報道,都要掌握盈利性、趣味性目標與公益性、客觀性之間的平衡,正視女性獨立主體地位,才能減少對女性價值與社會角色的刻板成見,化解用“貼標簽”的方式一味迎合大眾口味的失范亂象。廣告媒介在談論女性真正的價值時,應當歸還女性自定義價值的權利,讓女性自己掌握命運。2016年由SK-II作為品牌方拍攝的女性主義廣告《她最后去了相親角》通過否定“剩女”稱呼,打破了對女性的年齡歧視,并贊揚了女性獨立、自信的美好品質,傳遞了正確的女性價值觀。
(三)加大對傳媒行業的監管力度
大眾傳播對公眾輿論起著強有力的制約效果,因此有必要凈化傳媒業態。一方面,媒體需要牢記社會職責與使命,以自律精神時刻進行自我監督,對煽動女性情緒與身份成見的內容進行自查自糾,加強內容審核流程的規范性。另一方面,大眾傳媒需要外界的監管。互聯網非法外之地,傳媒機構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者,需要受到法律法規與相關政策的制約,受到來自社會公眾的監督,以防止錯誤性別觀念的肆意滋生,為傳播先進的女性價值提供保障。
注釋:
①黃榮生,林卿.論英漢語言中的顯性與隱性性別歧視[J].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02):59.
②[美]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1.
③譚琳,齊鳴宇.媒體呈現:女航天員的性別角色——以S網對女航天員劉洋的報道為例的性別分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3(02):147-148.
④劉伯紅.女人到底在干什么?——透視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J].中國女性,2006(02):24-25.
⑤譚曉倩,張志安.新媒體環境下媒企關系的變革及關鍵問題[J].青年記者,2020(28):16-18.
⑥鄭杰.試析自媒體情境下的新新聞主義[J].視聽,2020(06):164-165.
⑦趙金.性別平等和大眾傳媒——訪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劉伯紅[J].青年記者,2008(16):54-57.
⑧劉曉紅.話語研究及其在教育學中的漸進[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01):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