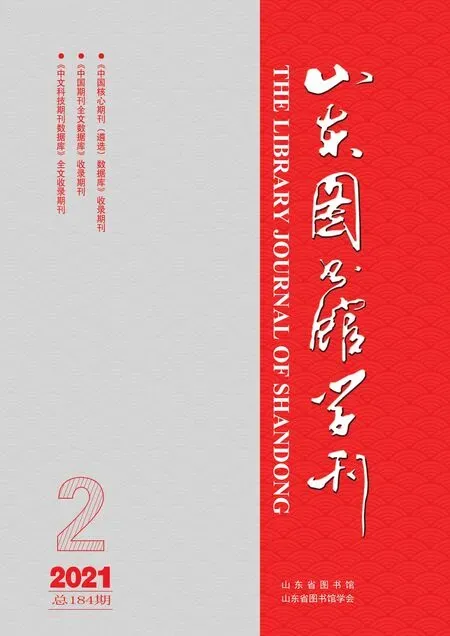目錄學經史關系探析
徐定懿
(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史》編輯部,江蘇南京 210095)
自從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對劉向、劉歆父子目錄學上的貢獻評價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1]自此,目錄學研究大抵都圍繞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樣一個思路上進行。然而,目錄學中書目編排的經、史關系問題,并不僅僅只具有現代意義上的書目分類與學術溯源意義而已。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書目系統中的經、史分類其實與經學史的歷史脈絡暗合。書目編排變化的歷史,其實暗藏著經學發展、變化史。
1 目錄學定位與經、史關系
首先應當從清末以來傳統目錄學的定位展開討論。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中對書目分類有這樣的論述:“古今學術,其起初無不因事實之需要而為之法,以便人用,傳之久,研之精,而后義理著焉。夫言理者必寓于事,事理兼到而后可行。故類例雖必推本于學術之原,而于簡篇卷帙之多寡,亦須顧及。蓋古之著目錄者,皆在蘭臺、秘閣,職掌圖書,故必兼計儲藏之法,非如鄭樵、焦竑之流,仰屋著書,按目分隸而已也。”[2]從此段論述可知,余嘉錫眼中的目錄學究其根本是“以便人用”還要“兼計儲藏之法”,用現代術語來說來說就是實用型學科,其目的是方便好用。關于七分和四部的關系,余嘉錫認為:“合而觀之,七略之變為四部,不過因史傳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諸子、兵書、術數、方技之漸少而合之為一部,出術數、方技則為五,益之以佛、道則為七,還術數、方技則為六,并佛、道則復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諸子一部。”[3]也就是說從七分到四部的變化完全是出于實用需要,因為史書增多,而諸子、兵書、術數、方技之類書籍變少,相對應的,書目也就自然有了調整。
余嘉錫對目錄學這種實用性學科定位的見解并非孤證,姚名達在《中國目錄學史》中對七分、四部有這樣的評價:“世之言目錄者輒喜以四部與《七略》對言,非崇四而抑七,即夸七而貶四。《隋志》之四部非荀(勖)、李(充)之后裔,乃《七錄》之嫡血乎?”[4]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從姚名達對目錄學的定義就能看出其根源:“目錄學者,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專門學術也。”[5]姚明達認為七分、四部其實沒有什么根本差異,四部于七分就是一脈相承。說到底,因為書目分類的實用需要,七分自然就過渡到了四部。姚明達的觀點實際上與余嘉錫相通,相較于前文余嘉錫的觀點更加徹底化:從七分到四部的變化,正是由目錄學實用性學科的定位所決定的。
目錄學的定義落腳為“專門學術”,這實則與中國古代目錄學的歷史境遇不符。中國古代目錄學并不是作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而存在的,在以官簿為正統的目錄學脈絡中,目錄學從屬于國家意識形態——經學的意味非常濃厚,對于中國古代的官簿來說,首要的是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這個“道”的載體,其次才是其學術價值,而且這個學術價值一直是出于不自覺的狀態,并非是帶有現代學科意識的學科規范而帶出的獨立學術價值。
然而自晚清以來的目錄學家多半是以學術考訂的眼光來看待目錄學。由于清末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當時的學者會自覺或不自覺的以西學為參照,以學科分類來規范目錄學研究。如果要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眼光來對傳統目錄學研究作一個總結的話,王欣夫引近人汪國垣《目錄學研究》的一段話做了很好的界定:
一,“目錄學者,綱紀群籍,簿屬甲乙之學也。匯集群籍之名為一編,而標題其書之作者篇卷。或以書為次,或以書之體制為次,要皆但記書名。踵事而興,則進而商確其體例,改進其部次。”這一類稱為目錄家的目錄。二,“目錄學者,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也。后人覽其目錄,可知其學之屬于何家,書之屬于何派,即古今學術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難考索而得。”這一類成為史家的目錄。三,“目錄學者,鑒別舊槧,讎校異同之學也。漢時諸經,本有今古文之不同,然藝文志必詳加著錄,非如此則異同得失,無所折衷。劉向必廣求諸本,互資比較,乃得讎正一書,則舊本異本之重視,蓋可知矣。”這一類稱為藏書家的目錄。四,“目錄學者,提要鉤玄,治學涉徑之學也。如龍啟瑞之《經籍舉要》,張之雅之《書目答問》,或指示其內容,或詳注其版本,其目的皆習見之書,其言多甘苦之論,彼其所以津逮后學,啟發群矇者,為用至宏。”[6]這一類稱為讀書者的目錄。[7]
汪國垣將目錄學劃分為四種,分別是:目錄家的目錄學、史家的目錄學、藏書家的目錄學和讀書者的目錄學。這四種分類已經觸及到中國古代目錄學內在的非單一屬性,書目絕非僅僅是一定規范的分類而已,目錄學對于不同的人來說具有多重的意義。在汪國垣看來:作為目錄家的目錄學更多是為匯編方便,因此部次會本身就是可商榷且一直有改進的;作為史家的目錄學則是為掌握古今學術源流承接,具有學術史的意義;藏書家的目錄學則具有校讎意義,以漢代古文經與今文經為例,今古文不同,必廣求諸本多方比對然后詳加著錄,這一過程就是校讎的過程;而讀書者的目錄學則具有治學途徑的意義,這其實與史家的目錄學有相通之處,目錄學的背后是學術史,因此對治學有重要意義。這樣的總結可以說是細致又有深意了。然而,這樣細致的分類卻都沒有點明目錄學受制于官簿背后的強大意識形態,不可能真的達到為學術而學術的目的。可見,對古代目錄學的研究不能僅僅是針對其具有匯編意義的一面,應當通過目錄形式和內容的變化,理解目錄學發生的經學背景乃至理解目錄學承載官方意識形態的非學術性的一面。這樣對目錄學的研究才是回到具體歷史語境對它本來面目的一種還原。
在進一步討論目錄學分類中經、史關系之前,有必要先對經與史的含義作出歸納。首先是經字,《說文解字》中,經的解釋為:“經,織縱絲也。”段玉裁對這個解釋進一步注釋為:“織之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8]成玄英疏《莊子·寓言》:“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中的“經”字:“上下為經。”[9]《漢書·五行志》中,顏師古對“還經魯地”中的“經”解為:“經者,道出其中也。”[10]從以上對“經”的解釋可以看出兩點頗有意味:第一,經為縱。天在上,地在下,人居中,因此人要對天有所領會,與天要有所關聯,那么這個渠道就是“經”。第二,道出于經。因為經是天與人的聯系,所以天道也只能通過經向人顯現。然后是史字,《說文解字·史部》,對史的解釋是:“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11]《周禮·天官》中對史的解釋為:“掌官書以治贊。”[12]《禮記·曲禮》中,孔穎達疏“史載筆”的“史”為:“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13]由以上對史的解釋可見,“史”首先是職官,其次是事件,而且是關于國家王朝的事件。綜上,經與天道更緊密,而史與人事密切。同時,與天道相關的經并不是高高在上,與人事沒有關聯的,它居于天道與人事之間,這是它“縱”的含義所確定的。
正是因為如此,對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來說,既然他們以天子自居,那么經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為經是天道的載體。而史所關的人事不是一般事件,而是國家大事。那么經在先,史在后,因為一個是天理,一個是人事,記人事也是為了諳天理。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四部分類經、史、子、集排列的時候,就能看出一個明顯的分野。經、史處于離王權中心近的位置,而子、集則處于離王權中心較遠的地位。
2 漢唐時期七分、四部的形成
從目錄學上追述經、史關系,大致可以《漢書·藝文志》為一個起點,同時,《漢志》作為流傳下來可見的七分法文獻,在目錄學上也具有深遠的影響。據阮孝緒《七錄序》,劉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而成。《別錄》是劉向校書時所撰敘錄全文的匯編,篇幅比較多。《七略》是摘取《別錄》內容成書,比較簡略,所以叫做“略”。《漢志》中如下記載:“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14]從《漢志》的七分來看,六藝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如果要以四部分類經、史、子、集來作一個對應的話,那么可以看到,《漢志》七分法沒有史類,或者說史類歸為六藝下的春秋略。查看春秋略下面的小序,是這樣記載: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圣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15]
春秋略的小序強調了這幾點:一,漢離周不遠,因此《漢志》使用的“史”更接近于史的原本意義。柳詒徵就曾指出:“古之有史,非欲其著書也,倚以行政也。史官掌全國乃至累世相傳之政書,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國之政事。”[16]因此,史在原初更重要的乃是行政意義。也正是基于此,春秋略小序強調的第二點也就順理成章了。二,禮。柳詒徵在《國史要義》中也曾指出:“歷夏商至周,而政務益繁,典冊益富,歷法益多,命令益夥,其職不得不分。然禮由史掌,而史出于禮。則命官之意,初無所殊。”[17]而且還點明了:“故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18]正符春秋略小序中所強調的“禮文備物,史官有法”“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里對七略四部的劃分有這樣的論述:“七略四部,名異而實同。荀勖、李充取六略之書合之為四。王儉、阮孝緒又取四部之書分之為七。觀其分部之性質,實于根本無所改革。今以經史子集相沿較久,故仍以此為綱,其不同者皆分別歸納其中,以便觀覽。”[19]也就是說,從根本上講,史在最初“七分”起始階段,就是從屬于經的,沒有客觀記錄歷史的史,史這一部承載了國家行政意義以及“禮”的宏觀內涵。
《漢書·藝文志》后具有轉折性,且與《漢志》一樣在目錄學上具有及其重要地位的正史史志就是《隋書·經籍志》了。它采用了四部分類法,事實上在《隋志》之前《中經新簿》已開始了四部分類法:
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20]
不過《中經新簿》對四部的排列是經、子、史、集。從《隋志》開始就采用了后世通行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從經、子、史、集到經、史、子、集的變化,反映出了官方書目不但具有收集、梳理文獻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文獻編排中體現出國家正統意識。文獻的分類已經由不自覺的承載官方道統意識,過渡到自覺將這種意識貫穿文獻分類的始終,且一直持續到清代。
《隋書·經籍志》經部錄入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以及小學類文獻,但在小學類文獻的最后部分還錄入了鮮卑號令一卷、婆羅門書一卷、外國書四卷以及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這類的文獻。如果參照史部和集部的分類的話,似乎鮮卑號令歸為史部或集部,婆羅門書、外國書以及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歸為集部更合適。但《隋志》的書目分類并不只是檢索分類的索引工具,在這個分類中隱含的是國家官方意志。鮮卑號令、婆羅門書、外國書涉及的是外邦,這與朝貢和王朝統治密切相關,而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則是代表國家一統的前代文獻。因此從國家官方意志來看,經部目錄收錄的內容除了通常認為的經典和圣人之言外,還有一層含義是和王朝政權最密切相關的文獻。前面所提的書目劃分,被姚名達斥為有“分類之非,編目之誤”[21],實質上《隋志》原本就不是按照姚名達依照的“嚴謹”標準來分類的。《隋志》的大序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經與史不同于子、集兩部的地位以及它們同國家王權的親近關系:“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綱紀,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22]“夫經籍也者,先圣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23]雖然《經籍志》包含經、史、子、集四部,但大序中提到的“經籍也者”卻只限于經、史,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經、史與子、集對國家政權來說完全不同的地位。
漢至唐作為本文探討的目錄學經、史關系的第一個時期,這也是中國古代目錄學官簿、史志由開端到成熟的時期。奠定了目錄學七分、四部的基本框架,在此之后的上千年時間里,這一格局雖有被突破的時候,但都未能成為主流。也就是說,七分、四部構成了中國目錄學的主脈。而這一目錄學上的主脈以及在其中占有極為重要位置的經、史關系,正與中國經學的發展伴隨始終。從漢至唐這第一個分期來看,這個時期的經學從漢代立五經博士到唐代官修《五經正義》,用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的話來說,正好也是經歷了從“經學昌明時代”到了“經學統一時代”[24]。與經學史相印證,目錄學從漢至唐也可謂是處于其正統期。經部與史部的關系也從最初同屬六藝略,到位列四部中的經、史二部。兩者與古代王朝的國家意志始終最近,同時,經、史二部亦同源。在目錄學的正統期,七分和四部都反應了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經學思想的內核,此時私家書目較少,且基本沒有超出七分、四部范圍都與“經學昌明”和“經學統一”相印證。
3 宋明時期目錄學分類的變異
目錄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是宋明。中國古代都是隔代修史,因此《隋志》之后的《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元史》都反應了宋明官修史志的狀況。《舊唐書》和《新唐書》都沿襲了從《隋志》以來確立的四部分類的傳統,沒有太大革新。《舊唐書》有《經籍志》,按甲、乙、丙、丁四部排列,對應于經、史、子、集。《新唐書》有《藝文志》,仍舊是按甲、乙、丙、丁四部排列,對應于經、史、子、集。《宋史·藝文志》也仍舊按經、史、子、集排列,但《宋志》著錄重復、差誤較多,故在所有史志目錄中,《宋志》最稱蕪雜。《元史》更是沒有《藝文志》和《經籍志》。不過,明正統時期,“楊士奇撰《文淵閣書目》二十卷,其體例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五十櫥,每書只著書名和冊數,而不著撰人和卷數。”[25]《文淵閣書目》的出現,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作為歷代官簿中為數不多的非四部系統(1)按:本文將四部和七分作為一個系統的不同階段來看,在前文關于漢唐目錄學部分已加以論述。的書目,它的非正統性正好對應于經學史上“積衰時代”[26],宋明性理之學的興盛,無疑是經學史上最為離經叛道的時期,而恰恰最能體現官方正統思想的官簿也表現出了非正統性。二、《千字文》在《隋志》和《四庫》中歸為經部。按《千字文》排列書目,雖然后代斥為草率的評論不少,但若要論立場,卻與其他正史官簿有相通之處,內里保留了經學正統性的核心。因此,宋明作為中國古代目錄學的變異時期,更需要關注的是私家書目的編排情況。原因有二:第一,從社會物質經濟發展的外部情況來說,從宋代開始隨著印刷術的進步,刻書發達,書坊增多,私家書目漸盛。第二,私家書目受官方正統思想影響較小,因此在不少時候能超脫四部分類,而且宋明在經學史上原本就是疑古、叛逆的時代,非正統思想代表的私家書目,更能體現宋明的時代思想內核。
宋代極為重要的兩部私家書目就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后來有人稱目錄學為晁、陳之學,足以表明他們二人在目錄學方面的顯要地位。《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都是采用的四部分類法。但如果細致比較又有所不同。《郡齋讀書志》中,晁公武按照四部分類法將文獻歸類,經類分: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孝經類、論語類、解經類、小學類[27]。相對于《隋志》,晁公武的經部分類中,沒有讖緯類,也沒有收錄緯書。史類包含:正史類、實錄類、雜史類、偽史類、史評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地里類、傳記類、書目類[28]。相對《隋志》,《郡齋讀書志》對“史”的分類有所不同,此外,另外一大區別是沒有簿錄類,《郡齋讀書志》將《太平廣記》收入子部小說類;將《河圖天地》歸為子部五行類。而《隋志》將同類的《河圖》與《河圖龍文》歸為經部讖緯類。《郡齋讀書志》集部,別集類收:《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而將《漢唐策要》《太平盛典》歸為總集類。
《直齋書錄解題》把歷代典籍分為五十三類,不標經、史、子、集,但實際還是按四部分類方法和順序,列經類十種,史類十六種,子類二十種,集類七種。《直齋書錄解題》沒有大序,只有七個類目有小序,用以說明類目的增創和內容的變化。“語孟類”小序,敘述了增創之由。“小學類”小序,重新確定該類目的著錄范圍是“文字訓詁”[29],“起居注類”小序重新確定該類目“與實錄共為一類,而別出詔令”[30]。“時令類”小序,則敘述了這一類自“子部農家類”列于“史部”的原因:“前史時令之書,皆入‘子部農家類’。今案諸書上自國家典禮,下及里閭風俗悉載之,不專農事也。故中興館書目別為一類,列之‘史部’,是矣。今從之”[31]。“陰陽家類”小序,說明了恢復這一類目的原因,“以時日、祿命、遁甲等備陰陽一家之闕”[32]。“音樂類”小序,說明了不再將樂列為經部的原因:“三禮至今行于世,猶是先秦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而前志相承,遒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圣經并舉,比亦悖呼”[33]。“詩集類”小序、“章奏類”小序,都說明其別為一類的原因是有單行本即“獨行者”[34]。從《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的四部分類可以看到,雖然沿襲了四部的傳統,但在收錄眼光上,以及四部之下小部的歸類上無疑是對正統四部分類有所打破的。以《直齋書錄解題》來說,它列小序的出發點更多是為歸類變化作出說明,而《漢志》和《隋志》序更大的作用在于載“道”。在這個意義上,私家書目更接近于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目錄學。
如果說宋代在目錄學是開了思想解放的先河,那么明代則是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明代自《文淵閣書目》后,私家藏書多不恪守四部成規。來新夏將明私藏書目概括為“按四分法類略有增減的目錄”和“打破四分法順序的目錄”[35]兩類。下面以明代幾部私家書目為例,來看視明代私家書目的特點。《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基本按經、史、子、集排列。卷中則分類有:類書、子雜、樂府、四六、經濟、舉業。卷下則有:韻書、政書、兵書、刑書、陰陽、醫術、農圃、藝譜、算法、圖志、姓氏、佛藏、法帖。除經、史、子、集外還有卷中分類已經是對四部分類的不恪守了,而卷中分類中小學淵源等歸為子雜,西廂記歸為樂府,這諸種歸類都是與傳統四部分類不符的。《紅雨樓書目》編寫仍舊以四部為體例,不過子目有所增加,但其宋集部分的排編體例較有新意。宋集部分,用表格排錄,上面一層為集的名稱,下面一層為作者的別號和姓名,十分便于觀覽。《趙定宇書目》記錄的趙定宇所藏的書目,“編寫形式實際上是賬簿式的,雖然也分了類,但類列極不精密。如開卷為:《天字號·史書》,而接下來則是《經類》《類書》《經濟》等,并無規律可尋”[36]。從上述引證就能看出,在明代,私家書目破四部分類之風得到了發展。
通過對宋明書目的梳理,能看到這樣的現象:即在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叛逆期,也是經學史上的疑古期,經、史、子、集的關系變得松散了,經、史也不再具有強烈的承載國家意志、道統思想的意義。并且經、史之間也不再有因為在天道人事所構建的正統皇權網絡中,有那樣緊密的關系了。這正是漢唐與宋明目錄學中經、史關系的區別所在。
4 清代四部分類的回歸
清代目錄學可分為兩期:第一個時期是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的對正統目錄學的回歸與集大成;第二個時期是晚清在西學影響下對目錄學的經世致用的倡導和現代學科分類意識的引入,這以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為代表。
《四庫全書總目》為我國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圖書目錄,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我國重要的古籍,在編排體例上,分經、史、子、集四大類,大類下又分小類,小類下又分子目。每大類與小類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語,簡要說明此類著作的源流以及劃分類、目的理由。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是對錄入《四庫》的全部圖書寫出的提要。《四庫全書》不論從規模上,還是編排體例上,都是對前代的集大成。而《四庫提要》更是對前代目錄學上有分歧的一系列問題作了一個總結。
《四庫全書凡例》首先闡明了全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切目”[37],然后表明目錄編排自《隋志》以下“擇善而從”[38],比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歸為集部,《四庫》隨《唐志》將“詔令”歸為史部,隨《漢志》將“奏議”歸為史部。有意味的是,在明代以破四部分類為體例之后,《四庫全書總目》不但能以四部分類為綱,而且能綜合前代,包括明代書目體例,然后整合于四部體例之下,且體系周嚴。縱觀古代整個目錄學史,能發現這樣一個規律:但凡在正統期,比如漢、唐、清代,則目錄分類明顯重經、史。但凡在嬗變期,如宋、明,則經、史、子、集分類都有打亂,且無所謂強調承載道統,因此在對待經、史、子、集上沒有特別明顯的輕重區分。《四庫提要》也反應了這個規律。在“經部總序”中,除了勾勒出整個經學從漢至清的歷史變化以及不同歷史階段的長短得失,而且還特別強調了皇權和道統,在這一點上,也正如皮錫瑞所言,是“經學復盛時代”[39]。“經部總序”的首句是:“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40]。即是對皇權的強調;倒數第二句為:“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41]。公理換言之也就是道統,這種對“公理”的追求,其實也就是對道統的強調了。《四庫全書》總目,在明代的叛逆與突破之后回歸了正統,但同時,也成為一個絕唱,隨著清朝的沒落,晚清西學的大量傳播,目錄學再也不能固守于四部傳統,經、史兩部所立于官方正統的地位,為“實用”所突破,正如經學在經過清代最后的輝煌之后走向了沒落一樣。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就是這種變革時期的產物。
1875年,張之洞刊印《書目答問》,將典籍按照經、史、子、集四部進行分類。在《書目答問》典籍分類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子部”。張之洞對該部分類作了較大調整。他在子部分類時說:“周秦諸子皆自成一家學術,后世群書其不能歸入經史者,強附子部,名似而實非也。若分類各冠其首,愈變愈歧,勢難統攝。今畫周秦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學尋覽,漢后諸家仍依類條列之”[42]。這是張之洞《書目答問》與《四庫全書提要》分類較為明顯的差異之處。除此之外,《書目答問》四部分類變化最大的,是在子部的兵家類和天文歷算類中,收錄了從西洋翻譯的書籍。也就是說,張之洞將當時西洋翻譯而來的書籍,納入了“四部”分類體系的“子部”分類中,將西學附屬于了中學。比如在兵家類中,列舉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刻本《新譯西洋兵書五種》,包括《克虜伯炮說》4卷、《炮操法》4卷、《炮表》6卷、《水師操練》18卷、《行軍測繪》10卷、《防海新論》18卷、《御風要術》3卷等,并稱贊這些西書“皆極有用”[43]。《書目答問》中,張之洞對經世致用十分強調:“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注本,事倍功半。今為分別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經部舉家有家法實事求是者,史部舉義例雅觴考證詳核者,子部舉近古及有實用者,集部舉最著者”[44]。對“實”與“實用”的強調已經遠離了經作為天道承載,史作為天道下的人事體現的傳統思路。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對子、集二部的極大重視,無疑就是對官簿重經、史的深刻反叛。由此,中國古代目錄學走到了它真正不可回避的變革期,到如今傳統目錄學已經不可能存在于現實實踐運用中。
5 結語
通過全文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目錄學的沿革與經學發展內在理路有著密切聯系,甚至可以說是互為表里;一方面,目錄沿革的歷史也就是經學內部發展、變化的歷史,而經、史關系無疑是目錄學沿革歷史中最為密切的一組關系。另一方面,通過對目錄學中各部的整體考量,能看出在代表正統國家意識形態的官簿中史部首先乃是與經部最為緊密反映出與國家王權的親近關系的,這不同于子、集兩部,《隋書·經籍志》中的“經籍也者”就只限于經、史。不過經、史也各有所側重,經與天道更緊密,而史與人事尤其是關于國家王朝的人事密切關聯。總體來講,如果在經學大背景下來審視古代目錄學的經史關系,可以發現這樣的變化曲線:但凡在經學正統期,比如漢、唐,目錄分類明顯重經、史。但凡在經學嬗變期,如宋、明,則經、史、子、集分類都有打亂,且無所謂強調承載道統,因此在對待經、史、子、集上沒有特別明顯的輕重區分。而清代則既是經學最后的復興期,也是書目分類上四部法集大成的時期;但同時到了清末,書目分類為“實用”所突破,正如經學在經過清代最后的輝煌之后走向了沒落一樣,書目再也無法恪守四部分類,經與史的特殊親緣關系也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