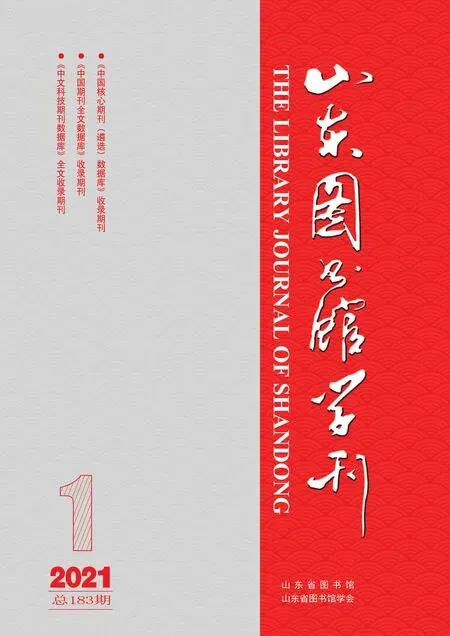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可持續發展模式研究*
——以浙江農村文化禮堂為例
陳 信 柯 平 邵博云
(1云南師范大學圖書館,云南昆明 650500;2南開大學商學院,天津 300071;3浙江大學圖書館,浙江杭州 310027)
1 引言
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重點難點在基層、在農村[1][2],農村文化資源分散、內容單一,各自為政、利用率低,重建設輕管理、難以持續等問題突出[3]。為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加強基層公共文化建設,如《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關于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等。特別是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到2020年,各地普遍建成各方面均達標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
目前,浙江“農村文化禮堂”、安徽“農民文化樂園”、甘肅“鄉村舞臺”、山東“農村文化大院”、湖北“農村文化廣場”、廣東中山社區綜合文化中心和廣西來賓村級公共服務中心等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成效顯著[4][5],為全國其它地區基層公共文化的建設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經驗。但目前這些實踐多見于新聞媒體的報道,學術界對此研究較少。本文主要分析和討論了浙江農村文化禮堂的建設模式及其特點,旨在深化國內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研究,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提供經驗和啟示。
2 浙江農村文化禮堂概述
鄉村振興離不開鄉村文化的振興。從2013年開始,浙江省各地開始按照省委宣傳部“文化禮堂、精神家園”的定位,以“五有五進”(“五有”即有場所、有展示、有活動、有隊伍、有機制,“五進”即推動教育教化、鄉風鄉愁、禮節禮儀、家德家風、文化文明進禮堂)為基本架構,大規模建設和推廣集思想道德、文體娛樂、知識普及于一體的農村文化綜合體(主要由禮堂、講堂、文體活動場所和展示展覽設施等組成)。至2018年底,浙江省共建成10000余家農村文化禮堂[6]。
根據浙江在線輿情中心2017年提供的相關數據,浙江省的文化禮堂熱度值居四地(浙江農村文化禮堂、甘肅鄉村舞臺、廣西村級公共服務中心、安徽農民文化樂園)之首,為96.82%[7]。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等中央主流媒體也對農村文化禮堂建設進行了多次宣傳報道[8]。總體來看,浙江的農村文化禮堂不僅數據顯著,實際成效也非常明顯。據《光明日報》報道,浙江農村文化禮堂成為“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9],逐漸融入村民的生產生活。有學者甚至認為,浙江農村文化禮堂的建設對于農村新型公共空間的轉型與重構具有標志性意義[10]。農村文化禮堂不僅是一個文化活動場所,它在傳統鄉土文化式微、淺薄和低俗文化肆意入侵,鄉土情誼離散、人際關系疏離化的背景下,對于農民精神世界的撫慰和凝聚、農民共同價值觀的塑造、農村社會資本和自治能力的培育、農村娛樂性文化向知識型文化的轉型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3 浙江農村文化禮堂建設模式
據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4956元,連續33年居全國各省區首位[11]。經濟的發展支撐文化的建設,浙江農村文化建設也一直走在全國前列。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浙江省的鄉鎮文化站、農家書屋、廣播電視村村通、農村電影放映、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和圖書館鄉鎮分館建設等項目和工程,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發展。由于各地的自然資源稟賦、人文歷史傳統、經濟基礎條件等存在差異,同時政府也鼓勵各地在建設文化禮堂時因地制宜、彰顯特色,因此,各地在農村文化禮堂建設過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建設發展模式。
3.1 橫向聯動:禮堂共建
浙江某些地區由于人口偏少或財政比較薄弱等原因,農村文化禮堂建設過程中采用合作共建的方式,由若干村、鎮和縣的農村文化禮堂聯合起來,實行“禮堂共建、資源共享”,對傳統的“文化走親、文化結對”形式進行創新,具體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村級層面。如溫州市平陽縣水頭鎮的7家文化禮堂成立農村文化禮堂聯盟,實行“禮堂聯盟+計劃聯排+隊伍聯建+節目聯演+活動聯辦”模式[12]。蘭溪市的“綜合禮堂”則由若干個村共同建設,或一個村建設、幾個村共用[13]。二是鎮級層面。如余姚市的“趕集會”,以鄉鎮、街道為單位,由各文化禮堂輪流承辦、其他文化禮堂共同參與舉辦,即每次活動確定一個文化禮堂為主辦單位,轄區其他文化禮堂協辦,共同組織開展文化活動[14]。三是縣級層面。如樂清市(縣級市)與文成縣成立農村文化禮堂縣級聯盟,簽訂文化禮堂聯盟協議書(又稱“一三五+N”,即每年一場高峰論壇、三個精品禮堂結對、五場走親活動和N個系列活動),共享人才、資金、活動和品牌等[15]。
3.2 縱向聯動:資源共享
從整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來看,農村的公共文化服務往往處于“神經末梢”和薄弱環節,迫切需要共享城市的文化資源。浙江農村文化禮堂在整體體系、某一專業或要素等方面開展文化資源共建共享,同時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更多資源。在農村文化禮堂構建體系中,臺州市三門縣依托“禮堂云”信息管理平臺建立農村文化禮堂總部、鄉鎮(街道)農村文化禮堂分部、村級文化禮堂的三級管理體系,實現農村文化禮堂總部與縣文化館設施、資源、人才、活動、信息等資源的共建共享[16]。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公共圖書館服務的進程中,“嘉興模式”曾引領全國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具體指總分館體系)的變革。從2014年起,嘉興市啟動鄉鎮分館升級改造工作,重點打造“一鎮一品”特色化鄉鎮分館,即鼓勵鄉鎮分館挖掘當地文化特色,開展獨具地方特色的服務活動,提供符合當地居民閱讀需要的圖書館服務[17]。紹興市柯橋區整合社會人才資源,構建區、鎮、村“四團三級”縱向禮堂服務隊伍體系。該體系有專家指導團、藝術團、講師團和督導團等,參與和指導各區域文化禮堂開展活動[18]。
3.3 實體聯動:行業協同
3.4 數字聯動:云端互動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手機在農村的普及,中國的農民網民激增(2019年6月達2.25億、占網民整體的26.3%,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手機成為農民獲取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浙江各地一方面在文化禮堂普及免費無線網絡,建設文化禮堂網站、微信公眾號和手機APP等互聯網平臺;另一方面整合各方面的文化資源,通過互聯網平臺推送給農民、線上線下交流互動,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多媒體展示。如臺州市路橋區委宣傳部組織研發的“路橋禮堂e家”APP,由禮堂展示、指數排名、工作資訊、資源·預約和隨手拍等五大模塊組成,集風貌展示、考核評估、信息發布、資源對接、實時互動為一體,具有多種新媒體(H5、VR)展示、文化資源按需點單、禮堂指數實時查看等優點[21]。二是多部門聯動。如舟山市定海區的“三個全民”(“全民閱讀、全民學藝、全民善行”)APP將“三個部門”(圖書館、文化館、團委各系統)公告發布、“三個全民”活動信息、“三個全民”福利兌換、樂幣排行等內容予以集中,統一推送三個部門的最新資源、活動信息[22]。三是多渠道推送。如溫州市的文化禮堂服務項目點單平臺分別在溫州文化禮堂微信公眾號、溫州文化禮堂網站、溫州日報電子閱報屏、溫州電信ITV寬帶電視設置了“點單平臺”服務入口,實現了“一個平臺,手機屏、閱報屏、電腦屏、電視屏四屏聯動”的效果[23]。
4 浙江農村文化禮堂特點
4.1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文化禮堂在建設過程中注意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挖掘與構建本地特色文化,將標準化與個性化相統一。首先在場所的選擇上,不少文化禮堂在原有的禮堂、祠堂、老廠房、舊校舍等基礎上改擴建,把本地已有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同時注重將文化禮堂的建設點選在群眾文化活動經常開展地,將散落在農村、社區各種文化場所,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民間博物館、紀念館、主題文化公園、市民廣場等場所作為區域內文化禮堂的配套場所有效地串聯起來,使之真正產生文化綜合體的效果。其次在文化禮堂的建筑風格、展示內容、活動形式等方面形成品牌和特色。目前浙江的特色或精品農村文化禮堂大致可以分為歷史資源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類、自然風光類、特色產業類等類別,如舟山市小沙街道毛峙社區文化禮堂的漁俗陳列館,樂清市前橫文化禮堂的百工展示廳,嵊泗縣菜園鎮金雞岙文化禮堂“漁民號子”非遺傳承活動,溫州市甌海區楊宅文化禮堂僑文化展示館,平陽縣昆陽鎮雅村村文化禮堂“機會館”等。這些農村文化禮堂不僅有本土特色的實物展示,還有依托各種實物開展的各種豐富多彩的互動體驗活動,用特色活動提升農村文化禮堂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4.2 融入鄉村產業振興
文化禮堂的建設需要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融入國家和地方發展戰略,以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浙江將農村文化禮堂的建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納入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建設體系”。農村文化禮堂在發展過程中注意同相關行業融合,走文旅結合、文創融合之路。如舟山市定海區各地文化禮堂充分挖掘農耕文化、漁俗文化、非遺文化等資源,開展民俗展示、民俗體驗、非遺陳列等活動,將文化禮堂與周邊自然及人文景觀串聯,打造文化禮堂鄉村休閑旅游圈[24]。臺州市路橋金大田文化禮堂探索“禮堂+社會化”模式,通過吸引文化企業積聚起各種文化形態30多種。禮堂內有折紙館、“扶雅書院”,有當地的文化品牌“花田市集”,吸納了如“東籬茶敘”“鳳梨沙畫”“盼盼手作”等20余家手藝項目入駐[25]。農村文化禮堂與文化產業、旅游業融合,實現二者協同發展,受到了當地居民和游客的好評。
4.3 鼓勵社會力量參與
近年來,我國政府開始規范和重視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產品和服務,專門出臺了《關于支持和規范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的通知》《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等政策文件。浙江各地通過文化禮堂基金、文化眾籌、文化創投等形式吸引社會資金,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建設和管理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同時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如杭州蕭山區戴村鎮提出“文化管家”概念,向社會購買和提供專業化的公共文化服務,承接該業務的杭州最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選派專業的“文化管家”精準挖掘本土文化,向戴村鎮各村的老百姓提供適合本地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務[26]。紹興市上虞區祝溫村成立文化禮堂鄉賢理事會,由村民共同出資設立祝溫村文化禮堂鄉賢公益基金,每年提取的利息用于文化禮堂開展文化活動[27]。除了資金眾籌,還有實物眾籌。如溫州市文成縣黃坦鎮的周岙底村文化禮堂有村民們眾籌而來的民國時期的嫁衣、清朝的碗碟瓷器、代代相傳的蓑衣和紡車等這些承載著當地的歷史積淀的老物件[28]。
4.4 強化制度設計
農村文化禮堂的可持續發展,完善的制度設計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浙江在文化禮堂建設前期即頒布一系列政策文件,以規范和保障農村文化禮堂的建設和發展,如《文化禮堂操作手冊》(1-6版)《關于推進農村文化禮堂建設的指導意見》《關于推進農村文化禮堂長效機制建設的指導意見》《浙江省農村文化禮堂星級管理辦法》《關于文化禮堂建設用地保障的若干意見》等,各地也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有相應的規范和政策。與制度設計相對應的是制度的執行與監督,對執行效果的考核與評價。浙江省對農村文化禮堂實行動態星級評定,定期評出不同星級(五星、四星、三星及以下)的文化禮堂以及“最美文化禮堂人”,并定期培訓農村文化禮堂管理員、文化大使、文化志愿者等文藝骨干,培訓內容有組織策劃、節目編創、舞美設計以及地方文藝挖掘創新等。此外,浙江各地的一些文化禮堂(如嘉興海鹽得勝村)設立文化禮堂理事會,為村民搭建文化自治的新平臺,幫助村民從參與者向組織策劃者轉變。
4.5 以農民需求為導向
任何一項價值觀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必然要融入人民的生產生活[29],一項事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建國以來,我國歷次農村圖書館建設的失敗,除了缺乏可持續的經費和政府關注外,這些農村圖書館沒有真正融入農民的生產生活、“缺乏群眾基礎”也是重要原因。與此相反,浙江的農村文化禮堂之所以能“活”起來,一是積極挖掘村民的文化潛力,讓村民成為文化活動的主角;二是禮堂活動貼近實際,讓村民感覺很親切。如杭州市蕭山區白鹿塘村文化禮堂在2018年重陽節時根據村里有老人想吃重陽糕和想看越劇的需求,專門策劃了學做重陽糕活動和越劇演出[30],這些根據群眾需求開展的文化活動直接提升了禮堂活動的滿意度和參與度。為推動服務項目與群眾需求有效對接,溫州文化禮堂“點單平臺”專門設計了《服務項目需求征集表》放于全市文化禮堂,方便基層群眾隨時填寫需求意向,同時通過平臺大數據分析,對群眾黏性差、評價低的項目及時調整,對群眾歡迎、點單火爆的項目及時增設,將群眾的“需求”與政府的“供給”精準匹配[31]。文化禮堂將政府建設的外部推動力轉化為村民的內在需求,將文化創造活動“賦權”給村民,在文化禮堂的物質形態中融入村民的精神和情感要素。
5 結語
浙江農村文化禮堂經過六年多的建設,逐漸形成自身特有的發展模式和特點,在縱向和橫向、實體和數字聯動中,注重因地制宜、融入產業振興、鼓勵社會參與、強化制度設計、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等,不僅拓展了農民的公共文化空間、重塑了農民的精神家園[32],也為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可持續發展探索了新的模式與路徑。浙江農村文化禮堂不同于以“一場兩堂三室四墻”為特點的安徽農民文化樂園、以“五個一標準”為特點的廣西來賓村級公共文化服務中心,亦異于上海松江的“3+4+X+1”模式和廣東中山的“三三三”模式,其核心在于注重利用行政資源的同時,挖掘文化禮堂的內生動力,既彰顯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地位,又扎根于源遠流長的鄉土文化,把政府建設文化禮堂的外部推動力轉化為村民普遍的文化認同和內在需求,使文化禮堂建設與村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結。
〔2〕〔10〕 湯敏.從祠堂到禮堂 浙江農村公共空間的轉型與重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