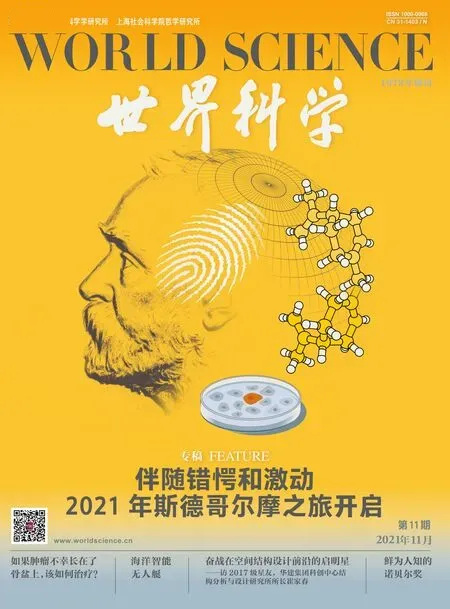生物學必須兼顧思想和數據
編譯 李軍平
大約二十年前,我的老朋友悉尼·布倫納(Sydney Brenner)在獲得諾貝爾獎之時對生物學界提出了一個警告,“我們正淹沒在數據的海洋中,卻又忍受著知識的饑渴。”布倫納憑借將秀麗隱桿線蟲確立為研究發(fā)育生物學的模式生物成為分子生物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因此,這一警告對今天的生物學界更具現(xiàn)實意義。
在參加研究講座時,我經常感覺自己淹沒在數據的海洋中。一些演講者似乎認為,只有堆砌大量的數據才能引起與會者的重視。他們忽視了邏輯框架、收集數據的目的、假設的測試過程、以及究竟可以產生哪些思想。研究人員似乎不愿意得出結論或提出新的思想,出版論文中同樣的情況也時有發(fā)生。在這一背景下,無論是糾結數據的意義還是討論具體的思想,似乎都不太恰當。
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文字描述和數據收集工作非常重要,但它們不是研究的全部。學術研究還需要觀點,即使是試探性的猜想,也是有益的;同時也要認識到,隨著事實和論據的積累,之前提出的觀點也會發(fā)生變化。
為何研究人員不愿提出新的觀點?或許他們擔心這些觀點是錯誤的,降低他們獲得晉升或資助的機會。但是正如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言,“錯誤的事實對科學進步非常有害,因為它們往往會持續(xù)很久;但是錯誤的觀點如果得到證據的支持,也沒有什么害處,因為每個人都能夠從證明錯誤的過程中獲得快樂;因為他們可以關閉一條通向錯誤的大門,而通向真理的大門往往也會同時打開”。換言之,雖然獲取正確的事實很重要,但新觀點和新思路也有很大的價值。只要它們基于合理的證據,并經得起糾正,就有存在的意義。
不要片面地理解我的發(fā)言,我們同樣需要新技術產生的數據來促進對世界的理解。“無假設研究”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培根(Bacon)在1620年提出了這一觀點,并將其作為“經驗方法”之一。他在《新工具論》中主張,建立科學真理的第一步應該是通過系統(tǒng)的觀察來描述事實。但這只是第一步。如果達爾文在描述了雀喙的形狀和大小之后就停止思考,而沒有繼續(xù)提出自然選擇進化的觀點,那世上就不會出現(xiàn)“進化論”。
下一步是從數據中提取知識。為了重新關注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改進工作流程,更加強調理論,并轉變我們的研究文化。應當讓開發(fā)新技術和新方法的工程師與實驗學家深入研究生物問題。只有深入了解生物學,而非僅僅收集海量的數據,我們才可能會提出重要的問題。而此類問題將促使研究人員勇于不斷探索數據,促進新模式和知識的發(fā)現(xiàn);此類問題也將進一步影響數據的收集方式。
其他必要的步驟包括:開發(fā)數據挖掘和機器學習程序等分析工具;確保數據可用、正確注釋和公開共享;模擬生物現(xiàn)象涉及的分子和細胞成分,以便分析動態(tài)行為和相互作用;哪怕只拋出問題而不求解也可能會有幫助,因為這將對模型構建方式提出更嚴格的要求。
此外,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理論支持。例如進化生物學家比爾·漢密爾頓(Bill Hamilton)和約翰·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以及遺傳學家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這些專家的論文充滿了豐富的生物學直覺,讀起來令人身心愉悅。這種思維方式將加速“從描述到知識”的轉變過程。理論學家可以在研究生命系統(tǒng)中的信息流時抽絲剝繭,幫助自己從泛濫的生物數據中洞悉真相。
如果希望以理論和知識為主導,則可能需要轉變研究文化。我們應鼓勵理論探索,將理論觀點納入實驗論文,以便使數據與研究內容相符。此類嘗試不應被期刊編輯和資助者視作毫無根據的猜測。“(專業(yè))領域的暴政”有時會阻礙不符合主流意識思想的產生,但這是錯誤的。評審委員會應當足夠大度,即使研究人員的觀點被證明有誤,但只有要可取之處,也應給予晉升或資助。
上述方法不僅會促進研究,也會改善教學。如果學生得知生物學是有思想的,且這些思想值得討論,他們能夠獲得更多的學習動力和靈感。
資料來源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