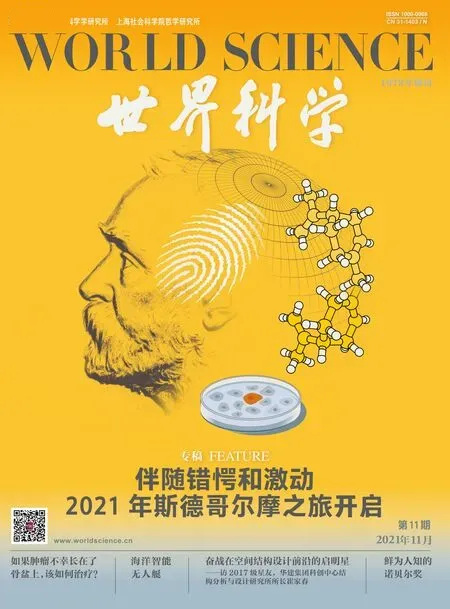改進科學教育:這不是火箭科學,但這更加難!
編譯 高斯寒
“這不是火箭科學,但這更加難!”這句話改寫自天文學研究者喬治·尼爾森(George Nelson)經常說的話。尼爾森當了11年美國宇航局(NASA)宇航員,執行過三次太空任務,其中包括“挑戰者”號航天飛機事故后的首個任務。離開NASA后的幾十年里,他拓展事業版圖,橫跨科學研究、工程學和科學教育等領域。在眾多職務之中,他擔任了西華盛頓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美國科學促進會“2061項目”主管,后者是一個著眼于改善科學教育的長期項目。尼爾森的這句話凸顯出提升科學教育體系的困難程度。
改善科學素養和科學教育的努力在最近幾十年里面臨許多挑戰。譬如說,美國的《2001年不讓任何孩子落后法案》強調了教師測試項目,結果侵蝕教師和學校的自主性,進而削弱和拖延了科學教育實踐上早該實施的改變。
本文強調了一些鼓勵物理學家參與改善科學教育行動的趨勢。盡管并不新鮮,但這些趨勢再度獲得科學家和科研機構的關注。這些努力的核心是認識到科學教育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并采用更廣闊的基于系統的方式。以基于研究的教學方法為基礎,物理學家能夠在學校、校外項目、國際事件和旨在改善科學素養的其他活動中與各方合作,發揮作用。

智利雙子星天文臺的費爾南達·烏魯蒂亞(Fernanda Urrutia)和兒童一起做濾色器實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勞倫斯科學展廳通過“數學和科學大探險”項目發起這個活動
善用最佳教學方法
我們從幾十年設計、實施和評估創新科學教育項目的經驗中明白轉變科學教育的挑戰。我們和新手教師、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博物館教育者、教育研究者、教育開發團隊合作過,而受眾從學前兒童到成年人都有。我們也和各個科學、工程和教育領域專業團體,各國政府和全球的非政府組織共事過。我們從實踐中學到許多經驗,知道如何才能教得更有效果。
許多科學家對于不同環境下的教學方法并不熟悉。幸運的是,有許多高質量的免費資源總結了針對不同背景下學習的研究成果。我們最近完成了一篇針對最佳教學實踐研究的綜述文章,強調了一些對科學家最有用的最佳實踐。盡管這篇綜述文章特定于天文學教育,但大多數建議都適用于科學和工程教育的所有領域。
學習要趁早
對于許多科學家來說,與教一群小屁孩相比,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更加容易,也更為熟悉。后者已經擁有數學和科學基礎,也選擇上過科學課程。教他們就好比射箭,射出一支箭,然后在箭命中之前把靶子放在著陸點。擊中靶心令人滿意,但也提出了一個問題:老師對年長的學生有多大影響?向更年輕的學生教授科學具有挑戰性,但能在他們高度成形(highly formative)和難以預測的早期發展過程中極大擴展他們的科學視角。
20世紀60年代初,哈佛大學教授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發起多項科學教育改革嘗試。他的關注重心是早期學習和所謂的螺旋式課程,即每年更加詳細地探究各科目,而不是將某個科目“留給”某個特定的年齡范圍——譬如說在十年級上化學課,十一年級上物理課。布魯納堅信,任何科學概念都可以改造后適用于任何一個年齡層。對于年幼的學生,參與科學活動和演示的做法會比給出言語性或數學性解釋更加有效。布魯納指出,人是通過嘗試騎車來學會騎腳踏車的,而不是通過看一本圖畫書或一頁指南來學會。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羅伯特·卡普拉斯(Robert Karplus)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勞倫斯科學展廳所做的工作提供了另一種改進初等教育科學課程的方法。卡普拉斯離開理論性的量子電動力研究事業,因為他相信教育年幼學習者的工作和大學科研教書工作一樣具有挑戰性,一樣有回報。卡普拉斯發展和支持了一個已經證明對各個年齡層學習者都有效的學習環模型。他的學習環理論假定,學習分為能夠周而復始的三個階段——探索、發明、發現。他的主要貢獻是強調實際動手經驗,而非以教材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卡普拉斯的學習環模型得到后世其他學者的修正,反映出對科學研究過程的深層理解。
初等教育的老師通常將工作重心放在傳授基礎的閱讀、寫作和數學技能上。雖然他們懂得最佳的教育手段——包括那些源自布魯納和卡普拉斯的方法,但要將他們的教書技能應用到教授科學上卻很困難。許多初等教育的老師對于科學主題的了解程度,對于如何有效地結合科學和核心教學內容,也缺乏自信。
科學家能與教師合作,克服這些困難。科學家懂得科學,而教師明白兒童們是如何學習的。更深刻地弄清年幼學生是如何學習科學的話,雙方都能從中獲益。教育者能明白學生對科學的錯誤觀念和幼稚理論,那么在這樣的教育者指引下,學生能更加成功地探究科學概念。至于科學家方面,他們和初等教育老師的合作能帶來許多回報,極富建設性。
學校里的角色
科學家能帶給學校的,不只是親身上陣或以視頻形式做報告和演示。傳統上,科學家是基于他們對一群學生或學校缺少什么做出的評估來決定在學校里承擔什么角色,而評估往往是根據他們自身的兒時經歷或在學校里的短期考察。一種更好的做法是讓科學家和教師合作,找出學生最關切的主題,提出最佳的應對方法。科學家還可對每天工作在教育領域內的教育專業人士的需求做出響應。
科學教師常常表示,他們需要接受更多線上教課方法的培訓,需要能獲取到高質量的交互式學習材料,掌握最新科學發現和技術的更多信息。他們也希望能有一位科學家隨時待命,能在電話中向他們解釋概念和術語,幫助他們找到合適的活動和演示,支援和鼓勵他們。大多數初等和中等教育層面的科學教師說,他們的教育背景不足以有效地教授物理學。教師對于更為專業的準備和支援工作的需求已經存在了幾十年,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項需求似乎越來越強烈。
要滿足教師們的需求,一個方法是科學家成為所謂的科學大使。擔任科學大使的科學家充當科學界和教育界之間的聯絡人,幫助教師尋找教育材料和教具,幫他們聯系大學或科研群體。科學大使必須明白教育體系的運作,譬如教育者如何接受培訓,要應付什么需求,每個年齡層的學生又是如何學習科學概念的。美國天文學會之類的專業學會常常在學術會議中提供科學大使培訓。
教室內的主動式科學學習
科學家常常驚訝地發現,學校內的許多科學課幾乎沒有花時間給學生實際鉆研科學。初等教育的學生進行簡單的物理學實驗的情況越來越少見,盡管那些活動已被證明能有效地讓學生對學科產生興趣。相反地,各個年齡層的科學課常常包含學習科學術語,記憶科學方法,閱讀和討論科學原理、定律以及科學家。
這些科學課未能允許學生玩科學游戲,結果科學課變得枯燥乏味又迂腐。羅伯特·耶格爾(Robert Yager)是美國科學教學研究學會和美國科學教育協會的前會長,他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做”科學更加有趣。
遺憾的是,學生們極少有機會玩科學——極少有機會進行真正的科學探究,也就是調查一個他們自行確定的問題,構想可能的解釋,針對各種解釋來設計實驗。相反地,學校的科學課意味著在小學、初中、高中的13年里學習游戲規則,做驗證類型的實驗,學習他人提出的、廣為接受的解釋,學習其他人構想和使用的特殊術語與步驟。
按照我們的經驗來說,天賦異稟的學生常常最容易因為沒機會參與科學提問和探索而感到沮喪。我們認識的一位極有才華的學生在初中時被科學教師打上了“難教、搗蛋”的標簽,差點因此而輟學。這個學生到底干了什么呢?他向教師提出質疑,詢問有什么證據說明地球繞著太陽運轉。科學家歡迎和激賞這樣的提問和質疑,而不會感覺受到威脅。那名學生如今是IBM公司的一位著名工程師。科學參與——而非教條主義的記憶背誦——激發出對于科學的熱忱。
自由選擇的教育

位于亞利桑那州圖森的薇拉·魯賓天文臺有一處少兒天文學咖啡館,里面可獲取基于電腦的工具,學生用這些工具來分析大型數據集。這家咖啡館也提供研究生、博士后的科學演講和與他們的非正式討論

諸如天文日或全國天文周之類基于社群的教育活動是將科學活動帶給廣泛受眾的有效方式。2019年在夏威夷州希洛的庫希歐王子廣場購物中心舉辦的這項活動中,來自雙子星天文臺的一位職員和一名學生一起探究濾色器。天文臺在活動中聯系當地社群,了解他們的教育需求
物理學家在選擇科學教育的角色時,常常傾向于學校與課堂。然而,在課外和校外項目中,仍然有其他機遇。這些非正式和自由選擇的教育場景包括課外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天文館、圖書館、可實際動手的科技中心、科研機構的訪客中心、街頭集市、社區活動、夏令營、科學咖啡館、科學節日等等。
科學家在那些場所可以幫助設計博物館展覽,為兒童發現中心建立科學項目,在圖書館發表演講。演講最好較為簡短,不要那么正式,留出足夠時間用于討論、辯論和廣泛提問,這樣能提高聽眾的興趣,提高參與度和滿意度。和其他領域相似,非正式教育領域在教學法背后也有著強勁的研究基礎。
打造科學資本
許多創新科學教育項目構建在“科學資本”概念之上,這個術語源自2013年的一份頗具影響力的英國科學教育政策報告《抱負:年輕人的科學與事業志向(10~14歲)》。科學資本是指個體的所有科學相關的知識、看法、體驗和資源的總和,包括他們知道和學習的科學內容、他們對科學的想法,以及他們日常與科學、與對科學感興趣的人打的交道。基于資本的教育生態系統視角鼓勵各種合作關系,給兒童提供在學校和其他場景學習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的機會,鼓勵系統性改變,為學習者創造一個支持系統。觸及或服務新社群的創造性方式已經在全球范圍得到成功施行,常常由科學家擔任關鍵團隊成員。譬如,科學家已經對鼓勵科學設計和視覺思考的項目做出貢獻,這類項目也被稱為STEAM,因為它們結合了STEM領域和藝術,能激發兒童的藝術興趣和視覺思維技能,促使他們追求科學和技術相關的事業。
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的科學教育副教授勞拉·康納(Laura Carsten Conner)與合作者研究了女孩如何看待科學,藝術與科學的聯結在構建她們的科學身份中的價值。她的研究構成了“自然的色彩”和“培養STEAM”項目的基礎。這些項目結合藝術和科學,包括在科學咖啡廳舉辦與科學家互動的活動,培訓教育專業人員如何整合藝術與科學進入課程,在暑期學院中用分光儀、光學顯微鏡、掃描電子顯微鏡等科學工具教女孩探索色彩等。
康納的項目證明了構建科學資本作為創新科學教育核心方式的重要性和價值。藝術與科學的聯結能觸及新受眾,為開始構建科學資本的學生提供一個鼓勵性環境。

“自然的色彩”項目中對藝術有興趣的學生使用顯微鏡、攝像機和分光儀來學習熒光、動物視覺、極化、顏料的光譜性質、光干涉和結構色彩的相關知識。該項目支持那些有興趣探索藝術和科學之間關系的學生、家庭和教育者,在亞利桑那州圖森和阿拉斯加州費爾班克斯舉辦了多次面向女學生的暑期學院
國際和全球項目
許多科學家告訴過我們,一些奇特的經歷是改變人生的大事件,譬如看萬花筒、觀察月球磁場、用紅外照相機觀察世界,看超導體的磁懸浮。許多科學家想要知道他們如何分享那些經歷。
科學家的一種方式是參與全球的教育項目,譬如慶祝伽利略·伽利萊使用望遠鏡作天文觀測400周年的2009國際天文年,2015國際光與光學技術年,2019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成立100周年活動,2020—2021國際聲學年。
國際項目大多由科學家志愿者領導,他們依賴贊助組織來鼓勵科學家成員的參與。為了在教育方面取得成功,國際年項目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和籌劃。假如擁有大膽而明確的目標,有一支科學家和教育者構成的多樣化隊伍來負責計劃和實施,那么這些項目都會更加成功。
2009國際天文年中,一個叫作《從地球到宇宙》的展覽展出了眾多望遠鏡獲取的天文照片,被翻譯成40種語言,用于70個國家的一千處展覽地點,包括公園、圖書館、地鐵站和機場。總共有1 000萬人參觀過這些展覽。伽利略教師培訓項目在志愿者的幫助下,在75個國家展開,構建了規模最大的國際天文學教師培訓班網絡。在包括美國天文學會在內的組織和個人支持下,三名美國科學家創造了伽利略學生望遠鏡套裝。這個團隊對于少兒缺少高質量但價格不貴的天文望遠鏡的情況感到遺憾,于是決定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獲得一些機構的支持和合作,設計、制造和向110個國家分發了25萬臺的高質量望遠鏡套裝,還附帶了教育材料。伽利略學生望遠鏡目前依然在生產,而它的教育材料能方便地免費獲取。
依照我們的經驗,科學家能給這些項目帶來巨大價值,因為科學家愿意分享自身對于科學的滿腔熱情。
科學家-教育者的融合

2019年,基普·索恩(Kip Thorne)與智利拉塞勒那大學學生團隊和美國光學紅外天文研究實驗室項目的負責人見面。該年7月的日全食中,他們在托洛洛山美洲際天文臺進行天文觀測。觀測重現了一個世紀前的著名結果,證實了廣義相對論所預測的光的彎曲。這個項目是愛因斯坦學校項目的一部分,為慶祝國際天文學聯合會成立100周年,它促進了全球各地推進創意項目,讓學生探索引力在天文學中扮演的角色
我們作為科學家與教育者的混合體,注意到每年都有更多科學家選擇投身于兩個角色,并將它們整合進自己的事業中。每個人給予科學家和教育者角色的份額都隨著他們的興趣、技能和事業階段而各有不同。許多科學家已經超出教育志愿者的程度,變成全職的教育和社群參與專業人士;一些科學家樂于在大學、科研實驗室、醫學中心或公司的支持下,作為教育和社群參與團隊的一分子,幫助、設計和實施新項目。
教育開發團隊中的科學家在科學調查過程之后對教育材料和項目進行建模,填補了一個重要的、或許是獨一無二的角色。例如,1992年,西弗吉尼亞州NASA未來課堂的克雷格·布勒頓(Craig Blurton)指導和監督了天文學、行星科學、生物學和環境科學領域的許多前沿教育軟件項目。他從全國各地請來對科研和教育都有熱情的科學家,和手下的教育研究者、多媒體開發人員一起合作。他們聯手創造出逼真的沉浸式仿真,允許學生作為團隊成員探索前沿科學問題。
他們的成果中,有面向高中學生、得到NASA支持的電腦程序“天文學村:探究宇宙”,面向初中學生、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支持的電腦程序“天文學村:探究太陽系”。這些教育軟件贏得許多獎項,包括《技術和學習》雜志頒發的年度最佳微電腦軟件殊榮。在虛擬的天文學村里,學生們以團隊形式用仿真儀器、太空探測器、地基望遠鏡做研究課題。他們在實驗室里做實驗,利用圖像處理軟件分析NASA、NSF和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的真實圖片和數據。最后,他們在模擬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研究結果,回答提問。
這些項目捕捉到了科研合作的精髓,讓學生們沉浸在真實的、前沿的課題中,譬如系外行星、越地天體、在太陽系搜索生命和尋找超新星等課題。它們也是最早的以中學生為對象、利用互聯網、電郵信息和復雜圖形處理的教學材料。
另一組科學家和教育者團隊由天文學家伊莎貝爾·霍金斯(Isabel Hawkins)領導,她在1997年至2008年間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太空科學實驗室的科學教育中心主管。他們為“數學和科學大探險”項目開發了創新的教學材料,他們推出的經全國測試的天文學教師指南借鑒了以研究為基礎的教學方法,即使對數學或科學背景有限的教師來說也很容易使用。
許多糅合了科學家與教育者的團隊已經開發出高質量的教學材料,捕捉到科學探索的真諦。對創建教學材料感興趣的物理學家可以加入這類開發團隊。
眼光放長遠
物理學家能夠懂得滴水穿石的道理。科學教育生態系統中的問題存在已久,頑固難治,要對付這些問題,需要持久的努力、持續性的系統改變。盡管科學教育取得了許多值得矚目的成就和創新,但在我們看來,美國和大多數其他國家科學教育的進步總體上飄忽不定,并不穩定。
所有年齡層的科學教育質量依然千差萬別。在美國,眾多城市分為不同學區,存在公立學校、特許學校和私立學校,這種制度幾乎注定了教育資源和教學上的不均衡。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他們家的地址或郵政編碼依然是對他們可實現的短期和長期教育成就的最佳預示變量。好學區和差學區的學校教育質量反差鮮明。
教師缺乏獲取高質量教學材料的渠道,也缺少如何用好教學材料的培訓。可供主動式學習和基于計算機的各種活動的實驗室常常落得年久失修、甚少使用的命運。針對科學教師的職業發展項目就算一開始取得成功,隨著時間流逝,也會因為資金匱乏而逐漸消失。新建立的項目和組織努力對付這些問題,但是他們僅僅取得一點兒進展后,就因為失去干勁或資金而放棄。

電腦程序使得學生能用從地基望遠鏡模、太空望遠鏡和行星際探測器獲取的數據模擬行星科學研究。在“天文學村:探究太陽系”程序中,中學生可以探索太陽系內可能的生命棲息地。該項目采用以研究為基礎的教學法,結合了典型的研究過程,其中包括定義不明確的科學問題,這些科學問題沒有明顯的正確答案
想要幫助改善教育的研究組織常常最終選擇與本地擁有優勢的市郊學校合作,而不是需求更強烈、能從合作中收獲更多的弱勢學校合作。科學家和科研組織也可能落入類似的陷阱,選擇那些會讓他們形象顯得高大上的項目,而不是那些有著更多教育價值的項目。與多樣化的社群建立教育合作關系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于是部分科學家們選擇了更加簡單的、能帶來大量宣傳的短期任務。
正式和非正式的科學教育體系都需要科學家和科研機構更長期的付出。反過來,科研機構必須重視、支持和獎勵科學家們的努力付出。遭受忽視的社群也需要額外的探索、對話和時間來與科研機構發展出真正的伙伴關系,讓對方了解他們的需求。
下一步
許多科學家想要幫助改善科學教育生態系統,但是給教師買幾塊磁鐵很容易,每年培訓一批新教師,讓他們懂得磁學則困難得多——容易的解決方法效果有限。假如你想要參與科學教育改善計劃,你首先需要擁有額外的知識和經驗來有效地改善本地、全國乃至全球的科學教育。
你為了弄懂本地社區教育系統的需求而付出的投資會給你和社區帶來豐厚回報。與教育機構合作,一起從事卓有成效的行動,這一點也至關重要,會幫助你避免個人獨自工作時出現的挫敗感。
那么,作為物理學家的你如何開始第一步?選擇你周圍的一處貧困地區,和一位教師或一名青年俱樂部領導者聊一聊,與他們建立長期伙伴關系,滿足他們的需求。鼓勵你所在的組織向當地困難社群投入資源,解決學生和教育者的更廣泛需求。回應他們的召喚,為他們提供服務,齊心協力改善科學教育。
資料來源Physics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