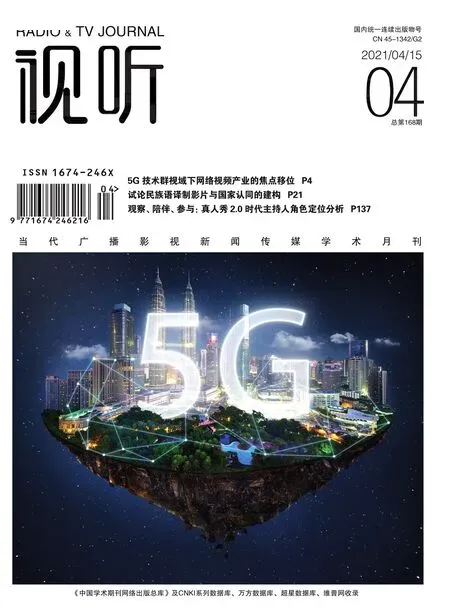語言、文化與類型:《少年的你》生存質感的雙重維度探析
□ 歐陽沛妮
莎士比亞的生存還是毀滅之問,在人類遭遇生存困境之際總能叩響思辨。是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毒箭,還是挺身而出去反抗人世間無涯的苦難,勇敢地斗爭?披著一件講述少年之間至純情感的故事外衣,內里卻涉及校園暴力、原生家庭、社會邊緣化等問題,影片《少年的你》之煩惱“躍然影上”。掙扎、變形、擰結的苦澀和青春時期的昂揚、希望、美好交織成影片生存質感的雙重維度。
一、雙面膠:視覺語言的二元對立與互話
所謂視覺語言,“是囊括了電影的畫面造型、黑白關系、運動、人物形象……等所有‘可見的’因素的視覺藝術創作方法。”①《少年的你》在第39屆中國電影金像獎中榮獲八項殊榮,累計票房達15.58億,其藝術性和商業性得到極大認可,離不開精彩的視覺語言呈現。
(一)人物的對抗與交集
主角陳念和小北,一個是大學霸,另一個是小混混。影片從光線的冷暖反差、兩人走在一起時一前一后的蒙太奇手法、一明一暗交叉的音樂剪輯等對比呈現,都在強調兩人之間的懸殊差異。影片中還有一對強烈的矛盾體,即以魏萊為首的校園暴力者和以胡小蝶、陳念等人為代表的受暴者。“奧地利動物心理學家康拉德·勞倫茲認為:‘攻擊行為是人和其他動物一樣所具有的普遍本能。這種本能發生于同類間及同階級人之間,以實現內驅力的釋放。’”②魏萊等人的校園暴力行徑被陳念告發背后折射出的,不僅是原生家庭和高考制度共同施予他們的壓力,更是他們在高度緊張狀態下去推動有機體活動的內部動力,即以攻擊他人來達到自身內部平衡的暴力溝通。
然而,人物的對抗化只是影片一個有利于塑造鮮明角色性格的敘事技巧。影片難得的是將少年那種亦正亦邪、難以厘清的混亂之感表達了出來。陳念和小北各自的人生規劃雖天差地別,但兩人卻有一種惺惺相惜的相互體認;小北在主流價值觀看來是個惡習纏身、被人瞧不起的小混混,但他重情重義,甘愿為陳念付出,這是倍受社會尊重而又珍貴的品質;在暴力權力上,魏萊看似占主導地位,但最終導致了陳念不可挽回的傷害;而魏萊訴諸暴力的根源,與母親錯誤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期待密不可分,可恨又可憐,最后淪為暴力的犧牲品。看似棱角分明的人物,在鏡頭語言的耐心刻畫之下逐漸祛魅;看似不可交融的生命,卻共享著生命最本質的可悲。這一過程展現了影片獨特的價值觀,讓人從校園暴力的一角去窺探更多現實的、人性的隱秘角落。
(二)空間的對位和匹配
“只要電影是一種視覺藝術,空間似乎就成了它總的感染形式”③。區別于現實空間的真實性,電影的空間是藝術性的,馬塞爾·馬爾丹更是將電影空間的處理概括為“再現空間”和“構成空間”。《少年的你》表現出地理空間、心理空間與藝術空間三個層面,每一空間的元素辯證統一,構成了新穎的電影空間表達。
片中,學校是陳念最常呆的地方,總伴隨著仰視鏡頭和大量的人流,給人一種神圣感以及中心感。與之相較的是小北的家,一間遠離城市中心、被掩蓋在巨大立交橋下的破舊小屋。學校與破屋是一組對比鮮明的地理空間,一方面突出了陳念和小北在文化背景、知識階層上的現實差異,另一方面,貼滿高考鼓勵語的學校和密閉的親密空間展現,是對高考制度的壓力和少年情感關懷缺失的反思。影片合理運用了這類對比式的地理空間,但并沒有停留在兩者現實的差異中,反而是積極建構兩者之間的“橋梁”。于陳念來說,學校即地獄。在小北家里,兩人得以傾吐最真實的想法。小北對陳念說:“陳念,你是第一個問我疼不疼的人”,這間小破屋逐漸轉變成兩人的私密情感空間。破屋與學校之間的道路,陳念在前,小北在后,保護與被保護,陪伴與被陪伴,就在往返中兩個地點的位置有了感情的牽連。
“人眼相當敏感……導演常會指引眼光到對比最強的區域,因為該區域會在其他較含蓄對比的區域突顯而出”④。影片以陳念為敘事中心,其心理化的對比式構圖讓人印象深刻。為了營造陳念和魏萊兩人的對抗心理和矛盾氣氛,影片常采用垂直式的構圖:魏萊或是處于樓梯的上方將陳念推下去,或是將陳念逼迫到潮濕小巷的角落。此時魏萊的狂暴與陳念的無力感在逼仄的空間中讓人體會深刻。可以明顯觀察到,當陳念和小北在一起時,畫面多采用橫向構圖。兩人騎著摩托車在大橋上穿越、訴說夢想時并肩的背影等橫向構圖打破了垂直的壓抑,將陳念和小北之間穩定而平等的感情細膩地刻畫了出來。
影片還積極探索新的電影藝術表達形式。影片中運用了大量的人物大特寫,同時穿插著或能解釋人物心境,或能渲染氣氛的全景鏡頭。如開始段落中有許多手機對話的特寫,充斥恐怖的表情和震驚的文字,突然鏡頭切換成許多學生圍觀的全景場面。兩者交叉剪輯,交代出一件驚悚、可悲的中學生跳樓事件。又如陳念被魏萊推下了樓,在醫務室里,陳念心情十分低落,當表達對胡小蝶的愧疚時,畫面閃回到陳念和胡小蝶在搬牛奶時的場景,“她們一直在欺負我,你們為什么不做點什么?”這一巧妙處理,讓觀眾瞬間明白了胡小蝶的死因,也讓陳念形象的另一面顯露出來,形成了一種電影語言的欺騙與拆穿,彰顯劇情前后極強的戲劇張力。
(三)指示的分離與耦合
成年世界講究秩序、效率,面對這一點,以描繪爛漫的少年世界為主的影片該如何接駁?強調權力的代表,用第三視角去展現,成為了解決的濫觴。《毛坦廠的日與夜》中,監控用來檢測學生的學習情況;《嘉年華》里,監控成為小米掌握的犯罪證據;《過春天》中佩佩去花姐家拿貨,門口的攝像頭記錄下她的通關手勢。這些青春影像里,以監控為代表的符號,都象征著一種成年世界的權力,用來定義、懲罰、審判人們的行為。《少年的你》中監控和手機攝像頭也充斥銀幕,一方面如同大他者的幽靈,界定監控與被監控的權力階層。另一方面它的符號指示性又賦予了它對前者的突破能力,它們也可以訴說美好。
“指示性的符號則關系能指和指涉物(referent)之間所存在的聯系,即是說符號的存在基于能指和指涉物在某一點上的契合”⑤。影片中的符號,一方面是以其權利所指為基礎的,魏萊等人在廁所向胡小蝶扔紙團的視頻、陳念被拍下的裸體視頻、監控之下的高考場景、小北經過攝像頭時故意將臉遮擋等等,都反映出著某種強制性的話語規范、權力的凝視,為權力機制發揮作用。誰在做什么?做得對還是不對?怎樣做才是對的?攝像這一符號,激發了這些本質問題。正如同福柯對話語的解析一樣,監控和相機“賦權”“限制”以及“建構”了劇中人的生活。然而,“話語生產、傳遞并強化了權力,卻也在同時破壞并拆穿了權力,使人們看到了權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⑥。這在影片中,直接表現為陳念和小北自以為能夠利用身份、年齡的優勢和監控的盲區,互相通氣來隱瞞警察。另一方面,指示性符號因為依賴于能指和所指的關系而存在,所以,當指涉物發生變化,作為能指的監控、手機等又將發生質的改變。在影片中,當手機記錄下的罪惡成為了訴諸法律的證據,當最后小北迎面直視監控攝像頭時,社會的規訓感轉向人情化。此前的對抗性、壓抑感被消弭,監控和手機轉變為了美好的見證。影片站在了指示性符號的分離與耦合的性質中間,在獨創了獨一無二的“少年法則”的同時,承擔下了對成年世界法則的反思。國家機器的強制性與無奈感,高考制度的未來主義與現實痛處,社會學視角下的校園暴力等,盡在其中。
從人物、空間、符號三個不同角度,對《少年的你》的視覺語言進行分析,即可發現它們的共同特征,即內部存在對抗性,同時它又能合理處理好對抗雙方的粘合,營造出影片復雜的生存質感。這種生存質感又反過來作用于影片的視覺語言,使得影片在視覺風格上獨樹一幟、不落窠臼。
二、青春殘酷物語:社會凝視下的越軌亞文化
“‘亞文化’相對于‘主文化’,指僅為社會上一部分成員所接受的或為某一社會群體所特有的文化”⑦。“越軌亞文化”屬于“亞文化”,是犯罪行為產生的重要根源;它在主流社會被認為是違法的,但在越軌群體中被推崇和肯定。埃里克森在他的人格八大發展階段中鮮明地指出,青少年階段是一個“同一性對角色混亂”的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少年們不斷探求“我是誰?”,他們通過加入各種小圈子來使自己擺脫角色的不穩定。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半成熟性,有些少年走向了主流文化,而有些則很容易誤入越軌的亞文化中。
越軌亞文化群體是影片表現的主角。陳念與賣假面膜的母親共同生活,她所接受的正規教育使她無法容忍母親的違法行為,以至于她一直處于極其矛盾而又痛苦的自我斗爭之中,表露出“我不需要交朋友”這般壓抑自身、隔絕他人的心理。“壓抑是一個穩定、主動的過程,它需要自我持續地消耗能量。壓抑大量強烈的想法和沖動使自我沒有剩余能量可以運作,沒有一個強大的自我,一場維持穩定人格的戰斗將會失敗”⑧。在同學們對母親的嘲諷和侮辱、魏萊等人的挑釁和欺負、尊嚴被一點點踐踏的暴力交疊中,陳念“死的本能”即“攻擊本能”最終爆發,防御機制轉化為反抗機制,一怒之下給了魏萊致命一擊。小北的越軌行為則直接表現為他的身份——以混謀生。他從小脫離教育制度,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解決問題的手段統統訴諸暴力。在他的觀念中,“挨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挨打以后我一定會打回去”“要么被人欺負,要么欺負別人”,暴力思想和反社會性已經溶于這一人物的血液。和陳念、小北底層社會少年形象不同的是,魏萊的家庭環境優越,她從小到大獲得無數獎狀,母親對她甚感驕傲。具有反差的是,魏萊甜美乖順的外表下,掩藏著一顆冷漠、暴力、兇狠的內心。很難想象,她是有多么心理扭曲,才會邊笑邊欺凌,還將不堪的場面用手機記錄下來?但越軌亞文化很難將某一個人定罪,因為它是一套團體規范,有許多“幫手”。在影片里則表現為魏萊身邊的朋友合力將犯罪推向高潮。可如果有人要背離這一團體規范,將會受到團體內部的懲罰,這正是影片中徐渺所反映出的問題。她需要得到團體的認同,如果她不去傷害陳念,她就無法在越軌群體中立足,自己就會被魏萊她們傷害。越軌亞文化,只可能使人陷入一個無盡的深淵。
影片中展現的越軌亞文化及行為,無不反射出施加在少年身上的以家長、老師等人為代表的高度社會凝視。成年社會、主流文化,在少年們身上灌注了許多規則:希望少年們遵紀守法,希望少年們能通過高考走向成功,希望少年們如期成熟、長大等。但少年們為什么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高考可以讓人擺脫窘困的環境,但這后面付出了哪些代價?少年們犯下錯誤,但又是誰教會了他們該如何長大?這些問題,誰來負責,又是誰來買單?科恩在《亞文化的一般理論》中曾指出:“青少年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拒絕和反抗,包括越軌和犯罪行為”⑨。作為主流文化中的父文化,無論是在父親角色缺失的陳念家庭、被父親拋棄的小北家庭,還是在因為一次高考失利被父親冷暴力的魏萊這里,是不可見、不可近、不可親的“缺位”。除此之外,作為主流文化的傳播基地,學校卻以成績高低來安排位置、臨近高考而有意回避具有風險的校園暴力問題、在拍畢業照時宣揚“畢業才是人生的開始”這種錯誤的價值觀等。而在法律層面,片中警察面對陳念和小北的隱瞞、緘默無從下手,竟然得靠欺騙陳念說小北被判了死刑才能讓陳念真正承認自己的錯誤,這種行為實屬讓人無奈又失落。主流文化的權威和尊嚴被大打折扣,主文化的價值引導嚴重缺失。
以犯罪少年構建的越軌亞文化群體和主流價值觀下的社會凝視發生了矛盾,同時產生了交集。影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試著區別兩者,又試著找尋調和兩者的方式。它破碎了以往青春片的粉紅色泡泡,升華了現實,引發了探討,成為一部具有獨特深層定位的青春現實主義佳作。
三、非常罪,非常美:少年氣和暗黑系的類型話語融合
自2012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與2013年《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在內地掀起了一股青春片熱潮,往后的青春片仍然延續以“男女糾葛”和“人物成長”為重心,很少有題材的突破與創新,致使受眾審美疲勞,青春片口碑下滑。《少年的你》之所以被公認為是近年來最好的青春電影,離不開它在青春片的類型元素中堅守愛情和成長的底色,又增添了犯罪片的亮色,打破了以往觀眾固化的青春審美,迎合了電影的超類型轉變。
“《少年的你》講的是少年的沖動,是一種‘少年氣’——這是少年時期所特有的”⑩。影片中,小北的少年氣表現在他為了保護陳念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陳念的少年氣表現在就算全世界都對她不好,她依然想要去保護世界,相信美好。少年氣也是導演曾國祥個人的創作特色,他的影片多充斥著一種朝氣蓬勃的浪漫氣息,能敏銳地捕捉到青春時期少年的心理與愛恨,這正是青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這當然與導演曾國祥自身的家庭經歷、社會學背景和跨文化成長語境息息相關。影片看似是一個青春期少年因互生情愫而不顧一切的愛情故事,但它的側面卻書寫著校園暴力、犯罪命案。如果僅僅從愛情來刻畫,整部影片也就會失去厚度。
影片的另一類型維度表現為影片大段暗黑的犯罪敘述。犯罪元素的運用是港人在電影表達中難以割舍的類型情結,在《少年的你》中,犯罪元素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置合。影片共有兩條敘事線索,一條是陳念和小北的情感線索,另一條是由校園暴力問題導致的一起兇殺案件。青春片講求情感的沉浸式體驗,犯罪片則強調冒險心理、反抗姿態。兩條線索的互嵌,拓寬了影片形式與風格、情節的發展和思想的深度。風格上,影片呈現出或明或暗、時而明朗時而壓抑的特點;情節上,打破了單一的敘事,讓校園暴力的影視化不顯得過度血腥和令人不適,也讓小北和陳念之間的情感羈絆更加合理;思想上,幫助觀眾樹立一個客觀的視角,去反思由青春引申出的社會的“罪”與“美”。此外,兩種類型碰撞,又讓各自找尋到新的表達方式。青春不再落入“癌癥”“車禍”“錯過”“彌補遺憾”等的套路,青春不應只有愛情,影片用現實之筆勾勒出更多成長的疑惑和非成熟的過錯。同時,片中的犯罪經過也一反邏輯縝密的常態,如片中,無論是一開始故意制造的胡小蝶死亡謎團,還是后來魏萊之死,所有的犯罪因果觀眾其實早已心知肚明,突破了強調“抖包袱”“造懸念”的犯罪片桎梏,讓觀眾更加有代入感。青春愛情電影多了一份現實主義的厚度,犯罪片又多了一抹新鮮的活力與溫度,這種“黑色青春”的特殊景觀,加強了影片與眾不同的氣質。
每一種類型,都對應著我們生活經驗中被放大、被極端化的某一個部分。影片將我們生活中那些不可承受之輕(少年的隱忍)和不可承受之重(成長的殘酷),交織在一起,叩擊了我們心目中那段最充滿生機又最壓抑痛苦的記憶,非常“罪”,但非常美。
四、結語
生存,還是毀滅?影片最終給了一個光明的答案。片中有句臺詞,“我們生活在陰溝里,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陰溝”和“星空”這一對反義物,正是影片痛苦又美好、壓抑又充滿可能的生存質感的兩面。影片也通過書寫這種矛盾,鼓勵更多的人關注校園暴力等問題,并對那些敢于揭露犯罪行為的少年以真誠的贊揚。在法律日漸完善的今天,人們期待能夠有更大的關注度投入到少年身上,給予少年以成人的尊重。成年世界和少年世界,唯有善意而又平等的溝通,才能在根源上阻止惡之花的綻放,讓少年們平安、健康地完成他們的成人禮。
注釋:
①許南明,富瀾,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163.
②張志勇.“暴力美學”視域下的校園霸凌題材影視化創作探析——以電影《少年的你》為例[J].新聞研究導刊,2020(02):113.
③[法]馬塞爾·馬爾丹.電影語言[M].何振滏 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169.
④[美]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M].焦雄屏 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53.
⑤[美]羅伯特·艾倫.重組話語頻道——電視與當代批評理論[M].牟嶺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1.
⑥[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七版)[M].常江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162.
⑦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第四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69.
⑧[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學[M].陳會昌 譯.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4:49.
⑨陳剛.《少年的你》的社會學意義 [J].當代電影,2019(12):24.
⑩陳晨.《少年的你》剪輯師張一博:理解是這部電影的核心[J].影視制作,2020(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