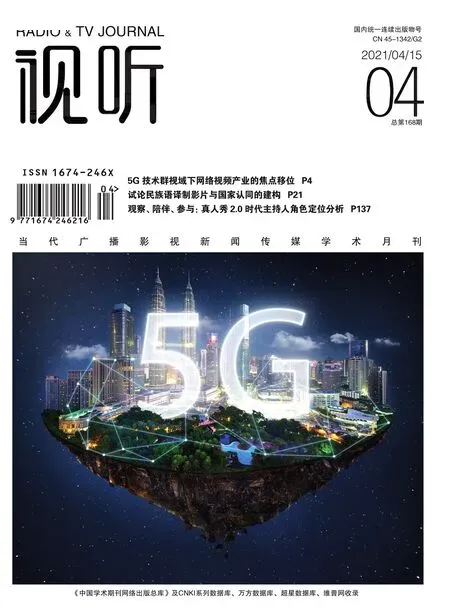青年亞文化的“去標簽化”表達
——以《脫口秀大會》為例
□ 朱晉儀
青年亞文化研究主要起源于西方國家,如芝加哥學派的“越軌理論”、伯明翰學派“風格—抵抗—收編”的研究成果等。他們都著重從階級和種族的視角出發對亞文化進行民族志考察和闡述。在長期的理論發展過程中,不同類型的亞文化被貼上了邊緣、抵抗、顛覆的標簽。雖然西方的亞文化研究范式仍能燭照現實,但其研究理論與我國所處的歷史和社會結構不同、階級參量不同,面臨的現實問題和困境也不同,因此芝加哥學派與伯明翰學派建立在階級、種族、抵抗概念上的亞文化標簽在我國并不完全適用,比如對風格的符號和階級意義的過分強調、遮蔽了亞文化歷時性個性分析、忽略了亞文化的正面價值等。伯明翰學派也認為,文化不是無中生有,它有自身所歸屬的意識形態,每一種亞文化都是一段獨特時期的表征,是對特殊情境的具體回應。可見,亞文化的標簽是不斷豐富與更新的。
一、網絡場域中的風格重構
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理論將“風格”這一概念定義為一種獨特的風格和符號系統,例如特定的衣著、言行、暗語和音樂等,是亞文化群體的“第二肌膚”和“圖騰”。赫伯迪格在《亞文化》一書中更是以“風格”作為研究的突破口,認為亞文化的顛覆意義通過“風格”得以體現:“亞文化所代表的對霸權的挑戰并不是直接由亞文化產生,更確切地說,它是間接地表現在風格之中,即符號層面”①。可見在西方研究理論中,亞文化“風格”首先是符號游戲,通過特定風格賦予群體有效性和一致性,以此聯系特定階級的特定人群,既區別于外部階級身份,也是內部文化認同的自我表述。與西方研究背景不同,網絡媒介是我國亞文化表達的主要場域,《脫口秀大會》也在新的場域中實現了風格重構。
脫口秀亞文化的“去標簽化”首先體現為“去符號化”。脫口秀沒有依托任何特定形式的符號,例如服裝、音樂、語言或表演形式來突出自我。相比于其他需要結合實物或外在視覺元素的亞文化,脫口秀要簡單得多。脫口秀舞臺僅需要一支麥克風,演員表演時的形象也與日常同構,風格更加簡單和生活化。其次,脫口秀演員和觀眾并沒有將自己圈定起來作為特定群體。以往的亞文化群體強調風格以區分“圈內人”和“圈外人”的界限,脫口秀的確將分散的個體青年聯結起來鑄造情感同盟作為“想象的共同體”而存在,但脫口秀亞文化群體在其參與性與象征性互動層面十分廣泛,卸下防御強調認同,拓寬了非主流身份青年之間聚訟紛紜的可能。最后,脫口秀亞文化集體身份通過發達的媒介力量彼此靠近和緊密依戀時,其目的并非反抗或斗爭,僅是精神層面上感性純粹的娛樂。亞文化顛覆、反叛及邊緣性的風格經網絡媒介的二度加工后被重構。
此外,《脫口秀大會》在亞文化場域發展中還融合了其他網絡亞文化——飯圈文化。節目播出期間出現了不少脫口秀演員之間的“CP粉”。CP即Coupling,源于日本同人圈,原指有戀愛關系的同人配對,現也指粉絲自行將影片角色配對,有時也泛指兩人間的親密關系,或用于搭檔組合的泛稱。脫口秀演員建國和雪琴的“雪國列車”CP、建國和呼蘭“建蘭春”CP等一時間產生了大量的追隨者。一些粉絲觀眾在看節目的同時還會將角色和真人的界限模糊,“磕CP”“粉絲向剪輯”等也成為節目人氣和熱度上升的重要因素。飯圈文化與節目的融合使得《脫口秀大會》不僅實現了吸引關注、收獲流量的娛樂意圖,也豐富了節目的可看性,提高了收視率。由此得以窺見,不同的青年亞文化群體依舊構建各自獨特的群體文化,但在滿足文化生產、消費、身份歸屬和話語表達后,也在不斷擴展自身文化范圍。網絡文化場域將出現越來越多緊密連接的亞文化之間的融合,亞文化版圖也將愈加豐富。因此,網絡場域中的脫口秀亞文化無論從認知建構還是行動表達都脫離了以往的風格特征,呈現出去符號化、打破“圈層”、融合其他亞文化形式實現跨圈流動等嶄新的“去標簽化”特性。
二、狂歡面具后的青年困境
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狂歡節是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產物,充滿了下里巴人笑罵嘲諷、追求感官愉悅的滿足。狂歡廣場上的民眾盡情謳歌、嘲諷、戲謔,放棄了高雅與低俗間的等級差異和距離。在巴赫金的狂歡理論中,“狂歡”只是人內在精神的容器與表達方式,其真正的精神內核并非顛覆而是表達。因此,同樣利用戲謔的方式,以表達為目的,追求感官愉悅的脫口秀“擬態環境”與巴赫金筆下草根階層拋棄規則和束縛,要求反抗并顛覆的“狂歡世界”達到了高度契合。
脫口秀舞臺所構建的虛擬文化場如同“狂歡廣場”為亞文化提供了話語空間,而脫口秀演員也通過“炸場王”“爆梗王”“諧音梗王”等戲謔稱號為自己“加冕”,脫口秀表演依托“狂歡”面具在“狂歡廣場”的包容之中摒棄現實語言規則和等級束縛,通過直率戲謔的語言營造爆笑氛圍,在狂歡中表達自我、宣泄情感、尋求認同。《脫口秀大會》作為狂歡化表達的代表,并不完全表現為離經叛道,除了自身的狂歡化表達之外,還具有延展性,處處體現了青年群體狂歡面具后的多重壓力和困境。
青年困境首先體現在與父輩文化的矛盾中。菲爾·科恩曾精辟地指出,“亞文化的潛在功能是表達和解決(盡管是想象式的)父輩文化中仍潛藏著的懸而未決的矛盾。父輩文化所產生的接踵而至的亞文化都可以被視為基于這一核心主題的不同變體。”《脫口秀大會》的表演中不乏對父輩文化的委婉調侃,例如“不吃早飯在我媽眼里嚴重得像違法行為”“父母眼中只有老師、律師、醫生叫職業,其他工作統稱打工”等來調侃父輩文化與當代青年思想的脫節以及青年群體在成長過程中對父輩文化的不適。學者馬中紅指出,網絡時代青年亞文化已脫離了“正面對決”和“公然抵抗”的形式,變得在規范內進行自我宣泄和滿足②。青年的不滿不再以正面沖突的形式進行,而是將其表達和訴求糅合到調侃戲謔的“狂歡”之中,以節目娛樂化的方式進行溫和“抵抗”。
狂歡的面具后還體現了這一代青年群體在面對自身社會身份時的焦慮。例如脫口秀演員龐博講到,自己看新聞時“有小學生在父母的幫助下研究攻克癌癥,而我上小學時連‘癌’字都沒有攻克下來”,調侃自己可能當不了“別人家的爸爸”,借此表達了90后面對“后浪”競爭時的巨大壓力和結婚生子焦慮。北方脫口秀演員House第一次見到南方的蟑螂又大又會飛時想告訴北方的蟑螂“你的同齡蟲正在拋棄你”,雖未直言卻借此話題將青年群體感受到的來自同齡人間的壓力掩藏在小蟲子的戲謔之中。
脫口秀表演忽略傳統正式交流中的禮儀和語言標準,在戲謔和狂歡面具的遮蔽下表達對父輩文化的抽離與反抗,以極為隱蔽的方式去釋義、共享、嘲解青年群體所面臨的共同困境,青年群體似乎也更愿將焦慮潛藏在狂歡面具后使自己處于心理舒適區。無論是處于從屬還是漸被關注的地位,脫口秀青年亞文化都隨著狂歡廣場的建構、青年群體狂歡感受的釋放而被延伸、暴露和重新“標簽化”。
三、儀式抵抗下的責任內核
伯明翰學派認為,青年亞文化的抵抗源于持續不斷的社會結構矛盾、階級問題以及相應產生的文化矛盾,青年亞文化產生于社會結構和文化之間的特別緊張點,它們反對主流、抵制主流文化,哪里有主流文化壓迫,哪里就有亞文化反抗。因此西方學派將亞文化與階級語境相聯,并給亞文化貼上了始終處于“儀式抵抗和反抗霸權”的標簽。
伴隨著脫口秀在我國的本土化發展,《脫口秀大會》作為以非主流呈現的亞文化娛樂節目并沒有發展為“抵抗”意義的公眾話語,而是在主流行為規范和文化價值的更迭中自覺承擔起了青年社會責任。《脫口秀大會》在既有的傳播語境中合理化后,青年們擁有了公開個性創作和社交表述的權力,通過內容輸出和群體認同而介入社會文化場域。雖然節目內容依然保留了亞文化為草根發言的階級意識、反叛父輩文化的世代意識和“儀式抵抗”特征,但抵抗的標簽無法掩蓋其背后的責任內核。
首先體現在亞文化青年群體的身份上。我國脫口秀演員并非是亞文化標簽中輟學、從事低收入工作,游蕩徘徊在社會邊緣的“無賴青年”,而是具備較高學歷和良好知識文化素養的青年群體,其中更是不乏北大、交大、哥大等全球頂尖高校的優秀青年,獨立的思考能力和知識儲備賦予了他們宏觀視野和更強的社會責任。他們以組織儀式化的姿態探討青年話題沒有文化差距,以青年的方式與主流文化達成共識。例如北大女生雪琴將人生的起點與終點問題類比為“回鐵嶺還是留北京”“宇宙有盡頭但北京的地鐵沒有”,深入淺出,也不彰顯優越感,即使是長期處于失語狀態的底層青年也能從中找到共鳴。
其次體現在主題內容中。從《脫口秀大會》“不就是錢嘛”“我們結婚嗎”“保持聯系保持距離”等主題中可以看出,節目內容輸出并不僅是為了娛樂和發泄情緒,脫口秀演員提及的擠地鐵、北漂、社交恐懼、身材焦慮等青年關注的共同話題恰恰是脫口秀亞文化對主流文化遺漏和缺失的補充。例如脫口秀演員們在面對青年群體間逐漸興起的“喪文化”時都以積極正向的方式引導青年群體“要改變、去面對、別逃避”,以戲謔、自嘲的態度和幽默風趣的“毒雞湯”將“喪”拋至腦后,青年的悲觀心理也因所屬群體對同一文化的分享得以釋放和消解。
可見儀式抵抗的背后,脫口秀亞文化的引導意圖大于抵抗意圖。脫口秀亞文化在主流文化的邊緣活躍生長,一方面對主流文化起到修補作用,激發主流對青年問題的重新審視和整編;另一方面又以年輕化的方式承擔起社會責任,迎合和引導青年審美趣味,不僅滿足了青年群體的“抵抗”需求,同時尊重與維護主流文化,成為一種既顛覆傳統又日新月異的青年亞文化表達。
注釋:
①[美]迪克·赫伯迪格.亞文化:風格的意義[M].陸道夫,胡疆鋒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②馬中紅.國內網絡青年亞文化研究現狀及反思[J].青年探索,2011(04):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