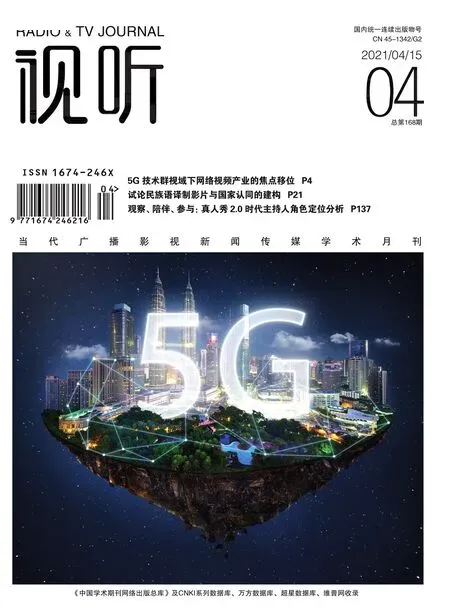詩性的虛構
——李滄東電影中的空間建構與敘事解構
□ 王晨雨
結構作者論提出了“一部電影”的概念,指的是作品系列中呈現的導演個人特征和總體風格。戴錦華認為,任何一位電影藝術家的作品序列中,都必然存在某種近乎不變的深層結構。導演的不同作品僅僅是這一深層結構的變奏形式,導演生存的時代、他所置身或參與的歷史、他的個人生活遭遇共同構成了那一文化的深層結構,并始終影響、制約著其可能的呈現方式。
一、空間建構:李氏虛構世界的外部空間與內部投射
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借由“文學景觀”為題,說明了文學世界的地理屬性,換言之,故事能形成自己的空間領域,例如《奧德賽》行旅模式建構的家園空間、《悲慘世界》建構的有意味的城市空間。作家出身的李滄東更為自覺地塑造了一個電影文學世界。他構建了一個想象空間,這里的景觀具有相似性:在社會底層艱難生活的邊緣人活動在城鄉結合的地方,他們大多性格純真且容易被社會利用,家庭關系簡單卻若即若離,在環境的打壓下感知到內心的荒涼和痛苦,周圍不時顯現的宗教力量卻如背景墻上的一枚道具,等待著主人公經過再回到起點,以此傳達對真實社會空間的思考和批判,尤其展現了外在世界的邊緣人處境、人際關系、宗教信仰、社會現實以及人物內部世界的精神危機和心靈痛苦。
(一)外部空間的架構:身份、經濟疊加的社會現實
1.邊緣群體空間
李滄東電影中的主人公身份卑微,如螻蟻般在社會底層掙扎生存。首先表現在職業上,他們處于無業的狀態,很難在社會上立足,以至于不停地作為侮辱與損害的對象。《綠魚》中,退伍即在經濟大潮中迷失的莫東投靠了黑社會,難逃被資本玩弄和抹殺的命運;《綠洲》中,輕微智障的鐘斗無法尋得一份正常的工作,只能聽之任之成為被家庭和社會驅逐的對象。其次表現在生存空間上,電影中借由狹窄空間表現主人公的處境。金永和破敗擁擠的棚屋、鐘秀與海美局促雜亂的房間,環境的惡劣預示了主人公逼仄、緊張的邊緣地位。
2.社會環境空間
受制于歷史、政治、偏見,人物在其中成為時代浮萍。出生于1954年的李滄東經歷了一個劇變時代。軍政統治的南韓經歷了政治經濟風暴,使整個社會遭受資本經濟沖擊、傳統道德解體等陣痛,而小人物恰恰是新舊交替期的犧牲品。李滄東尤其塑造了金永和這樣一個時代造勢的落魄兒,他也曾是純真樂觀的青年,卻剛好成為歷史塑造的完美受害典范,背后隱約透露出的光州事件、亞洲金融危機是李滄東想要說明的:孱弱的個體根本無力與社會大環境對抗。韓國影評人郭樹競評述道:他的墮落和自殺雖是個人選擇,可是看不見的、強逼他選擇的就是歷史。
社會偏見也插足著社會空間,性別偏見、殘疾人歧視、階層差距都肆虐在李滄東的外部空間里。性別偏見在李滄東電影世界里很常見,美愛與莫東一樣依賴資本力量謀生,莫東靠出賣體力,美愛只能出賣性資源,這是性別結構不平等的社會強加給女性的身心負擔。殘疾人歧視在《綠洲》里最見端倪,重度麻痹癥公主和智力輕障礙鐘斗結成了一對奇異的組合,他們被主流社會所排斥,活動空間十分有限,周圍人不愿意也很難理解他們。階級差距在近作《燃燒》中表現得十分外露,以鐘秀與海美為代表的底層青年與精英階層本形成了對立,本帶著精英階層的優雅,對周圍事物和他人有一種掌控感。而鐘秀與海美同屬底層,海美是推銷員,卡債附身;鐘秀是失業大學生,以打零工為生。三人的交際是一場災難:鐘秀得以窺見富人階層的上乘生活而對粗劣的自身生存感到羞愧;海美超越了生存困頓,期冀在精神上達到富足;本卻在物質高峰中感到精神空虛。
(二)內部空間的呈現:人際關系與精神世界
人物置身的宏觀世界因為過于抽象顯得不能把控,所處的人際關系網也顯得疏離冷淡。一方面表現為家庭關系的淡漠與疏遠,李燦東電影中的家庭要么處于解體邊緣,即不和諧,例如鐘斗無法融入家庭,遭到家庭隱形的驅逐;要么處于半解體狀態,即不完整,尤其是家庭成員缺失,例如沒了父親的鐘秀、海美。另一方面表現為人情淡漠,個體置于孤獨的邊緣,例如《詩》中獨自找尋著生命意義的美子。
李滄東電影里的人物受荒誕物質世界的感召,精神上異化成憤怒、孤獨、迷茫、空虛的外在。這些個體或如莫東奮斗無果般不甘、迷茫;或如金永和作為歷史人質死亡般悔恨、氣憤;或如鐘秀殺死富人般迷茫、憤怒。他們在生存夾縫里獨自舔舐內心創傷,找不到精神解救的方法,有的沉淪了,正如歷史里的金永和;有的尋求宗教的幫助,正如李申愛,但他們無疑都在悲情命運里異化成一個充滿痛苦的人。李滄東把有意識的個體和無意識的存在物體組合起來建構成統一的物質世界,這些景觀和宗教、家庭等道具元素組合在一起,超出了陪襯意義,而形成主角效應,在有意味的空間里使個體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處境更加凸顯。
二、敘事解構:親情、愛情、宗教及其個體的實際不在場
李滄東認為悲劇能夠更好地表現生活,并在談及“綠色三部曲”時提出:“我的角色是普通人,可能失去了很多東西,或碰到了厄運,可是他們擁有一種動力,期望找回他們原來失去的東西,所以我的電影里的綠色表現的就是這種動力。”這種動力對于李氏電影人物來說并不是主動萌發的,而是在偶發性事件激勵下才開始審視自己的漂泊性,從而進行艱辛的精神探根之旅,陷入到存在主義哲學中“自為存在”的精神困境,最終消失或繼續存在于荒誕世界,完成虛無主義的哲學表達。這種思考在《燃燒》里達到頂峰,意象和隱喻構建的謎題將繼續和主人公在故事里存在,處于無解狀態。對此,李滄東說:“我常常用發問的方式對敘事進行解構。不是構建敘事,而是消滅敘事構建本身。”影片一直在踐行這種價值觀,一方面是人物結局的殊途同歸,人物在物質世界潰敗卻在精神世界找到一絲希望;另一方面是流淌在主人公周圍世界的敘事要素缺席,造成了眾多實際不在場的對象。
(一)家庭敘事:親情的不在場
家庭是社會最小的組成單位,李燦東電影人物的邊緣化始于家庭空間,他們一邊身處成員解體的家庭中,某些家庭成員永遠缺席;一邊面臨情感解體,彼此隔絕。家庭成員的解體在《密陽》中最為具象。申愛先后喪親,她的家庭空間完全破碎,只剩下自己和記憶中如此真實的親情,親情變成了一種幻覺。《詩》里,一心找尋生命之詩的美子具有向上的生活態度,和孫子的二人之家平淡溫馨,卻遮掩了親情的巨大危機:其疼愛的外孫造成了被侵犯少女的死亡而不知悔改,和睦的表象下其實深藏愛的沙漠;女兒嚴重缺席,只在結尾處匆匆露面。到了近作《燃燒》,父親缺席衍變為母親的失職,底層出身的鐘秀與海美感受到的家人之愛極為貧瘠,他們的母親能想到的最懇切的話是請他們記得還債,傳統的慈母形象消失了,更凸顯出親情的涼薄。而本看似生活得更為幸福,但過于彬彬有禮的母子顯得極為不自然,暴露出矯飾后的親情面貌。當血緣僅僅成為家人共同生活的證明時,很難說實質上的親情是否存在。
(二)感情敘事:愛情的不在場
李滄東電影世界里困于生存的底層群體們,極少擁抱過愛情,資本、歷史、罪惡都敲打著愛情的脊梁驅逐它們離開:莫東與美愛的愛情在資本力量面前太過弱小而放棄了;金永和與尹順仁的愛情簡單美好卻被罪惡的歷史給作弄;美子為湊足自殺少女的補償金,答應了癱瘓會長的性要求而“敲詐”了一筆,會長的“好感”釀成了傷害。愛情或許存在過,但都消失了,或變形為一種單純寄托欲望的客體,與愛情無關。
到了鐘秀與海美的關系,愛情已經成為一個疑團。海美消失后,鐘秀常去海美的公寓喂養真假難辨的貓,幻想著照片的海美,對著窗外再無光線的高塔自慰。李滄東在訪談中表示:“自慰就是自己一個人的性愛,類似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喝酒一樣,鐘秀在想象里與美化過的海美交合,與自己的大腦進行性愛,實際上海美并不在愛情現場,也就很難說兩人到底有沒有愛情。”而鐘秀為找尋海美做出的種種偵探行為,摻雜了太多外部因素,例如與本的階級對立、尋求自身存在證據的心理、道德感的作用等,愛情也隨之成為謎底。
(三)信仰敘事:宗教的不在場
宗教已經成為李滄東電影中的特定意象,充斥在主人公的周圍。這些奮力掙扎在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物同時遭受著來自對生命意義求索不能的困惑、無助、憤怒的痛苦,親人的宗教努力遭到他們的無視,或是他們自己努力從宗教信仰中找尋精神解脫而無解。宗教沒帶來任何實質性的拯救,顯得孱弱而可疑。美愛無助時便振振有詞地祈禱,但是莫東被殺的慘烈并不能被宗教緩和半分。金永和的太太弘子是虔誠的基督徒,不僅在餐前進行感恩祈禱,還在初夜前進行祈禱,可以說是一種獻祭般的犧牲儀式。諷刺的是,感恩祈禱不僅沒有使大家生活得更加美好,反而在見證著我行我素的荒誕,乃至雙方共同背叛了性的專一,更加證明著宗教的真實不在場。
導演李滄東對宗教的態度也是十分復雜的,他多次表示自己并不是信徒,只是一個具有宗教性的人,即相信痛苦具有某種意義。在電影世界里,他一方面讓宗教元素滲入人物的日常現實生活和倫理關系,另一方面又不斷加以嘲諷和顛覆進而使宗教與現實剝離,最終指向生命存在的深刻性。《密陽》借女主人公申愛的經歷對宗教進行了凝視,申愛只想過平凡的生活,卻先后失去了丈夫、兒子,面對殘忍的世界無法自處,聽從教徒的勸告信奉了宗教,但隨之發現罪犯也借助宗教率先原諒了自己的罪過,這使申愛深受打擊,開始懷疑宗教中關于寬恕的可疑力量,并用身體對宗教展開了戲謔。
《馬太福音》第15章第14節說:“任憑他們吧,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里。”電影中流露出對諸如藥店老板這群偽劣宗教販子的嘲諷,也借此發問宗教是否真具有強大的救贖力量。有學者提出:那種近乎強迫式的傳教方式、表面上的儀式感以及功利性的期待都不是宗教的正常態勢,這也使環繞主人公的宗教行為都變得無意義,繼而變成宗教實際不在場的證明。宗教在李滄東的電影中看似難以為繼。在《燃燒》里,布拉曼族饑餓之舞啟蒙了海美的存在意識,飽受生存之苦的海美跳過了小我的憤怒企圖在大我里找到位置,但宗教的喚醒作用十分有限,舞蹈過后海美不得不回到現實世界中來,反而引來了更大的迷茫與痛苦。
(四)人物敘事:個體的不在場
李滄東電影中的邊緣小人物在社會上勉強有立錐之地存活,讓現實剝奪了他們本該單純美好的人生,依舊以入世姿態掙扎奮斗,尋求自身的存在,西西弗斯般對抗著厄運,最終卻回到原點。
《薄荷糖》里的金永和更像是歷史操盤手的一枚棋子,無法擁有人生的主動權,兵役、誤殺、警察局做事、金融危機、離婚似乎都不在金永和的控制中,只有列車把“我要回去”的呼喚帶回遠離大背景的個人歷史,才能到達那個鳥語花香的郊外下午。那時,金永和真正存在著,有著攝影家夢想,在歌唱中,為自己處在美麗世界而流淚。
《詩》更具有存在消失的意味,衣著得體時髦、面容姣好的老婦人美子平靜地生活著,然而老年癡呆癥的威脅、孫輩罪惡帶來的拉攏,都使她仿佛抽離了環境,有著人生虛無的感覺,只有從詩歌這種更加虛無的體例中尋找意義。故事的明線是寫詩,病痛和孫輩犯罪是兩條暗線。暗線首先是肉身痛苦,阿茲海默癥使美子正在遭受失憶,最終甚至將忘記自身的存在;其次是精神傷痛,疼愛的孫子參與犯罪而無悔過之心,另一方面美子還要籌備賠償金。幾個男孩的父親約美子相聚餐廳商討如何息事寧人,美子被花草吸引,走出餐廳,一面透明的落地玻璃將美子與幾個男孩的父親們隔成兩個空間,父親們所在的餐廳空間暗淡無比,美子處在燦爛明亮的陽光下,抽離了罪惡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尋詩的明線展現了美子觀察世界的視角,美子坐在石階上、足球場上、鄉下田野,想到的詩句跟鳥兒、花草、杏子、微風有關。這是一種消除個人中心化的視角,與天地萬物彼此獨立且共生著,是一種靈魂的絕對自由。從這個意義上看,個體似乎消匿了,也就是說,美子從身體到心靈正在逐漸消失。
三、結語
李滄東所建構的獨特造型空間借由邊緣底層人物、荒涼人情沙漠、孱弱宗教信仰等,既刻畫了歷史現實碾過的轍痕,又傳達出對社會制度缺陷的不滿與抗議,更以詩意的虛構世界激發存在與虛無命題的哲學思考。李滄東構建了一道被侮辱被損害的小人物在社會領域、個人場域對抗社會現實與痛苦心靈的景觀,同時解構了參與敘事的諸要素,消解了敘事構建本身,帶給我們多義性的解讀視角,對創作者和理論批評工作者具有現實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