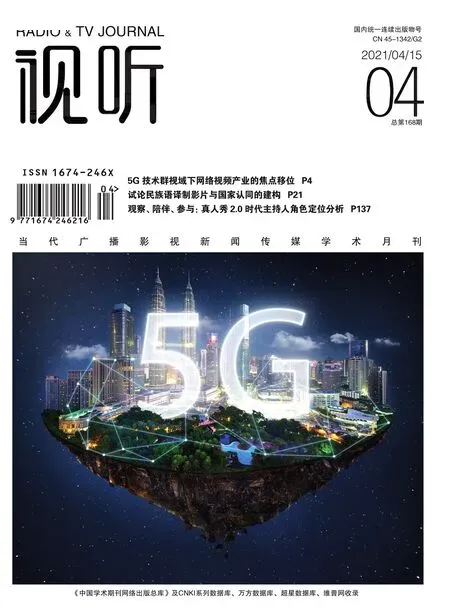社交媒體時代粉絲文化的負面效應探析
——以“肖戰粉絲事件”為例
□ 任正雨
社交媒體時代,粉絲群體在網絡空間中找到了情感的依托,他們迅速集結起來,形成聲勢浩大的規模,通過“多重”的粉絲身份尋求身份認同,并取得了豐富的文化實踐成果。社交媒體語境下的粉絲及其文化正逐漸從網絡“溢”出,以全新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現實生活與社會文化。然而,一直以來為人所詬病的“狂熱”“癡迷”等負面評價同樣表明,粉絲文化的一些消極影響不可忽略。隨著粉絲群體規模的擴張,在社交媒體的放大下,粉絲的過度非理性行為和粉絲文化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
一、社交媒體時代粉絲文化的新景觀
(一)粉絲社群結構得以重塑
1.媒介使用成為粉絲聚集的基礎
在前互聯網時代,粉絲大多還是以分散的地緣而存在,粉絲間的交互行為和信息傳播形式也較為原始。進入互聯網時代,尤其是社交媒體時代,多元化的信息發布形式以及富媒體元素促成了粉絲文化的蓬勃發展,并呈現出別樣的網絡文化景觀。社交媒體平臺在迷群的聚集和蔓延上起到了促進作用,成為迷群聚集的基礎。當前,微博成為國內粉絲規模最大、行動范圍最廣泛的社交媒體平臺,各個領域的粉絲在微博平臺上聚集,粉絲與普通受眾的空間界限變得模糊。此外,國外的社交軟件如Instagram、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也吸引了國內外大批藝人,成為大量粉絲聚集的社交平臺。
2.飯圈用語成為獨特的交流工具
粉絲社群不僅具有較為高度的組織性和權力等級的劃分,而且有其獨特的交流工具——飯圈用語,作為網絡語言的分支,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網絡平臺各個迷群的“方言系統”。飯圈語言圈層性顯著,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以病毒式的速度繁殖和擴散,并快速充斥整個網絡空間,許多網絡用語已經漸漸被主流話語體系收編。飯圈用語具有兼容并包、繁衍力強的特點,經由網友的符號解碼,可變化成多種形式,也可衍生出多種含義,在多種語境下適用。
3.群體規范保障粉絲社群運行
群體規范是指“群體成員共同遵守的已經確立的思想、評價和行為的標準”。群體規范和價值觀念是粉絲社群“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群體規范有利于約束粉絲個體的行為,保障粉絲社群有序運行。群體規范雖然不具備強制執行力,但具有較大的引導和規勸作用,群體規范在運行中往往依靠粉絲的自覺遵守和相互監督以達到最終目的。但粉絲社群規范也使粉絲個體迫于群體壓力,在行動上與社群保持高度一致。在不理性的行為上,個體害怕遭受孤立,不敢輕易發聲,從而轉向沉默和附和。
(二)非理性消費行為盛行
“文化消費主義”研究學者費斯克認為“粉絲”是“過度的讀者”,過度性是粉絲最大的特點。在消費社會中,“粉絲”帶動消費的能力尤為突出,粉絲文化正踏上商業化道路。“粉絲”購買偶像代言的商品往往不是因為其實際的應用性,而是因為通過對符號意義進行消費進而獲取偶像粉絲的身份認同,通過身份認同獲得群體歸屬感。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指出:“在消費社會的所有物品中,有一種比其他一切更美麗更具內涵的存在,那便是身體。”網絡選秀節目將偶像的身體進行編碼成為一種符號供“粉絲”消費,“粉絲”被偶像的外形所吸引,除了模仿偶像的審美標準,對虛榮生活的追求是隱藏在消費身體符號背后的本質。
(三)粉絲情緒極端化傾向
社交媒體時代,粉絲群體作為青年亞文化的主要人群,天生具有“反叛性”,在追星過程中呈現出情緒極端化傾向,尤其是當前網絡空間中的謾罵掐架、人肉搜索等網絡暴力現象屢見不鮮。社交媒體時代,網絡空間的匿名性、信息群集化和裂變式傳播,加劇了青年群體的情緒傳播。
當前,不同粉絲群體之間相互謾罵攻擊在社交媒體上十分常見,極端情況下粉絲群體情緒會波及到粉絲以外的人。如2月27日后,肖戰粉絲對CP粉的質疑作出回應,對所有的評論做無差別攻擊,甚至波及路人。粉絲文化所蘊含的情緒化表達,對粉絲文化向健康合理的方向發展產生了阻力,同時也不利于形成風朗氣清的網絡空間。
二、社交媒體時代粉絲文化的負面效應
在“肖戰粉絲事件”中,依托社交媒體平臺飯圈的高度組織化、規模化和效率化,這種粉絲群體自組織的力量也折射出了社交媒體時代粉絲文化的負面效應。“肖戰粉絲事件”是一個縮影,它所反映出來的是“飯圈”在幾年以來的諸多負面現象極端化的結果,例如對偶像幾乎是無保留的絕對崇拜,以及針對對家粉的永無止境的互相攻擊,而達到現在這樣利用外部資源來鏟除對手的程度,或許只是必然進化的一步而已。
(一)國家機器動用下的“飯圈政治化”
飯圈政治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由于媒介技術的相對不發達和媒介接近權的不易獲得,粉絲與偶像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也不頻繁。偶像更多是用來仰望的,粉絲與偶像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弱關系。社交媒體時代,資本對流量的追逐使得粉絲有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偶像不再高高在上,而是需時常與粉絲互動并努力滿足其期待,“粉絲成就偶像”的意味更加明顯。
在此基礎上,飯圈政治化的屬性逐漸凸顯,從早期有組織有紀律的嚴密分工,到逐漸激烈的斗爭,再到“假手于人”,利用國家機器、第三方平臺來對對方進行攻擊,飯圈粉絲爭論的話題在不斷豐富、擴大和上升,斗爭模式也在不斷升級,社交媒體環境隨之更加復雜,粉絲和粉絲之間可能并無實質性的利益沖突,但赤裸裸的仇恨卻已然形成。在這個過程中,粉絲“意見領袖”起到了異常重要的作用,他們在群體中呼風喚雨,既是動員者也是組織者。
在肖戰事件中,肖戰唯粉在看到《下墜》配圖時,認為偶像被女化、被侮辱,因而率先開戰。在粉絲頭領“巴南區小兔贊比”和“來碗甜粥吧”的號召和帶領下,肖戰粉絲紛紛參與到為偶像維權的行動中,不斷指責對方創作自由無度、傳播色情信息、有違道德倫理,致使外鏈網站陷入被墻風險。
(二)群體極化下的群盲行為
互聯網曾被認為是最符合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設想:互聯網的匿名性讓人們更容易表現出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人們可以更自由地溝通和交流,并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但是當文化的層次被集中,當人們涌進微博的超話和論壇,群體之間的互相影響就開始朝著不受控的方向發展。匿名性成為非理性發言的擋箭牌、自由交流變成互相攻擊、批判精神成為反對不同聲音的后盾、代表公利的討論變成維護私利的“一鍵舉報”。
通過對飯圈進行解構可以發現,粉絲群體把偶像當作自己的心理寄托,在某種程度上,粉絲群體內部是一個類似信息繭房的結構。數以千萬計的群體里,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偶像保持最好的幻想,并在群體內部一致性不斷加強的過程中,變得對其他負面信息敏感多疑,便容易滋生極化心理和群盲行為,于是各種粉絲之間的互撕行為屢見不鮮。
此次肖戰事件也是一樣,因為認為文章內容有女性化、污名化偶像的嫌疑,于是通過人肉作者、網頁舉報、打舉報電話等方式轟擊“異端群體”,有些粉絲甚至爬墻去國外網站留言,聲稱自家正主被打壓迫害,尋求海外粉絲的幫助。這些行為已經脫離法律意識的正當維權,演變為極端化的群盲行為。
(三)盲目崇拜下對流量明星的“捧殺”
這種對明星極度癡迷、用盡一切手段追求以至于失去應有的理智和常識的粉絲,也被戲稱為“腦殘粉”,他們對于偶像的著魔已經達到極端的程度,以至于所作所為都顯得歇斯底里。在他們眼里自家偶像是完美無缺的,因此任何人的負面評價都會招致粉絲的猛烈攻擊。這種行為不僅容易招致“路人”的反感,還會反噬到自家偶像身上,給偶像“招黑”。盡管粉絲群中也有理性追星的人,但由于“腦殘粉”的長期存在和影響面廣,公眾對粉絲持有的“瘋狂”“沖動”的刻板印象始終揮之不去。
肖戰的困境也是許多流量明星的困境。流量明星,顧名思義,是依靠互聯網的流量堆砌而成的明星,他們的人氣不是由自己決定,而是有賴于粉絲的支持和打榜。粉絲既可以捧紅你,給你增添流量和人氣;也隨時可以脫粉,甚至回踩,造成反噬。因此,流量明星除了時常要迎合粉絲們的情感訴求外,還要承擔起引導價值觀的責任。粉絲行為,偶像買單,部分粉絲不理智的行為最終只會反噬到流量明星身上,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三、結語
社交媒體時代為粉絲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豐沃的土壤,使粉絲文化表現出獨特的時代特征,并逐步蔓延,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現實生活。粉絲群體內部長期存在的極端情緒化、娛樂化傾向等消極因素導致的負面效應也應引起重視。娛樂化并非肆意妄為,如果一味放縱而不加以有效約束,所引發的負面影響會相當可怕,比如鼓勵語言暴力、行為失范、敗壞文化藝術等都會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身陷娛樂文化的集體狂歡中,不僅會令人迷失自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產生群體極化行為,也會不利于媒介文化的健康發展。針對這些問題,一方面應努力提高粉絲自身的文化修養和媒介素養,增強自律能力;另一方面應規范媒介行為和粉絲行為,理智追星,使粉絲文化朝著正面、積極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