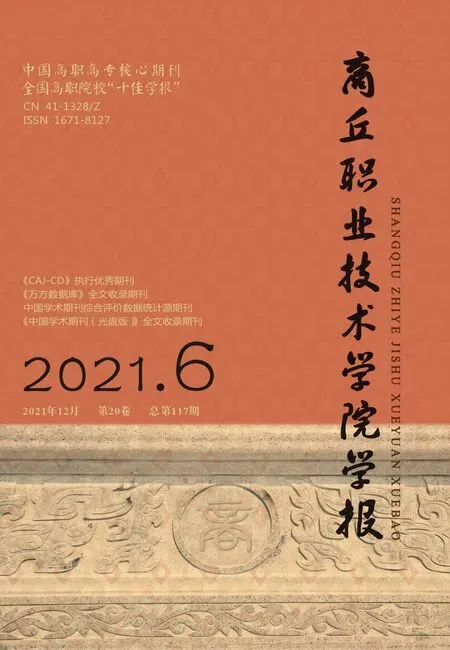從碑刻文獻看清代貴陽林木保護
陳李子祚
(貴州師范大學 歷史與政治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近年來,學界在對碑刻的整理研究過程中,對清代貴州民族地區的林業經營及管理情況進行了分析,并取得了數量較為可觀的研究成果①,部分研究還詳細探討了民族地區與林業相關的生態文化②。然而,多數研究僅限于清水江的苗、侗地區,對貴州其他區域的林業保護事業著墨不多。貴陽市保留的一部分有關森林保護的碑刻,是喀斯特地區有關林木保護的重要史料。筆者擬對貴陽地區所存錄的林業碑刻進行整理、研究,探討貴陽地區參與林木保護的主體,及林木保護對當地人的生態意義。
一、清代貴陽自然環境概述
貴陽市在清代隸屬貴陽府,今下轄南明區、云巖區、烏當區、花溪區、觀山湖區、白云區、開陽縣、修文縣以及息烽縣等區縣。貴陽位于貴州省中部,受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影響,雨量充沛[1]240,其境內多山,史載其“復嶺環列,四塞崇崗”,山地眾多,氣候垂直差異明顯,當地雨熱條件十分鮮明,“冬不祁寒,夏無盛暑,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暖,夏則晝熱夜涼”[2]17,適宜多種林木資源的生長。乾隆《貴州通志》載貴陽所種林木分別有松、柏、柳、椿、槐、楓、烏桕、梧桐、棕櫚和冬青等[2]285。有學者注意到,明清初期由于國家用木、貴州山地經濟的開發和城市建設的需要,貴陽林木資源種類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經濟林的種類和種植范圍有所增加[3]。同時,特殊的地質與氣候條件造就了貴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貴陽則屬于喀斯特山區城市③。但是,喀斯特地貌下的生態環境顯得較為敏感和脆弱。由于喀斯特地貌所含有的碳酸鹽巖廣布,使得土壤層較薄,在山地條件下,包括降落的地表雨水在內的地表徑流很容易滲透入地下,導致地表保水能力較差,而過分的經濟開發會造成山區林木減少,植被的破壞進一步削弱本地區地表水土涵養能力,嚴重制約地區農業生產。歷史上,貴州就存在“黔田多石,土多瘠而舟楫不通”“地埆不可耕”的現象。在喀斯特地貌以及人類不合理開發的影響下,地表難以保持水土,巖石裸露,從而呈現出荒漠化景觀[4]。清政府針對“黔中無地非山,盡可儲種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種,以致樹木稀少”的弊病,于是下令貴州全省廣栽樹木。乾隆五年(1740),張廣泗上奏,議“令民各視土宜,逐年栽植”,數量自每戶數十株到數百株不等,對多行栽種者予以獎勵,令百姓留心看護,還規定保護不力的懲罰措施,若牲畜“肆行放縱,致傷種植”,以及“秋深燒山,不將四圍草萊剪除,以致延燒者,均令照數追賠”[5]22-23。在政府的支持下,貴陽地區的林木資源更加豐富。道光《貴陽府志》載,當地林木除原有的松、柏、柳、冬青等木種外,尚有杉、檉、白楊、黃楊、櫸、樗、漆、橡、楮、榆、榔樹、糯米樹、楠、梓、楸、泡木桐、銅錢樹等林木種類[6],其中一些林木作為手工業產品的原材料,與貴陽的山林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3]。同時,貴陽的天然林木景觀得到存護,例如,翠屏山“林木蔥菁,百鳥啾唧”,東山“石壁峻峭,萬木擁護”,南岳山“古柏虬松,窅然深秀”[7]。經過近百年的林木栽植、保護歷程,貴陽森林資源得到了較大的維護。應注意到,盡管適宜的雨熱條件為大批的林木生長提供條件,但是敏感的生態環境也使林木保護格外重要。
二、碑刻中的林木保護類型
(一)寺院林木的保護
前文所論及的東山、南岳山等山,為佛門寺院之山場,其林木得到了很好的保育。而有關寺院山林保護的資料,可見黔靈山的兩通“護法”碑。兩通“護法”碑記載了乾隆后期弘福寺住持向官府稟求禁采山中林木以保風水之事。因碑文內容大體一致,故節錄其中一通“護法”碑的第二段碑文以示事情之面目。碑文如下:
貴州貴陽府貴筑縣正堂加五級記錄六次董:抄奉欽命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五級記錄十五次汪:為嚴禁砍伐竹木,以培山林事:
照得省城北門外有黔靈山,為會垣之屏障,風水攸關。康熙初年,前撫部院曹相其形勢,乃捐金建寺,供奉諸佛。山既高爽,寺頗幽靜,實為省會第一禪林。乾隆五年,藩司陳以山場寬展,界址廣闊,諭令住持僧偏種竹木杉松數萬株,以覆蔭寺宇而壯觀瞻,并禁附近居民樵采。嗣是數十年來,竹木成林,郁蔥在望,頗為巨觀。
但距城太近,地方官間或因公伐取一二株應用,并無大害。乃差役等借稱公用,肆意砍伐。而附近奸民,因而效尤,十數年來,操斧斤入山者,殆無虛歲。若不嚴行禁止,則千章萬個,向之蔥然深秀者,轉盼間化為童山,省城風水,漸恐凋傷,不得不明切示禁。
茲據住持僧圓奇稟請禁示前來,除行貴陽府貴筑縣加意保護,并一體嚴行禁止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住持山僧及軍民差役人等知悉,嗣后山內一切竹木,務須任其長養,勿得作踐砍伐。倘有差役等謊稱官用及奸民等公然砍取,并游人等順便攀折,立許寺僧扭稟地方官,先行枷號山前示眾,從重究辦。
若不肖僧人勾通串合貨賣取錢,一經訪聞或別經發覺,均按律重究。本司言出法隨,無稍寬貸,各宜稟遵勿違。特示,右諭通知。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九日示
告示 實貼山門曉諭[8]127-128
黔靈山在被確立為貴陽佛教名山之前,還是“荒煙野樹,人跡罕至,固虎豹之宅,而狐貍之居”,即尚未被大規模開發的原始山林。據《黔靈山志》記載,康熙十一年(1672),赤松和尚來此地“結草為蓬,植樹開徑”,修建佛寺,招徒授法,遂漸成一大事業[9]48。碑文所言“黔靈山,為會垣之屏障,風水攸關”,得到時任巡撫曹申吉的認同,以為“此山關系通省龍脈”。乾隆五年(1740),“藩司陳以山場寬展,界址廣闊,諭令住持僧偏種竹木杉松數萬株,以覆蔭寺宇而壯觀瞻,并禁附近居民樵采”。時任貴州布政使陳德榮鼓勵貴州民人栽種樹木,于省外購買松、杉木種,并在貴陽主要山地進行人工造林。嘉慶《重修南岳山碑記》曾記錄類似的造林行動:“乾隆年間,藩憲陳委員往江西買松、杉三萬余株栽于此山……蓄護成林。”[1]240《清實錄》亦有記載:“省之上舊無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樹六萬株于城外各山。”[5]24此后數十年間,山中僧人均栽護樹木,使得黔靈山中的林木生長“頗為巨觀”。
另一通“護法”碑則闡述了山林養護和人類活動之間的矛盾。碑文載:“至乾隆三十□年,經前臬憲高修理神廟,發票差役赴山砍樹,不惟不發價□值,且有飯食、繩索之需。自此端一開,培植風水之山,即為公事動用之山。”[8]126或為地方官員用作他途,或有差役借故砍取,或有民人另行偷采,特別是乾隆年間,杉木的人工栽植,成為當地人砍伐的契機。這些行為都對黔靈山上的林木造成了破壞。鑒于此,黔靈山僧人請求官府出面,禁止因官府公事需要而在黔靈山采辦木植,禁止居民寺僧私砍盜賣。經過官府的干預,黔靈山林木保護得到了地方條例的保障。
無論是“樺檜陰森,六月不受暑”的東山,及“巨木數根”的獅子山,還是“攢木千章,圍繞如幄”的黔靈山,皆以保護“風水”為名而得養護山中森林。
(二)民間村寨對林木的保護
從現存碑刻的記載來看,少數民族村寨或出于對祖□□先墓地風水維護的考量,多通過鄉規民約的形式來保護林木。如高坡杉木寨嘉慶十六年(1811)《龍村鎖鑰》碑記錄當地苗族羅姓族人的喪葬習俗[9]95-96。碑文曰:
蓋聞山川秀,乃天地生成;人丁發,沾祖宗德行。但此墳塋,自古遺留,迄今億萬余年。惟恐有人不認宗族,廣錢營利,剖腹藏珠之際,合寨傳齊公議:初攬(?)捐銀,鳩工好師,誠固封鎖,口口佳城。伏愿遺骸與金玉同堅,冥福與丘山并厚。伏維萬生,永鎮斯土,厚德無疆,功崇萬古。今辟新阡,山環水聚。敢竭微忱,潔修榆稀,嘗蒸簋簋,禱祀口先,無驚無怒,底眾先靈(?)。孔寧□固,千秋永安。而我眾殊臻,千村萬聚,至今四圍永鎖。儆戒后人,次再無欺無藏,自始至終而興于世。佑啟后人,蘭桂騰芳。耄耋期頤之久,
自古迄今瞻仰。萬古不磨,而眾等口口佐為序。告曰:從今已(以)后不許誰人再伐再賣,如有不遵者,眾問皂祭,封山通知。謹告。
(以下省平寨、杉木寨羅姓諸人)
眾名通計六十七房,齊全協力,合行建記。
信士羅文魁助筆
嘉慶十六年歲次,八月上浣日二寨同頓恭立戒禁
有學者指出,碑中的羅姓宗族栽植、保護風水林的行為體現其傳統的祖先崇拜和民族風水信仰[10]。通過全族共立規約以栽植林木,既是出于宗族利益的需要,客觀上也保持了當地山林的環境。苗族的一些盛大活動秩序規范中,也包含了保護林木的準則。“跳場”是苗族青年男女交際、互通媒妁的重要活動。《黔南識略》中有苗族“孟春合男女于野,謂之跳月。擇平壤為月場,以冬春樹一本植于地上,綴以野花,名曰花樹。男女皆艷服,吹蘆笙踏歌跳舞,繞樹三匝,名曰跳花。跳畢,女視所歡,或巾或帶與之相易,謂之換帶,然后通媒妁”[11]的記載。道光二十七年(1847)“蒼坡苗族跳場”碑重新確定了跳場活動的秩序,“定期于是月(即正月)十三、四、五等日為止”,制定對違規行為的處罰措施,若有惡徒砍伐樹木,“估割青山”,一經拿獲,“傳齊在約之人,罰銀三兩入公”[9]98。今烏當金華鄉下鋪村所立的咸豐元年(1851)“禁止碑”,論述對其所居村寨風水進行保護的必要性,“凡我同堡(鋪)之人自祖來黔住此數百年,四面山坡乃是我堡風水,理應培補”,并開列禁條:“涼亭內不準挖泥,小山坡不準開石挖泥,割柴葉、茨草;貴州坡不準開石挖泥;大石坡及敲邦候不準開石挖泥、看牛,割柴葉、茨草……,若有不從者,罰銀四兩六錢。”[12]45
在布依族聚居的村寨中,不乏對林木保護的關注。白云區大林村光緒十九年(1893)“護林”碑中記載了趙氏族人為培植風水,禁伐山林之事:
蓋聞顯富榮貴,皆由地脈而發生,地靈人杰,實由水秀山清,思吾寨居數百余載,前后左右護蓄樹木繁多。后世分蓄各房,砍伐太多,因事族人畜不寧,其闕甚大,恐有傷于風水,故祖父輩則能行修碑記禁止。自昔之后,各管各業,不謂今古,仍再砍出賣,眾族聞之,不忍砍伐損傷,恐畏風水有陋,人畜被闕。至今所有后山香樟二株,系趙德茲之項,已今(經)出賣在外,眾族恐別人砍伐有傷,故特將高祖萬友墳會銀,損下伍兩伍錢與德茲買蓄,永遠培植風水,因此謫議,若不造立碑記,恐后眾族子孫無知,亂行砍伐出賣,特造此碑,以諭后代,其他竹山,系是德茲子孫管業,日后不得以地爭樹。眾族亦不得以樹占山,水秀山清,地靈人杰,顯富榮貴,由茲出焉。謂非吾族子孫,永遠厚幸也夫。
大清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眾等公立[13]
由碑文可知,趙氏祖先所居之地先因護蓄有方,使得“樹木繁多”,后因分家析產,族人沒能延續護蓄之風,以致“砍伐太多”,甚至由于宗族成員“各管各業”,而往昔山中林木,不論古今,俱被砍伐出賣。出于對傷害風水的擔憂以及造福后代的心理需要,趙氏宗族支持趙德茲一支經營風水林,并立下此碑以示后世子孫。
今南明區云關鄉木頭村布依寨所立的光緒十四年(1888)鄉規碑,記錄了官府允準當地寨民立定規約,以杜絕“不法之徒,或偷盜,或□火燒山,藉泄私念(忿)”,或“外來乞丐,欺壓鄉里”之危害。其中,分別針對“偷盜竹木,盜竊菜蔬者”的兩項鄉規中記載:無論是否本堡之人,一律按照原物價值十倍罰之;遇有放火燒坡,查出縱火者,以十兩銀罰之[12]46-47。在今花溪區布依族鄉竹林寨所保留的一通大概是嘉慶二十四年(1819)的封山育林碑,主要內容為培育當地風水,不得上山砍伐,違者罰銀數兩[14]。
此外,貴陽的其他民族村寨也存在類似的禁開山林、保護樹木的規約,如湖潮鄉元方村的一通禁約碑中便記有“禁山林竹木草廠園坎,若有亂坎(砍)一根拿獲三兩戒眾”④。黨武鎮翁崗村的《永垂不朽》碑中有禁止放火燒山,若有違反則罰銀二兩④的記載。黔陶鄉騎龍村的《有言奉告騎龍寨公議鄉規碑》則規定:“一議大池□長天元小寨巖馬□嶺及廟山,不準砍伐討嫩□,如有貪者□;一議放火燒山□□銀一錢罰銀三錢,作封山之□□□□□□□□;一議砍大樹松崽扳□銀一錢罰銀一錢。”④
碑刻中所記載的貴陽村寨的林木保護,通常涉及該村寨或寨中某個宗族的切身利益,林木保護的輻射范圍并不如在官府命令影響下的同類行動廣,卻能深刻反映該地村民在林木保護過程中所體現的生態意識。
三、清代貴陽林木保護的特點
(一)林木保護主要目的在于培護風水
前引碑刻記載了不同主體參與的林木保護行為,以民間村寨的林木培育為主,并且多數碑刻都反映出某村或者某一宗族為培護風水而護育山林。
傳統風水觀念認為,“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山脈、河流走向以及風的來勢等因素都決定了居住地和墓葬之“氣”的好壞。為使“氣”不散,人們在選擇居住地或者葬地時通常遵循“得水為上,藏風次之”的原則,即要有良好的山水環境。一般而言,良好的自然環境有著豐富的植被山林資源,即“土高水深,郁草茂林”。在挑選葬地時,“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為地之美。所謂童山、埆頑、土脈枯槁,無發生沖和之氣,故不可葬[15]”。荒山曝石,林木不生,不能藏風,而不足以聚生氣。石漠化現象出現的地區,不符合傳統風水觀對地利的要求。對于民族地區而言,祖先墓葬周圍栽植林木,作遮風避雨之用,以保祖先之安息,造福于后世[10]。在某人看來,若其祖先墳山遇采伐林木而壞風水一事,便輕易招致禍端。道光八年(1828)“奉縣禁止”碑中便記載劉品中看護墳山,擔心有傷風水而反對開窯采煤,請求官府調停一事。大林村趙氏護林碑中有“顯富榮貴,皆由地脈而發生,地靈人杰,實由水秀山清”的記載。在村民所信仰的風水體系中,他們相信“山環水抱”的狀態,即當地安定、健康的自然環境,能夠哺育當地人的身體和心靈,給予其宗族“陰福”。因此,需要于“后山”栽培風水林,保佑宗族興旺,并鞏固宗族成員之間的聯系。在傳統風水觀念的影響下,關系“省城龍脈”的黔靈山,其林木保護得到了官府的肯定。寺院和民間對山林的保護,其目的都是為了培護風水,以期平安。風水的重要性在于,無論地方政府的法令還是碑刻形式的鄉規民約,都對濫砍濫伐山中林木、破壞風水的行為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二)純樸的生態認知觀念
前文所用碑刻記載的林木保護行為,突顯了風水觀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漢、苗和布依等民族通過封山育林等形式保護本村本族之風水,并希冀通過對風水林的栽護,得到祖先的庇佑。今花溪黨武鎮當陽村中所存《篤意栽培》碑可茲參考。
天下之山祭,源于昆侖,分支于寰宇,遐陬僻壤,無非此一脈之錯□村落。龍蟠鳳落而水帶山襟亦鐘靈焉。大寨后山一座,縱橫里許,東至本寨屋,李姓買黨姓山腳土,南至大路,北至場上店。屋后自來竹木暢茂,因之人土登賢書,此以知后山為風水所關也。自乾隆三十五年,不法之輩砍伐,寨迎神踏勘護蓄。至五十二年奸徒又起,縱火而焚,估占開挖,眾等控,奉恩批斷,伊出銀封護,永不容敗壞風水。閱數年,惡又猖獗復行砍伐,姓又迎神踏勘,總不能制彼婪心,寨內小人輩遂借口成貪,竟爭霸種更余地矣。漸至圳土,啟石何異,敲骨吸髓,邇來寨內豐歉不一,貧富不齊,無風水之敗于此山也。眾姓慘目傷心,復于是年公議迎神再勘本寨后,除場上屋后,俱入后山內,當場不準曬谷,栽石為界,安頭察護勒石為銘永侵占等情,倘有不遵,盜取木石草芥開挖者,一經拿獲,公同送官究治。指及私嚼隱忍,亦同送究,頭人眾姓臨事退避及唆揆侵占者,罰銀十兩,山口空地公議為井泉,龍王廟地。
又本寨于嘉慶十三年買意事
公田五坵小土兩塊只許安佃毋窯□種均次至□□
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孟春月下浣□□□□重修三門神坐………④
后山為風水重地,其林木茂盛,在當地人看來,宗族事業的成功正有賴于后山的保護和風水林的栽培。乾隆至嘉慶年間,不法之徒對后山林木的采伐以及亂墾田土敗壞了地方風水。人們認為,這樣的行為導致村寨的歉收和貧窮,于是訂立規約,禁止破壞后山重地。
王利華指出,幅員遼闊的中國,生態環境和民族文化多元一體,各地區、各民族人民在與自然交往的漫長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生態觀念和價值體系。他將以漢族社會為主的傳統中國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方式劃分為實用理性、神話宗教、道德倫理和詩性審美等四類。在王利華看來,從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乃至一草一木,于古人而言都具有神性和靈性,并對其日常生活施加影響[16]。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借由風水觀念,將其所居之山林河流,看作是地方神靈。不尊重后山生態環境的開發行為會給宗族乃至村寨招來災禍,災禍的表現形式或為糧食作物的歉收,或為人丁的衰落。一些少數民族將某些特定種類的樹視作本族本村的生命象征。例如,在苗族的神話傳說中,“楓香”(或作楓樹)就被看作是孕育始祖生命的神樹,同人一樣具有生命,栽種楓樹可保本族本村的平安與人丁興旺[17]。苗族百姓在祖先墳墓邊栽種林木,以保衛祖先葬地不受風雨的侵襲,并且通過長期的蓄養樹木,逐漸衍生出純樸的生態觀念,并潛移默化地使人們產生自覺保護當地生態的行動。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山林的保護也是對生命的關懷。而關于風水林的碑刻禁約一定程度上則成為人們保護區域生態環境的共同準則。此外,人們又將捍衛祖先后山、葬地風水林的行為,視為有利于后人的祈福行為,該行為實際上又體現出了人們在認知生態環境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倫理性,所以,碑刻中的禁約常常是宗族或整寨甚至聯寨共同締結的,這些禁約傳之后世,起到了教育、警示宗族、村寨成員的作用。
總而言之,人們對林木的保護多受到風水觀念的影響,在對涉及宗族、村寨利益的林木保護中將一些林木、山河看作是具有生命意義的象征,對林木的保護即是對生命的關懷,這催生了純樸的生態保護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人們為維護風水而栽蓄林木的行為,逐漸演變成了對環境保護的自覺活動,客觀上促進了區域生態的良性發展。
四、結語
清代碑刻中有關貴陽各地區林木保護的內容,少數涉及寺院山林,大多數都反映了貴陽民間鄉村及民族區域的培育風水林活動。人們所開展的栽蓄、保護林木的行動,并不具備今天自覺的生態意識與環境保護的主動性。但是,在風水觀的影響下,漢、苗、布依各民族無論是出于對山河林木等自然環境的敬畏,還是出于對祖先的崇拜和信仰,都已具備較為原始的生態認知和意識,并在客觀上使栽蓄風水林的行為成為改善喀斯特區域環境的有利助推力。一方面,碑刻作為一種重要史料,值得繼續深入發掘與利用。另一方面,碑刻中為保護林木而由鄉村、宗族自行締結的禁約,起到了教育和規訓的作用,幫助我們了解清代人們眼中的生態觀,尊重并理解鄉村社會在環境保護中的角色及其蘊藏的民族文化內涵。正如有學者指出,喀斯特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為其適應生態環境提供重要資源[18]。對貴陽林木保護碑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借助民族智慧,進一步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注 釋:
① 張應強:《從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馬國君:《清代貴州梵凈山有關生態保護碑刻資料四則》,《西南古籍研究》2006年(刊期不詳);王會湘:《從“清浪碑”刻看清代清水江木業“爭江案”》,《貴州文史叢刊》2008年第4期;吳大旬,王紅信:《從有關碑文資料看清代貴州的林業管理》,《貴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張應強:《區域開發與清水江下游村落社會結構:以〈永定江規〉碑的討論為中心》,《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09年第3期;李波,姜明:《從碑銘看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社會規約》,《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3年第2期;李鵬飛:《清水江流域林業生態保護中的獎懲機制:以林業碑刻為研究文本》,《農業考古》2014年第6期;李斌,吳才茂:《“養命之源”:清代清水江流域的當江與爭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許南海:《貴州民間的生態意識:以鄉規民約碑刻為例》,《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4年第4期;嚴奇巖:《清水江流域碑刻林業碑刻的生態保護功能》,《鄱陽湖學刊》2019年第5期;劉榮昆:《清代黔西南地區涉林碑刻的生態文化解析》,《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嚴奇巖:《清水江流域林業碑刻的生態文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頁。
③ 李興中:《貴陽城市喀斯特環境及其治理保護》,《中國巖溶》1988年第4期;聶躍平:《貴陽城市喀斯特環境變化特征》,《貴州地質》1992年第4期;高紅艷,刁承泰:《試論喀斯特地貌對城市發展建設的影響:以喀斯特山區城市貴陽為例》,《中國巖溶》2010年第1期。
④ 趙興鵬:《區域社會史視野下花溪清代碑刻調查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貴州民族大學,2017年,第110-111、113、127-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