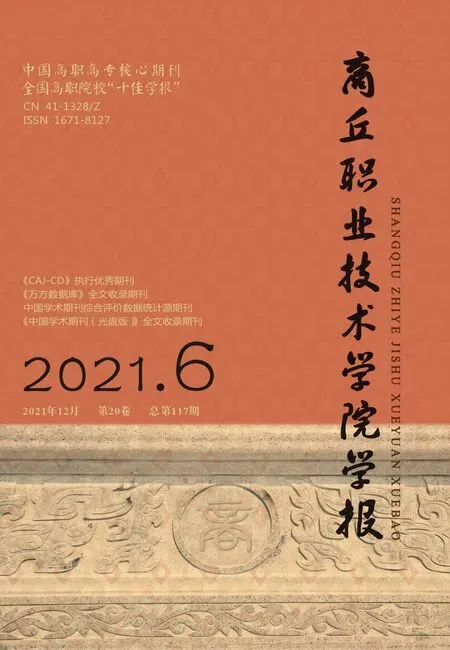大變局時代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及策略
李征宇
(商丘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河南 商丘 476000)
在2017年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放眼全球,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誠然,縱觀近百年以來的世界發展,全人類在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苦難,走出冷戰格局下核戰爭的恐怖陰影后,又陷入“美式治天下”一家獨大的霸權時代。強權支配下的世界秩序激化了新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直接催生了新的全球治理亂局,致使多年來全球局部沖突不斷,戰事頻發,而每場沖突的背后都能看到美國的身影。時至今日,美國的綜合國力、影響力已經顯現出了下降趨勢,這一點從其消極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態度就可見一斑;反觀由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卻表現出了強大的活力,國際影響力顯著提高。同時,半個多世紀的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也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群體崛起”。在這關鍵的時間節點,整個世界已經由原來的“一極多超”的模式向著百花齊放的格局轉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然而,在這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政治、經濟、生態、文化、安全等領域又凸現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面對這些新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適時地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解決思路,為如何解答這些新的問題提供了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方案。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意義
在應對當前風云變幻、復雜莫測的全世界治理困局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在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要“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這也是中國為當前世界各國解決所面臨的不同難題而提供的一項具有“普適性、有效性、系統性”的中國特色解決方案。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創新性理論,其實質是對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繼承,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必然的發展,更是對馬克思主義強調的解放全人類這一終極目標的追求和深層次的貫徹。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政治層面的現實意義
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指通過某種有效的途徑在人類社會中建立起一種平等、互利、共贏、合作發展的良好關系。共同體,可類比自然界的共生關系,即兩種或多種生物之間形成一種密切互利的合作關系,其中一方為另一方的生存發展提供幫助,同時也能獲取對方提供的幫助,它們之間互相依賴,彼此間互利。而在人類社會中要形成這樣的“共同體”模式,必須以平等互信為基本前提,而這個前提正是構建這種良好發展模式的有效途徑。對于人類社會,這樣的“共同體”的形成,也就完成了不同個人、不同國家間的意志的趨同與統一,而馬克思指出,個體只有存在于共同體中,其才能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2]。該含義擴展至國家層面,就是國家的自由而全面地發展也要置身于由不同國家構成的共同體中。政治互信是建立起國家間良好關系的基石,更是促進兩國經貿合作與安全的必要條件。那么如何才能找到建立這種互信的政治關系,從而構建國家間的命運共同體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與國之間要“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3],只有這樣,國與國在交往中才能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而建立起有效的政治互信。現在出現的許多解決全球問題的方案收效之所以甚微,就是因為他們出發點不是平等,不是對話,而往往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外加軍事、經濟手段脅迫,以一種對抗的態勢來解決矛盾,最后只能將矛盾激化。比如巴以沖突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所謂的盟國為獲取更大的利益,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來制訂解決方案的。因此,要解決這些難題 ,必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式,使國家間協商對話、結伴前行,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互信關系。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經濟層面的現實意義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們這顆藍色的星球日漸演變成為一個全人類生存的村落,全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4],這一點在經濟領域體現得最為突出。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2008年,一場起源自大洋彼岸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席卷全球,這場次貸危機也使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就業壓力增加。近年來,在全球金融危機余溫未消的大環境下,個別發達國家以保護本國利益之名,設置貿易壁壘,大行貿易保護之實,全球自貿體系受到嚴重挑戰,如此一來,大量依靠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發展中國家,就無法從國際合作分工體系中獲取原本應用的紅利,進而使國際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由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質就是要突破當前國際貿易所面臨的困局,為全人類繪制一幅開放、包容、普惠、平等、共贏的發展藍圖。唯有如此,當南北各國在經貿合作中都秉持共贏的準則時,才有將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貧富差距逐漸縮小的可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濟實質就是一個經濟共同發展的集合體,共同體內部是一種共同發展的模式而非單個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指各成員國間形成共同發展的信念,以一種共同前進的發展模式代替單獨發展,促使全球各國能夠在形成共同體的過程中逐漸走上包容、平等、互惠、共贏的發展之路。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文化層面的現實意義
文化作為文明的載體,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折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是,要尊重不同文明,文明沒有高低之分,包容文明差異,積極開展文明交流消除隔閡,實現文明多樣性的長期共存。隨著冷戰鐵幕的揭去,全球兩極爭霸格局的消亡,長期積存在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隨著外界約束的消失而逐漸顯現出來。20世紀90年代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①,不僅沒能解決全球治理亂局的現狀,反而導致了更多新的以“文明”為幌子掩飾下的沖突的出現,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是這種“文化沖突”論調在本質上是要以“文明差異”代替“意識形態差異”,將文明作為新的分裂世界的新戰線。因此,這一方案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它只是用偷換概念的伎倆將歷史的車輪向回推——割裂世界。與西方所推崇的“文明沖突論”所不同的是由不同文明背景的世界各國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各種不同的文化互相尊重、彼此交融、共同發展,進而使不同的文明長期和平相處,實現和而不同,并能引導它們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從而為整個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提供巨大推動力。從本質上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兼容并包的整體,它是建立在成員國之間相互平等、尊重彼此、互利發展的基礎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呈現出的豐富多彩、百家爭鳴的文化現象,是其基本特征的反映。
(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生態環境層面的現實意義
生態環境作為全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放眼全球化時代背景的當下,某一局部區域的生態環境問題,往往會引發全球反應——海洋污染、大氣污染、臭氧層空洞、厄爾尼諾現象、不可控的森林大火、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等,這些無不直接影響到全球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如今,環境問題不僅影響到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比如反復出現的極端天氣、自然災害、全球升溫等),還會成為引起國家間的矛盾、沖突的導火索,環境問題甚至已經超越了自身的屬性,日益成為一種政治問題。比如發生于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不僅使鄰國人民恐慌,還引發一系列外交風波。從馬克思的“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共同體”[5]的觀點來看,無論從人的層面還是國家的層面來思考,構筑一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能夠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生態系統,是全人類得以持續發展的基石,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追求和倡導的。
(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安全層面的現實意義
從馬克思關于共同體的論述來看,安全是共同體存在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安全作為保障,共同體是無法形成并成長的。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要構建一種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內部環境,唯有如此才能發展。這就要求共同體內部的各個成員間要實現政治互信進而上升為一種彼此間安全互信的態勢,如此,在形成一個和諧團結的共同體后,其也能為共同體內的各成員提供安全的屏障。約瑟夫認為:“國與國之間在安全領域的良性互動,會使彼此間形成一種緊密聯系的互為依靠的關系。”[6]當前,世界各國間的聯系與日俱增,已經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的模式,在這種大背景下各國間在本質上其實已日漸聯結成了一種共同命運體的結構體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象在國家之間已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如今,已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以一己之力構建起全球安全框架,如何實現全球安全已成為一個突出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難題,只能構建起一個以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為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一旦這樣的共同體形成,各成員之間方能體會到共同體所帶來的安全保障以及和平穩定發展環境所帶來的紅利享受,彼此之間就會有將共同體維護好的主觀意愿,而要實現共同體的長期穩定,共同體內部就必須要形成一種安全的環境,如此也就化解了當前所面臨的“安全困境”這一難題。如果能在全人類社會建立起這一共同體,即實現了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那么全球的安全問題就可迎刃而解。所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全球安全難題的根本途徑。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策略
雖然這是個整體相對穩定、大國間基本和平相處的時代,但全人類仍面臨著許多懸而未決的困局——局部地區局勢緊張、沖突不斷;冷戰思維、強權政治仍然影響著全球頭號強國的政治思維;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讓原本就復蘇緩慢的全球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傳統安全問題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背景下,非傳統安全已然粉墨登場,跨國犯罪日益猖獗、網絡安全頻遭威脅、公共衛生事件頻發;失敗的治理策略,尤其是西方世界日益顯現的亂局,已經使世界開始對“華盛頓共識”[7]的信心日漸喪失,一系列的混亂使得尋求一種更平等、更包容、更公平、更有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想法變得更加迫切,這種全新的模式就是全人類命運共同體模式,唯有不斷向著此模式發展,全球問題才能得到有效解決,全人類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在國際政治關系中,構建新時代的新型國際關系體系
回望歷史不難發現,以往國與國之間往往都是訴諸戰爭來解決爭端。戰爭和武力沖突不僅沒有解決爭端,反而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磨難,而且伴隨科學技術的發展,新的具有更大殺傷力的武器不斷出現,現代戰爭幾乎給交戰國帶來毀滅性的創傷,尤其是核武器的使用,將會導致全球的災難。因此,在如此背景下,構架起新型的國際關系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問題。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間要不斷深化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問題和挑戰,發揮大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正向積極作用,抵制歧視、對抗、封鎖,倡導平等、對話、合作。國家間要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價值取向,秉持一種開放、包容的精神,從而實現交流互鑒、創新進步。國家間有必要經常性開展一些高層次的交往和政治對話,加深對彼此的了解,逐漸形成一種全面、多層次、寬領域的對話合作格局,構建起一種通過對話合作來解決國家間爭端的機制,當這種機制逐漸顯示其優越性后,將會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國與國之間的權力爭端不僅可以在這種新型的國際關系中通過對話和交流的方式來淡化,還可以促進區域穩定、經濟發展,進而使它們能夠主動參與構建并維護這種新型國際關系的活動中來,最終,使得各國間整合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體系。因此,構建起一種可以使各國間能夠彼此維護和相互依存的新型國際關系體系,為各國提供一個可以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獲益的開放平臺,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
(二)在經貿交往中,形成能夠維護彼此共同利益的思維模式
以往的傳統國家利益思想是狹隘且極端利己的。在這種傳統思維主導下,國家間很難形成對彼此的信任,反而是構筑各種壁壘以保護自己的利益。這種行為嚴重阻礙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國家間經濟的兩極分化,這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大的不公。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促使著參與其中的各方重新審視傳統意義中的國家利益觀。各國必須要在各自利益和共同發展之間重新審慎選擇,固守自身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共同利益思維卻有助于人類突破與生俱來的貪婪以及保守主義的束縛。各國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進行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從而可以形成倍增效應,如此,不僅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還可以幫助發達國家盡快走出經濟危機的陰霾,并在相互合作中尋找新的經濟創新發展點。在未來的全球發展中,各國間的經濟聯系必將越來越緊密,逐漸會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而這種共同利益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在文化上,尊重彼此,既互學互鑒又保持自身特色,和而不同
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不同歷史共同構成了地球上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人類文明的發展終究是不能離開文化交流的。中國的火藥和指南針在傳至西方后,直接推動了武器的發展和普及;同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傳播到中國后,催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僅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還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明了方向。當前,互聯網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將世界各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只有文明間進行充分共享和交流,才能減少因文明差異而引發的爭端,從而加速世界文明的進步,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內在動力。
(四)在對待生態上,將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作為涉及人類生存發展的核心問題來對待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無節制地開發利用,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也給人類自身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無論是哪個國家污染了環境,消耗了資源,都會破壞全人類的生態環境。任何國家和個體的存在和發展,都要以一定的自然環境為基礎的,同樣,由成員國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更需要有穩定并且可持續提供各種生存發展所需資源的自然環境。因此,構建良好的生態環境體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要義之一。良好的生態直接決定著共同體將來的發展前景。良好的自然生態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得以存在的基石,也是保證共同體能夠健康發展的動力。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必須秉持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嚴懲破壞環境者,并建立健全各種生態環境治理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好生態環境。
(五)在安全上,堅持正確的安全觀念
如今,雖然全球大環境處于和平狀態,但是各種各樣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層出不窮,相互交織,當面臨這些安全問題時,我們需要做出正確的抉擇,要有全局意識,必須保證共同的安全、集體的安全[8],只有如此才能為共同體提供安全的保障,同時還要時刻關注政治、軍事、經濟、生態、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安全,因為在共同體內部這些領域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如果某一方面出現了問題,也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因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我們需要通過合作互信來保障安全,以共同發展、共享發展成果來促進安全。
三、結語
在嘗試了不同治理方案都無法解決當前日益嚴峻的全球治理困局后,習近平總書記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贊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有希望也是最有前途能解決全人類發展瓶頸的理論,因為它不僅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而且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預計在不遠的將來,隨著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未來人類一定可以走出現在的困局,世界也將會更加美好。
注 釋:
① 文明沖突論是指由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創建的理論。在冷戰剛結束、蘇聯解體不久,塞繆爾·亨廷頓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提出了后來一直被許多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文明沖突”理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該理論的觀點集中體現在其著作《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