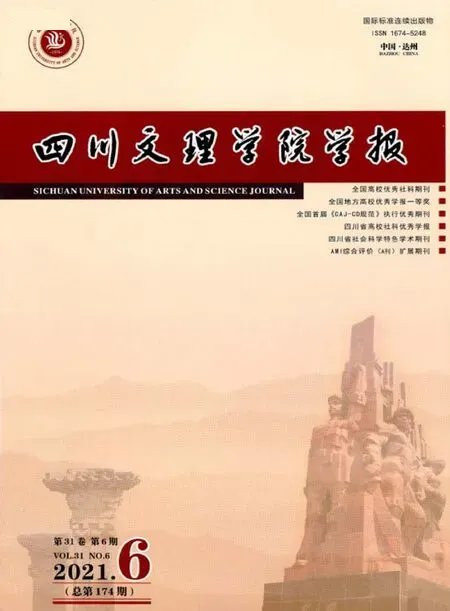聆聽自然之聲:屠格涅夫的詩化小說
楊利亭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海淀 100872)
十九世紀俄國經(jīng)典作家屠格涅夫的自然描寫和詩化風格,形成于他對自然情境的有意營造、自然情性的細致描寫和自然人物的精心塑造。“自然不僅賦予了屠格涅夫以語言和關(guān)切,還給予了他以此言說生活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人身上的自然性的創(chuàng)作才能”。[1]不論是描寫十六歲少年的青春夢幻和情感懵懂(《初戀》)、刻畫陷入愛情的少女那疾風驟雨般的內(nèi)心風暴(《阿霞》),還是講述被現(xiàn)實物欲扭曲的“茨岡女人”的自然情欲(《春潮》)以及人物形象的自然性特點,屠格涅夫均以大師般的詩化文字,表達了對人的自然的與反自然的生命經(jīng)驗的相關(guān)哲思。
俄國文學批評家米爾斯基(1890-1939)在他的《俄國文學史》中,以對照式的評論,強調(diào)了屠格涅夫與普希金在客觀敘述上的相似性。同普希金一樣,屠格涅夫不僅擅長于以次要人物的言行舉止,凸顯主人公的形貌和氣質(zhì),而且還注重通過營造主人公所處的社會語境和自然氛圍,間接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主人公形象。“如同普希金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之所為,屠格涅夫同樣并不分析、解剖其主人公,不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他不揭示主人公的心靈,他僅營造環(huán)繞他們的氛圍,其方法部分地表現(xiàn)為展示他們在他人身上之反映,部分地表現(xiàn)為極其精細地編織一種與之呼應的環(huán)境,這一手法會立即派生出一部詩化小說”。[2]261正是這種借助營造環(huán)繞在人物周圍的環(huán)境,繼而讓人物漸次出場的方式,使屠格涅夫式人物與托爾斯泰塑造的心靈辯證式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論爭中刻畫人物形象的創(chuàng)作風格區(qū)分開來。
屠格涅夫是一位舉世公認的抒情大師,在他的作品中,抒情色彩和自然元素俯拾即是。在批判現(xiàn)實主義引領眾星云集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的時代,屠格涅夫以其獨特而又澄澈的自然抒情文字,創(chuàng)立了一種新的文學風格——詩化現(xiàn)實主義。與此同時,屠格涅夫的作品又總是依照生活本來的樣子描述它,總是“選擇最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作為題材。它們充滿真實,與此同時卻又富有詩意和美……它同時避免夸張的漫畫和感傷的仁慈這兩種危險。它完美無缺”。[2]254屠格涅夫的中間風格且不帶任何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詩化現(xiàn)實主義的落腳點,依然是對現(xiàn)實人生的關(guān)懷。米爾斯基提醒道,屠格涅夫“思想似乎能呼應每個人的抱負,他幾乎觸動了能激起公眾共鳴的每一根心弦”。[2]253
一、青春幻夢與自然情感
屠格涅夫的自然抒情式寫作,首先眷顧了對處于少年男女和他們最初所經(jīng)歷的情感的悸動和青春的幻想的鋪敘。“初戀的全部奇跡在他們身上呈現(xiàn)出來了。初戀也跟一場革命一樣:昔日單調(diào)規(guī)則的生活制度瞬息之間被打破了,青春站在街壘上,它的鮮艷的旗幟在高高飄揚——不管前面等待它的是什么:死亡也好,新生活也好,它都興高采烈的歡迎”。[3]135
屠格涅夫曾聲稱,《初戀》是他“所有小說中最具自傳色彩的小說”。[4]79福樓拜認為該小說對于處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認知,為后來作家樹立了典范。[4]78就此看來,屠格涅夫的藝術(shù)財產(chǎn)不僅屬于過去,也將對未來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敞開大門。《初戀》講述了一對陷入初戀那時而狂喜、時而絕望的情感處境中不能自拔的少年男女的故事。十六歲的貴族少年弗拉基米爾對外表清純、內(nèi)在成熟的鄰家女孩齊娜依達一見鐘情,后來卻痛苦地發(fā)現(xiàn)齊娜依達的初戀,卻是他自己的父親。
小說《初戀》一開篇,就交代了主人公弗拉基米爾十六歲時的青春幻夢和愛情理想。十六歲的弗拉基米爾,正處在想象力無比豐富和活力亟待釋放的年紀:是以自己充足的想象力去解釋自身及其周遭的一切、用果敢的行動力向他人和世界證明自己的年紀;是一個無比羞澀又不乏莽撞沖動的年紀。“那時候我的血在沸騰,我的心在發(fā)痛,有一種極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覺。我總是期待著,又好像有什么東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對什么都感到好奇,我整個的身心都準備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動,一直繞著那些同樣的形象急急地轉(zhuǎn)來轉(zhuǎn)去,就像雨燕在晨光中繞著鐘樓飛翔一樣;我沉思,我憂傷,我掉下了眼淚;然而即使在有音樂旋律的詩歌,或者黃昏的驚人的美所引起的憂傷和眼淚中間,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歡樂感情也還像青草似的生長起來”。
一個人在投入激情時,渾身都是自我意識,他只以自己的想象來看待自我與外在以及二者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處于青春期的愛幻想的弗拉基米爾,便時常將自己想象成一個騎著白馬的逍遙騎士,希望為個人榮譽和愛情權(quán)益而英勇戰(zhàn)斗。弗拉基米爾對愛情和女性的認知,還處于一種朦朧的、未成型的純理想階段:“我記得那個時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愛的幻影在我的腦子里差不多還沒有成型,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覺的到的一切的中間,已經(jīng)有一種新鮮的、說不出來的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預感——一種半意識的、羞澀的預感偷偷地在那兒隱藏了……我整個身體充滿了這種預感,這種期待:我呼吸著它,它跟著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實現(xiàn)的”。[3]99
由青春的活力、豐富的想象力和無所顧忌的行動力構(gòu)成的少年氣質(zhì),注定在面臨挫敗時,瞬間變得呆若木雞、驚慌失措甚至有意不惜自我欺騙、拒絕承認挫敗來逃避現(xiàn)實。當弗拉基米爾發(fā)現(xiàn)父親和齊娜依達在午夜約會時,他拒絕相信自己的愛情遭到了欺騙,他用未成年人的想象力否棄了他見到的事情:“我不想知道,是不是沒有人愛我;我更不愿意承認,并沒有人愛我。我躲開父親,可是我不能躲開齊娜依達……我覺得有火在燒我一樣——我何必知道使我在其中燃燒、而且融化的是哪一種火——既然我覺得燒得舒服,熔得舒服。我完全任憑我自己的種種印象來支配我,我欺騙我自己,我避開過去的回憶,又對于自己預料到會發(fā)生的事情,故意不去想它……這種苦惱大概也不會持續(xù)多久,突然一聲霹靂,一下子結(jié)束了一切,把我丟到一條新的軌道上去”。[3]159-160
孩子走向成熟的真正標志,是他不再相信現(xiàn)實中還存在魔法和童話。當孩子突然意識到原本在他看來無所不能的父母,并不會真的施展魔法,而是他自己附加的主觀想象夸大了現(xiàn)實中的未知時,他便走出了青春的迷惘期,因為他正在開始接受現(xiàn)實中的不完滿。
處于青春期的弗拉基米爾,只選擇自己愿意相信和接受的東西,他會把對人與物的片面化感知,視為絕對和全部,因而他總是沉浸于追逐的過程而無暇顧及結(jié)果的成敗,然而,結(jié)果的成敗卻會徹底改變他對現(xiàn)實與想象的認知,而在那時,他卻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踏出了青春期的河流,一步就邁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二、純潔天使與茨岡女人
三位一體的“自然·女性·抒情”結(jié)構(gòu),既是屠格涅夫塑造質(zhì)樸善良、清純動人的女性形象的藝術(shù)需要,也是暫時遠離物欲橫流的社會現(xiàn)實的男主人公的情感寄托,還是屠格涅夫?qū)θ说脑甲匀挥牟豢啥糁啤ι衩刈匀涣o法被理性所控制的反思式求索。
在屠格涅夫筆下,時常出現(xiàn)兩類氣質(zhì)截然相反的女性:純潔天使和茨岡女人。自然環(huán)境里孕育的純情少女,質(zhì)樸自然又清雅純潔,堅信人性的美好和愛情的圣潔,總是充滿希冀地等待戀人的出現(xiàn),與此同時,對內(nèi)心所愛又充滿柔情和愛慕。即使無法擁有內(nèi)心所向往的愛情對象,也會默默祈禱和祝福對方;被物欲橫流的社會所裹挾的欲望扭曲的“茨岡女人”,冷艷傲慢又市儈詭詐,因為被壓抑的自然欲望得不到滿足,便以誘捕的方式控制和征服戀慕自己的男性,最終又冷酷無情地拋棄對方。
(一)純潔天使
屠格涅夫的自然抒情式寫作,往往通過主人公在悔恨中打開記憶的閘門,憶起早年在自然狀態(tài)下對異性萌發(fā)的自然情感,又無意間錯過向意中人表達愛的時機,最終失去愛情,抱恨終生的慣常講述模式,緩緩打開故事之門。屠格涅夫的《阿霞》和《春潮》便是講述男主人公因錯過表達愛的時機而最終永失所愛的詩意感傷小說。
屠格涅夫短篇小說《阿霞》,講述了一個尚未開始、就已結(jié)束的愛情故事。人在自然情境中萌發(fā)的自然情感,有時容不得一絲理性的猶豫和思量。來自俄國的貴族青年H.先生,很像遇見朱麗葉之前的憂郁的羅密歐,正陷入愛情的失意和痛苦中,他主動到萊茵河畔去排遣憂愁,卻在不經(jīng)意間遇到了俄國同鄉(xiāng)加京和他的妹妹阿霞,在經(jīng)由對阿霞性情的挑剔到憐憫再到深愛的過程中,H.先生經(jīng)受了愛情來臨時的悲喜交加和最終永失所愛的無盡悵惘。
“自然音調(diào)所特有的平和節(jié)制,將性格顯示于其界限之內(nèi),予以多重而溫和的層次變化”。[5]屠格涅夫?qū)Π⑾夹蜗蟮乃茉欤拖袢致匪箛跗じ耨R利翁帶著深沉的愛去精心雕刻而出的女性塑像,那樣立體鮮活,生機勃勃又自然純真。阿霞,是一個擁有天真面孔和自然氣質(zhì)的十七歲少女。“她那略帶褐色的有著美麗的細小的鼻子,差不多帶孩子氣的臉頰和明亮的黑眼睛:這個臉型里有一種獨特的、特殊的東西。她的身材優(yōu)美,但尚未發(fā)育完全”。[3]44
屠格涅夫?qū)ε匀宋锏男睦砻鑼懖⒉欢嘁姡喾矗?jīng)常通過對人物的外在形貌的細節(jié)刻畫與對人物所處環(huán)境的側(cè)面描寫,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內(nèi)心。在《阿霞》中,屠格涅夫通過主人公H.先生的視角,去打量內(nèi)心處于愛情萌動而外在又活潑異常且羞澀無比的阿霞形象——“我從沒見過比她更好動的人。她從來也沒安靜地坐過一陣;她一會兒站起來,跑進宅子里去,又跑出來,低聲唱歌,一會兒她笑起來,而且笑得非常古怪;她好像并不是在笑她所聽到的,只是為了跑進她腦子里的種種思想笑著。她的大眼睛發(fā)亮地、大膽地望著你,但有時她的眼瞼微微地低垂,于是她的眼光立刻變成深沉而溫柔的了”。[3]46
阿霞是一個貴族及其女仆的私生子,她自幼經(jīng)受的知識性教育全部來自父親,而作為女性生命存在的必備教育卻是殘缺的,她對異性的認識和情感還只停留在父親和兄長加京身上。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阿霞會被自己初見H.先生便愛上對方的那種激烈情感所驚嚇的原因。因此,在最初與H.先生相處的過程中,阿霞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有意無意地處于躲躲閃閃和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她既忍不住靠近H.先生,又礙于少女情竇初開的羞恥和自己出身的卑微而妄自菲薄——作為美麗動人的女仆和貴族出身的男主人后代的阿霞,她既對自己私生女的身份深以為恥,又對自己抱有這種恥辱而感到痛苦。
阿霞對H.先生如疾風驟雨般的愛,不僅揭示了她非正常的出生、成長經(jīng)歷,而且也印證了她殷切渴望在愛情中確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失敗。阿霞無法接受H.先生對自己傾心相托的愛情持求全責備的絲毫猶豫態(tài)度,她也不能確定H.先生是否會因為她復雜的出身而放棄他們之間的愛情。在阿霞看來,對愛情的猶豫,就是對愛情的拒絕;對愛情的拒絕,就是對她的人格尊嚴的否定。最終,阿霞因拒絕面對愛情的失敗和受辱的人格被H.先生的言行所證實,于是便極力央求兄長加京將自己永遠帶離H.先生的世界。
當一個人處于愛情之中,他并不能確認那就是愛,而總是用內(nèi)心的焦慮不安和情緒的時漲時落,去解釋他所遭遇的疑慮和困惑。為了擺脫內(nèi)心焦慮和情緒波動,他時常會對他的所見所聞斷章取義、主觀臆斷。然而,適得其反,他的這種主觀臆斷會使他陷入更深的迷惘和憂郁中。愛情是個瞎子,遇上誰就是誰。然而,被丘比特的箭瞄準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如此幸運,因而面對這不確然的幸運,他也就通常采取視而不見的中立態(tài)度。面對阿霞瞬息萬變的情緒和復雜的成長經(jīng)歷,H.先生卻產(chǎn)生了猶豫和退卻的心理,他覺得跟阿霞這樣未成熟的、情緒變幻不定的女性結(jié)婚,是難以想象的。
剛遭遇愛情失意的H.先生,并不知道在自己打量少女阿霞時,不自覺地帶上了一種戀人的眼光。然而,H.先生最初并不清楚阿霞時而活潑又時而出奇安靜的舉動,皆是因為愛上自己的不自覺反應。但H.先生通過觀察阿霞的外在形貌特點、反復的神情變化和令人難以捉摸的言行舉止,還是敏銳地洞見了阿霞內(nèi)心的焦慮不安和莫名驚惶。H.先生的這種敏銳洞見,正是引領讀者發(fā)現(xiàn)他和阿霞有意無意間早已愛上彼此的征兆。直到H.先生意識到自己即將永遠失去阿霞,是何等恐懼和痛苦時,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早已深深地愛上了阿霞。
同樣,中篇小說《春潮》中的純潔天使,是男主人公薩寧一見鐘情的德國糖果店里的女孩杰瑪。薩寧被杰瑪溫柔含蓄的性格和自然清純的形貌所深深吸引。薩寧初見杰瑪,便注意到了她獨特的自然之美:“杰瑪?shù)谋亲勇燥@大些,可是鷹鉤形的輪廓卻極為秀美,上唇有些淡淡的茸毛;然而臉色卻柔潤光澤,跟象牙或乳白色的琥珀別無二致。秀發(fā)上的波狀光澤就像畢蒂宮里珍藏的阿洛里畫的朱迪斯,兩只深灰色的眼睛的周圍是細細的黑邊兒”。[3]268與此同時,杰瑪眼中又交織著的歡欣鼓舞和驚魂甫定,似乎又暗淡了它們的光澤(with a black ring round the pupils, splendid, triumphant eyes, even now, when terror and distress dimmed their luster……)。[6]
(二)茨岡女人
屠格涅夫經(jīng)常用老鷹和蛇來形容冷艷傲慢又市儈狡詐的“茨岡女人”,這類女性就像魔鬼撒旦的化身,不惜用各種手段去誘惑涉世未深的異性愛慕者,而在獲得征服者和控制者的優(yōu)越感的同時,又讓后者逐漸喪失自我的分辨力和決斷力,完全被愛欲的烈火所席卷、所征服,淪為愛情的奴隸和獵物。
對“茨岡女人”而言,愛情只出現(xiàn)在誘惑和征服對方的過程中。“茨岡女人”想要獲得的是肉體欲望,而非靈肉合一的愛情。“茨岡女人”最初以楚楚動人的柔弱形象引誘追求者,繼而又以強勁的肉欲激情獵捕和鉗制追求者。“茨岡女人”令“每一個遇見她的人都會踟躕不前,不是因為面對著一個‘美神’,倒是因為面對著那強勁的,像是俄羅斯的又非俄羅斯的,是茨岡的又非茨岡型的風華正茂的女性肉體的魅力……”[7]然而,“茨岡女人”不需要與戀慕者成為知心戀人、靈魂伴侶,她甚至不需要戀慕者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她要的是對方絕對的臣服與膜拜,而非雙方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對話格局。
屠格涅夫中篇小說《春潮》中的已婚女貴族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便是典型的“茨岡女人”。為了暫時擺脫生活的空虛,她不惜以乞憐和誘惑的方式,接近已經(jīng)與德國姑娘吉瑪有了婚約的男主人公薩寧,使后者對她由憐生愛,并于不自覺間進入了她預先設計的情欲圈套。在薩寧淪為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肉欲的獵物后,她又逐漸喪失了對薩寧的興趣,最終還無情地拋棄了薩寧。
“茨岡女人”是一個施虐者,她持續(xù)尋找的是與她的施虐行為相匹配的受虐者。弗洛姆認為,施虐者具有三種傾向——“一是讓別人依賴自己,以絕對無限的權(quán)力統(tǒng)治他們,以便讓他們僅僅成為自己手中的工具,像‘陶工手中的泥土’;二是不但有以這種絕對方式統(tǒng)治別人的沖動,而且還要剝削、利用、偷竊、蠶食別人,把別人吸凈榨干,不但包括物質(zhì),而且還包括情感與智慧之類的精神方面;第三種施虐傾向是希望別人受難,或看別人受難”。[8]在“茨岡女人”主導的施虐與受虐關(guān)系中,作為施虐者,她不是想要毀滅受虐者,而是對受虐者的身心進行全面的訓誡與控制。然而,當受她剝奪的受虐者的自由意志和行動意志徹底喪失時,她對受虐者的征服欲也將隨之消失。也即,當她精心馴化的受虐者完全受制于她時,她反而對受虐者徹底喪失了興趣。因此,施虐者最終會拋棄已淪為受虐者的愛慕者,繼續(xù)尋獵下一個受虐對象。
“茨岡女人”是作者在《春潮》中隱喻的海底丑惡的怪物,它毫不留情地攫住了人的意志和欲望,令他難以掙脫,最終在錯失美好的情感和青春不再的遺憾中悔恨終生。在小說《春潮》一開篇,屠格涅夫便運用了一個生動的自然化修辭,來交待男主人公薩寧孤苦而漂泊的一生。在薩寧的人生起伏和海水漲落之間,具有驚人的一致性,似乎愛情的迷霧和自然里的煙霧一樣,會遮蔽人的視線,阻斷前進的航向,還會像海底丑惡的海類怪物突然出現(xiàn),讓那搖擺不定的人生之舟不可避免地傾覆于那不知名的可怕力量中。“生活的海洋在他的想象中跟詩人描寫的不同,并沒有狂濤怒浪,是的,在他的想象中,生活的海洋是風平浪靜、清澈透明的,一直可以看到那幽暗的海底;而他自己卻坐在一只容易翻覆的小船上,在那幽暗的積滿淤積的海底隱隱約約地伏著像大魚似的、丑惡的怪物;那是生活中的痛苦、疾病、悲傷、瘋狂、貧窮、盲目……他凝視著:瞧,有一個怪物離開幽暗的海底,越升越高,樣子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可憎……再過一分鐘,小船就要被它拱翻了!可是它又模糊了,又沉下去,沉到海底——它又伏在海底,只是微微地擺動著海鰭……可是命中注定地一天一到,他的小船會被它拱翻的”。[3]46
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老婦人》的老婦人形象,有助于我們理解“茨岡女人”的形象:可怕的老婦人是“我”無論如何掙扎和反抗,都無法逃脫的被詛咒的命運:“一種奇異的不安漸漸控制了我的思緒:我開始覺得,老婦人不只是跟在我身后走,而且是在決定著我的方向,她在催促我時而向右,時而向左,而我卻在不由自主地服從著她”,“無論朝哪個方向,我都像一只被獵人追趕的兔子……全都一個樣,一個樣啊”。[9]
三、自然化的人物形象
在短篇小說《阿霞》中,屠格涅夫?qū)⑷宋锼茉旌途拔锩鑼懭跒橐惑w,進一步凸顯人身上的二重性:人性與自然性,也即社會性和自然性。在該小說中,無論是對阿霞人物形象的塑造,還是對阿霞哥哥加京形象的塑造,都體現(xiàn)了“人身上的自然和自然中的人”的形象合一。
(一)加京肖像的自然性
不論是從外貌塑造上,還是從人物所處的年齡階段的描述上,敘述者修辭都體現(xiàn)了一種近乎自然詩化的格調(diào):“蜷曲發(fā)亮的頭發(fā),露出來的頸項,玫瑰色的面頰,他本人就像早上一樣的新鮮”。[3]48“青春不像一道噴泉在他的心里涌流,而以寧靜的光照耀”。[3]53
事實上,對加京自然化形象的塑造,也間接折射了他的內(nèi)在形象——質(zhì)樸的心靈和溫和的性情。在國外旅行H.先生“我”原本并不樂意遇見俄國同鄉(xiāng),因為他無法適應同鄉(xiāng)們臉上露出的偽善而夸張的驚訝表情以及僅僅出于禮貌作出的應酬。但是加京卻與那些俄國同鄉(xiāng)不同,在“我”第一次跟他交談時,就被他真誠而友善的面相和聲音所打動。
加京是一個讓人感到親近且自在的俄國貴族青年,就像每個人都欣然接受陽光的溫和普照,每個接觸加京的人似乎都能從他那種溫和而舒適的存在狀態(tài)中,獲得交談的樂趣與內(nèi)心的寧靜。“世界上的確有這樣一種幸福的面容,讓人人都樂意望它,就像它在給你溫暖,給你安慰似的,加京就有這樣的臉,溫和的、討人喜歡的臉。大而溫柔的眼睛,柔軟的蜷曲的頭發(fā)。他講起話來有這種調(diào)子,即使你還沒有看到他的臉,你只聽見他的聲調(diào),也會感覺到他在微笑呢”。[3]44
(二)阿霞肖像的自然性
H.先生,也即第一人稱敘述者兼主人公對阿霞形象的認識不斷發(fā)生變化。在H.先生眼中,阿霞從最初的鄰家調(diào)皮少女、輕佻做作的貴族女性到故鄉(xiāng)俄羅斯的普通少女的變化,也體現(xiàn)了阿霞形象逐漸從社會化到自然化的轉(zhuǎn)變過程。
阿霞身上不斷彰顯的自然氣質(zhì),讓“我”愈加覺得一種家鄉(xiāng)的親切感和質(zhì)樸感。“我覺得阿霞完全是一個俄羅斯的少女,還是一個普通的少女,幾乎就像一個女仆。她穿著一件窄小的舊長袍,頭發(fā)梳在耳朵后面,靜靜地坐在窗前,帶著一種樸實的、溫順的神情在繡架上刺繡,就像她一輩子沒有做過別樣事情一樣。她幾乎什么也不說,只是凝神地望著她的繡品,她的臉上籠罩著一種平凡的、日常的表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們家鄉(xiāng)的卡佳、瑪霞們來”。[3]55
屠格涅夫用剛發(fā)新枝的野果樹和正在發(fā)酵中的酒,比喻阿霞尚處于孩童和成人的混沌狀態(tài)。“然而,她卻不像一位貴族小姐,在她所有的舉動里有一種不安寧——就像一棵剛接枝的野生的果樹,一種還在發(fā)酵的酒。”[3]55這形象而生動的比喻并未僅僅停留在揭示阿霞的成長過渡期,它也與后文敘述阿霞初次感到內(nèi)心的愛情萌動時,所產(chǎn)生的惶恐和羞澀相呼應。阿霞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對父兄之外的異性產(chǎn)生的奇特感情。阿霞甚至痛苦地認為,對異性的愛會損害對兄長的愛。阿霞還不能真正區(qū)分開愛情與親情的關(guān)系,因而在她覺得愛情和親情相沖突時,她便產(chǎn)生了強烈的負罪感。
(三)H.先生情感的自然性
與阿霞和加京身上肆意流淌的自然性相比,H.先生身上的自然性似乎更多地被掩蓋在理性意識之下,他的自然情性似乎總是在受到他者自然性的觸發(fā)而間接產(chǎn)生的,是后知后覺的。
就H.先生最初對阿霞的輕慢態(tài)度來說,就可見一斑。H.先生最初是帶著挑剔的眼光去看待阿霞身上的自然性的,并將這種自然性視為故作矜持的,甚至是矯揉造作的。直到H.先生意識到阿霞身上渾然一體的自然性,與其愛情的純粹和內(nèi)心的質(zhì)樸緊密關(guān)聯(lián)時,才真正意識到了這種自然性的珍貴和美麗。然而,正如陷入愛情中的人多是非理性的,與此相反,H.先生過度的理性反而阻礙了他最終與阿霞在愛情上的進一步展開。詩意感傷的愛情小說《阿霞》,提示讀者:愛情最初是非理性的,當愛情來臨時,不要因過度權(quán)衡未知的結(jié)果而猶豫不決,因為過度權(quán)衡愛情的利弊,最終可能失去的不止是愛情對象,還有自我的人生。
結(jié) 語
屠格涅夫通過塑造三類自然本性失衡的人物,向我們揭示了人生的幸與不幸的真相:恰當?shù)淖匀磺樾裕瑫炀腿撕屯晟迫耍欢^度的自然和反自然情性,會損害人甚至毀滅人。第一類,過度沉醉于自然化情感與想象中的人,會因懼怕面對現(xiàn)實中殘酷的真相而選擇重新蒙上自己的眼睛(《初戀》中的弗拉基米爾,《阿霞》中的同名女主人公阿霞)。第二類,頭腦過于理智以致遮蔽了自己與生俱來的自然本性的人,在聽到戀慕對象那熾烈如火卻又真情流露的愛情表白時,會因感到極度震撼而懷疑對方情感的可靠性,最終反而失去了整個人生的幸福(《阿霞》中的H.先生,《春潮》里的薩寧)。第三類,那些陷入物欲橫流、曲意逢迎中不能自拔的人,最終會因喪失原本的自然情性,于不自覺間走上反自然性的虛榮之路,他們誤把持續(xù)的引誘、征服和統(tǒng)治對方,作為不斷施展自我魅力與彰顯自身權(quán)力的利器,而這利器所映現(xiàn)出的,卻是他們的自然情欲被徹底扭曲的模樣(《春潮》中杰瑪?shù)奈椿榉蚝同旣悂啞つ峁爬蚰?——“陶醉于活動掩蓋人之生存的實在;當激情退卻時,根本的空虛和形而上的孤獨這種經(jīng)驗就會油然而生;生存的焦慮就會冒出來,要求安撫;而安撫焦慮的通常方法是用新的活動來消遣”。[10]
只有原本具有自然情性的人,才能洞見和邂逅他人身上的自然性;才能在自然景象中尋得與自我相契合的情境。人類只有真正進入自然的腹地,諦聽自然本身的言說和沉默,才能從中找到平復情緒和凈化心靈的良方;只有自我和他者(他人、自然)雙方都敞開心扉,才能走入彼此的內(nèi)心,既能實現(xiàn)真正的對話,也能共享大地的安寧,并在這大地的安寧中,聽見萬物的存在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