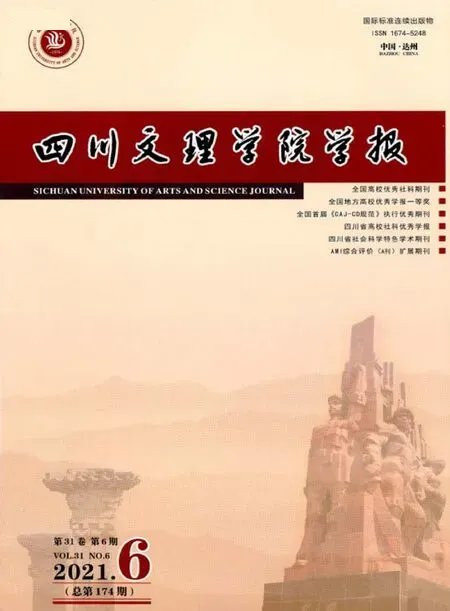從《紅樓夢》解讀清代女性的閨閣文化意蘊
張譽尹,杜 雙
(1.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與歷史系,香港 999077;2.自貢衡川實驗學校 辦公室,四川 自貢 643000)
自明朝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萌芽,市民階層不斷在擴大。至清朝,市井商業繁榮更甚,據英國計量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研究表明,在“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的財富總量約占據全世界的三分之一。[1]社會風尚也由明初的質樸尚儉轉變為鄙儉崇奢,人對物的要求愈發精巧別致,居室設計上亦能體現出清人對生活美學的追求。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居住空間的布局將儒家宗法制貫徹到底。整所住宅里,內院閨閣是最為私密幽靜的所在。它是女子日常活動進行的重要場所,更是主人性格和人格的延伸。《紅樓夢》作為閨閣文學的代表,是研究古代女性生活的重要文本。因此,《紅樓夢》可為現代學者研究清朝女性閨閣文化和了解清代女性生活提供參考。“閨閣”背后的文化意蘊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探索。
一、閨閣內院的空間布局
在中國古代社會,幾千年來在宗法制的影響下,家庭的秩序須符合倫理綱常,長幼尊卑有序,男女有內外之別,住宅空間的區域劃分處處體現著禮法。可以說正是嚴密分化的住宅空間“提供了婦女生活的物質性框架,予男性和女性領域的分離以具體的形式。[2]”空間的嚴格區分于司馬光《書儀》也有記載:“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3]可見不論是民居住宅還是天子行宮,都有內外之分,男主外女主內,不可逾越,內外的公共區域也不可混用。明清時期,居民住宅總體特征為坐北朝南,方正對稱有中軸線,富足人家至少有前后兩院,以兩側抄手游廊相接。居正中大堂為尊,兩側廂房又以東面為尊。內院通常都在宅子最后面,私設出入通道可使女眷出入不與前門相擾,確保私密性。《紅樓夢》中林黛玉初進榮寧二府就是從內院空間進行敘事的,“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也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的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眾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眾小廝退出,眾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黛玉扶著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4]46這一大段描寫節奏緊湊,眾婆子小廝進退有序,一套下來行云流水,昭示榮府內外有著嚴格的空間劃分,制度森嚴。林黛玉為女眷故由角門送進內院,轎夫這等外男不可以入,直到垂花門前,小廝們退下,婆子上來,可見垂花門則是介于內外院之間的一道屏障。
內院里女眷們的住處方位也與關系的親疏、身份地位的高低密切相關。且看:“王夫人忙攜黛玉從后房門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后院了。”[4]50可知賈母和王夫人各自擁有一套獨立后院,相距不遠,且王夫人與賈政的小院在東,賈母在西。“賈母的婆子們帶領黛玉過榮禧堂,來到東邊三間耳房...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房炕上橫設一張炕桌,桌上磊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4]108這三間東耳房,東廊三間小正房,家具坐褥都半舊不新,這就是賈政夫婦二人的居室。這東小院與東廊三間小正房,理應是同一區域,整體屬于榮禧堂東邊的附屬跨院,而東廊三間小正房后門經后廊往西出西角門,便是賈母后院。不知為何以賈母的地位要住在西邊,榮禧堂東邊的院子面積甚小,且呈長條矩形,不甚大氣,想必賈母才愿意住在西側吧。
又見第七回周瑞家的從王夫人處出來,“穿夾道從李紈后窗下過,隔著玻璃窗戶,只見李紈在炕上歪著睡覺呢,遂穿西花墻,出西腳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往東屋里去...只見奶子正拍著大姐兒睡覺呢。”[4]206周瑞家的送宮花路線暗暗說明了鳳姐后院處于宅子西后側,而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中賈瑞躲在西邊穿堂兒里,“趁掩門時,鉆入穿堂。果見黢黑無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關。”[4]312可以知道賈母的院子與鳳姐院子是由一條東西穿堂連起來的,相連緊密,可見鳳姐深得賈母歡心。且鳳姐與賈璉的臥室居院子正中,符合其主人身份,大姐兒的閨閣在東屋,也彰顯賈璉夫婦對女兒的珍愛之意。
林黛玉住的是瀟湘館,且看瀟湘館的布局:“里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只見進門入門便是曲折游廊,階下石子漫步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里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床幾椅案。從里面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后院,有一大株梨花倚著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4]412可以看出瀟湘館如此精巧雅致的院子也有一個后院,于翠綠修竹中層層深入,穿過三間房舍,再穿過一個小門,來到了后院,梨花芭蕉的遮掩下才看到兩間小小的房屋,讓人想起桃花源記的世外桃源來。林黛玉必然是居于后院之中,幽靜不被打擾,符合她清冷獨處的性子,且與寶玉的怡紅院距離較近,也暗示了二人關系更為親近。
再看寶釵的蘅蕪苑,蘅蕪苑不與各處相連,需要乘船過得港洞或者從山上盤道而行,過了一個朱欄板橋,接著看到的是“一色水磨磚墻,青瓦花堵……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只見許多異草……賈政因見兩邊俱是抄手游廊,便順著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卷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4]蘅蕪苑抱水而居,以古樸磚墻為屏,四面環石。蘅蕪苑本身地理位置已經很偏僻了,不與其他各處大陸連著,院子四周又有石塊遮蔽,封閉性已然極強。這符合寶釵在賈府的身份,在賈府她雖然有王夫人這個姨娘,可終究比不得賈母珍愛的黛玉,她在下人眼里也始終是外人,因此她住在蘅蕪苑這偏僻處不與其他住處相連,在關系上有親疏遠近之別。
二、閨閣陳設
宗法制決定了房屋住宅須得遵從尊卑長幼等級設立。院子的方位和大小彰顯主人的身份地位,而室內居室設計則是主人財力和品味的最佳象征。不同于明代居室的簡樸情趣,清代室內環境營造在整體風格上更趨華美繁縟,室內的設計風格和家具都更趨于裝飾化、精致化、世俗化和奢侈化等。
而臥室,作為供人下榻休息的居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私人空間。臥室不為外人所見,不需要彰顯主人的優越之處,故臥室修建設計得不如廳堂恢弘大氣,臥室的陳設器物、裝飾風格皆更隨意自由,更能體現居住之人的脾氣秉性。
《紅樓夢》第五回就借賈寶玉之眼探究了一番秦可卿的閨房,房內擺放的家具器皿、文人字畫都隱晦的表達出秦可卿的風流香艷。“剛至房門……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秦氏臥室墻上掛著的是《海棠春睡圖》,楊貴妃醉顏殘妝,鬢亂釵橫,別有一番風流滋味。旁邊的對聯看似是應和畫上的美人醉酒,也有一種醉生夢死不愿醒來的旖旎。再看“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報過的鴛鴦枕。”[4]149從秦可卿低微的出身來看,這些所謂的武則天的寶鏡以及趙飛燕立過的金盤是不是真品無從考證,這些文字都是以寶玉的視角展開,不免添加了人為主觀的想象。女子的臥室中有寶鏡,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說明秦氏是一個注重打扮的人;《詩經》有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象征著男女之情,木瓜放在金盤里又多一層富貴奢靡之意;榻與床不同,榻的尺寸較小,高度很低,是作為休閑小憩的臥具,榻有招待貴賓之意,這里秦氏讓寶玉睡榻也有此意;而珠帳、紗衾和鴛鴦枕這些床上用品則處處彌漫著夫妻日常生活氣息。
《紅樓夢》里關于黛玉在瀟湘館的臥室有很多描寫篇幅,其裝飾風格與秦氏就大相徑庭了。“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幾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挑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于他念。”[4]432又見第四十回賈母攜眾人帶著劉姥姥賞園,以劉姥姥的視角看黛玉的閨房:“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黛玉聽說,便命一個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放著滿滿的書……”[4]441這些雖是零零散散的片段,但幾處碎片拼湊在一起也有了大概總體的印象。黛玉的閨房偏小,賈母也說這屋子窄,可從臥室的布局設計來看卻極盡風雅。臥室外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竹的姿態蒼翠,傲然挺直,文人喜竹并因其品行高潔,并常以竹自喻。月光從紗窗傾瀉而下,伴著竹葉沙沙作響,所以連賈政也感嘆道:“若月夜能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文中沒有刻意提及屋內其他器皿陳設,單看書架上滿滿的藏書和案上的筆硯,可見這間臥室與黛玉身上喜愛文墨且清冷的氣質十分相宜,烘托出黛玉高潔的品性。屋內有幾,可供讀書寫字;簟,竹席,由李清照的“紅藕香殘玉簟秋”可得,還有作為空間隔斷的屏障“湘簾”,也是用竹子做成,這兩樣竹制裝飾與屋外的湘妃竹相得益彰,更有幽靜涼沁之意。這樣清幽的環境里,唯一增添絲絲生氣的是那只鸚哥,為黛玉解解悶兒。鸚鵡素來在中國古典詩詞中就有著不同象征意義。其一,它的美麗外表、聰明辯慧,以及常年貯之金籠都成為中國古代女性處境的一種象征。柳永的《甘草子》就寫出了深閨女子的滿腔愁緒:“池長憑闌愁無侶。奈此個、單棲情緒。卻傍金籠共鸚鵡”。其二,鸚鵡不同于凡鳥卻被困金籠,“古往今來恨莫窮,不如沈醉臥春風。雀兒無角長穿屋,鸚鵡能言卻入籠。”曹公將鸚鵡放于黛玉房中,絕非偶然,意指黛玉縱使才資過人卻只能和鸚哥一樣不得圓滿,落得香消玉殞的結局。黛玉房中的裝飾還可以從第八十九回寶玉去瀟湘館窺見一二:“一面看見中間掛著一幅單條,上面畫著一個嫦娥,帶著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著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邊略有些云護,別無點綴,全仿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斗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著……寶玉指著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么?’怎么這么短?”[4]518李龍眠即李公麟,北宋時期著名的白描大師,這幅斗寒圖仿的是他的畫法,自然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嫦娥圖了。掛此畫在室內,嫦娥清冷出塵的仙姿倒是與瀟湘館的幽冷相為契合。再說嫦娥一人飛去廣寒宮,身邊無一親人,和在賈府無依無靠的黛玉一樣孤寂。故此黛玉將從小撫弄的琴掛在壁上,也能看出她對從前父慈母愛的生活十分眷念。
《紅樓》關于閨房記載詳細的還有薛寶釵的房間:也是第四十回劉姥姥進大觀園,“進了蘅蕪苑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并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4]539-540寶釵素來不喜花兒粉兒的,周瑞家的送宮花那一回就已經明說過寶釵喜素了。蘅蕪苑中種植的皆是奇草仙藤,散發著冷冷幽香,倒十分符合寶釵不愛粉紅的性格,不脫俗套。況整所蘅蕪苑透出冷來,寶釵正是一位服著冷香丸的冷美人,處處都是冷意。再看室內陳設,“雪洞”二字言簡意賅地概括了寶釵閨閣的特點:清冷。房內并無玩器,所以室內色彩十分單調。案上放著一只土定瓶,瓶中有幾只菊花,頗有幾分“采菊東籬下,悠然現南山”的天然去雕飾之感。幾本書,一些茶具,就連寢具也是單一古樸的。書中交代了關于寶釵性格的一些線索,比如將大紅襖兒穿在里面,在手腕上帶著麝紅珠子,其實她并不是一味的抗拒紅色,而是將自己的欲望喜好選擇深埋起來。就如同這間“雪洞”,空無一物,符合她藏拙守愚、穩重內斂的性格。
要說姑娘中屋子最富麗堂皇的應數探春,賈母也對她的房間贊譽有加。“三間屋子并不曾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并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詞云: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4]564臥室的布局就很開闊,三間屋子打通,顯得明亮大氣,與瀟湘館的“曲徑通幽”剛好相反。再看器皿擺設,花梨大理石大案、斗大的汝窯花囊、一大幅《煙雨圖》、大觀窯、大盤、大佛手。探春房內所設的器物一反女兒家的纖小可愛,全部都是大號的,可見探春不是一般尋常的閨閣女兒,有著和男子一樣的豪爽做派。探春閨閣的第二個特點是:多。她案上的文房四寶數量已相當可觀,就連屋內裝飾用的菊花和佛手也放的滿滿當當。白菊花品性高潔,佛手色澤金黃,放在室內即可觀賞又可凈化空氣,使室內清香。探春用鮮果花朵代替香薰,其天性應是崇尚自然的。且看她壁上掛著的字畫,江南水鄉瞬息萬變的“煙云霧景”,米芾的繪畫追求正是“天真平淡,不裝巧趣”的風貌;出自顏真卿之手對聯的釋義則是“像煙霞一樣散漫而不受拘束,像泉石一樣隱逸而天然”。僅僅是這室內的字畫就有一種天然野趣,與“秋爽齋”的“秋爽”二字極為相宜。探春是三春中最出眾的,她有著“裙釵一二可齊家”的能力,文采斐然,處事進退有度。賈母和王夫人對她總是與二春有些不同,更為看重。“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床上懸著蔥綠雙銹花卉草蟲的紗帳。”屋子里最能證明探春地位的就是這架拔步床了。拔步床又稱為架子床,通常設有四根或六根立柱,三面設有圍欄,而且還有床頂。結構較為封閉,隱私性非常強。拔步床的造價極高,雕刻工藝精美繁雜,花紋華麗多樣。正是因為其價值不菲所以才能夠凸顯主人的身份和財富,常作為富貴小姐的陪嫁之物。探春的房里有這樣一架拔步床,足以證明其賈府小姐的尊貴身份,也可得知雖是庶出可她在賈府還是很受捧的。
三、閨閣生活
前文主要涉及到閨房的構造空間和陳設藝術,但在居住空間內發生的人為活動同樣也值得我們關注。居住空間與居住者的活動需要密不可分,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方能拼湊出一幅幅活色生香的閨閣畫卷。
在繁瑣嚴格的制度教條下,古代女性的娛樂活動大多是撫弄纏繞的針線,賞花烹茶,對鏡梳妝。女子都愛妝飾,晨起第一件事便是梳妝。清朝才女王貞儀就有一首《梳頭歌》就將女子晨起妝發的過程完整地記錄下來:“細沐微熏濕雙鬢,芙蓉綰髻開帷鏡……麟梳緩逐青絲掠,鳳篦斜隨弱縷揚。纖纖玉指盤翠色,云鬟半偏描不得。花鈿貼罷成新妝,腰肢已自慵無力。調朱弄粉親盤鴉,青入眉峰黛色斜。梳罷背人還對影, 一枝簪得海棠花。”女兒家嬌媚慵懶的姿態惹人憐愛,讓人對這位坐在鏡前梳妝的女子產生無限遐想。《紅樓》里也不乏這樣的情節,第四十四回,寶玉素日最喜紅,一身脂粉氣,他的臥室被劉姥姥誤認為小姐的繡房。他房里和女子一樣有一個妝臺,拿出自己的胭脂為平兒上妝。這一段的描寫極美,用紫茉莉花研磨的粉一排排的在瓷盒里,輕白紅香,甜膩潤澤;用花露蒸成的胭脂盛在白玉盒子里,如玫瑰凝脂一般。且上妝手法須輕柔,粉要用玉簪花棒兒輕輕蘸取,胭脂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平兒只覺得鮮艷異常甜香滿頰。可見當時女子的妝品工藝已漸趨成熟,更是相當精致,她們對自己的容貌舉止都有一定的要求。
“婦容婦德婦工婦言”這四德,女子在閨閣里最常做的就是女工了。寶玉在第八回里離了王夫人去看寶釵,“寶玉掀簾一跨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4]138。寶釵是紅樓里最能體現儒家精神的一個人,做人行事深諳中庸之道,也常勸誡寶玉作為男子要承擔家業,爭取功名。她將女紅刺繡看作女人的本分,白天陪著賈母王夫人問話,晚上還得繼續做工直至三更天。這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生活,這是整個中國古代女性的縮影。女子不事農耕,但須得成日紡織做工補貼家用,故所有女子皆能做工。刺繡也能隱晦的表達對心上人的愛意,第三十六回黛玉在窗外悄悄瞧見寶釵坐在寶玉床邊,拿著他的肚兜繡起來,這讓黛玉醋意大發。而黛玉也曾坐在窗下為寶玉做香囊、絡子等掛件,刺繡將三個人敏感復雜的關系纏繞在一起,理不清更亂罷了。富家小姐尚可將刺繡拿來消遣時間,但作為低人一等的丫鬟來說,女工是工作分內的事。第五十二回里,病中的晴雯向墜兒罵道:“要這爪子做什么?拈不得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4]607可知針線活兒對于女婢來說是很要緊的手藝,是吃飯的家伙。而晴雯在病中仍咬著牙替寶玉縫補雀金裘補了一夜,讓人憐愛又感動,好一個忠勇手巧的丫頭。
在明清時期,貴族階層女子讀書識字的現象增多。社會風氣推崇詩學才女,她們既能為門第添光,也可更好的相夫教子。如明末《女范捷錄·才德篇》就抨擊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論:“夫德以達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故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貴乎有德。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女子之知書識字,達禮通經,名譽著乎當時,才美揚乎后世。”清代之后,女性文學更加繁榮。據單士厘編輯而成的《清閨秀藝文略》中所記載就有二千三百多位女作家的三千多種作品,這還只是三十年間所記錄下的,遺漏詩稿尚未計入,數量已是相當可觀。女子的日常生活豐富了很多,她們吟詩作賦甚至結成詩社,女性家族群體成員之間還相互唱和。《紅樓》中林黛玉尚在林府時,林如海已經為她請了先生教她讀書。黛玉才進賈府時也曾說自己只讀了四書,可見書香世家的小姐是要能讀書寫字的。明清社會吟詠之風盛行,“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造成了許多世家大族,生活在具有豐厚傳統的文化氛圍中,使得女作家的出現更加具有普遍性。”[5]此時社會涌現出許多女作家群體,而且多以家族關系面世,如江南吳江葉氏家族,家族女性皆擅長詩詞,且有集子傳世。這一風氣在《紅樓》更得以體現,她們成立了海棠詩社,作了菊花詩再到螃蟹詠,殊不知女子的才學不輸須眉男兒。黛玉時常悲戚自憐,一時傷懷就能隨手作篇七言律詩來,是何其的瀟灑;寶釵性溫平和,作詩也是四平八穩,更有男子的胸襟氣闊;湘云見柳花飄舞便能偶成一小令,字字鮮趣活潑。女兒家學詩的風氣從香菱身上亦可體現,起初不知音律無法入門,得黛玉的指點后,燈下苦讀孜孜不倦,竟能講出詩的妙處了。雖然讀書寫字對她這樣的下人來說毫無用處,但香菱向學之心卻比其他人都真,誰能不說苦心求詩的香菱著實憨厚可愛呢。
結 語
由于古代嚴格的性別區分,內院閨閣的方位一般在住宅后方,較為私密封閉,不為外人所見。從《紅樓》中可知:閨閣的方位布局與主人的身份地位息息相關,閨閣陳列是女主人的性格投射,閨閣活動雖然單一卻不乏有趣。即使生活在狹隘的一方天地,女子還是會在清晨坐在妝臺前對鏡梳妝開始一天的忙碌,午后的陽光灑進碧紗窗,用汝窯白玉杯煮茶品茗,在中秋品蟹對月吟詠,晚間點起一盞油燈繡起碧水鴛鴦。中國古代女性一直生活在倫理道德的禁錮下,內院閨房是她們永恒的牢房亦是承載著歡聲笑語的地方。雖為女子有諸多的身不由己,可她們還是想著法兒的讓日子變得新鮮有趣。“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就算命運如柳絮紛飛不可把握,也想抓著僅有的光亮活著。青春不過一場恣意歡笑,這些明媚女子的笑聲不應被人忘記,閨閣里時光也不全是虛度。大觀園的一幕幕傾瀉靈動如雨落,醉倒了一片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