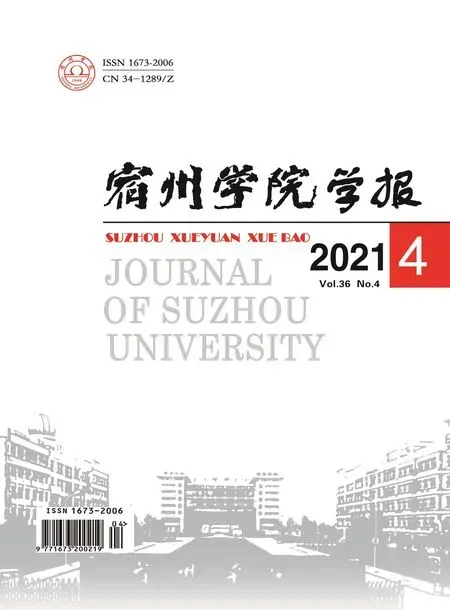李誠與歷史地理學研究
劉文靜
安徽大學歷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1 問題的提出
清末民初的桐城派,于近代復雜多變的歷史環境中艱難發展。在繼承桐城派思想的眾多學者中——李誠,一個普通的教師學者,他的名字與作品并未為大多數人所知曉,目前,學界對他本人和著作的研究亦十分稀少,所發表的大多為總結性和追悼性的文章。如諸偉奇撰寫的《李誠先生與文化傳承》,此文亦是《李誠全集》的序文,文章高度概括了李誠的個人經歷與學術建樹[1]1-9。王達敏在《桐城派學者李誠先生年譜初編(1906—1949)》一文中,依據地方志的記載、李誠的相關文章以及他建國后的工作檔案,采用編年的形式,簡略記述了這一階段李誠的生活、求學、工作經歷,對于李誠的研究而言極具學術價值[2]。他在另一篇文章《論桐城派學者李誠的經世致用精神》中,認為李誠一生秉持求真致用的理論精神,在分析時局的數篇文章和經史研究中所作的釋古之篇都深深表達了他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體現了其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3]。其他涉及李誠的文章都是追悼文,如他的學生馬茂元所作的《致敬老》、吳孟復的《敬夫李先生傳》等,都收錄于《李誠全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克強述寫的《追憶李誠先生》,他認為李誠是一位有實無名的學者、通曉國故的專家,生活樸素卻對國家、民族具有強烈責任感的飽學之士[4]。李誠的作品,無論是文學還是史學都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但目前學界對其研究過少。本文以《李誠全集》為基礎,從歷史學的角度對李誠在歷史地理學的成果進行研究,具體深入分析他的學術成就。
2 李誠的生平概述及學術歷程
李誠,原名澤宗,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陰歷)出生于安徽省石臺縣占大鎮南源村,是桐城派末期名不見經傳的一位學者。幼時勤奮好學、天資聰穎,“秋浦上下譽之為神童”[1]1265。清王朝覆滅后,于1924年入姚永樸掌教的秋浦周氏宏毅學舍求學,因其出色的表現得到姚永樸的賞識。在求學期間,他撰寫了《山西形勢論》這篇文章,得到師長及同學的高度贊揚。兩年后考入南京國學專修館,完成學業后又伴學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馬其昶左右,得其中肯,聘為馬家的私塾塾師。此后李誠就與教師這一身份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任教于桐城馬家雙桂樓私塾、郎溪中學、崇實中學、貴池中學、潔瑩中學、蕪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黃麓師范、阜陽中學、昭明國專、江南文化學院等校,著名學者馬茂元、舒蕪、吳孟復等均受教于他,這期間,他在勤懇地傳道授業的同時依舊堅持鉆研學問。著名學者王達敏曾評價李誠的教學風格是“謹遵桐城派家數,但卻又對駢體文情有獨鐘……”[2]。需要注意的是,他還是一名愛國主義者,時刻留心時局、關心國事。
從青年時期起,李誠就心系祖國,時刻牽掛著民族的未來。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他認為研究歷史軍事地理學可以為國家戰爭的勝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1938年10月,憤然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李誠寫出《貴池歷代兵事志》一文,這是他研究歷史地理學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使用文言文的表述方式闡述了貴池自漢代置縣到清朝的戰爭史,他指出貴池在歷史中經常有兵亂的原因是:“自漢至清,廢興非一,而戰爭在江上者,則貴池為要沖。其歷兵革具如此。”[1]975并總結出貴池歷史上兵禍最嚴重的兩次:一是元末明初,二是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兩者都歷時了10年之久。1939年,李誠又撰寫了《山西抗戰之我見》,此文亦是他研究軍事地理的先鋒之作。文章從地理形勢、自然資源和戰略戰術等方面細致地分析了山西省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認為我國的抗戰必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勝利。
1949年,他被分配到黃山管理處工作。1953年,經著名歷史學家李則綱推薦至安徽省文史研究館任圖書和文史資料管理員一職,長達25年。他的歷史軍事地理學的代表作《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與《三國戰爭志》、歷史文化地理的主要作品《輿地人文紀要》、有關歷史災害地理的《歷代自然災害年表》和其他相關文章均執筆于此時期。李誠先生一生刻苦鉆研學術,著作頗豐,但他于1977年7月23日在合肥的突然逝世導致了一些著作沒有完成,也沒有出版面世。后幸由諸偉奇教授等人的精心點校,《李誠全集》于2019年5月通過海天出版社得以出版。他的全集包含了其文學和史學的大部分作品,史學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歷史地理學,其中又以歷史軍事地理為主,涉及歷史文化地理、歷史地名和歷代自然災害的研究,李誠的研究內容廣博、編撰方式獨具特色、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
3 歷史地理學作品的編撰
李誠的歷史地理學作品的編撰從內容上看有如下幾個特點:(1)以中國史的研究為主體內容。李誠的文章俱在論述中國的歷史,部分涉及外國的內容也是圍繞著中國史展開的,例如,他編寫了關于中國歷代與周邊政權交往的《民族紀要》,是以國家為基礎分別簡略敘述其與中國的外交史,近代以后的內容則僅列舉了向各國派遣大使的年份。其另一篇有關中外時局的文章是《一九七一年上中樞書》,此文論述了東南亞的局勢,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毛澤東軍事理論分析了對印度支那戰爭以及泰國、馬六甲海峽軍事布局的具體內容,并提出先支援泰國革命,以此為基礎再支持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的革命進程,最終得以控制馬六甲海峽以抵御美日的侵略意圖。這些觀點需要在考慮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繼續考證,李誠在文章中也聲明這僅是個人的、片面的、理想的觀點。(2)通史與專史相結合的編撰方式。李誠認為“通史與專史的研究可以相互促進”[1]6,并在文中指出深入研究專史能為通史的編纂提供優質材料,提升通史的質量。但他在史學編撰方式上力求以通史的形式表達,其代表作品《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歷代自然災害年表》和《輿地人文紀要》都是以通史的形式呈現,李誠較為重視通史的優劣,認為“在有了好的通史基礎上,歷史哲學才具有科學性”[1]7。(3)李誠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偏重于軍事地理方面。在《李誠全集》中,涉及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占全書的近百分之七十,而歷史軍事地理學的內容又占其百分之七十,剩下的百分之三十為歷史文化地理學、歷史地名和歷史自然災害的研究內容。他的代表性作品有《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三國戰爭志》《輿地人文紀要》以及《歷代自然災害年表》。
李誠的歷史軍事地理代表作是《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1941年,中華大地深遭日寇的殘忍蹂躪,“李誠下定決心開始了研究中國歷代軍事地理的學術計劃”[2]。這個計劃的最終體現就是李誠前后用了約二十多年的時間編寫的《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但由于突然離世,這部著作只完成了唐朝的軍事地理概論,其后附有《三國時代漢水流域考》《嬴秦疆域擴大考》《西漢人文表》《三國人表》和《(三國)今地名對照表》。此書論述了中國歷代軍事戰爭史,與以往普通的戰爭史所不同的是,它依照正史的內容,融合了多種體裁,并且著重探討了地理形勢對戰爭的重要性,打破了橫向記述的傳統。如李誠在評論十六國時期戰爭特點時,認為:“是故建國立邦者之于雄區優勢,不僅知所以取之,尤在知所以守之。人謀、地利,兩大因素,若配合得宜,實足以制國家短長之命也。至此十又六國,戰爭之跡,或勝或負,疆場之間,一彼一此,又譬若棋劫,則概論詳矣,此不具云。”[1]88但李誠不是地理決定論的擁護者,他強調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而不是決定性,地理形勢只有在戰爭時期才能對歷史的進程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其具體的問題還需辯證看待。
他的另一部重要軍事地理學作品是《三國戰爭志》,這部書按照時間順序分蜀、魏、吳三部分記述了這一時期的戰爭概要,內容側重于戰爭策略和戰爭地理。作者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及胡三省的《資治通鑒音注》中有關戰爭的內容編纂而成,內容多為史料的編排序列,幾乎沒有自己的評論,僅在蜀和吳的篇尾附有汪琬與呂祖謙的評議。此書是李誠在編寫《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的過程中意識到三國時期在中國戰爭史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另開一篇將三國史中的相關史料集中堆積而成,便于學者的研究查閱。《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中也有三國時代的軍事地理的內容,《三國戰爭志》與其不同的是:(1)內容更為詳細,相比而言多了近兩倍的篇幅。前者逐年記述了三國的戰爭史實,后者僅敘述了其中的重要事件;(2)除了基本史實,作者增添的內容不同。前者增加了具體描寫群雄的內容,后者則有《東漢十三部表》和關于袁術、袁紹以及三國遼東地區的軍事情況的論述;(3)文末的評論內容相對較少。前者僅在每一國別的篇末有評論,且缺少對魏的評論,而后者評論較多,大部分事件后都附有一些名家的評語。
在研究歷史軍事地理學之余,李誠對歷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也是碩果累累。最具代表性的是囊括全國省市縣歷史文化的《輿地人文紀要》,此書是以建國后規劃的行政區域為基礎,按照行政級別分區域記述了地方人文景觀、歷史沿革、自然資源以及著名人物等內容。這部著作是傳統歷史地理研究方式的體現,也可以說是中國地方志近現代人文內容的簡略編排。其具體內容旨在強調每一個地方突出的古今人文特點,特別增加了近現代的部分。而關于安徽省的內容則排列在《清代安徽學術》之后,具體的文章有:《安徽古今》《安徽古代史的一頁》《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館》等。上述文章與專門撰述貴池人文的《貴池掌故》以及其他有關安徽人文的文章一起自成體系,突顯了李誠安徽學者的身份。
與此同時,李誠還編寫了一部《歷代自然災害年表》,這部作品遵照時間的順序詳細記述了中國古代六個時期的自然災害情況,亦是由于辭世的緣故,唐朝之后的內容缺失。作者是根據通史、古籍中有關災害內容的記載、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編纂而成。書中所記載的內容十分詳細,每一朝代的每個區域都依時間順序簡潔地羅列出其中影響較大的自然災害,章節后都附有災害表格,可直接查閱,表格中對一些災害還有詳細的描述。但由于沒有完整地梳理出中國歷代自然災害的詳情而使這部作品的史料價值略有降低。
4 歷史地理學作品的編撰特點
李誠立志于編寫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專門通史,在研究的過程中所觸及的領域較為寬廣,因此所寫內容十分繁雜。但是,他在撰寫時采用了不同的文體和結構,既沒有使用統一的格式,也沒有生搬硬套過去的形式,他認為研究歷史地理要在對已有資料詳細搜集和科學判斷的基礎上,“創造新的體制的著作,以適應今天的學術水平,以期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1]1156因而他的文章具有獨特的編纂特點,詳細歸納解析如下:
第一,多種體裁的靈活使用。李誠在撰寫歷史地理學的文章時以自己所掌握的中國古代傳統史學的編撰體裁為基礎,根據不同的寫作內容將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編年體以及相關的表志體裁進行相應的排列組合后再運用。
他撰寫歷史軍事地理所用的體裁是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和編年體的混合。如《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通篇是按照朝代先后的順序編排,而其中的每一章節又使用了不同的編纂方式。三國時代先是以紀傳體的格式論述了十一個具有關鍵意義的人物,內容則僅僅表述相關人物的戰爭經歷,文末偶爾會附上作者的簡單評論。在此之后,作者又運用紀事本末體分別將蜀、魏和吳的戰爭史呈現出來,并且在文末附有陳亮、王夫之、鄭與僑等人的評論。兩晉和十六國時期都是用紀事本末體分政權記述其戰爭史,文末少有評論。南北朝時期的編撰則是編年體和紀傳體的結合,南朝分政權,先介紹了戰爭背景,再依時間的先后順序用表格的形式列出詳細的戰爭情況,最后分析該戰役的政略和戰略;北朝政權更替頻繁,除了后魏是和南朝一樣的編撰方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是依照時間的順序撰寫于同一個章節,文末都沒有評論。隋代內容的編寫使用紀事本末體,以征討的對象為標題,記錄了八次著名的戰爭。唐朝,總體上是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結合,篇目的編排按照時間順序,第一部分用紀傳體記述了唐朝統一過程中征討的地方起義首領的戰爭經歷;第二部分記錄了征伐周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戰爭;第三部分著重描述了安史之亂的戰役經過;第四部分只有一篇敘述劉展擁兵亂戰的文章,全書止于此。而《三國戰爭志》的主要內容是記述三國時期的戰爭概要,此編“包羅了紀傳、紀事、本末、編年以及編年體中的綱目的多種體裁,每國自成一個長編,有原有委,按年紀錄,每年有綱有目”[1]392。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池陽雜俎》中的《貴池歷代兵事志》,“ 此書體例,一仿 《史記》八書”[2]。其他單篇文章的格式則是簡單的小論文,篇幅較短,不再贅述。
而在歷史文化地理相關作品的編撰過程中,李誠則參考了中國古代地方志的格式。他說:“新的時代要求,即對過去朝代的各個地區有一個正確了解,所以這種新體制的著作,勢不能不應運而生,那就是歷史地理和方志的一元化的著作。”[1]1159如《貴池掌故》就是按時間順序,摘錄史書、名人著作和地方志中關于貴池的記載內容,其后附有桂超萬丹盟的十六首詩。李誠對歷史地名和歷代自然災害的研究作品都是照搬紀傳體表、志的格式進行撰寫的。前者的內容與結構和古史沒有太大的差異,僅僅可作為考證的工具。但是后者的撰寫方式需要詳細地說明。對中國歷代自然災害的研究成果體現在《歷代自然災害年表》中,它的大體結構是災情簡文與災害年表相結合的格式。其內容按照時間的次序,分先秦、西漢、東漢、三國、西晉和唐時期載述。每篇第一章總寫這一時期的災害情況,并在開篇詳細羅列編寫此章所參考的史書;第二章則寫各地區的災情,文字簡明扼要;最后一章按照時間的順序,標注相應年號,分雨水、旱蝗、風霜冰雪寒暑、饑疫和地震,將其災害情況濃縮在表格中。
第二,求真致用的學術宗旨。求真致用是中國史學家自古以來的優秀傳統品質。李誠在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過程中很好地繼承了這個傳統,并不斷地在字里行間中體現出來。
李誠師從桐城派,承襲其治史思想的特征,主要體現為重視史料的考據和搜集。桐城派的學者認為這是追求歷史真實性的必要手段,表明了他們治史的求真性。馬其昶曾說:“凡一代名臣魁儒,遺文軼事搜討尤勤,此其功在天下,后世更何如耶。”[5]34姚永樸在《與清史館論修史書》中也認為修史“應搜閱典籍,按日撮鈔,以為預備,不可遽責以起草。茍蓄材既富,下筆亦復何難。”[6]134李誠認為,研究歷史可以從正史、方志、詩文集、筆記和天文史料中找尋資料。他在《關于研究歷史地理的幾點意見》和《怎樣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自然災害規律》兩篇文章中總結了具體的搜集資料的途徑、方法、要求和特殊事項:(1)搜集正史和方志中的各種史料后,要注重探討和發現其中所蘊含的客觀規律。(2)在搜集繁雜的史料過程中要結合現實需求,所用資料貼切當下情況,力求所寫文章能為國家建設發展提供借鑒的效果。(3)尊重歷史的客觀性。“在著手研究歷史地理的時候,遇到許多從現在看來是不重要而在當時卻關系重要的資料,應該給予它應有的地位,這就是照顧到歷史真相,保存著客觀過程。”[1]1158(4)所收集的資料必須是貫通性的、全面的,也就是全國的相關材料都要集齊。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局部自然災害的研究按照自然區域比按行政區域的劃分更具科學性。(5)在資料收集的工作中還要注意史籍的特殊情況。由于政治和人為遺漏、銷毀而造成的資料缺失,不能盲目判斷情況。例如,“封建王朝對國都所在地的自然災害事件,記載得多而詳;距國都較遠地區,記載得較少而略。”[1]1163因此,不能籠統地以偏概全。
對于史料的考據,李誠的研究成果呈現在地名考證方面。首先,他堅持有地必考的考證原則,體現了歷史地理學史地結合的研究方法。無論哪篇文章,只要涉及到地名,李誠一定會在地名后或者著作后的附錄里寫出其古今的歷史名稱和具體位置。即使一個相同的地名在不同的文章出現也會重復解釋,從不一筆略過。比如在《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中,三國時代記述姜維伐魏時,寫道:“景耀五年,出洮陽,戰侯和。”[1]26李誠在此句后為洮陽這個地名作了詳細的注釋,他先是摘錄了《通鑒》注“洮陽,洮水之陽也。侯和在塞內”[1]26,再加以《通典》的注“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1]26。得以佐證,最后加上自己的考證內容:“唐臨洮郡故治,在今臨潭縣西南。”[1]26而在《三國戰爭志》描述同一件事的時候,李誠也為洮陽直接引用了《通鑒》作了注:“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1]417。兩處考證的注釋主體一致,僅根據具體內容而略作變通。其次,他廣集史料,利用不同種類的史料進行考證。李誠在考證地名的過程中,主要的注釋來源是正史中的《資治通鑒》。此外,還采用了歷史地理學類的著作,如《讀史方輿紀要》《水經注》與《太平寰宇記》等,還有典章制度類的史料,如《通典》《后漢志》《長安志》等以及個人著作——楊佺期《洛陽記》、張瑩《后漢南記》等。再次,李誠的考據審慎細致,格式多樣,并且點出了一些誤傳。在《中國歷代軍事地理概論》中,簡述了諸葛亮第五次伐魏:“圍祁山,戰于上邽、鹵城。”[1]23在其后的注釋明確指出:“六役中,祁山之役僅僅兩次,俗謂‘六出祁山’者,誤也。”[1]23
李誠研究歷史地理學歸根結底是為了能夠以史為鑒、經世致用,即史學研究的致用性。李誠關于歷史軍事地理的研究方法直接繼承了徐松、張澍和俞正燮的學術傳統。晚清史地學者大多心系家國大事,他們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經世致用。郭書蘭總結徐松的學術特點是“務實求新,以經世致用為目的,對史料的采摭非常審慎。”[7]徐松亦說:“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邊防、食貨、兵志,皆其所有事也。”[8]再如醉心于方志學的張澍,他“編纂方志其目的在于經世致用,把地方志提到與史書同等重要的位置”[9]。特別需要提及的是俞正燮,他在研究中國邊疆史地時特別關注民族關系,寫出了《駐札大臣原始》《喀爾喀伊犁》《阿拉善》《蒙古》等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很高的邊疆民族關系著作。這對李誠創作《民族紀要》和《南中七郡》有著直接的影響。
在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下,李誠提出研究歷史地理要注重時間性和區域性,適當地做到兩者的有機統一。在時間上,斷代或者按照朝代特點劃作若干時期或階段來研究是比較合適的時間斷限方法。而在區域上則是要將所收集的資料中所有關于此地的內容歸結到一處,再按照時間或其他順序編排。在此基礎上,“能夠一朝一朝地積累,一地一地地明確,然后使各朝代有其時間性,各地方有其區域性,并且有機地體現兩者的統一。”[1]1156有關區域性的研究,李誠提出歷史地理和方志研究的一元化。歷史地理研究的資料來源除了正史,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中國古代的地方志。但是,由于種種緣故,地方志的質量層次不齊,這就需要研究者自己去排查史料,從大量無用的史料中獲取極少的有用信息,造成研究過程的繁雜化。在作者所處的年代,中國古代地方志的研究工作正處于大規模的收集和整理階段。從歷史地理研究的角度出發,李誠主張,“為了正本清源,把每一朝屬于每一地區的一切事件,廣泛搜集;在這一工作中,凡所有載籍、實物、口碑、傳說,無所不包。那么方志中所有有用的、正確的資料也就被這種披沙煉金的方式挑選出來了。”[1]1159需要明確的是,這僅是從研究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去搜集和整理地方志的手段,也表明了二者一元化的可行性。
第三,傳統與時代結合的研究之路。與中國近現代的很多歷史地理學者一樣,李誠的學術歷程也“是舊式研究方法和新式的結合創新,旨在探討一條創新的研究之路”[10]。
李誠的學術經歷和特點以新中國的建立為隔點,可分為兩個時間段進行探討。新中國成立前,李誠接受了舊式的私塾教育,為他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功底。在此基礎上,桐城派的治史思想和傳統的史地研究思路,對李誠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我國史學研究的主流思想,學界大多學者都逐漸接受此學說。李誠在建國前就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有所涉獵,在之后的史學研究中,更是在秉持自身優秀傳統史學思想的同時,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進行探索真知。他在學術研究中,全面地收集史料,謹慎地鑒別資料,在求真求實的基礎上尋找其中的客觀規律。同時,他的史學研究也都極力地與現實要求相結合,辯證地看待現實問題。
在研究歷史軍事地理時,李誠也參考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家的理論思想。1924年,李誠在秋浦周氏宏毅學舍所作的《山西形勢論》和抗日戰爭時期所寫的《山西抗戰之我見》兩篇文章最能體現他建國前后思想的轉變。《山西形勢論》是根據中國歷代的史料記載,分析出山西成為要塞的原因——地形和兵力的優勢,認為“若更能得一方之歡,防戍益少,兵力益足,然后依形勝之自然,相時而作,庶可以有為矣。”[1]1149但是,李誠作此文的時候正值求學時期,還未接受新思想,對當前國內國際形勢未能準確的把握,加之日本還未全面侵華,他彼時的觀點不是很客觀,也不能算是研究性的作品。而在《山西抗戰之我見》一文中,李誠認為我國在山西擁有地理形勢、物資和人力、戰略戰術的優勢,高度肯定了中國共產黨敵后戰場的功勞,突出贊譽了運動戰的成功,高度地贊美了軍民合作的戰斗方式,堅定了抗日戰爭必勝的信念。彼時,李誠的文章已具有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覺悟,這也促成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最終提高了自身的認知和學術水平。
總體上看來,李誠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還是以舊式的方式為主,即使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進行文章的編撰,但從表達方式、編寫內容以及編撰方法等方面都溢滿著清末民初桐城派的味道。他的代表著作《中國歷代軍事概論》與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還有一些相似之處。《讀史方輿紀要》論述了地理形勢對于戰爭的重要性,以及主要戰役在歷史進程中的影響。它的內容特點是“歷代州域,以朝代為經,地理為緯;省府形勢,以地理為經,朝代為緯,經緯互持,縱橫并立,眉目清晰,體例新穎”[11]。和李誠相同的是他們都具有經世致用的治學思想,重視地理形勢在戰爭中的作用,辯證的看待人物和策略的作用,著作的內容都聚焦歷史軍事地理,但也不忽視人文經濟以及其他自然因素。而他們的不同之處,李誠在其序文中也指出,他認為顧祖禹的著作更注重于橫向史實的羅列,與此相反,他則偏重于縱向的論述;顧祖禹書中論述歷代州域形勢的篇章,在其一百三十卷中只有九卷,但他的這部書全部都在闡述此內容。
第四,文白結合的語言描述方式。收錄入《李誠全集》的作品,其語體是白話文和文言文的雜糅使用,篇幅、位置的不同所使用的語體不盡相同。
李誠文章的大部分內容使用的語體是文言文,而這些文章的寫作年份大都在建國以后,對此,他的解釋是:“此書是用文言寫出,卷帙也還相當多;假如改用語體,字數起碼要增加三分之二,這就是迫使作者不得不采用了過時的文言。不僅因為文言是語體的提綱,而且握管之際可以少寫幾個字。”[1]8這也體現出老一輩學者勤儉節約的生活作風。另一方面,作者寫作的參考資料主要來源于用文言文寫成的古代史書,并且文章中的一些注釋和評論也是從中引用,如果都用白話文則會失去原有的意義和韻味,同時也會增加作者的翻譯量,延長創作時間。這也是桐城派的修史特點之一,在修史的過程中十分重視文字的表達,甚至提倡使用雅潔的古文來修史。如姚永樸在《史學研究法·史文》開篇中說道:“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況史也者,尤為經過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使無文以張之,何以廣見聞而新耳目乎?”[12]雅潔這一文論由清代著名學者方苞提出,“所謂書寫雅潔之語言,是指在歷史著作中的語言文字表述準確、詳略得當,敘事詳實不拖拉。”[13]在全集中只有大部著作的序言、不成系統的小文章以及登報上呈的文章使用白話文體,這是響應當時學界要求,亦是方便現代讀者需求的行為。
5 結 語
李誠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多集中于軍事地理方面,這在整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也是少見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李誠的研究內容不僅與國家軍事大事相關,還與社會民生的小事緊密相連,這充分顯現出其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而與現實密切相關的研究,將對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建設貢獻學術力量,正如藍勇認為對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無疑會對今天的經濟建設提供許多借鑒和參考,可對未來的發展提出具有規律性的預見”[14]。這體現了他學術的現實意義。
李誠在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僅局限于歷史地理學,還有清代學術史以及安徽地方史的內容。除此之外,他內容豐富的全集中也包含文學研究,其中涉及對桐城派學者的評論、對唐宋八大家的研究、唐持盈先生遺詩和一些雜著讀書隨筆。因此,對于李誠著作的繼續研究還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對于桐城派的研究,學界多偏重于文學方面,關于桐城派后期學者的研究又以馬其昶、姚永樸等為主,從史學的角度亦得出了大量的史學結論。相較而言,對于一些學識豐富卻無甚名氣的學者學術成果的研究較少。這就造成了桐城派史學研究的不均衡,對李誠的史學成就研究,正是在更廣闊的范圍內發掘桐城派學者的史學成就,也有利于桐城派研究的均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