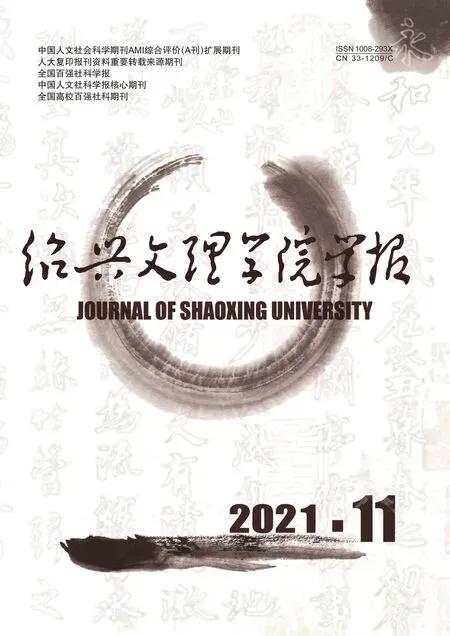“逸”與“易”:唐彪《讀書作文譜》對(duì)歐文的評(píng)價(jià)及其古文觀念
魏 榕
(北京大學(xué) 中國(guó)語言文學(xué)系,北京 100871)
清初塾師唐彪,字翼修,金華人。作《讀書作文譜》十二卷,為習(xí)舉業(yè)者傳授讀書作文之路徑,是研究清人教學(xué)法的重要文本,對(duì)了解基層塾師與普通士子的讀書作文實(shí)踐具有獨(dú)特意義。在卷十“評(píng)古文”的“歐文”一則中,唐彪稱歐陽修文章“為古學(xué)津梁”“宜為后人取法不置”,引茅坤《廬陵文鈔引》,稱贊“得太史公之逸者,獨(dú)歐陽子一人而已”[1]3545,標(biāo)舉歐文獨(dú)得《史記》之遒逸風(fēng)神。然而在《讀書作文譜》“韓文”一則下,唐彪又引朱子“韓不用科段,直將說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有結(jié)構(gòu);若歐曾卻各有一個(gè)科段”“韓文高,歐文易學(xué)”[1]3544諸語。在與韓文比較中,使歐文的“易學(xué)”特色含有文章等第降格的意味。但在“評(píng)古文”的“總評(píng)”一則下,唐彪則重新強(qiáng)調(diào)歐蘇文章的易于入手,稱“初學(xué)者尤宜先讀,以為造就之階,則工夫易于入手矣”[1]3548。將其比為初學(xué)者的“造就之階”,正是緊扣“易學(xué)”這一特點(diǎn)來極力推崇。唐彪在論及歐文時(shí),著重強(qiáng)調(diào)其“遒逸”與“易學(xué)”兩個(gè)特點(diǎn),而“易學(xué)”這一特色又同時(shí)兼具褒貶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
閱讀《讀書作文譜》,能夠感受到唐彪的古文觀念,包括其對(duì)唐宋古文家的等第判斷、對(duì)古文優(yōu)劣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乃至其背后的各種思想資源,時(shí)常存在著種種縫隙、含混與矛盾之處。唐彪《讀書作文譜》論唐宋古文的框架,延續(xù)了傳統(tǒng)文章學(xué)以“家數(shù)”為依據(jù)的劃分慣例。學(xué)者胡琦在《宋元理學(xué)家讀書法與“唐宋八大家”的經(jīng)典化》一文中指出,唐宋古文譜系以“大家”為中心的經(jīng)典化發(fā)展歷程,可以追溯至宋元理學(xué)家的讀書法[2]。而在朱子一系理學(xué)家的觀念里,韓愈無疑是唐宋古文“大家”中的冠首,韓文則是古文學(xué)習(xí)次第中的第一入手處。在最為詳盡地闡釋理學(xué)家讀書功夫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程端禮專列“讀韓文”一章,稱韓文為一生之“作文骨子”[3],強(qiáng)化了韓文在唐宋古文家中的至高地位。然而隨著后世各派古文家的次第登場(chǎng),這一“韓文至上”的古文等第漸漸產(chǎn)生了某些松動(dòng)。尤其在明代,經(jīng)由歸有光、茅坤等人的提倡,新的古文統(tǒng)系被建構(gòu),歐文漸漸呈現(xiàn)出與韓文比肩甚至在某些方面壓過韓文的趨勢(shì)。
在唐彪的《讀書作文譜》中,其對(duì)歐文“遒逸”的推崇、對(duì)歐文“易學(xué)”的復(fù)雜態(tài)度,實(shí)則包含著多種古文觀念的影響,并能由此透露出唐彪個(gè)人對(duì)古文功用的看法。因此以唐彪對(duì)歐陽修文章的評(píng)價(jià)態(tài)度為切入點(diǎn),可以幫助我們探尋唐彪古文觀念的成因,以及在這種古文觀念的背后,作為塾師的唐彪編寫《讀書作文譜》的用意所在。
一、“得太史公之逸者,獨(dú)歐陽子一人而已”
在《讀書作文譜》中,唐彪不僅引茅坤《廬陵文鈔引》說明歐文上承《史記》之“逸”,又自言“歐文胚胎乎《史記》”[1]3545。可見唐彪對(duì)歐文的推崇與歐文對(duì)《史記》的繼承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即有文人指出歐文與《史記》的聯(lián)系,例如韓琦言:“子長(zhǎng)、退之,偉贍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4]19蘇軾亦稱歐陽修“記事似司馬遷”[4]90。然而最先將歐文與《史記》的關(guān)系以所謂“遒逸疏蕩”的“風(fēng)神”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應(yīng)屬明代唐宋派古文家歸有光與茅坤。歸有光在評(píng)點(diǎn)歐文時(shí)言:“風(fēng)神機(jī)軸,逼真太史公。”[4]544茅坤在《刻史記抄引》中稱《史記》“疏蕩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間”[5]820,以“疏蕩遒逸”形容《史記》。在《刻漢書評(píng)林序》中稱:“《史記》以風(fēng)神勝……惟其以風(fēng)神勝,故遒逸疏蕩,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齒頰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5]567則將《史記》之“風(fēng)神”歸結(jié)為“遒逸疏蕩”的風(fēng)格。在《廬陵文鈔引》中,茅坤在對(duì)《史記》的“風(fēng)神所注”進(jìn)行一番形容后,最終導(dǎo)向“得太史公之逸者,獨(dú)歐陽子一人而已”[6]324的結(jié)論。可見在茅坤的論述中,已明確將歐陽修作為得司馬遷“風(fēng)神”的傳人,而所謂“風(fēng)神”,即是“疏蕩遒逸”的風(fēng)格。
茅坤對(duì)“遒逸”的偏愛,也影響了他對(duì)唐宋古文家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比如其編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卷首的《論例》篇中,他在開篇即對(duì)比了韓歐“碑志體”文章:“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志,予獨(dú)以韓公碑志多奇崛險(xiǎn)譎,不得《史》《漢》序事法,故于風(fēng)神處或少遒逸,予間亦鐫記其旁。至于歐陽公碑志之文,可謂獨(dú)得史遷之髓矣。”[6]15茅坤在此以“風(fēng)神”“遒逸”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韓愈碑志文“于風(fēng)神處或少遒逸”,而歐陽修則“獨(dú)得史遷之髓”,因此認(rèn)為歐文更勝一籌。實(shí)際上茅坤構(gòu)建了一個(gè)新的古文統(tǒng)序,正如他在《廬陵文鈔引》里所言:“西京以來,獨(dú)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fēng)神所注,往往于點(diǎn)綴措次獨(dú)得其妙解,譬之覽仙姬于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shù)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所以獨(dú)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xué)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dú)歐陽子一人而已。”[6]324
司馬遷為西京以來第一人,而能夠接續(xù)司馬遷“逸調(diào)”文脈的,惟歐陽修一人。雖然茅坤也將韓愈的位置提得很高,稱“累數(shù)百年而得韓昌黎”,但是韓愈畢竟“別開門戶”,并不在史遷風(fēng)神的文脈里。這樣的文統(tǒng)構(gòu)建,實(shí)際上包含了一種將歐文位次升格的意味。學(xué)者黃卓穎在《茅坤古文選本與批評(píng)——“逸調(diào)”的提出、運(yùn)用及其意義》一文即指出:“(茅坤)新建起一個(gè)最高的經(jīng)典序列和文家譜系。具體來說,就是將歐陽修從以往的‘韓歐’‘歐曾’‘歐蘇’等并稱中分離出來,進(jìn)一步拔高,賦予其西漢以下第一人的地位,直接司馬遷的傳統(tǒng)。”[7]103
在此還要特別關(guān)注一點(diǎn),在唐彪引述這段《廬陵文鈔引》的文字時(shí),刪去了“累數(shù)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一句。其目的固然可能出于簡(jiǎn)省文字篇幅,但也恰恰可以證明,在唐彪的觀念中,韓愈并不在這個(gè)由司馬遷開啟的文章譜系之中。通過這樣的刪減,使得“司馬遷——?dú)W陽修”這一統(tǒng)序更為清晰明了。
茅坤對(duì)歐文的推崇、對(duì)“遒逸”風(fēng)格的欣賞,顯然影響了唐彪的古文觀念。在《讀書作文譜》“評(píng)古文”一節(jié)中,唐彪共6次引用茅坤語,僅次于對(duì)朱熹的引錄(8次)。而唐彪對(duì)“遒逸”風(fēng)格的喜愛,也特別體現(xiàn)在其對(duì)《史記》文的評(píng)價(jià)中。在“評(píng)古文”一節(jié)中,“《史記》”一則篇幅最長(zhǎng),大約是評(píng)韓歐文的三倍,足見唐彪對(duì)《史記》的重視。唐彪稱《史記》:“如天馬行空,不可蹤跡,可謂化工之巧,非人力所能仿佛矣。”“其筆端變化, 或起或伏, 或即或離, 縱橫出沒, 不可捉摸。”[1]3541-3542著意強(qiáng)調(diào)《史記》文風(fēng)“不可蹤跡”“不可捉摸”的“化工”境界,此與所引茅坤之“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間,可望而不可挹者”諸語,大抵相類。唐彪稱“司馬子長(zhǎng)之文,為古今第一”[1]3541,即與茅坤古文譜系中的判斷相一致。
在歸有光、茅坤之后,類似的推重歐文的觀點(diǎn)屢見于晚明清初文人的論說中。例如艾南英極崇歐文,曾稱“即以史遷論之,昌黎碑志,非不子長(zhǎng)也,而史遷之蹊徑皮肉,尚未渾然。至歐公碑志,則傳史遷之神矣”[4]626。他對(duì)比韓歐碑志,認(rèn)為歐公傳史遷之神,其論調(diào)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所言大致相同。又如文壇宗主錢謙益稱歐陽修“其功不下于韓”,并贊美其“綽有太史公之風(fēng)”[4]642,同樣認(rèn)可歐文直承《史記》的文脈。再如魏禧,也曾論及歐文之風(fēng)格,“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fù)、參差離合之致”[4]689,這同樣是針對(duì)其遒逸疏蕩的藝術(shù)特色而言。由此可知,晚明以至清初,對(duì)歐文與《史記》的關(guān)系及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已有不少討論,并形成相當(dāng)?shù)墓沧R(shí),而這些觀點(diǎn)也很有可能加深唐彪對(duì)歐文的認(rèn)同感。
二、“易學(xué)”背后的復(fù)雜態(tài)度
在“遒逸”之外,唐彪對(duì)歐陽修文章的另一個(gè)重要評(píng)價(jià)即是“易學(xué)”,然而這一評(píng)價(jià)背后卻暗示了較為復(fù)雜含混的古文觀念,這也正是導(dǎo)致唐彪對(duì)歐文等第判斷模糊的關(guān)鍵問題所在。
(一)朱子古文評(píng)論的影響
前文已提及唐彪“評(píng)古文”一節(jié)中,對(duì)朱熹的引用次數(shù)是最多的,其中涉及到對(duì)歐文品格進(jìn)行判定的,主要是這一條:
或問于朱子曰:“要看文以資筆勢(shì),助發(fā)義理,何者為要?”
朱子曰:“予看《孟子》、韓文不用科段,直將說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有結(jié)構(gòu)。若歐曾卻各有一個(gè)科段矣。”
又曰:“韓千變?nèi)f化,無心變,歐有心變。韓文高,歐文易學(xué)。”[1]3544
這段話引自《朱子語類》“論文”。朱熹認(rèn)為韓文“不用科段”“無心變”,而歐文“有科段”“有心變”,故此判定韓文高于歐文。在上述語境中,歐文的“易學(xué)”是一個(gè)略帶貶抑色彩的評(píng)語。實(shí)際上在朱子的古文評(píng)論中,他不止一次提到“易學(xué)”這一概念。例如在比較韓文與柳文時(shí),朱熹說:“柳文是較古,但卻易學(xué),學(xué)便似他,不似韓文規(guī)模闊。學(xué)柳文也得,但會(huì)衰了人文字。”[8]3302-3303在這里,柳文的“易學(xué)”同樣是一個(gè)較為消極的判斷。那么受到朱熹古文評(píng)價(jià)的影響,唐彪在“韓文”一則下,以韓文為“至虛靈之文”,稱其“如海市蜃樓,千形萬態(tài),不可摹擬,茲約一言以贊之,曰:百體具備而不落窠臼者”[1]3544,著重強(qiáng)調(diào)韓文的不可摹擬、不落窠臼,也即“不易學(xué)”之處。因此以朱子所謂之“易學(xué)”內(nèi)涵來衡量,則唐彪在“韓文”一則里表露的態(tài)度,無疑是歐文落韓文一等。
實(shí)際上,在朱熹的文章觀念里,《史記》并不是合適的文章取法對(duì)象。朱熹曾明確表示:“《史記》不可學(xué),學(xué)不成,卻顛了,不如且理會(huì)法度文字。”[8]3320-3321那么在朱熹看來,學(xué)文章究竟該從何入手呢?朱熹在指點(diǎn)學(xué)人文字功夫時(shí)表示,作文當(dāng)“看得韓文熟”,同時(shí)反對(duì)“先看柳文再看韓文”的做法,認(rèn)為“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8]3320。由此可知,朱熹主張以韓文為學(xué)文入手處,而如柳文之類,雖然“易學(xué)”,但并不意味著要先學(xué)。在朱熹之后,朱門學(xué)人程端禮則將朱子的文章觀念更為明晰化,制定了一套讀文作文的功程軌則。在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中,“讀韓文”是為作文而準(zhǔn)備的重要功課,而歐文等其他唐宋古文,則是在讀過韓文之后“選看”即可的。此外,程端禮還引錄其師果齋先生史蒙卿之語,史蒙卿將讀書比作煉銅,是“極用費(fèi)力”之事[3]。由此可知,在理學(xué)家的觀念中,“學(xué)”這一環(huán)節(jié)本就不是“容易”的事。
(二)“作文”的實(shí)用導(dǎo)向與“切近易入目”的方便之法
在朱子一系理學(xué)家的讀書法中,韓文的等第高于歐文,學(xué)文亦以韓文為先。在“韓文”一則中,唐彪似乎接受了理學(xué)家對(duì)“易學(xué)”的貶抑態(tài)度,然而縱觀《讀書作文譜》中的古文評(píng)論與學(xué)文、作文法,唐彪其實(shí)更多地體現(xiàn)出一種對(duì)“易學(xué)”特點(diǎn)的積極接納與提倡。在“評(píng)古文”的“總評(píng)”一則中,唐彪指出:“至于永叔、子瞻之文,初學(xué)尤宜先讀,以為造就之階,則工夫易于入手。”[1]3548在這里,他對(duì)歐蘇文章的推崇正在于“易于入手”。在接下來的“論讀古文”一節(jié)中,唐彪更是討論了唐宋八家之文與周秦兩漢之文的關(guān)系,雖然認(rèn)為八家之文皆出自周秦兩漢之文,不可“尊八家而忘周秦史漢”,但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茍躐等為之,不讀八家而竟驟希乎周秦史漢,恐不能學(xué)其高雋,而且有畫虎不成之弊矣,故學(xué)古宜以漸入也”[1]3551。通過這段討論可以發(fā)現(xiàn)唐彪更重視“漸入”,強(qiáng)調(diào)應(yīng)該為學(xué)人設(shè)立可以次第漸進(jìn)的學(xué)文階梯。
唐彪在“評(píng)古文”后,又依次討論了“論讀古文”“論選古文”“作古文宜自成一家”,可知其落腳點(diǎn)在于作文。縱覽整部《讀書作文譜》,其大半內(nèi)容也都是在為作文服務(wù),而作文的最終導(dǎo)向?qū)嶋H上即是應(yīng)對(duì)科舉的時(shí)文寫作。因此在這種極具現(xiàn)實(shí)針對(duì)性的作文目的下,“易學(xué)”批評(píng)背后所關(guān)聯(lián)的古文格調(diào),以及理學(xué)家“切磋琢磨”的讀書涵養(yǎng)都不再是眼下的第一要?jiǎng)?wù)。對(duì)唐彪以及《讀書作文譜》所面向的那些急于應(yīng)舉的士子而言, “易學(xué)”“易入”恰恰是最急迫的需求。
其實(shí)在《讀書作文譜》中,唐彪不僅只在學(xué)古文的環(huán)節(jié)推崇漸進(jìn)易入的方法,在整部書中,唐彪都始終不忘為學(xué)子設(shè)立“切近易入目”的方便之法。比如在《讀書作文譜》卷一開篇,唐彪就首先聲明:“凡書之首卷,不得不將根本功夫言之,正慮初學(xué)見之,以為迂闊無當(dāng)也,然不可因此將全書棄去不閱。后盡有切近易入目者,請(qǐng)隨意從后卷閱起可也。”[1]3395《讀書作文譜》首卷第一則為“學(xué)基”,主要討論的是一些綱領(lǐng)性的為學(xué)準(zhǔn)則。而唐彪在此已經(jīng)顧慮到追求實(shí)用指導(dǎo)的士子可能會(huì)對(duì)這些觀念性教條產(chǎn)生厭倦,故而在最開篇便事先說明此后“盡有切近易入目者”,可隨意從后卷閱起,姿態(tài)不可謂不平易。
又如在讀經(jīng)的問題上,唐彪考慮到各人資質(zhì)與精力差異,他“為科舉之士籌,為下資設(shè)法”,設(shè)立了“刪讀諸經(jīng)法”,對(duì)“中資”“下資”之人皆有不同的安排。再如論及時(shí)文與古文時(shí),出于對(duì)大部分士子應(yīng)舉需求的考量,他主張“科舉之學(xué),除經(jīng)書外,以時(shí)文為先務(wù)”[1]3402“童子幼時(shí)急需在于時(shí)藝,故當(dāng)先讀時(shí)藝,至?xí)r藝讀二百篇后,則當(dāng)半月讀古文,半月讀時(shí)藝”[1]3404。此外,作為一位在基層常期任教的塾師,唐彪也能充分考慮到士子求學(xué)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種種現(xiàn)實(shí)困難,比如他主張讀經(jīng)須有師講解,但是又考慮到“貧者欲延師而授,恐力有不能”,于是“余再三思維,設(shè)為三法”[1]3407,其積極嘗試解決學(xué)子實(shí)際問題的態(tài)度可見一斑。
據(jù)趙伯英、萬恒德的推算,唐彪生于1644年前后,也即明清易代之際,活躍于康熙年間[9]。唐彪具體生平經(jīng)歷已難詳考,但根據(jù)仇兆鰲、毛奇齡序文中“向者秉鐸武林,課徒講學(xué),人士蒸蒸蔚起”[1]3385“出為師氏者若干年”[1]3384等表述,可知唐彪有著極為豐富的基層教育經(jīng)驗(yàn)。而在明清時(shí)期,士子對(duì)科舉的熱衷程度已遠(yuǎn)遠(yuǎn)超過朱熹、程端禮等理學(xué)家所處的時(shí)代,時(shí)文寫作也因此成為大部分讀書人的首要任務(wù),顧炎武就曾在《生員論》中指出:“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jì),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chǎng)屋之文。”[10]正如劉曉東在《明代的塾師與基層社會(huì)》中所總結(jié),明中葉以后“民間社會(huì)對(duì)童蒙教育之價(jià)值需求,漸由重‘德’轉(zhuǎn)向了重‘利’”,父兄“每見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覽,便恐妨正業(yè),視為怪物”[11]。雖然時(shí)人對(duì)此現(xiàn)象多有批評(píng),但世風(fēng)畢竟難以扭轉(zhuǎn),埋首帖括、窮究制義仍是大部分讀書人的選擇,而唐彪既為當(dāng)時(shí)執(zhí)教塾師,則其所慮必為學(xué)生功名考量,如其所言:“功名既得,則有功業(yè)傳于后,豈不更勝文章傳后者乎?”[1]3471由此可窺見其價(jià)值取舍,亦可知《讀書作文譜》所急之“要?jiǎng)?wù)”仍在于舉業(yè)。所以出于現(xiàn)實(shí)的需求,唐彪雖了知理學(xué)家對(duì)“易學(xué)”的批評(píng),但仍要大力標(biāo)舉“易學(xué)”的實(shí)用價(jià)值。
三、《讀書作文譜》的引文資源與唐彪古文觀念
唐彪對(duì)歐文復(fù)雜態(tài)度的背后,體現(xiàn)了《讀書作文譜》思想資源的多元性,這一點(diǎn)也體現(xiàn)在他的引文選擇上。在《讀書作文譜》中,唐彪“多引他人之言”,且在《凡例》中特別聲明:“天下之理有歸一者,亦有兩端者,歸一者易見,兩端者難明……是書于古人之議論有不同者,必兩存之。”[1]3393因此當(dāng)考察唐彪的引文情況時(shí),可以發(fā)現(xiàn)其引文選擇的兩個(gè)特點(diǎn):一、選擇范圍廣;二、不同觀點(diǎn)之間有時(shí)存在矛盾。
在最能反映唐彪古文觀念的“評(píng)古文”一節(jié)中,唐彪即引用了朱熹、蘇軾、林云銘、陸西星、王世貞、茅坤、林駉、歸有光、錢謙益、葉適、胡應(yīng)麟、凌約言、林艾軒、金履祥等多人的觀點(diǎn),不僅時(shí)間跨度上至北宋下至清初,且上述諸人古文觀念、身份立場(chǎng),乃至學(xué)問層次的高下都各不相同。例如“蘇文”一則中,唐彪既引葉適贊蘇文“真古今議論之杰”[1]3546諸語,同時(shí)又引朱熹“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文章,有才性人便須收拾規(guī)矩,不然文字蕩無結(jié)構(gòu)”[1]3546-3547,從另一個(gè)角度表達(dá)對(duì)學(xué)習(xí)蘇文的顧慮,而朱熹與葉適思想觀念與治學(xué)路徑本身即存在針鋒相對(duì)之處,這也是唐彪有意“兩存之”的表現(xiàn)。又比如在《讀書作文譜》中,我們常常很難判斷唐彪的古文趣味究竟更傾向于“周秦史漢”還是“唐宋八家”,其原因就在于他對(duì)復(fù)古派與唐宋派的觀點(diǎn)都有接受吸納,比如從引文上看,唐彪對(duì)王世貞與茅坤的觀點(diǎn)皆有引錄。另外,唐彪不僅廣錄名家之語,更能向下兼容,例如在“史記”一則下,唐彪引宋人林駉文字,而該段內(nèi)容出自林駉編著的《古今源流至論》。據(j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可知,該書是“供場(chǎng)屋采掇之用”、服務(wù)于科考的類書,《四庫總目》雖稱其有一定可取之處,但畢竟“體例近俗”[12]。唐彪在巨儒文宗之外,又能向下關(guān)注舉業(yè)用書,這也正是與他的職業(yè)特性及《讀書作文譜》的編寫目的緊密相關(guān)的。此外,唐彪也并不排斥儒學(xué)之外的經(jīng)典資源。在其分列的歷代古文經(jīng)典中,即設(shè)有縱橫家的“國(guó)策”與道家的“莊子”兩則內(nèi)容,且在“莊子”一則下,更引錄道教內(nèi)丹家陸西星之語。與此同時(shí),為本書作序的仇兆鰲本身也對(duì)道教丹法頗有研究,由此或可推見唐彪于儒學(xué)之外的好尚趨向,更可見《讀書作文譜》觀點(diǎn)容納度之廣。
唐彪的引文選擇具有較大的包容度和多元化特征,而這種引文方式所導(dǎo)致的一個(gè)情況,即是當(dāng)我們閱讀《讀書作文譜》時(shí),難以從中獲得明確的古文譜系,或者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認(rèn)為,唐彪或許并沒有想要建立一個(gè)嚴(yán)密的古文譜系。可以與之進(jìn)行對(duì)比的是理學(xué)家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在《讀書分年日程》的“讀韓文”一章中,程端禮所引用的內(nèi)容皆出自朱熹本人及私淑朱子的真德秀,以及朱子再傳弟子、程端禮之師史蒙卿這三人之中,且其選錄的引文有許多都是對(duì)“朱子之意”的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例如他引史蒙卿之語,稱真德秀《文章正宗》“一本朱子之意”,又稱“能次朱子之文有華有實(shí)者,惟真魏二先生而已”[7]。程端禮對(duì)引文的選擇實(shí)際上也強(qiáng)化了朱子、真德秀、史蒙卿這三人之間的傳承連接,又因其是史蒙卿的弟子,而將自己及其編纂的讀書法一并納入到朱子一系的師法統(tǒng)系中。在程端禮的古文評(píng)價(jià)體系中,其對(duì)古文家的高下等第及古文家內(nèi)部承繼關(guān)系的判斷,皆來源于上述朱門統(tǒng)系的古文評(píng)判,思想資源十分清晰明確。因此,相比于唐彪,程端禮所建立的是一個(gè)嚴(yán)謹(jǐn)有序的古文譜系。
相比于理學(xué)家對(duì)義理與師法的重視,唐彪無疑對(duì)作文的現(xiàn)實(shí)目的更為關(guān)注。唐彪的目的并不在于培養(yǎng)理學(xué)傳人或古文大家,也無意于成為某個(gè)古文派系的擁躉,他并不像程端禮一樣擁有一個(gè)明確而貫徹始終的指導(dǎo)綱領(lǐng),因此呈現(xiàn)在《讀書作文譜》中的古文觀念時(shí)常顯得較為含混。《讀書作文譜》主要面向的是廣大急于考取功名的普通士子,在引文資源的選擇上,他“集眾美”以求“詳備”,目的在于供學(xué)者取用。唐彪稱:“吾未見有不讀古文而制藝佳者,亦未有制藝佳而反不獲科第者。”[1]3409讀古文的目的在于作時(shí)文, 實(shí)用性才是《讀書作文譜》的最終導(dǎo)向。
當(dāng)考察了唐彪背后的思想資源,并理解其引文選擇的目的之后,再次回歸到唐彪對(duì)歐陽修文章的評(píng)價(jià)問題上,可知《讀書作文譜》引文與評(píng)語所呈現(xiàn)出的對(duì)歐文的復(fù)雜態(tài)度,正是來自于其廣泛引錄的編纂方式與多元的思想資源。唐彪一方面受到傳統(tǒng)理學(xué)家文章觀念的影響,一方面又吸納了明代以來新的文章趣味,《讀書作文譜》“集眾美”的編寫原則使得取向各異的古文觀念同時(shí)呈現(xiàn)。同時(shí),作為塾師的唐彪在“評(píng)古文”時(shí),又勢(shì)必要考慮“作古文”的實(shí)踐目的,所以《讀書作文譜》雖然保留了朱熹對(duì)“易學(xué)”的批評(píng),但依然選擇向舉子大力推介歐文,其中一部分原因固然來自茅坤古文觀念的影響,但最關(guān)鍵的因素仍在于歐文“易學(xué)”的實(shí)用導(dǎo)向。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在清初的教育實(shí)踐中,對(duì)古文的評(píng)價(jià)不僅僅是文學(xué)層面的文章品鑒,更關(guān)涉現(xiàn)實(shí)的時(shí)文寫作以及背后的功利目的。唐彪《讀書作文譜》對(duì)歐文的復(fù)雜態(tài)度恰可作為一個(gè)生動(dòng)的案例,幫助我們理解這些古文觀念的思想資源是如何落實(shí)到實(shí)際的作文學(xué)習(x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