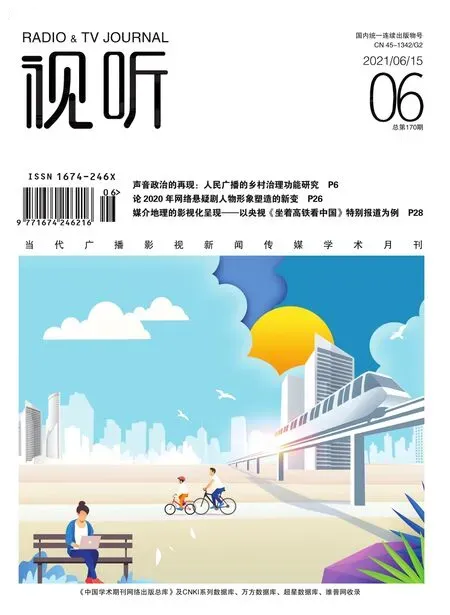論2020年網絡懸疑劇人物形象塑造的新變
□ 鄧知凡 符繼成
懸疑網劇自2010年播出的《毛騙》后一直頗受關注。2020年夏天,愛奇藝懸疑欄目“迷霧劇場”正式宣發,推出懸疑類精品化制作劇集,其播出的懸疑自制劇《隱秘的角落》可以說引爆了一場網民追劇的“狂歡”。緊接其后播出的《在劫難逃》《沉默的真相》以及優酷專欄“懸疑劇場”自制劇《摩天大樓》,都在各大社交平臺保持居高不下的熱度。觀察2020年大熱的幾部懸疑網劇,可以看到,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產生了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劇集在建構人物形象時試圖打破形成定勢的傳統角色認知,塑造更有社會價值的故事內核。這種改變,對于懸疑網劇的傳播效果顯然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一、中心視角:從警界下沉到平民
懸疑題材網劇誕生以來,將警察、法醫等刑偵人員放在劇情的中心位置,以專業視角展開敘事,不僅能給觀眾帶來“過關斬將”的成就體驗,更能突出主角在劇中的地位。依靠主角推動案件進展,屬于典型的罪案劇。典型的罪案劇(Crime show)是講述各類警探為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秩序而偵破犯罪案件、抓捕犯罪分子的故事①。如早期的懸疑網劇《暗黑者》(2014)、《心理罪》(2015)、《法醫秦明》(2016)等,以警界人員破案工作為主要看點,加以公安部門對專業刑偵知識作指導,能讓觀眾更直觀、更真實地體驗警界一線的工作。中國公安部直屬的事業單位和宣傳文化主陣地之一金盾文化影視中心就曾參與出品2017年熱播的懸疑網劇《白夜追兇》。然而典型罪案劇中模式化的破案情節設計,在快速更迭的市場環境下,極易被同質化作品淹沒。
2020年的懸疑網劇中,敘事視角開始從警界人員下沉到平民,警察在劇中的戲份比重大幅度下降。在中心視角上,用情感復雜的普通人代替晝夜不休的破案精英,而這些視角的變化也帶來了情節上的相關變化。
首先,增加接地氣的日常生活場景是塑造鮮活平民角色的關鍵。豆瓣評分高達8.9的《隱秘的角落》走上2020年懸疑網劇的“神壇”。這部劇的吸睛之處不僅在于緊張刺激的犯罪情節,也在于融入了南方沿海小城當地居民的生活場景:貼滿牛皮癬的街道、操著方言打麻將的廠工、街邊糖水店喝糖水等畫面,在悠閑散漫的生活節奏中添加了戲劇沖突。另一部高口碑懸疑劇《沉默的真相》中突出了“飯桌文化”,吃火鍋、吃外賣、組酒局的畫面屢屢出現。這些生活化情節與涉案情節相互交織,在現實與荒誕、平凡與離譜、生活與戲劇的巧妙結合下,碰撞出典型罪案劇中難以存在的參與感和真實性。
其次,平民在劇中的作用從“無能者”轉變為“引導者”。中心視角從警界下沉到平民,扭轉了平民長期的被動地位和“受害者”形象。如《白夜追兇》中,酒吧女老板劉音是主要出場人物中的一名普通人,在偶然發現關宏峰和關宏宇的秘密后,沒有去警局揭露,而是一直默默幫助他們,為他們提供交換身份的落腳點以及案件線索。其他典型罪案劇中的普通人除去“兇犯”和“受害者”身份之外,也以點綴、輔助作用居多,而2020年,普通人在劇中從輔助作用開始轉變為引導作用,個人意識和話語權顯著提升。影視作品在構建虛擬社會的框架中,借助情節發展為普通人賦權,即“通過弱勢群體自身的參與,激發其潛能,令其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社會資源和自身的命運”②。平民在劇中的命運不再任人宰割,而是具有充分的主觀能動性。網劇《隱秘的角落》中,朱朝陽的后媽王瑤經歷了喪女之痛后,懷疑女兒朱晶晶的死與朱朝陽母子有關,于是開始對他們進行瘋狂的復仇。王瑤喪失理性的種種舉動,引導著劇情節奏由緩變快,氛圍逐漸焦灼,配合演員出彩的演技,使得這部寫實派作品高潮迭起。在另一部網劇《摩天大樓》中,鏡頭對準了大樓里的居民,有保安、建筑師、小說家、房產中介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案發后,警察對他們逐一走訪調查,案發現場的第一目擊者是樓棟的保安,正當警察懷疑他對受害人懷有特殊的感情時,保安透露已婚的建筑師與受害人有婚外情關系,而建筑師矢口否認,告訴警察受害人的鄰居小說家有被害人的鑰匙,經常直接進入她家……每個看似可疑的人物都會將線索引導到下一環節,在一眾普通人的合力推動之下主導劇情方向。
總的來說,中心視角的下沉,源于影視創作的平民意識增強。此類影視劇注重發掘平凡人物身上的故事,與傳統上出身不凡、外貌姣好、能力強大的主角形成區隔,平凡人物經歷的苦與樂能夠引起更多觀眾的共鳴。平民化影視劇針對普通人的偏好,發掘小人物身上的力量,倡導積極生活,實現“草根”的自我價值。
二、核心人物:從個體到群像
從2020年以前熱門懸疑網劇劇情的簡要概括可以看出,以大主角為核心已成為國產刑偵劇的定式。《心理罪》(2015)主要講述了“犯罪心理學天才方木,調查兇殺案件,探尋善惡真相的故事”。《法醫秦明》(2016)“以法醫秦明的視角展開,講述了其與法醫助理李大寶、刑警隊大隊長林濤攜手其他警官屢破要案的故事”。《白夜追兇》(2017)講述了“刑偵支隊隊長關宏峰為了洗脫弟弟關宏宇的殺人罪名,一路破獲多起案件的故事”。觀眾在劇中跟隨主角的單視點和行動軌跡,能在感官上極大滿足“獵奇”的視聽需求,相反,在單一視點下,會導致觀眾被“牽著鼻子走”,擠壓了自主思辨的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群像的出現帶來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首先,從人物角色塑造上看,將不同性格的人物交織在一起,豐富了故事層次,形成聚集效應。在美劇中,善于運用群像人物的聚集效應能最大程度“吸粉”。美劇有意通過刻畫出許多立體多面、性格復雜的渾圓型角色,這一獨特魅力能夠使電視劇打動喜好不同角色的觀眾,從而擴大觀眾規模,集聚效應下實現口碑收視雙豐收③。國產網劇《隱秘的角落》中,表面單純心思復雜的朱朝陽在放貴重物品的柜門上夾頭發絲;樸實善良的嚴良想送朱朝陽一支鋼筆當生日禮物,因為沒錢,于是幫老板干活換鋼筆;單純機靈的普普假裝迷路的小孩,用“調虎離山”計騙警察陳冠聲。三個角色在劇中組合碰撞,在人物的聚集效應下,觀眾根據對人物的喜好度自發聚集成媒介社群。對于塑造的人物群像能否構建品牌文化,這是影視文化一個不可忽視的功能。如美劇《權利的游戲》,在吸附性文化品牌生成中,多元文化并存,拓展品牌聯想,以喚醒多元受眾群體的原型集體記憶,可以在短時間內贏得世界各國粉絲群體的青睞,使品牌迅速成長④。
其次,從空間場域和情節上看,是單一視點到多視點、簡單敘事到情感敘事的轉變。人物之間的身份、感情、利益、恩仇相互交織,觀眾通過劇情構建的擬態社會將自己投射進去,替角色做思考、下決定,與角色共情。2020年9月,高口碑網劇《沉默的真相》在播出期間讓網友大呼“心疼”“無力感”,年輕檢察官江陽受到大學同學李靜的委托,調查李靜前男友侯貴平之死。侯貴平在山村支教因發現了黑惡勢力卡恩集團的犯罪事實而被殺害,檢察官江陽、法醫陳明章、刑偵副隊長朱偉三人約定協作查案。在調查過程中每當找到一點線索就會被卡恩集團派人銷毀,江陽甚至被栽贓入獄,出獄時又患上絕癥,而兇手依舊逍遙法外。劇中多次出現人證被謀害、物證被銷毀的情節,讓線索一度進入死角。情節的“斷崖”式設計讓觀眾的情緒也跟隨主角的信心不斷坍塌重建。現實主義的寫實情節豐滿了逆境中的人物,塑造了江陽的意志、朱偉的勇氣、陳明章的智慧,缺一不可的三個元素共同推進案件發展。這部劇在情節設計和人物塑造上摒棄了傳統的“爽劇”理念,構建了一個“反烏托邦”社會。
在人物與人物交織的關系網絡中,上述網劇塑造群像代替大主角這一趨勢,避免了傳統上二元對立的戲劇矛盾,在豐富的視角下形成更多劇情突破口,以當下社會現象充當劇情內核,傾向于推及背后的因果關系,這樣的敘事語言與以往“過目則忘”的追劇體驗拉開差距,做出引人深思和回味的精品劇。
三、塑造技巧:從臉譜到人性
2020年之前,大量懸疑劇為了在短時間內吸引觀眾,劇集大多選擇了“1+N”復式敘事結構。“1”指劇集中的核心主體劇情,貫穿全劇,大致可根據是否參與推進劇情發展而分為兩類。“N”則代表劇中呈現的數個獨立案件⑤。比如典型代表作《白夜追兇》,主線是刑偵支隊隊長關宏峰幫助被冤枉的弟弟關宏宇洗脫殺人嫌疑,支線是兄弟兩人分別在白天和黑夜扮演同一人偵破不同的要案。常見的“1+N”形式由于需要快節奏的破案效率,在犯罪動機上容易造成簡單歸因,如第一個案件中,身患尿毒癥的兇手的行兇理由是嫉妒那些擁有健康身體但是整日不出門工作的人。罪犯與受害人的社會身份、家庭和心理環境的介紹流于表面,符號化、臉譜化色彩濃重,這是一種刻畫人物的公式化傾向,指人物的好壞以及性格一眼就能看出,每個人都個性鮮明、特征固定。《法醫秦明》(2016)、《白夜追兇》(2017)、《原生之罪》(2018)等早期懸疑網劇中的人物也非黑即白,由警界人士為代表的“紅臉”和罪犯為代表的“黑臉”組成。雖然人物之間的二元對立更容易產生沖突,但也容易導致網絡懸疑劇市場傳播內容趨同,讓觀眾產生視覺疲勞,不利于市場的創新發展。
在2020年播出的網劇中,人物性格逐漸褪去臉譜、程式化的特點,塑造出游走于善惡之間、擁有七情六欲的人性化角色,打通了虛構與現實的屏障,更加貼近現實,貼近受眾。
人性化角色刻畫的是活生生的、其性格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可以是光明正義的好人慢慢沉入邪惡深淵,也可以是為非作歹的壞人仍留有惻隱之心。《隱秘的角落》中殺人魔張東升痛下殺手殺害了妻子及岳父岳母,行兇過程卻偶然被三個小孩目擊,三人并以此做要挾要他交出三十萬封口費。但是當小孩們遇到困難迫不得已去尋求張東升幫助時,張東升仍然答應幫助他們并把他們好好安頓下來,甚至主動提出帶他們去吃麥當勞。作為毫無人性的殺人犯,卻在與孩子們的相處過程中流露出對他們的憐愛疼惜,角色的惡與殘存的善相互交鋒、相互包容,塑造出了令人膽寒卻無人厭惡、有血有肉的角色。《沉默的真相》中,縣檢察院吳副檢察長雖然戲份不多,但是這一角色也真實反映出人到中年的不得已。主角江陽在接觸棘手案件之初,求女友讓她父親,也是自己的上司吳副檢察長幫忙,檢察長表示自己盡全力支持江陽繼續查下去。江陽出獄后,迫于之前的線索全部中斷以及自己罹患絕癥而不得不放棄查案,這時,臨近退休的吳副檢察長找到他,并交給了他一封多年前收到的匿名信件——侯貴平案中最關鍵的證據,并表示為自己當初的懦弱后悔不已。在江陽等人與卡恩集團苦苦斗爭時,因為懼怕引火燒身和黑惡勢力對家人的報復,他選擇了沉默。
人作為具有復雜思維的個體,不能將其簡單地歸類,人性化的角色擁有自己的性格、人格,在影視作品中投射出有血有肉的個體。以往的單面化塑造、非好即歹的人物設定帶來過度神化或丑化的弊端,觀眾要么眾星捧月,要么咬牙切齒;而人性化就像一面生活中的鏡子,賦予了角色真實性,讓角色活了起來。2020年的懸疑網劇融入了當下網絡上持續討論的社會議題,比如“原生家庭”“家暴”“留守群體”“性別偏見”等,在構建現實問題的框架下,人性化在這些社會問題下凸顯出最真實的“真善美”和“假惡丑”,從網絡場域引向反思場域。
四、結語
總而言之,從警界到平民,從個體到群像,從臉譜到人性,懸疑劇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變遷不是偶發的變化,而是藝術作品開始關注社會現象的標志;不是塑造個人英雄的工廠,而是照亮平凡群體的聚光燈。多樣化視角下,觀眾“并不關注是否學到什么新的東西,而是注重在規則化的儀式程序使特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得到描述和強化”⑥。
網絡劇逐漸重視對現實議題的加工與重塑,這是文化進步的表現。在市場傾向于將網絡劇商品化、娛樂化的當下,精品網絡劇嘗試融入嚴肅的社會議題,通過生動的情節和鮮活的人物代替傳統的說教,在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價值,傳承社會文化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網絡媒介的發達和上網人群的壯大使得網絡輿論對社會產生全國性影響,上述網劇選擇融入充滿爭議的議題,也是社會未曾解決的難題,用問題意識為社會發聲,讓議題重新活躍以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這也是精品網劇值得贊揚和傳承的品質。
在今后的懸疑網劇市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僅僅是用于承載善惡的工具,更是現實議題在劇中的“實體化”反映。具有社會價值的內容才更有傳播力,能產生思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注釋:
①蔡之國.論網絡熱劇《白夜追兇》的敘事藝術[J].現代視聽,2018(03):24-27.
②丁未.新媒體與賦權:一種實踐性的社會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9(10):76-81.
③冷凇,王云.融媒環境下中美電視劇創作趨勢比較[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9(11):73-77.
④趙楠,張海韻.IP劇吸附性文化品牌構建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04):128-133.
⑤李玥.新媒介語境下網絡涉案劇的敘事策略研究[J].現代視聽,2020(04):43-47.
⑥王晶.傳播儀式觀研究的支點與路徑——基于我國傳播儀式觀研究現狀的探討 [J].當代傳播,2010(03):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