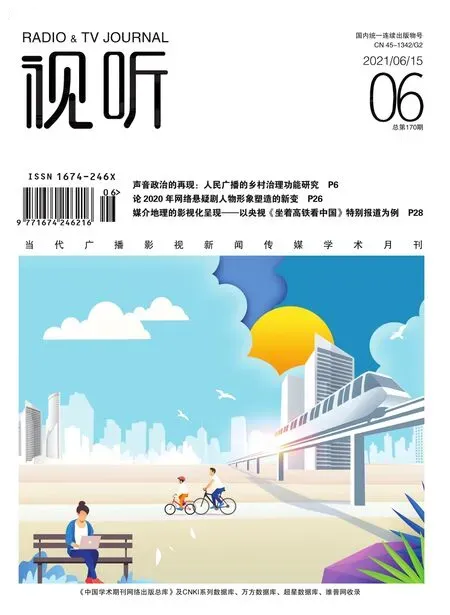紀錄片《回家過年》的文化內核
□張昱
一、新時代背景下的視點聚焦
紀錄片《回家過年》以春運為背景,通過一個個鮮活人物形象的塑造,譜畫出新時代背景下中國人對“回家過年”的重視和渴望,用全新的眼光聚焦群眾,觀察平凡人在年關將至時刻的動人故事,以多視點聚焦敘事策略,結合每個故事中的零聚焦視點和多線敘事共同表現主題。同時,通過對故事中一些元素的著重描寫和細節的捕捉,塑造出更豐滿、更立體的人物形象。從“人”和“事”(物)兩個緯度進行設計,在進行影像敘事的同時,實現了影視作品的藝術性追求。
(一) “典型人物”和多視點敘事
《回家過年》采用多視點聚焦敘事,選擇了數量可觀的表達對象。他們的職業各有不同,包括工廠里的打工者、快遞小哥、邊境哨所的戰士、金融都市的高級白領等;年齡上分布廣泛,從剛剛上學的小童到事業有成的中年人均有涉及。在春運來臨的時刻,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身份——返鄉者。形形色色的返鄉者,各式各樣的返鄉路,創作團隊通過更豐富的視角和更周全的視點將春運及其文化內核——“家文化”,通過一個個普通人的故事“講”出來,不是選擇宏觀的審視態度,而是以豐沛的人文情懷深入群眾,作品的覆蓋范圍很廣,條件也很復雜,但正是這樣的選題才更具時代意義。創作者們以小見大,將大題進行小做,通過樹立典型人物形象,使“中國工人”這一形象更加立體和深入人心。
社會生活題材的影視作品往往同民族認同、家國情懷、社會關系等宏大主題密切相關,在創作時基于對宏大主題的尊重,在內容的選擇和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可供創作者進行藝術加工的操作空間不大。但《回家過年》的創作團隊并沒有局限于宏觀敘事,而是選擇將主題通過具體的人物和事件進行表達。盡管“家文化”這一宏大主題并不等同于個體具象之和,但典型人物身上的故事更像是一個激發受眾對抽象概念下“回家過年”這一主題進行理解和想象的符號。在羅蘭·巴爾特的理論體系中,“涵指”是能指和所指所結合的“直指”背后之含義。在這里,“家文化”及其對所涵蓋受眾的影響成為影像背后的“涵指”。通過這種“寄情于事”,復雜的社會問題被從特定視角具象到了具體的事件上,多樣化、倫常化題材的選擇使作品的呈現有效避免解讀的片面性,也讓受眾更容易得到代入感。“回家過年”不僅成為作品的主題,也是作為推動事件發展的重要元素而存在。
(二)家鄉味道和符號表征
《回家的路有多長》中對飲食進行了三個階段的刻畫。伴隨第一階段呈現的是返鄉者們歸途前的心理活動和準備行為,以蒙俊源為主要表現對象,首先,他和妻子在工廠宿舍吃著簡單的晚餐,在宿舍內和妻子、朋友一起制作臘腸,幾人交流的內容中包含對家鄉和遠在家鄉的親人的思念以及對于回家的展望,通過對人物表情的特寫,表現出幾人的真摯感情。和妻子在工廠食堂吃飯時和遠在老家的孩子通話,昏暗的燈光下,兩人依偎在一起,緊盯著手機屏幕,飽含希望的目光讓人不免為之動容。為滿足孩子的愿望去市場購買雞腿、玩具等環節通過輕松的配樂、靈動的剪輯暗示了兩人心中的喜悅和迫不及待想要踏上歸途的情緒。第二階段則是分成兩條敘事線,通過平行蒙太奇的剪輯方法分別表達歸途中的蒙俊源和其家人雙方的行事舉動。蒙俊源和車隊同鄉在途中便民服務站共進午餐,蒙俊源“兩夫妻,炒一個菜,裝兩個飯,差不多就夠了”的言論讓精打細算的外出務工者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吃飯時,外出的游子們談起接下來的返鄉路,表現豐富的情感,讓觀眾對他們接下來的行程更添了一分期待。另一邊,蒙俊源父親蒙法錦和小外孫蒙軍淞為“頂梁柱”的歸來進行準備。一頓有“家的味道”的晚飯是家人共同的期待。第三階段中,林發乾回到家鄉后第二天,和孩子共度了一上午的歡樂時光后,“滿載年貨趕回家吃飯”。此時不管是背景音樂還是畫面呈現的景象,無不體現著主人公心中因回家過年而產生的歡欣。
二、文化內涵中的認同召喚
(一)家文化與文化尋根
家文化是根植于中國人思想中的重要觀念。馬克思·韋伯在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表示,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精神支柱是宗教信仰。在中華文化的語境下,盡管宗教的確對社會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但作為中國人精神內核的思想支柱是家文化,這種家文化帶給家庭關系中每個個體乃至社會中的每個個體以強烈的歸屬感和相對清晰的自我認知。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每個人的社會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社會關系。家文化作為中華文化基因中尤其重要的一部分,為中國人尋找自身的存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盧作孚認為,中國人的第一重社會生活便是家庭生活。“家”在中國人眼中是近似于信仰的存在,而每逢農歷新年,外出打工的游子們的返鄉路也在某些程度上具備了“朝圣”的味道。遠方的“家”不僅僅是對每個游子有著極強吸引力的旅途終點,更是一種“來處”,對“來處”的追尋也為他們的返鄉路增添了“尋根”的寓意。
家不僅是“鄉”,城市同樣也成為務工人員的“家”。廣東省深圳市更是提出“來了就是深圳人”,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城”與“鄉”的二元對立,而且也是對在外地工作的每一個個體歸屬感的賦能和強化。《沙縣一家人》中的胡開燁就表示已經把北京看成自己的“第二個家”,他把孩子從老家福建沙縣帶到北京,兩歲就被接到北京,在北京生活長達十余年的大女兒和出生在北京的小女兒理所當然地把北京看作自己的家,反而對父親的老家——福建沙縣表示陌生,她們的同學好友都是來自北京這樣一個她們成長的城市,而對過往時光的記憶也大多與北京相聯系。或許在她們眼里,北京已經是自己生活的代名詞,在返鄉的火車上,大女兒更是立志要通過高考的方式“殺回北京”。一個“回”字,不難看出她們對于北京深深的認同。但當一家人乘坐火車出站時,對北京百般眷戀的大女兒看到來接他們的家人,幾乎是毫不猶豫地迎了上去。家人作為家鄉的代表,常常被背井離鄉的外出務工人員化為“家”的符號。這種符號的意指是居于家鄉,和家人共享生活之樂,背后的涵指則是一種對家鄉信仰式的向往。
《回家過年》的主人公們從騎摩托車返鄉到網上搶火車票回家;從兒女南下陪伴“候鳥老人”到父母上京幫助兒女照看家庭,遇到困難,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也要回家過年,各種不同的返鄉方式和不同的團聚方法體現出中國人對回家過年的相同期許。家人的身邊就是家,回家就是和家人團聚,更是體現了中國人對于“家”和“年”的強烈情感。
(二)民族認同和文化歸屬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對民族共同體所產生的認同進行研究,認為空間的邊界對認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地理環境對居民的生活和心理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種影響催化了個體對所居住族群和地域的認同,在認同的作用下個體和個體所匯聚群體的交互日益緊密。
《遠在中國的家》中,來自南非的伊恩辭掉工作從家鄉來到廣西的舊縣村定居,起初為優越的地理環境所吸引。在當地特色臘腸的制作上,伊恩和當地人對行為的動機有所不同。當地原住民制作臘腸的行為更多是出自對傳統的沿襲,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儀式感再現,而作為沒有相關記憶的外來者伊恩,這一活動的進行對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參與,不僅是與當地人的交互行為,更是通過這樣的行動和交互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并親身感受一種文化傳統。雙方對于制作臘腸的行為同樣存在共同點,其相似之處在于,雙方眼里臘腸的制作逐漸成為一種形式,制作的內容也早已超越了臘腸本身。通過另一條敘事線,鏡頭向觀眾呈現伊恩父母在南非的生活,在他們的燒烤爐上出現了同臘腸長相相似的香腸,這種對雙方相似的隱喻為接下來伊恩父母來到中國參與中國新年的慶祝埋下伏筆。伊恩遠在南非的父母眼里“家”的概念同樣是廣泛的,來到中國并住進由孩子改建而成的房子里后,伊恩母親一句“我們到家了”尤其令人感動。
伊恩盡可能地向父母展示中國和中國新年獨有的魅力,這些都是吸引他留在中國的理由,也是帶給他“家”的歸屬感的重要一環。讓兩位老人找到“家的感覺”的不僅僅是安靜的村落和優美的風光,更是這片孩子曾付出過心血的建筑以及在此居住多年的孩子,盡管初來乍到的兩名老人談不上對這片土地的認同,但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家。伊恩成為他們和這片土地連接的紐帶,熱情的當地原住民帶來的美食和書法作品等同樣是“家”元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恰逢中國傳統的農歷新年,小村落里的“年味”外化了中華文化中“喜慶”“和諧”等元素。“回家過年”中的“家”是具有多重含義的,不應對其進行狹義的理解,伊恩和父母融入當地人生活中共度新年,在異國他鄉感受年味的他們同身邊人一起分享快樂。中華文化兼容并蓄,對于“家”元素的感知也是為全人類所共通的。在新年背景下,這樣一幅共同體的美麗畫卷被鏡頭如實地記錄下來。
三、結語
《回家過年》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通過片段化敘事,刻畫了春運背景下回家過年的群像,對內容的取舍讓紀錄片呈現出恰當的節奏和合適的內容體量,飽含文化內涵的內容設定讓作品在具備藝術性的同時兼顧了文化意蘊和社會意義。央視紀錄頻道以“為時代中國存像”為使命,為社會現實題材紀錄片指出了創作和發展的方向。《回家過年》作為當代中國影像的重要組成部分,真實、深度、動人地講述了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呈現了中華民族家文化的深刻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