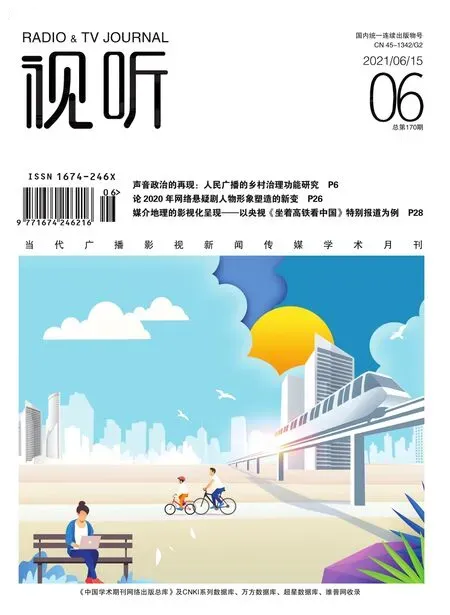互聯網背景下“脫域”陪伴形成與影響探究
——以網絡直播為例
□ 李晨顏
吉登斯所說的“脫域”是指:“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以先進科學技術為支撐的互聯網社會正在快速發展,形成了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機器系統與人的系統結合而成的網絡空間,成為與陸、海、空、太空并行的第五大空間。
克萊·舍基認為互聯網塑造了一個生命空間,每個人在這個虛擬空間內都能成為媒介出口。社會化媒體對于群體、組織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人們可以利用社會化媒體完成一種“脫域”陪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足不出戶的國民雖然在地域上互相分離,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孤立狀態,但是在互聯網中,地理位置各異的用戶在網絡空間中通過“網絡直播”等形式隔著屏幕交流、對話,形成了以網絡技術為基礎的“脫域”陪伴。大量網民在網絡中積極討論議題、觀看直播,互相取暖、陪伴,是研究網絡社會中“脫域”陪伴的極佳樣本。
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直播的具體形式
網絡直播是一種互動型媒體應用形式,“是通過錄屏工具或者手機在互聯網平臺上對表演、展示、互動等行為進行實時呈現,是一種新興的在線娛樂或服務方式”。表演者與觀眾、觀眾與觀眾之間互動交流,形成了以互聯網為媒介的不在場交流,共同處在“直播”這一儀式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網絡直播”為網民帶來了與以往不同的體驗與感受,網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互動,實現“脫域”陪伴。
(一)慢直播
2020年1月27日,“央視頻”客戶端開通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的慢直播。直播開始3小時,引來30余萬“云監工”在線觀看,開播4天后,觀看總人數已破億。在網絡直播熱潮下,這種沒有主播、音效和特效,慢節奏、無修飾、超時長、無間斷的慢直播受到熱捧,主要原因有以下兩方面。
其一,網民們形成了陪伴式交往的“泛在共情”,是一種脫域式的陪伴。處在“網絡瞭望塔”中的網民有一種權力的想象,加之VR慢直播帶來的虛擬陪伴,不僅使處在不同地域的網民與武漢聯系起來,也將觀看直播的網民普遍聯系在一起。
其二,被疫情隔離“賦閑”在家的網民是孤獨、無力的個體,面對的是疫情帶來的負面情緒。24小時無間斷的直播,為孤獨的個體提供了精神寄托:盡管去不了戰疫一線,但只要在看直播,就與武漢同在。這種陪伴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網民的消極情緒,彌合了地理位置上的距離,看似無組織的網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人們希望為他們已經相信的東西尋找確信,并傾向于接受與自己想法相類似的觀點”。參與到慢直播中進行“脫域”陪伴的網民聚在一起,共同感受著“泛在”的媒介權力。
(二)直播式線上教學
受疫情影響,教育部緊急發布有關推進高校在線教學和管理、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學、中小學“停課不停學”等文件,確保在延遲開學的情況下,保證學生的正常學習活動。直播式線上教學活動應運而生,各校老師紛紛做起“網絡主播”,各學段的學生成為觀眾。調查發現,疫情的嚴重程度對情緒惡化程度有影響、居家隔離對高校學生的學習和研究狀態有明顯的負面影響。通過互聯網媒介進行直播式線上教學是符合實際的方式。
網絡直播教學的受眾是在校學生,中小學生心理承受力、自我約束力不及成年人。通過直播教學,將散漫、情緒低落的學生聚集在網絡中。這種聚集是一種跨地域的重聚,可有效避免孤獨感、散漫感帶給青少年的影響,社會責任感重新被賦權。
(三)直播帶貨
2019年被稱為“直播帶貨”元年,是電商領域的新風口、新模式、新功能。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全民直播時代加速到來,“云復工”“宅經濟”“零接觸”等促進了直播電商的發展,迎來了網絡直播的新高峰。商家通過“直播帶貨”,使隔離在家的網民可以最直觀地看到商品,再加上主播的推薦與互動,受眾容易激情購物。另外,由政府部門支持的“網絡直播”在疫情期間成為主要直播形式,也成為武漢等地區滯銷貨物、農產品輸出的主要渠道。例如,人民網在抖音短視頻平臺開辦以“湖北重啟,抖來助力”為專題的網絡直播。全國網民雖然到不了武漢,但是通過觀看直播、購買武漢特產、刷禮物即可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脫域陪伴”的形成條件
(一)技術降低門檻,聚合更加容易
“脫域”一詞是在先進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基礎之上提出來的,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人們從地域關聯上脫離出來。在數字媒體背景下,人類社會重新部落化,技術的神話為“脫域”陪伴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互聯網技術消除了信息的地方性局限和集體性反應所面臨的壁壘”。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8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0.4%。直播技術使受眾在觀看網絡直播時有沉浸、敞視、陪伴的體驗,人們在互聯網中聚合起來,在社會化媒體平臺中交流與陪伴,滿足精神需求。
2003年SARS疫情期間,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是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人們主動發聲的渠道較少,在網絡中聚合也就無從說起。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則不同,異地個體在技術賦權的基礎上,在互聯網平臺中凝聚在一起變得非常容易。他們積極討論,為抗擊疫情等社會公共事務獻力,互相陪伴以減少消極情緒。
(二)現代公共領域的形成:社會化媒體
哈貝馬斯所言的公共領域是指:“在這一領域中,公民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言論不受約束,是介于市民社會和國家政府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在今天廣泛應用的社會化媒體中,政府、大型利益集團組織的干預相對較少,技術的加持使受眾自由發聲、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當代的“公共領域”。
社會化媒體不僅具備社會交往功能,同時也為公眾提供了關注、參與政治的新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無論是面對積極消息,還是消極信息,網民都會主動聚在一起討論,引發輿論高潮。通過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以點贊、轉發、評論的方式形成“強關系”加“弱關系”的跨圈層傳播,表達自己的看法。
(三)社會心理:網絡社會中孤獨的人
美國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爾認為,我們為了連接而犧牲了對話。網絡在線使我們逃離現實生活遁入網絡中,同時擁有雙重身份。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在場不交流”和“不在場交流”的現象,這其實是彌補了人性中缺失的一面。正如日本傳播學者中野收所言的“容器人”那樣,人們的內心世界是孤立、封閉的,他們也想打破孤獨與他人接觸,但是這種接觸只是容器外壁的碰撞,并不希望對方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
互聯網社會中的“脫域陪伴”并不是連續不斷的,網絡社會中的人可以選擇連接、斷開、重新開始等,恰好彌補了現實生活中的空缺。疫情期間的網民是孤獨的,他們選擇在互聯網中互相陪伴、緩解焦慮,但疫情過后恢復正常生活時,他們又會選擇暫時斷開這層連接,回歸現實生活。
三、“脫域陪伴”形成社會治理的新能量
在我國,微博已經成為網民關注社會公共事件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成為網民聚集起來為社會治理貢獻力量的主要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每天有2億以上的微博用戶通過微博關注疫情最新進展、設置話題討論、組織公益捐款等。
(一)基于共享形成的合意機制
在互聯網中,互相陪伴的個體是匿名的,他們可以選擇公開真實身份或用網絡ID代表自己。匿名性為網民提供了一個暢言的安全前提,網民在虛擬空間中戴著“匿名”面具,大膽發表己見。目標一致、意見相同的人基于共享形成合意,信息共享成為主要傳播方式,有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例如,在疫情期間以微博“話題”為單位形成的“陪伴”是常見形態,使線上求助變得合理有序,成為當時社會治理的有效輔助方式。例如在#新冠肺炎求助患者#這一話題中,患者或患者家屬在話題中發文求救,經轉發后,網友紛紛提供搜尋方法與途徑,共享知曉信息。使得線上求助變得合理有序,成為疫情期間社會治理的有效輔助方式。
(二)線上線下形成的聯動機制
互聯網社會中形成的合意若想延續到現實社會中,不僅需要合意、分工,還需要有強有力的共同目標或愿景將人們聚合起來。但是面對特殊議題時,在互聯網中互相陪伴的人們可以發揮力量,促成線上線下聯動機制的運作。
例如,在疫情期間,面對“處于生理期的女護士長時間穿著防護服難以解決生理期問題”,引發社會對女性醫護人員的關注。話題一經擴散,網絡群體即經過有組織的策劃募捐、聯系線下廠家等流程,最終將醫護物品送達女性醫護工作者手中。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還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女性生理衛生用品納入疫情保障用品清單。
四、結語
先進技術賦權、現代公共領域、普遍的社會心理等條件促成了“脫域”陪伴的形成,對現代社會治理、調解社會負面情緒有著積極作用。不可否認的是,互聯網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脫域”式陪伴,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群體組織,發展到現在不免會出現一些局限性與難題。但是,隨著媒介素養教育納入國民教育之中,公眾媒介素養不斷提升,“脫域”陪伴帶來的網絡無序難題也會隨之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