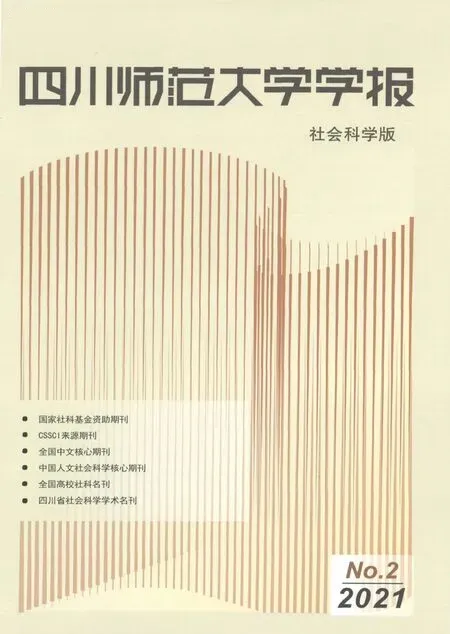國民革命前后中國共產黨對自身領導地位認識的歷史考察
李亞男 王久高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領導黨和執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是中共在總結近百年來領導中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經驗基礎上對自身定位的明確概括。然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領導權、同盟軍、武裝斗爭等理論和實踐問題還處于探索階段(1)高彬《為什么六大以前沒有提出指導思想問題》,《學習時報》2013年7月29日,第3版。。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底國民革命時期結束近7年的時間里,受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影響,中共對自身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認識經歷了初探、妥協、糾偏和走向成熟的一系列變化。本文從中共對自身領導地位認知的幾個分期入手,梳理和剖析當時黨的領導人對形勢的判斷過程,以此充實和豐富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學說內涵。
一 從“指導者”到“合作者”“監督者”
從做工人運動的“指導者”到做革命聯合戰線中的“合作者”與“監督者”,這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前對自身革命角色的歷史判斷。這樣的歷史判斷首先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因為初創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并未形成對革命局勢和國內各階級狀況的基本認識,共產國際的指示就是建黨的模板。另外在革命理想主義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最初以組織城市工人運動為政黨活動的主要內容。經過一年左右的工人運動實踐,經歷了多次失敗的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實力和革命局勢逐漸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開始積極尋求與其他革命政黨的合作。
(一)做純粹的工人運動“指導者”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一大提出了四條綱領,主要內容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又說“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并且“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2)《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與一大綱領相比,一大決議在黨際關系上的態度更加明確,要“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對現有其他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3)《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6頁。。中共一大黨綱和決議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根本目的是通過社會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并且為了保證革命性和純潔性,在組織上要實行徹底的“關門主義”,體現出想要改天換地的強烈愿望,以及與一切反動勢力斗爭到底、毫不妥協的革命斗志。
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有俄文和英文兩個版本,官方采用的是俄譯本。在俄譯本中,中共一大沒有使用“領導”一詞,而是對工人階級要“支援”,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管理制度要“承認”。同樣,在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的很多正式文獻中對黨與革命的關系較多使用“指導”而很少用“領導”。比如1922年7月1日,陳獨秀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答黃凌霜》的書信中說道:“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所以要想無產階級底革命與專政實現,非去掉我們厭惡首領、厭惡指導者的心理不可。”(4)《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答黃凌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17頁。由此可見,此時中共還沒能樹立對一切革命要素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領導意識,側重于強調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教育與技術指導功能,面對革命形勢時更多以工人階級的教導員面貌出現而缺少主人翁精神。這與建黨之初黨的理論準備不足尤其是對如何領導開展工人運動的實踐經驗不足密切相關。
實際上,當時有少部分早期共產主義者認識到了黨對無產階級革命領導地位的重要意義。1920年,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兩封信中說道,“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四種利器”——黨、工團、合作社、蘇維埃,其中黨是“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5)《蔡和森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給毛澤東的兩封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447-448頁。。毛澤東在其后的回信中表示“沒有一個字不贊成”(6)毛澤東《致蔡和森》,《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但是,一方面這種認識沒有成為黨內主要認識;另一方面,中共此時雖認識到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黨相較于工團、合作社、蘇維埃政權而言處在領袖者的中樞地位,但對于黨應該領導怎樣的革命、在整個國民革命中應該處于什么角色還沒有清晰的認識,只是把領導的對象集中在組建工會和發動工人罷工上,對農民階級的同盟關系和對士兵的組織領導還處于理論準備階段。正如1926年初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回憶的,在一大到二大之間的時期,“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是非常復雜的,同志們容易發生誤會,以為無產階級政黨只應做無產階級事情,其實這是不對的,是錯誤的”(7)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3-804頁。。后來,毛澤東在接受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也談到:“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工作做得非常少。”(8)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頁。
(二)做革命聯合戰線中的“合作者”“監督者”
經過近一年的革命實踐,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做起來著實是一件艱難的大事業”,缺乏組織性的無產階級只能是一盤散沙,“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9)《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答黃凌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16、117頁。。另一方面,在工人運動經歷的種種困境面前,中共認識到一大綱領的局限性以及無產階級政黨尚不具備獨自領導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實力。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改變了之前關門主義的態度。1922年5月23日,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群報》上發表《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指出“在中國,從事勞動運動的黨派,像共產黨、無政府黨底勢力都還微弱;其他政黨,只有國民黨對于勞動運動表示同情,而且頗有力量”(10)陳獨秀《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頁。。因此,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應該本著黨義,對于勞動運動,比他黨加倍的努力”,要求自己的黨員必須勇于為勞動群眾的利益犧牲,“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產黨,不然便是假共產黨”(11)陳獨秀《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251、252頁。;另一方面,“在同一目的之下,共產黨、無政府黨、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在勞動運動的工作上,應該互相提攜,結成一個聯合戰線(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沖突,才能夠指導勞動界作有力的戰斗”(12)陳獨秀《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251頁。。在這條聯合戰線上為了達到革命目的,中共必須“監督他黨不使他們有利用勞動運動而做官而發財的機會”(13)陳獨秀《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陳獨秀文集》第2卷,第252頁。。此時中共認為,“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14)《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91頁。,國民黨既同情勞動群眾,又是中國唯一有能力領導國民革命的黨派,所以與國民黨合作,與其他政黨結成聯合戰線,是指導勞動群眾作有力戰斗的最佳出路。在聯合戰線中,中共與其他黨派的關系是合作與監督,監督其他黨派不要背離和傷害勞動群眾的利益。
這一態度轉變在中共二大上得到確認。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以下簡稱二大《議決案》)進一步說明了此時中共對其他黨派由排斥到聯合的轉變原因。二大《議決案》認為,在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狀況下,民主革命雖然指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于無產階級也是有利益的”。所以“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15)中共二大《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39頁。,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但同時二大《決議案》也強調,這么做并不代表無產階級政黨投降于資產階級民主派甚至淪為其附屬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勝利后可以完全解放無產階級,“乃因為在事實上必須暫時聯合民主派才能夠打倒公共的敵人——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所以共產黨在民主聯合戰線中“亦只是聯合與援助,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并”,“不可忘了自己階級的獨立組織”(16)中共二大《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39、140頁。。
受共產國際的影響,中共在具體的斗爭策略上也從堅決“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變為通過參與議會揭發批判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性。中共二大《關于議會行動的決議案》指出:“革命的議會行動,成為激起或輔助無產階級一類革命風潮的重要方法之一。”(17)中共二大《關于議會行動的決議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47頁。即使在帝國主義的掠奪和軍閥混戰的背景下,中國資產階級的議會只在形式上成立,但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及貧苦農人群眾”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應當跑入這類時常被封建的武人勢力所脅迫破壞的議會中去”,目的是為了“高聲告發代謝不窮的由國際帝國主義所收買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惡”,從而“醞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同時又在各級議會中,“辯護無產階級和貧苦農人經濟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國幼稚的資產階級對于勞動者一切的壓迫”(18)中共二大《關于議會行動的決議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48頁。。這里所說的“封建的武人勢力”是指以北洋軍閥為代表的各地封建軍閥勢力,此時中共不僅加入由各革命黨組成的革命聯合戰線,還嘗試通過“合法”途徑向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開火。與單純依靠發動工人罷工相比,中共的斗爭途徑更加多樣化。
二 在國共合作中對革命領導權認識的轉變
經過民主聯合戰線的初步實踐,中國共產黨更加堅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此,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勸導和孫中山的意見下,最終國共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實現了聯合。然而,國民黨內部左右派的分化以及國民黨左派的不成熟導致很多維護工農利益的政策并未得到落實。面對這種情形,中共四大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
(一)做國民黨領導下的“同盟者”
中共三大繼續了二大的觀點,認為“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群眾的黨”,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19)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59、258頁。。此前中共試圖通過民主聯合戰線和國民黨建立黨外合作,但都沒有成功,孫中山只接受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這一種途徑。曾經同孫中山會談過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中共應當正視現實,接受孫中山的建議。在1922年8月的西湖會議上,雖然大多數中共黨員不同意黨內合作,但馬林借助共產國際的權威使建議被通過。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認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而且“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20)《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237頁。。
調試時,需要手動給光電傳感器一個輸入信號,檢測輸出電平是否正常。給L298各個輸入端口加上電平,觀察電機的運轉情況是否正常。檢查小車能否前進、后退、停止和轉彎等。各項檢查都通過后,加載完整程序。
于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決定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而且“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21)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59頁。。中共三大宣言更是直接表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22)《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76頁。但國民黨有兩個弊端,一是寄希望于帝國主義的援助,二是集中全力于軍事行動,忽視對民眾的政治宣傳。為了彌補國民黨的不足,中共明確了自己在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中的責任與使命,即宣傳引導工人和農民參加國民革命,并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進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1924年8月,國民黨改組半年后陳獨秀再次肯定了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運動,這個運動的領袖應該是中國國民黨;民眾若不認識國民黨和國民黨若不認識自己,都是中國革命之最大障礙!”(23)陳獨秀《寸鐵》,《陳獨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可以看出,此時中共黨內主流思想認為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袖”,中共是在這個“領袖”領導下的“同盟者”。
針對陳獨秀的觀點,黨內很多同志表達了不同意見。瞿秋白、鄧中夏、彭述之寫了一系列文章,通過對中國各階級物質基礎、思想覺悟的分析,結合對世界革命潮流的判斷,在理論上堅持認為只有最具革命徹底性的無產階級才能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例如,1924年11月,鄧中夏在《我們的力量》中指出,“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24)鄧中夏《我們的力量》,《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頁。,因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強而革命性不足,所以只有無產階級“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25)鄧中夏《我們的力量》,《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186頁。。然而,此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陳獨秀,其他同志的看法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這些不同意見為中共四大提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問題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奪取革命領導權思想的萌發
隨著國共合作中矛盾的不斷顯現和國民黨內部左右派的分化,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第一次在中央文獻中提出無產階級對革命領導權的問題。由于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兼具推翻帝國主義侵略的世界性與推翻本國資本主義壓迫的階級性,所以中國的民族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做領導者才能勝利。因此,中共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指導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26)中共四大《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6頁。。四大通過的《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以下簡稱四大《議決案》)分析了目前中共在國民革命中地位和目的的變化,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已經入一個新時期”,必須調整工作方針,認清“國民黨是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國民族運動之全部”(27)中共四大《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3頁。。四大《議決案》的第三節直接用“中國各社會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趨向——無產階級之領導地位”(28)中共四大《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7頁。做標題統領全篇。中共必須學會在國民黨中保存和發展自身實力,以斗爭求團結。同時不能再把國民黨視為一個整體,而是要在思想上、組織上不斷擴大國民黨左派的勢力,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29)《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系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536頁。。
從中共三大認為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袖”到四大提出無產階級要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絕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彭述之等人極力將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照搬回國,提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30)彭述之《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第9頁。。這一思想對中共四大產生了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可以從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考察報告中得到答案。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刊登了維經斯基考察廣東政局和國民黨發展情況的報告。維經斯基認為:國民黨在廣東執政一年半以來,“絲毫政治工作沒有做,——使在國民黨之下能建立一個城市貧民的基礎,對于農民亦是如此。恰正相反,廣東工人及農民往往看著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束縛他們的國家機關。”(31)維經斯基《廣東政府與國民革命》,《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第25頁。對國民黨右派來說,他們“已經不滿意國民黨政策的模糊,竭力想他右傾,使他去代表富有階級的利益,終至于與世界帝國主義妥協”(32)維經斯基《廣東政府與國民革命》,《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第26頁。。對國民黨左派來說,他們雖然知道國民革命的社會基礎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群眾,但他們只是機械地增加工人黨員的數量卻沒什么實質性作為,企圖單純依賴于通過發展軍事力量來取得國民革命的勝利,以為“一切實際工作及經濟組織都可以暫緩——‘讓他們晚些再組織工會罷’”(33)維經斯基《廣東政府與國民革命》,《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第28頁。。維經斯基批評說,國民黨不懂“軍事行動只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這種行動非以勞動平民的利益為根據不可,——國民黨不明白這一點確是一個根本錯誤”(34)維經斯基《廣東政府與國民革命》,《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第25頁。。面對這種情形,作為國民黨內部“共產派”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有所作為,奪取革命領導權,防止國民黨右派徹底占上風,產生革命路線偏離正軌的危險。
幾個月后,無產階級成功領導五卅運動的表現及由此引發的省港大罷工給了中共極大鼓舞,更加堅信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35)周家彬《階級與黨:中共革命領導權雙主體的形成與整合(1925-1935)》,《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年第4期,第53頁。。然而中共并未搞清楚無產階級究竟該如何奪取領導權,在什么意義上才算奪得了領導權。1928年4月,瞿秋白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分析了當時黨內對無產階級奪取革命領導權的三種看法:其一,在國共合作中“只要國民黨能聽從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便可以說實際上的領導權在共產黨之手”;其二,要爭領導權,“無產階級的工人便不應加入國民黨;不要用國民黨來集合革命勢力”;其三,認為共產黨要在國民黨內爭得領導權,“一直到排除資產階級的右派至于凈盡”,要發展到“變國民黨為純左派的政黨”。(36)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瞿秋白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370頁。三種思想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第一種和第三種思想都認可黨內合作的形式,但第一種認為只要國民黨在思想上認同共產黨的革命主張,那么共產黨就已經在實質上掌握了革命領導權;第三種思想認為必須在組織上把國民黨改造為一個純粹的左派政黨;第二種思想則主張國共由黨內合作轉向黨外合作,認為共產黨不必爭取國民黨的領導權,這點上又和第一種思想有相似之處,即共產黨要爭奪的是革命領導權而非國民黨的領導權。瞿秋白認為,這三種意見“在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政策史上,是極端混淆交錯的”,中央主要持第一種意見,摻雜著第二種思想,第三種意見流行于廣東。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旨意下,當時的中共把希望寄托于國民黨左派,從而做“‘極左派在野黨’,美其名曰國民黨外的‘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而將當前之國民革命領導權讓給‘純國民黨’”(37)瞿秋白《中國共產黨與機會主義》,《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第166頁。。
三 幻想依靠國民黨左派掌握革命領導權
孫中山的逝世導致國民黨內部左右分化進一步加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此時的中共將武漢國民政府作為繼續國民革命的主戰場,幫助國民黨左派壯大實力。汪精衛等雖曾以左派的面貌出現,但具有很大的動搖性和投機性。“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左右派實現寧漢合流,大肆捕殺共產黨員。然而此時中共在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下,對國民黨左派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一)做國民黨“極左派在野黨”
孫中山逝世后,隨著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斗爭的發展,國民黨內部的左右分裂進一步擴大,出現了以戴季陶、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戴季陶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黨員”(3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頁。,完全背離了孫中山主導的國民黨一大確立的綱領和政策。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制造了中山艦事件,監視和軟禁了大批共產黨人。1926年5月15日,他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所謂的《整理黨務案》。蔣介石借此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還打擊了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在這種形勢下,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指出:“組織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國民黨,以充實其左翼,更加以無產階級及農民的群眾革命力量影響國民黨——這樣去和左派國民黨結合強大的斗爭聯盟,以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如此才能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39)《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頁。
1926年12月初武漢國民政府成立。面對國民黨內部日益激烈的派系之爭,在12月中旬的漢口特別會議上,中共進一步調整了行動策略,通過了《國民黨左派問題決議案》,認為中共要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對以汪精衛為首的左派國民黨給予厚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占),并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群眾(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40)《關于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第506頁。。之后,這種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斷在黨內蔓延。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中共五大召開,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認為革命現階段需要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這個政權只有“以無產階級作領導,才能解決現在革命中的重要問題,并引導革命向非資本主義之發展方面進行”(41)《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為了鞏固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當前革命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土地革命,為提高工人的生活質量和工資而奮斗(42)中共五大《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183頁。。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仍然堅持認為,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政權必須通過國民黨的組織形式,因為國民黨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合作的黨,在目前的情形下,如果共產黨不能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地位,則無產階級便不能在全國取得領導作用。這意味著中共黨員絕不能退出國民黨,否則便失去領導革命的舞臺。共產國際還認為,在目前階段提出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口號是不適宜的,如果即刻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必然被認為“是越過國民黨這個群眾的組織及國家的政權”(4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353頁。。基于以上判斷,共產國際為中共指明兩個任務:一方面要在城鄉勞動群眾中極力為國民黨發展黨員;另一方面,要積極參加國民黨左派領導的武漢政府。
1927年5月21日,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迫害,中共中央認為必須與國民黨左派建立更加親密的關系,并喊出“保衛革命的國民政府”(44)《關于湖南事變以后的當前策略的決議》,《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261頁。的口號,以支持壯大武漢政府的力量。這一系列舉措相當于把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國民黨左派身上,幻想做國民黨“極左派在野黨”。實際上,中共由于沒有正確判斷出哪些是國民黨的真正左派,出現了將革命領導權寄托在汪精衛等“假左派”身上的重大失誤。
(二)做國民黨左派的“重建者”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爆發,武漢政府撕下偽善的面具,與南京政府商量寧漢合流的計劃。隨后,中共中央在“八七”會議上發布了告全體黨員書,指出“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后的武漢政府已經和蔣介石政府無異,摧殘工農運動,殘害革命將領。這一事件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徹底破裂。“八七”會議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認為,國共合作破裂只是國民革命的中斷而非結束,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后,“中國的國民革命的任務,并且必須工人階級負起全副的責任,聯合最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偉大力量——中國的農民,來實行”(45)瞿秋白《中國革命是什么樣的革命?》,《瞿秋白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頁。。此時,中共已經認識到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者不是資產階級而只能是農民。為了建立黨對農民暴動系統的、有計劃的革命領導,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為中共六大草擬的《關于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確定了黨領導農民進行堅決斗爭的方針,這是建黨以來中共第一個關于土地問題的黨綱。
然而,國共合作的破裂并不代表中共已經完全放棄了對國民黨左派的幻想,還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此時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都相當幼稚,難以獨當一面,而且共產國際也認為中共應該“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46)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頁。。陳獨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里說道:“‘八七’會議以后,自從南昌暴動一直到占領汕頭,共產黨仍舊是隱藏在左派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在群眾中只看做是國民黨的內哄,并沒別的什么。”(47)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文集》第4卷,第252頁。陳獨秀認為從“八一”南昌起義到9月24日起義軍占領汕頭,中共沒有以獨立的面貌領導群眾暴動,而是仍借助國民黨的影響力行事。從8月21日《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中可知,雖然中共中央認識到“共產黨之組織和正確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漲之決定勝負的動力”(48)《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頁。,但因為國民黨仍是各階級重要的政治聯盟,而且在共產黨下級黨部的宣傳下國民黨在基層群眾中已深入人心,為了吸引小資產階級加入革命聯盟,中共不應該放棄國民黨這塊招牌,而且要大力恢復國民黨左派。此時中共扮演了國民黨左派重建者的角色,幻想通過重新塑造國民黨左派來獲取對國民黨的主導權,從而進一步領導國民革命。
四 從放棄幻想到獨立領導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國民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但這并沒有停止中國革命前進的步伐。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失敗的痛苦經歷中明白了深刻的道理,首先要徹底放棄對國民黨左派的幻想,走上獨立自主領導革命的道路;其次要在總結工農暴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從而擔負起工農武裝割據與蘇維埃政權的“領導黨”角色。
(一)徹底放棄對國民黨左派的幻想
在國民黨的殘酷鎮壓下,工農武裝暴動經歷多次失敗,中共在實踐中逐漸認清國民黨左派也是不可靠的。1927年9月19日,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決定放棄對國民黨左派的幻想,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蘇維埃取代國民黨作為領導工農群眾的旗幟。然而,此時中共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上尚未完全擺脫對國民黨左派的依賴。其實,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湖南省委早在8月20日就提出“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49)《毛澤東年譜(198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頁。,但中央的復信否認了這一觀點。10月8日,彭公達在關于湖南秋收暴動的報告中再次提醒中央,國民黨已經蛻變成軍閥“爭權利搶地盤的工具”,“國民黨這塊招牌已經無用”,“主張用C.P.名義來號召”(50)彭公達《關于湖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542頁。。10月6日,趁奉晉軍閥混戰之機,北方局制定了農民暴動計劃,一方面要喊響“殺國民黨新舊右派及一切反革命的叛徒”的口號,一方面“大旗用兩面,一是大紅旗上寫著‘土地革命’四大字,旁書‘工農兵聯合起來’,一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民黨旗”(51)《中共北方局暴動計劃》,《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535頁。。口號與旗幟的不同,體現出北方局要給外界造成一種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內訌的錯覺,這么做一是要借助國民黨的影響力充分發動群眾,二是以國民黨左派的名義保存中共已轉入秘密工作的實力。20天后,徹底轉變思路的中央給北方局回信,指出“暴動的旗幟應該是工農自己的紅旗,國民黨的名義應即取消”(52)《中共中央關于對暴動計劃的意見給北方局的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587頁。。11月5日,根據中央指示,北方局將決議案改為“前此所謂仍然要國民黨招牌的政策,現在已決絕的拋棄了”(53)《中共北方局關于北方政局及黨的任務的決議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613頁。。比如之前的“民選革命政府”改為“農工兵平民政府”、“革命委員會”改為“工農革命委員會”、“工農軍總”改為“工農革命軍”。這么做是為了從政權的名稱上徹底破除“繼承國民黨正統”的心理和“類似國民黨式的大元帥府或國民政府的空名義”,使暴動的權力機關,應當是革命群眾自己的機關(54)《中央通告第十五號》,《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604頁。。
類似于北方局的現象并不是個案,很多地方黨部并未領會中央決議,仍在國民黨中保留同志并借此名義發展工農斗爭。對此,中央于12月31日發表對國民黨工作的通告,命令一切同志必須退出國民黨并進行反國民黨的工作,“撕毀青天白日旗豎起鐮刀斧頭的紅旗”(55)《中央通告第二十五號》,《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831頁。,如有遲疑立即開除黨籍。就此,直到1927年底,中共才徹底完成了從局部到整體、從理論到實踐上徹底放棄以國民黨左派名義組織暴動的轉變,走上獨立自主領導革命的道路。
(二)做工農武裝割據與蘇維埃政權的“領導黨”
雖然在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茨“左”傾盲動主義影響下,處于革命低潮的工農運動遭受了嚴重打擊,但中共在總結工農暴動的經驗教訓后得出很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性革命理論,如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文家市召開前委會議時提出了轉向農村的革命新道路;在三灣村改編軍隊,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標志著中國革命中心從城市轉向農村偉大實踐的初步勝利。1927年11月,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海豐縣蘇維埃政府成立。12月,無產階級第一個城市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成立。盡管這些蘇維埃政權存在時間并不長,但都為中共積累了領導政權的寶貴經驗。
從起義勝利、蘇維埃政權建立的那一刻起,作為領導黨的中共便要面臨三個最大的困難:第一,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第二,在第一個困難的基礎上,蘇區會面臨外部經濟封鎖、商品嚴重不足、資本家關閉工廠、工人大量失業等問題;第三,土地革命后,由于僧多粥少的緣故,農民很可能得不到原先期望的土地面積,引發恐慌與對政權的不滿。此外,還有交通不便、移風易俗、基層黨組織不穩固等問題,都是中共領導蘇維埃政權之初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涉及到政治建設、經濟恢復、軍事發展、社會革命、文化進步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和管理經驗。這些困難能否解決,決定著中共的革命事業能否成功,決定著中共未來是否有能力做一個民族的領導黨、一個國家的執政黨。
經過斗地主、分田地、毀契約、消債務、組織赤衛隊、編練工農軍、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一系列步驟,民眾在實踐中深切感受到只有共產黨才是徹頭徹尾為工農奮斗的政黨,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才能解除一切鎖鏈。對中共自身來說,經過成功領導工農兵群眾建成第一個蘇維埃政權,黨認識到了自身領導革命實踐的力量和斗爭智慧,堅定了領導土地革命的信心,與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黨與蘇維埃政權的關系方面,中共明確了領導黨與政權之間的權力邊界,認為蘇維埃政權是“直接之民眾政權”,“必須經過群眾大會或代表會議選舉,絕對禁止由黨部指派式之組織”;“一切權力屬于蘇維埃”,“黨只是在其中取黨團作用,不得由黨員完全包辦蘇維埃的工作”(56)《中共中央給湘東特委的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79頁。。這些認識和做法都為后來建設革命根據地和在中央蘇區的執政實踐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成為了正式領導政權的預演。
五 總體評價
綜上所述,在國共合作前后,中國共產黨對自身革命角色和領導地位的認識,隨著革命形勢和實踐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變化過程。主要表現為:從純粹做工人階級“指導者”到做革命聯合戰線的“合作者”、“監督者”;從國共合作的“同盟者”到國民政府的“極左在野黨”;從幻想重建國民黨左派到走向獨立自主領導土地革命。促成這一系列轉變的原因,既有中共對自身實力、基本國情、革命形勢由淺入深的認識,又有共產國際的外部干預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由于對此時中國革命特殊性和規律的認識還不夠深刻,斗爭經驗還比較缺乏,在中共奪取革命領導權的探索中始終穿插著兩組理論與實踐的錯位關系。第一,出現了理論上認識到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領導權而實際上無產階級政黨放棄革命領導權的錯位。具體表現為:雖然中共四大認識到了無產階級對中國民族革命的領導權,但并不清楚這個領導權究竟怎么落實,也沒有提出具體方案。于是在實操過程中,中共作為無產階級的政黨卻只能借助于國民黨分享的政治資源,屈居于國民黨之下(57)周家彬《階級與黨:中共革命領導權雙主體的形成與整合(1925-1935)》,《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年第4期,第62頁。。第二,國共合作徹底破裂后,中共在逐漸放棄對國民黨左派幻想的過程中存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錯位。具體表現為:“八七”會議之后雖然中共明確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者不是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而是廣大農民群眾,但在實踐上沒有立刻完全拋棄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直到1927年底有的黨部依舊以國民黨左派名義組織工農暴動,結果多數起義和暴動的失敗使革命力量進一步受損。面對殘酷的現實和血的教訓,中共不得不走向農村,開始獨立領導工農運動、成立蘇維埃政權。
雖然這一時期中共逐漸認識到無產階級政黨獨立領導革命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形成成熟的領導理論,對工人、農民、軍隊、青年的領導方法也還在摸索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黨與工會的關系方面,雖然1921年8月就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專門領導工人運動,但中共五大認為“黨與工會,在過去仍未能有正確的關系,不是使工會成了黨的附屬的機關,即是工會完全脫離了黨的指導”(58)中共五大《職工運動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205頁。。而且黨還存在對工人階級命令主義的錯誤觀念,和強迫罷工、強迫進行武裝斗爭的做法(59)中共六大《政治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頁。。這說明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共名義上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和先鋒隊,但在實踐中并沒有完全確立對工人階級的正確領導。在黨與農民的關系方面,“八七會議”上瞿秋白總結道,中共前五次代表大會都沒有制定關于農民問題的黨綱,而且“對于農民問題差不多沒有注意”。理論上都知道農民是無產階級的主要同盟軍,但“關于土地問題,誰也不曾說起”,農民已經自發動員起來了,“農民政權與土地的問題成了事實的問題,中央才一步步‘落后的’追著農民群眾走”(60)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瞿秋白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頁。在黨與軍隊的關系方面,國民革命時期中共沒有自己的軍隊,只能依靠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南昌起義也是以國民黨左派名義、利用起義部隊打響了第一槍。“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做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61)《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記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393頁。的著名論斷促使中共開始重視軍事建設。在黨與青年團的關系方面,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黨與青年團差不多完全不發生關系”(62)《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640頁。。12月《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關于黨團關系通告第十九號》指出,各地黨團關系惡劣,黨對團的工作缺少指導與幫助,甚至團的會議黨不派人參加,“以致團員看不起黨,罵黨是機會主義組織而單獨領導群眾斗爭”(63)《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關于黨團關系通告第十九號》,《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753頁。。
總之,在國民革命前后,由于自身實力較弱而且沒有形成成熟的領導理論,中共在實際上并沒有取得革命的領導權,也沒有在勞動群眾中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但是,中共作為最具革命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已經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在之后的探索中,中共從一個充滿革命理想主義的幼小政黨成長為找準了革命道路、看清了前進方向、認識了自身力量、明確了斗爭策略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成為中華蘇維埃政權的領導黨和革命統一戰線的核心力量。縱然歷經重重挫折,但中共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并勇于改正錯誤,最終走上了獨立自主領導革命并取得偉大勝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