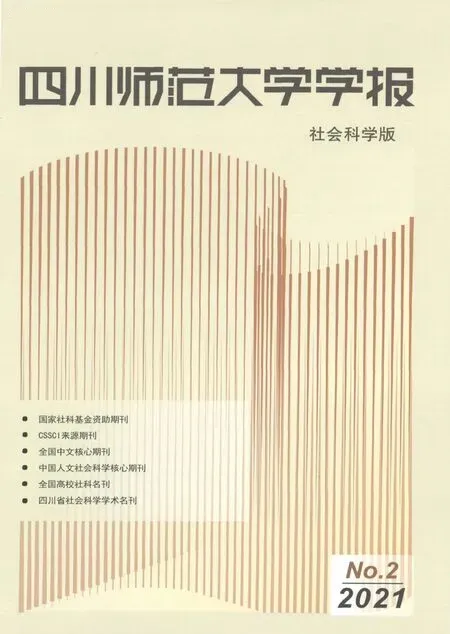論普通法視域下法條競合的演進與啟示
——兼論中國語境下的路徑選擇
付 恒
一 普通法系視域下法條競合現象的存在性
在大陸法系中關于法條競合的理論著述豐富,但在普通法系國家,幾乎難覓法條競合著述的蹤影,似乎在英美刑法的教科書中也找不到與之相對應的概念,當然更遑論對法條競合類型的精細化研究。根據普通法系的特點,通過學理上的通說思維大致可以得出兩個主要論斷:一是認為普通法系因刑法典的闕如,故而沒有具體罪名的法條規定,當然也就不可能出現所謂的法條競合現象;二是認為普通法系國家在秉承先例原則的前提下,以經驗為邏輯起點,以追求實用主義為價值目標,因大多數情形下已有先例和經驗可循,司法上并不迫切需要專門研究一行為觸犯數法條的適用問題,以至于在普通法系下缺失了法條競合、想象競合等與罪數相關的基本概念。
上述論斷似乎在普通法系的語境下一語中的地揭示出了問題的根源,然而普通法系下究竟有無法條競合現象?在對此問題揭示之前尚須解決兩大問題:第一,代表普通法系的英美刑法究竟有沒有刑法典?刑事單行法規?抑或刑法法條?如若有,當然就存在法條競合的可能性;第二,如若沒有,英美法系判斷一行為構成犯罪的標準又是什么?這個標準無論是理論上的犯罪構成抑或實踐中的判例規則是否也存在重合的可能性?如若存在這個標準,當然也就存在法條競合的蓋然性,只是行法條競合之實,冠之以其他稱謂而已。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須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對英美刑法的立法流變歷程做理論上的尋蹤與梳理。
二 英美關于法條競合的立法與司法概況
(一)英國有關法條競合的立法與司法概況
英國刑法的淵源由普通法和制定法兩部分構成,其中普通法是英國刑法最主要的法律淵源,制定法則是英國刑法的另一個重要法律淵源。普通法濫觴于人們的長期習慣,并通過各級法院法官的判決和裁定不斷加以完善和發展。制定法則是把普通法加以整理、修訂和充實,主要由國王批準的上議院和下議院正式通過的法案構成。現今英國大部分罪名幾乎都是由制定法創設而成,也有部分制定法是議會將普通法的原則用條文加以細化規定而成。制定法的主要功能是對普通法的原則進行說明,也可以對普通法中某些闕如進行補正。這種功能就決定了它并不像大陸刑法典一樣,在刑法總則的規定下制定統一的分則體系,而是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而產生數量眾多而雜亂的規定(1)趙秉志、黨劍軍編譯《英國刑法的新走向——法典化》,《中央檢察官管理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第67頁。。
自16世紀伊始,英國學者便傾心于法典編纂理論的研究并付諸司法實踐。在Jeremy Bentham提出系統的法典編纂理論之前,英國刑事法律界在嘗試著將制定法和案例上的某些內容做法典化的努力方面,已經積累了不少法典編纂的經驗。但正如美國學者Gunther A. Weiss所指出:“到目前為止,法律學者一直關注歐洲大陸法典化的歷史,而有關法典化在普通法系中的相關作用仍然不甚明確。”(2)Gunther A.Weisst,“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no.2 (Summer 2000) : 437.直至19世紀,英國刑法改革出現了去“不成文”法傳統轉而走向法典化的趨勢。此舉引發了推動改革的法典編纂派與以法官、律師為主流的保守派之間的爭論與博弈。改革派在推動法典化的進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例如,英國在1981年編纂完成了《英國刑法匯編》,但直至1989年4月,英國法典編纂委員會才公布了《關于〈英國刑法典〉的最終報告》和《刑法典草案》。在強大的普通法傳統的抵制下,法典化努力最終功虧一簣。正如曾任英國刑法改革委員會主席的Brook大法官所言:“倡導刑法法典化的改革者沒有找到務實、可行的法典化方法:在于其主張法典化的觀點還沒有得到社會大眾的普遍認同,社會民眾沒有感覺到現行刑法可能存在的問題和改革的必要性;在于社會民眾很難接觸到刑法的基本部分……”(3)何榮功《英國刑法的法典化改革之路述評》,《中國審判》2013年第1期,第73頁。英國刑法法典化運動雖然功敗垂成,但從19世紀開始的刑法法典化改革對英國刑法的系統化和規范化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促使普通法不斷吸收大陸法系成文法之精義而得以行穩致遠。
英國以判例法為主,刑事法典化起步較晚,加之缺乏成文法文化傳統的底蘊,并且由于英國沒有明確規定構成要件的概念,導致其制定法在法條競合問題上缺乏直接規定(4)趙秉志、黨劍軍編譯《英國刑法的新走向——法典化》,《中央檢察官管理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第68頁。。這體現在無論是刑事制定法上的具體犯罪規定還是普通法上的隱形犯罪規定,均通過不同的差異化的具體案例判決將每種犯罪類型予以個別化處理,而非抽象的歸納構成要件。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陸法系中探討各個犯罪構成之間究竟是否存在競合的理論,在英國刑事法制體系的構架下近乎成為多余。應當注意的是,由于刑事制定法是英國刑法的另一個重要法律淵源,它不僅可以對判例的原則進行說明,也可以對判例中某些闕如進行補正,所以制定法中存在著很多關于罪名的內涵和外延的具體規定。有鑒于此,英國為數眾多的不同刑事制定法中當然也就存在著罪名之間發生競合的可能性,從而產生法條競合的司法適用問題。
面對一行為觸犯數罪的司法處理,英國刑事法律界特別強調對危害結果的關注,不區分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嚴格奉行有罪必罰的原則。在普通法系中,形式上的數罪(如法條競合)均被認為是實質上的數罪,對各罪所判處的刑罰必須進行嚴格相加。毋庸諱言的是,這種做法會直接導致刑罰過分嚴厲而失去均衡性。自20世紀50年代伊始,吸收原則(同時執行原則)和限制加重原則開始被廣泛吸納采用(5)任彥君《數罪并罰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頁。。例如《英國刑法匯編》中規定了一行為觸犯數罪的并罰方法——同時執行制度。所謂同時執行是指罪犯的數個判決在相同時間和地點同時執行,其執行效果相當于大陸法系的吸收原則,但是在理論上又不同于吸收(6)吳平《數罪并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頁。。以同時執行為例,犯罪嫌疑人使用故意損壞財產的方式實施盜竊,因盜竊罪被判處5年有期監禁,因損害財產罪被判處1年有期監禁。當盜竊罪被判處5年有期監禁執行完畢之時,損害財產罪被判處的1年有期監禁相當于在4年前已經執行完畢。從適用效果上看,這種并罰方法與大陸法系的并科原則近乎一致,但其判決確立的數個宣告刑是彼此獨立的并且按照判決順序依次執行。質言之,英國刑法對于一行為觸犯數罪的處理模式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對觸犯的罪名分別處刑;二是依次執行各罪所判處刑罰,但刑期并科。通過刑期并科的量刑手段來糾偏因認定一行為觸犯數罪而被并罰的不公正結果,從而實現罪刑均衡的價值目標。
(二)美國關于法條競合的立法與司法概況
與英國處理法條競合問題的模式相比較,美國不僅有犯罪類型個別化的法典化嘗試,也有普通法上的類型化經典判例,同時還在法典中對該問題的處理做出了專門具體的規定。成文法在美國法律體系中作為重要的法律淵源,其地位和分量足以與判例法平分秋色。尤其是在聯邦刑事立法方面,刑事單行法規幾乎構成了刑法淵源的絕大部分。
美國刑法的法典化運動濫觴于1790年國會頒布的《治罪法》。此后,大量單行刑法及附屬刑法如雨后春筍般涌現。1879年,美國國會任命專門委員會校訂和編纂刑事法典。1909年,《編纂、修正、改訂聯邦刑事法規的法律》正式頒布,共計14章536條。但該法典并無總則的規定,且各個章節之間留有很多空白法條,以便于后來增補。1926年,美國正式制定《聯邦法典》(UnitedStatesCode);1948年,國會通過修正、法典化及實施有效法律的法令,創制了《聯邦法典》第十八主題犯罪及刑事程序(7)李仲民《美國聯邦刑法法典化述評》,《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第7頁。。該刑法典被定義為“法律的系統收集,歸納或修訂”(8)Julie R.O’Sullivan,“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is a disgrace: Obstruction statutes as case stud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96, no. 2 (Winter 2006) : 643.,其目的在于加強各個州之間刑事立法的統一性。但法典條文的章節“按照字母流排序排列、零散而沒有邏輯”(9)Ronald L. Gainer,“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Past and future”, 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2, no. 1 (April 1998): 92-93.,對個罪的定義冗長而不明確。“1971年1月7日,國家聯邦刑法改革委員會向總統和國會提交了關于全面修訂實體聯邦刑法的提案。這項工作是在國會授權的基礎上開始的,旨在改善刑法典的體系”(10)John F.Dobbyn,“A proposal for changing the jurisdictional provisions of the new federal criminal code,” Cornell Law review 57, no. 2 (January 1972) : 1.。《聯邦法典》雖經歷多次修訂,但其基本面并無太大變化。《聯邦法典》“這些缺陷不能修復或通過增加新法規補救,因為它們是根本性的”(11)Robert H. Joost, “Federal criminal code reform: Is it possible?”Buffalo Criminal Law Review 1, no. 1 (April 1997): 195.轉引自:李仲民《美國聯邦刑法法典化述評》,《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第13頁。。
進入20世紀以后,美國立法及判例數量呈現幾何級數量的膨脹,由于聯邦刑法太過細化,加之理論上不完整,缺乏實踐的操作性,已令司法者無所適從。1962年美國法學會編撰并公布的《模范刑法典》,被譽為美國近代刑法法典化的里程碑。回顧美國的刑法法典化進程,“《模范刑法典》不是第一個或最具有雄心的刑法編撰,但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刑法法典化編撰嘗試”(12)Paul H.Robinson,Markus D. Dubber,“The America model penal code: A brief overview,”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0, no. 3 (Summer 2007) : 320.。
源于普通法系傳統的影響,美國刑事司法理論中也沒有構建法條競合的相關概念。當在判例中出現了一行為觸犯數罪的客觀現象而危及“禁止雙重危險原則”(double jeopardy)之時,現代美國刑法理論與實務都采取了相對的變通措施,對大陸法系法條競合類型中的包容關系予以了立法承認,并將此類情形全部作為一罪加以處理。《模范刑法典》首次在第1.07條中專門做出了具體規定,并將其稱之為“當一行為超過一個罪行時的起訴方法”(Method of Prosecution When Conduct Constitutes More Than One Offense)。尤其在第1.07條第一款和第四款中更是詳細規定了一行為構成“數罪”處理的一般原則與特殊例外規則,以實現有罪必罰原則和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平衡(13)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Model Penal Code,1962-05-24.。雙重危險原則作為美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其基本含義是“禁止多項起訴和多重處罰同樣的罪行”(14)Carissa Byrne Hessick & F.Andrew Hessick,“Double Jeopardy As A Limit On Punishment,” Cornell Law Review 97, no. 3 (November 2011): 46.,其義理在《模范刑法典》第1.07條到1.11條的規定中從不同的方面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彰顯。
一般原則規定當被告人實施一行為而觸犯數個罪名之時,對于所犯各個罪名均可予以追訴。特殊例外規則規定了當同一行為觸犯數罪時,不得做兩個以上的有罪認定的五種情形。(1)一罪被他罪所吸收的。第1.07條第四款規定了存在以下三種情況時,犯罪被吸收:“a.被指控的一罪成立的全部或部分事實已被包含在他罪之中;b.被指控的基本犯罪吸收該種罪的未遂或教唆;c.被指控的某一罪名對于同一人、同一財產或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損害較輕,或者可責性比較輕,那么損害和可責性較重的吸收較輕的。”(2)一罪僅為他罪的共謀或其他預備行為。(3)如果被告人只有一個相同行為時,為確定數罪的實行,需要認定不同的事實。(4)存在一般與特殊關系的情況。(5)某持續性行為被規定為犯罪,并且持續行為未被中斷的。(15)美國法學會《美國模范刑法典及其評注》,劉仁文、王祎等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頁。第一種情形和第四種情形大致分別對應大陸法系法條競合理論中的吸收關系類型和一般與特殊的關系類型。第1.07節的規定充分說明,美國刑法體系中雖然沒有法條競合的相關概念,但并非不存在法條競合的客觀現象并對如何處斷提出了獨特的適用原則與方法。
三 普通法系法條競合處置方案的評析與啟示
概言之,籠統地認為普通法系對法條競合的相關問題研究毫無建樹是不符合實際的,認為對于一行為觸犯數法條實行過于苛嚴的有罪必罰原則也是有失偏頗的。畢竟不同的法系之間,同樣面臨著如何實現法條競合犯罪刑均衡的共同任務。因此,總結、提煉與反思普通法系下的法條競合處置方案,或能使我國的法條競合理論與司法實踐得以借力滋養而綻現異域新花。
(一)借鑒普通法系的“找法”路徑
普通法系借助于先例制度和陪審制度,針對法條競合個案的路徑導向值得大陸法系學習和借鑒。事實上,法條競合理論建立的目的無非是要解決一行為觸犯數個法條應當如何適用來達到罪刑均衡的目的,說到底是要解決如何在實踐中“找法”的問題。大陸法系是在承認法條之間存在競合的前提下,在對法條競合現象分類的基礎上,運用形式邏輯學和刑法解釋學的方法,提出針對不同類型的法條競合采取不同的司法適用原則的方法來實現罪刑相適應。普通法系則繞開錯綜復雜的法條而另辟蹊徑,其主要著力點并非放在法律邏輯以及解釋技術層面,而主要是通過對實體和程序雙重維度的技術設計來“找法”,以實現個案正義。
一方面是普通法系在實體法層面通過先例的適用來回避抽象繁雜的法律條文解釋。與大陸法系的司法體制不同,普通法系國家實行先例制度。在這種制度模式的架構下,法官在審判案件之時,必須以先前的判例作為指導,有效地避免了抽象繁瑣的法律條文分析,讓裁判者的思維更多地集中于案件的事實、證據的認定以及程序是否正當等相關問題,而非拘泥在法條應當如何分析、如何適用的語境下考慮問題。“它使法院在一個法律問題每次重新提出時就重新考察該問題的作法成為不必要”(16)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頁。,從而縮短了法條競合個案的處理過程。同時在思維模式上則更多地側重于通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使得案件的判決結果符合罪刑均衡的理念。
另一方面,對于“找法”涉及的實體和程序問題,普通法系通常采用雜糅的方式進行合并規定。通過這樣的技術處理,涉及相關問題的實體性規定和程序性規定便相對集中,較大陸法系中實體法、程序法分別規定的找法路徑更為簡潔明了。例如,《模范刑法典》1.07條第一款主要是從實體上規定一行為觸犯數罪的處理原則;第二款規定了對數罪分開進行審理的程序性限制;第三款規定了法庭啟動分開審理數罪的權限;第四款規定一罪吸收他罪的三種具體情況;第五款規定法庭是否有義務對被吸收的犯罪向陪審團提出具體的指控。(17)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Model Penal Code,1962-05-24.由此可見,第一款和第四款主要涉及實體問題,第二、三、五款主要涉及程序性問題。處理一行為觸犯數罪的實體和程序問題均在同一條文中予以全部規定,盡顯普通法系簡約、高效之風范。
另外,在制度的設計上,陪審團制度的設計理念與制度安排,巧妙地將草根階層的“常識、常情、常理”融入到案件事實的認定過程之中,有效地化解了精英階層與草根群眾在“找法”路徑上的價值評判差異。此種設計之精髓在于力圖避免出現大陸法系學者在自行構造的理論經緯中違背“常識、常情、常理”所做出的刑法解釋與司法處斷。因為“出于解決糾紛的需要,司法必須要考慮民眾的倫理性需求和慣常性行為方式,必須以更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來運作”(18)李擁軍《當代中國法律對親屬的調整:文本與實踐的背反及統合》,《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4期,第71頁。,而陪審團制度在進行犯罪事實的認定上,無疑是一種以普通大眾的生活經驗為基礎,以滿足人倫、人情、人性需求為出發點,以合理的價值考量為終極目標的獨特司法運作方式。
(二)吸納其對有罪必罰原則的“糾偏”技術
對于普通法系通常采取的對同一行為構成兩個以上犯罪的“有罪必罰”原則,不能一味地加以批判和否定。所謂“有罪必罰”原則是指當一個行為觸犯兩個以上法條規定的罪名時,普通法系堅持以行為觸犯的法條為標準確定基本的罪數,并且不設上限的原則。這一點顯著區別于大陸法系在罪數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換個角度思考,至少普通法系這種在定罪問題上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這不僅反映了其對犯罪認定的謹慎態度,也彰顯了其法治精神的基本理念。“有罪必罰”實質上是應然層面的法則,普通法系對這一原則的恪守,更是體現了對應然原則的遵循。在實然層面上,雖然被告因同一行為可能構成兩項以上的犯罪時,被告可能會因每項罪名而被起訴,但事實上可能并非會判處構成多項罪名,或者即使判處了多項罪名也可以通過刑法典中的吸收原則或者同時執行制度加以矯正而達到罪刑均衡的目的。
從罪名的角度看,美國《模范刑法典》通過1.07節中規定了不得重復處罰的五種情形來避免對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過度認定。例如,被告的客觀行為符合上述五種情形,那么被告雖然在理論上會被指控多項罪名,但事實上多項指控的罪名會被某一項指控的罪名所吸收而僅構成一罪。多項指控的進行體現了對法治原則的尊重,吸收原則的執行實現了對避免“雙重危險”原則的恪守。通過對“有罪必罰原則”和“吸收原則”的貫徹,實現了法治精神與罪刑均衡的協調與統一。
從刑罰的角度看,英、美兩國解決法條競合問題的“同時執行”制度成功地化解了有罪必罰原則在罪數認定問題上可能導致的罪刑失衡。由于《模范刑法典》中并非一一涵蓋了法條競合的全部類型,當出現一行為觸犯數罪的行為不屬于五種吸收情形而被認定為數罪時,必須對每一個罪的刑罰悉數執行,這樣的做法則顯得過于苛嚴。普通法系獨樹一幟的同時執行制度,即是從刑罰的角度來糾正對罪名過度評價而造成的刑罰失衡。通過最大限度地發揮法官自由裁量權的作用,從而消解法條競合被裁定為數罪所帶來的重復評價和罪刑不相適應的問題。它的適用標準是同一行為,即針對于同一個行為的判決才能適用同時執行制度。如果基于同一行為的數罪判斷,連續執行則構成“雙重處罰的危險”,這是英美立法明令禁止的。于是按照同時執行的方法便可以取得按照大陸法系相關理論處斷近乎相同的效果。另外,作為判斷同一行為的依據,普通法系從理論上提出了“同樣的證據”、“同樣的處理”、“同一立法目的”等標準。“同一立法目的”標準與大陸法系在判斷法條競合上的法益標準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保護法益就是立法目的(19)李貴方《自由刑比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頁。。
(三)吸收其最大限度消解競合的解釋技術
在刑事立法和刑法解釋技術上,普通法系在易于混淆的罪名設置上,通過澄清罪名的內涵與外延,最大可能地消解法條之間發生競合的可能性,這種技術路徑值得大陸法系反思與借鑒(20)饒景、蔡鶴《英美刑法中的法條競合》,四川師范大學法學院《師大·西部法治論壇》2017年2期,第45頁。。在罪名的設置上,普通法系大多采用了“互斥論”的基本立場,即在罪名的內涵釋義上將容易發生法條競合現象的罪名之間解釋為對立關系。尤其是概括的罪名之下多采用對立關系的模式設立關系模糊的個罪,從而避免了各個罪名之間是否發生競合的判斷。例如,“英美普通法和制定法把殺人罪(criminal homicide)分為謀殺(murder)和非預謀殺人(manslaughter)兩大類”(21)儲槐植《美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頁。。為了防止謀殺罪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聯罪名之間的競合,通過對立模式的學理解釋將謀殺罪又分為:蓄意謀殺罪(intent-to-kill murder)、故意重傷謀殺罪(intent-to-do-serious-bodily-injury murder)、極端輕率謀殺罪(depraved-heart murder)、重罪-謀殺罪(felony-murder)、拘捕謀殺罪(resisting-lawful-arrest murder)(22)對于謀殺罪的類型分類,在美國并沒有統一的立法模式或理論學說,這里采用了美國大多數學者承認的分類標準。。將非預謀殺人罪(manslaughter)分為非預謀故意殺人(voluntary manslaughter,如激情殺人)和過失殺人(voluntary manslaughter)(23)Emily Finch & Stefan Fafinski, English Legal Syste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93-113.。又如,在美國的刑法理論和實踐中,通過區分財物交易過程中所有權是否轉移來劃分以欺騙方式實施的盜竊罪與詐騙罪的界域,在這類型的案件中“盜竊罪的控方要求證明在起訴狀中指控的盜竊是以何種形式實施的。因此,如果起訴狀指控偷盜罪,控方就不能獲得侵占罪或詐騙罪的裁判”(24)德雷斯勒《美國刑法精解》,王秀梅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頁。。
四 我國現行制度的癥結
(一)《刑法》總則中缺失法條競合和想象競合的原則性條款
“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競合(罪數)論的體系建構可謂‘五花八門’,當屬刑法知識體系中最‘雜亂’的一章。究其原委,除了競合理論本身的復雜性(包括德式競合論抑或日式罪數論之模式選擇上的博弈)原因,我國刑法長期缺乏競合(罪數)問題的總則性規定(即無法可依)亦不無關系。”(25)王彥強《“從一重處斷”競合條款的理解與適用——兼談我國競合(罪數)體系的構建》,《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98頁。毋庸諱言,與德日體系的立法不同,我國《刑法》總則中缺乏有關競合問題處理原則的一般性條款,只是在分則個別個罪條文中規定了部分競合關系的處置條款(26)例如,刑法中提示可能存在法條競合的注意性規定“本法另有規定,依照規定”;提示可能存在想象競合的語詞“有前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某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本處之所以表述可能存在想象競合,這是因為在交叉關系的法條競合、吸收犯以及牽連犯等處斷的一罪中,同樣適用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但這些碎片式的規定由于缺乏統一的原則指導,常常會出現相互抵牾的情形而讓實務界無所適從。
例如,行為人在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過程中,以暴力抗拒執法檢查,在《刑法》不同的條文規定中處遇迥異。《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方式抗拒緝私的,以走私犯罪與妨害公務罪數罪并罰;但是在第三百一十八條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和第三百四十七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中,又將“暴力抗拒檢查”的行為作為法定刑升格的條件。相同的行為卻沒有得到相同的處遇,競合問題在刑法典規定中的沖突可見一斑。
某甲利用信用卡詐騙4000元的行為,在司法實務的處斷過程中似乎既符合信用卡詐騙罪,又符合普通詐騙罪的行為類型,屬于法條競合的屬種關系類型。司法人員往往會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普通詐騙罪“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的提示,排除普通詐騙罪的司法適用,僅適用特別法條的信用卡詐騙罪。而問題在于甲沒有達到信用卡詐騙罪的入罪數量標準,應當作無罪處理。按照法條競合的提示性語詞,卻得出了似乎在構成普通詐騙罪的前提下的無罪結論,這也頗令實務界感到無所適從。為了突破這一困境,《刑法修正案(九)》對分則相關競合條款進行了系統性調適,大體形成了“從一重處斷”條款、“從特別規定”條款和“數罪并罰”條款三種類型主導的局面。但由于《刑法》總則中關于競合問題的原則性規定闕如,在實踐中仍舊會出現個案處理中的巨大分歧。普通法系通過明確“有罪必罰原則”和“吸收原則”的內涵,并在實踐中加以嚴格貫徹,實現了在處理法條競合犯問題上,法治精神與罪刑均衡的協調與統一。在現行制度的架構下,若能從競合處置條款中歸納法條競合、想象競合的一般性處置原則,則能夠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問題的處理,提供相關明確的法律適用原則。
(二)刑事指導案例缺失相關法條競合的典型案例
在成文法傳統占統治地位的大陸法系,案例同樣是刑法學研究的基礎。刑法理論中絕大多數真問題的發現都是圍繞著具體鮮活的案例而展開的。長期以來,我國司法機關也高度重視對刑法典型案例的歸納和總結,注重類型化案例的示范效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頒布,標志著我國案例指導制度的正式建立。作為我國司法實踐的一種有益嘗試,案例指導制度已經實施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共計頒布了139個指導案例,其中刑事指導案例22個(截止到2020年2月17日)(27)《刑事指導性案例》,北大法律信息網,2020年2月17日訪問,http://www.pkulaw.com/case/。,這些指導案例在司法實踐中正在被廣泛運用,發揮著參照、示范、規范、監督等重要作用。
但是當下我國案例指導制度也存在著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由于目前刑事指導案例的數量較少,覆蓋范圍也非常有限,特別是22個刑事指導案例難以涵蓋刑事司法實踐的典型法律難題,更缺少關于疑難競合問題的典型案例,這就不能對實踐中如何處理交叉競合、屬種關系競合以及整體法與部分法的競合起到典型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已經頒布的刑事指導性案例存在部分案例指導力與說服力不強的問題。多數案例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在重申司法解釋或者是回應社會公眾關切的熱點問題,缺乏對案例中蘊含的法理和規則做進一步的抽象和解釋。在英美法系,先例之所以能夠發揮巨大的司法指導作用,除了其本身具有法律效力之外(28)在案例的效力上,英美法系的先例制度與我國的案例指導制度具有不同的內涵。英美法系中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所有的既定判例就是法的淵源。我國的案例指導制度是在繼承大陸法系成文法傳統的基礎上,運用典型案例解釋現行法律、指導法院審判活動,從而維護司法統一的司法改革舉措。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自身沒有法律效力,僅僅只是適用成文法律而已。指導性案例在我國顯然不屬于法律淵源,當然法院判決也就不會“造法”,但可以為成文法的運用提供豐富的案例素材。,還表現為在辨法析理上尤為透徹,特別是能夠給予后案法官充分的法律指導與啟迪。特別是一些影響深遠的法學理論以及里程碑式的結論往往都是通過先例判決來對既定規則進行補充和突破(29)例如,美國第五憲法修正案雖然規定了反對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但這僅僅是一種原則性的規定,在具體適用中當如何啟動或者受限并未加以明確規定。通過1965年的格里芬訴加利福尼亞州案(Griffin v. California)的判決結果,對這一修正案進行了補充和完善,衍生出即使被告人沒有提出反對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仍然應當受到該權利的保護的規則。參見:Griffin v. California, 380 U.S. 609, 615(1965)。。事實上,“案例指導制度的首要功能是創制司法規則,因為只有司法規則才能為此后審理相同或者相似案件提供參照”(30)陳興良《刑法指導案例裁判要點功能研究》,《環球法律評論》2018年第3期,第6頁。。
(三)競合問題的處斷常缺乏“常識、常情、常理”
“司法審判的進路在于從案情出發,從事理出發,訴諸常識常理常情,從事理切入講求法理,公正裁判以達至解決糾紛之目的”(31)魏俊斌、帥佳《法與不法:比較法視野下的德國判例與“于歡案”一審》,《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53頁。。但作為指導司法實踐的競合處斷理論卻存在著偏離“常識、常情、常理”的傾向。例如,有學者主張想象競合犯“其本質是危害行為的競合,其同一的自然行為蘊含了多個具有刑法意義的行為。因此,以多個犯罪構成分別評價想象競合犯,其實是以多個犯罪構成分別評價其所競合的多個行為。可見,從想象競合犯的本質觀之,也不存在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的問題”(32)莊勁《犯罪競合:罪數分析的結構與體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頁。。因此,對于想象競合犯的處斷原則應當數罪并罰。從專業視角關照,由于同一自然行為蘊含了多個刑法意義的行為,侵犯了多個法益,因此數罪并罰似乎并不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但從大眾的視角來審視,草根階層深信行為人明明只有一個行為,卻要被數次評價,遭到數次處罰,明顯有悖于“常識、常情、常理”。至于學者所謂的被處罰的一行為是“多個具有刑法意義的行為”,在大眾看來只是學者自娛自樂的概念游戲,對于民眾而言是難以理解的。正因為精英階層與草根群眾在對待個案正義上的價值評判差異,才導致了近年來諸如“辱母案”“昆山案”等爭議判決的出現。事實上“在刑法領域,也要以生活經驗為基礎制定法律與解釋法律,付出經驗之外,作合理的價值判斷”(33)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頁。。
如何解決此種沖突?如何在競合問題的處斷上融入更多的“常識、常情、常理”?吸納普通法系下的陪審制度之精髓,立足于本土資源的司法制度考量,人民陪審員制度無疑是有效化解沖突的選擇路徑。“作為一種旨在彰顯司法民主與權力制衡的制度,陪審制度設立的初衷即在于通過陪審形式,讓普通民眾直接參與到司法審判的進程中來,并在此一進程中通過參與案件審理、獨立提出案件處理意見等方式,強化審判權運行的社會監督和制約,實現民眾政治意愿的充分表達”(34)步洋洋《中國式陪審制度的溯源與重構》,《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5期,第91頁。。其本質不在于業內人士的職業支持,而在于草根階層觀點的融入,以便形成不同價值觀念與知識譜系、思維模式的碰撞,凸顯個案處斷過程中草根路線與精英思維的博弈與平衡。
五 中國語境下法條競合的制度路徑選擇
(一)刑法典總則中增補“一行為觸犯數罪”處理原則的修正案
當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時,可能構成想象競合也可能構成法條競合。當一行為真實地構成數罪時符合想象競合;當表面上觸犯數罪名,但僅適用一法條便可以對其不法內涵予以充分評價時則構成法條競合。對于想象競合,無論是《德國刑法典》還是《日本刑法典》都在總則中做出了原則性規定,而對于不符合想象競合規定的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情況,德、日則僅在理論上對其不同的類型應當如何適用刑罰分別加以探討。例如,《德國刑法典》總則第三章第三節“觸犯數法規的量刑”之第五十二條對“一行為觸犯數罪”進行了原則性規定。該規定指出,行為單數觸犯數個刑法法規,或者數次觸犯同一刑法法規,系想象競合(Idealkonkurrenz)。前者稱為同類想象競合,后者稱為異類想象競合。對于想象競合犯,采用結合原則(Kombinationsprinzip)科刑(35)《德國刑法典》,徐久生、莊敬華譯,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對于因各法條本身存在的交叉、包容關系而導致表象上觸犯數個刑法條文,但事實上只能適用其中一個法條的假性競合,亦即法條競合(Gesetzeskonkurrenz),《德國刑法典》并未加以明確規定。德國刑事法學理論認為法條競合在本質上是犯罪單數,因此并不存在競合問題。《日本刑法典》在總則中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了一行為同時觸犯兩個以上罪名的是想象競合犯。對于想象競合犯,應當按照其最重的刑罰處斷。在《日本刑法典》中也同樣沒有關于法條競合的概括性規定,致使對該問題的處理模式與德國如出一轍,僅在學理解釋和司法判例中予以探討(36)《日本刑法典》,張明楷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5頁。。這看似雷同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個“真問題”,即:為什么德、日均不在總則條款中對法條競合的構成要件與處斷原則加以規定而僅規定想象競合的要件與處斷原則呢?一是簡化問題的需要。當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時,要么是想象競合要么是法條競合。當總則性條款對想象競合做出了要件規定后,一行為觸犯數罪不屬于想象競合當然則歸屬于法條競合,總則自然沒有必要再對法條競合做出同樣類似的規定。加之法條競合的類型復雜,不可能在總則性規定中進行詳細列舉與闡釋。雖然美國在《模范刑法典》中對法條競合做出了相關具體規定,但也僅涉及到了吸收關系與屬種關系兩種類型。二是強調想象競合的處斷不能按照普通一罪的處理模式。前文已述,法條競合的本質是犯罪單數,實質上僅有一個法條得以適用,是假性競合。對此按照一罪處罰即可,而無需在總則中予以強調。想象競合的本質是犯罪復數,實質上符合兩個以上的法條,是真實的競合。對此必須在總則條款中做提示性規定,強調其不能按照普通一罪處罰的原則來進行。
想象競合的構成要件和處理原則可以借鑒德日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刑法體系的特點,在《刑法》總則中予以明確規定。考慮到法條競合的類型較為復雜且理論上爭議較大,可以對其不作具體規定,但可以吸納美國《模范刑法典》的經驗,對于法條競合的構成要件和處理原則在《刑法》總則中予以統一規定,以防止在個罪中分別規定所造成的抵牾。例如,前文所述某甲利用信用卡詐騙4000元的案例,若總則中對法條競合做出了上述規定,那么我們可以在司法上明確該行為必須在表面上觸犯數個法條,而只有一個法條可以對其不法予以充分評價。依據第二百六十六條普通詐騙罪“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的提示,說明該行為根本不符合普通詐騙罪的犯罪構成,依據信用卡詐騙的入罪數額標準也達不到相關要求。由于該行為沒有觸犯數個法條,當然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競合問題,對其僅能按照違法行為處理而非犯罪行為處理。
(二)增補類型化的法條競合案例,完善刑事案例指導制度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選取社會關注度高、法律規定比較原則、具有典型性的法條競合疑難案例予以發布,特別是當前社會熱點中涉及的交叉競合、屬種關系競合以及整體法與部分法競合的三種代表性案例。通過對三種法條競合類型典型案例判決來進行辨法析理,回應社會訴求,指導司法實踐。例如,近年來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崛起,快遞行業中有關侵犯財產的犯罪頻繁發生。特別是對于快遞行業員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侵犯客戶財物行為所導致的競合罪名當如何進行認定,是當前刑事司法實務應當正面回應的問題。那么此類犯罪行為究竟是論盜竊罪?侵占罪?抑或職務侵占罪?圍繞上述競合問題,就可以通過典型案例的裁判要點進行釋法析理,澄清三罪之間的競合關系并給出司法處斷結論。唯其如此,方能達到釋疑解惑、正本清源之目的。
其次,要充分發揮刑法指導案例裁判要點的多重功能,從而滿足對于特殊刑事案件的公平正義要求。梳理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22個刑法指導案例,不難發現裁判要點已經漸入刑事理論與司法實務的視域,成為司法規則的荷載主體,秉承著該類典型案例的義理精華。未來的案例指導制度改革,要進一步加大對裁判要點的學理剖析,更加充分發揮其司法規則的創制功能(與司法解釋相比較而言,刑事指導案例能夠更為細致、具體地創制類型化規則)、條文含義的釋義功能(通過規則的細化對刑事法律規定本身進行解釋與厘定,明確法律條文的具體含義)以及理解沖突中的釋疑功能(通過類型化案例的辨法析理解決法律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沖突)(37)陳興良《刑法指導案例裁判要點功能研究》,《環球法律評論》2018年第3期,第6頁。。
最后,指導案例的裁判要點優化,一方面要在對類型化案例的案件事由、爭議焦點、定罪與量刑依據的高度提煉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充分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與大數據,將高度凝練的裁判要點和關鍵詞通過多種網絡平臺予以公開發布,以實現快捷、高效、準確的檢索。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司法工作人員的對典型案例的知曉程度,還可以借助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力量充分挖掘典型案例的價值與功能,同時法官也可以通過閱讀簡明扼要的裁判要點節省“找法”的時間,從而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三)構建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本土化進路
從兩大法系來看,現代陪審制度主要表現為以英美法系為代表的陪審團制度和以大陸法系為代表的參審制度兩種模式。20世紀末,大陸法系的參審制度呈現出了吸收、借鑒、融合英美法系陪審制的趨勢。這種趨勢一方面表現為新引入陪審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以方興未艾之勢,在大陸法系的傳統領域內蔓延。例如,“1995年,西班牙頒布《陪審團法》,開始采用英國式的陪審團制度;2009年,日本開始實施《關于裁判員參加刑事審判的法律》,在制度層面正式確立兼具大陸法系參審制度與英美法系陪審團制度特征的‘裁判員制度’。2017年11月,我國臺灣地區司法院公布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實現由形式監督的‘觀審員’到實質參審的‘參審員’之轉變”(38)步洋洋《中國式陪審制度的溯源與重構》,《中國刑事法雜志》2018年第5期,第89頁。。但在這種融合的進程中,部分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兩種制度在體系與價值上激烈的碰撞,最終導致回歸單一模式。例如,基于對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在司法上的區分困難,德國試圖移植陪審制的努力最終歸于失敗并回歸到了參審制。事實上,日本雖然引進了陪審制但也沒有區分裁判員與法官在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上的職權差異,而是強調在此過程中,應當融入裁判員的社會經驗與社會知識,防止法律職業精英們忽視一般國民社會經驗的技術專斷。因此兩種模式的交融,既必須立足于各國的歷史經驗與法律文化傳統,又必須符合國內刑法語境,滿足司法民主的訴求。
一方面,在我國現行司法體系下構建以“事實審”和“法律審”徹底分離為基礎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不僅不具備可操作性,且只會給司法實務徒增困擾。例如,在審理涉嫌“猥褻兒童罪”的庭審過程中,按照“事實審”和“法律審”相分離的模式,陪審員在庭審中需要對是否存在猥褻兒童這一事實問題進行認定。但是否是兒童的判定不單純是一個事實問題,還涉及到法律的評價和判斷,是否屬于猥褻行為也涉及到經驗法則的評價而不是單純的事實判斷。從司法實際運行的經驗來看,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總是糾纏在一起,往往難以分割。因此判斷“兒童”是否遭受被告人實施的“猥褻”行為侵害,必須在整體上加以評價,而不能在庭審中機械地加以分割。因此,現行陪審制度需要的是“事實審”和“法律審”的相對分離,而不是絕對分離,更需要的是職業法官與陪審員之間的協商信任與通力合作而非相互制約。2018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將七人合議庭中的人民陪審員權限限縮為事實問題認定上的決定權,法律問題上的保留建議權(39)2018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陪審員法》第二十一條和二十二條分別規定:“人民陪審員參加三人合議庭審判案件,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發表意見,行使表決權。人民陪審員參加七人合議庭審判案件,對事實認定,獨立發表意見,并與法官共同表決;對法律適用,可以發表意見,但不參加表決。”。這一規定正是對“事實審”和“法律審”相對分離的立法肯定,或許對于司法判決的民意基礎和社會效果會更加有利。
另一方面,在人民陪審員的選任上,借鑒英美法系中對陪審員“無知美德”的要求,復歸人民陪審員本有的平民視角,保留陪審員作為一般國民的社會經驗與社會知識,避免“專業化”導向下的“被法官化”現象。在現階段,首先,要逐步廢除關于陪審員崗前、定期、日常法律職業培訓之規定。刪除關于陪審員選任的學歷資格要求,明確規定在法院所轄區域內,凡是具備選民資格且未被剝奪政治權利,能夠正常表達的公民均可被選為人民陪審員。其次,為凸顯人民陪審員作為“草根”階層代表的廣泛性,應當充分吸收社會不同民族、年齡、性別、行業的人員參加陪審工作。尤其要在廣大農村地區吸收農民參加與農民有關的陪審案件,在城市社區探索將陪審引入的途徑和方式,建立社區人民陪審員制度。最后,將隨機抽取陪審員的程序上升為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剛性要求,在相關法律中明確違反該程序的否定性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