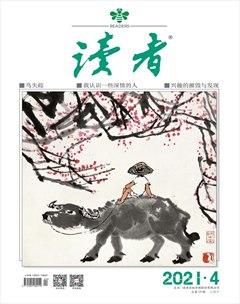那棵樹和那張臉
許慧晶 徐晴
《棒!少年》是一個關于回家的故事——一群處在困境中的少年如何通過棒球撫平自己的來處,找到自己的歸處。
2015年,中國國家棒球隊前隊長孫嶺峰創辦了“強棒天使”棒球基地,他從全國各地的貧困地區招募了十幾名7到10歲的困境少年,他們大多是留守兒童和孤兒。孫嶺峰想用10年的時間培養他們,讓他們參加國家、國際比賽,成為職業選手,或者作為體育特長生走進大學,最差的結果也可以留在強棒天使隊做教練,擁有一份工作,改變自己既定的命運。
2017年10月,紀錄片導演許慧晶走進基地,開始記錄這個故事。2020年7月,《棒!少年》獲得第14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獎,豆瓣網評分一度高達9.3。
一位觀眾看過影片后在影評網站上寫道:我會牢牢記住最后一個鏡頭里的那棵樹和那張臉。
關于那棵樹和那張臉,以下是《棒!少年》導演許慧晶的講述。

新的東西
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基地還在北京昌平的郊區。基地不大,前面是生活區,中間是飯堂,往后走穿過一扇小門,就到后院,有一個長條形的場地,不是一個標準的棒球場地,但地上鋪著毯子,就當棒球場用了。
孩子們正在訓練,每個人都穿著一身棒球服,很精神。當時你很難將眼前的這些孩子和貧困聯系起來,但他們大多數都是事實孤兒,要么是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要么父親或者母親已經過世。
作為一個公益項目,愛心棒球基地招收球員的標準很簡單——家庭貧困,年齡在7歲至12歲之間,身體健康,能夠達到平均身高,沙包能扔得遠。但實際上,因為這些孩子都來自貧困家庭,營養狀況并不好,所以很多孩子的體質都達不到同齡孩子的水平。
中場休息時,很多小朋友都在圍著教練玩耍,我注意到一個小朋友靜靜地坐在休息區的破沙發里,玩著一個黃色的小恐龍玩偶。他的眼神非常憂郁,有一種莫名的傷感,感覺心里藏著很多事,那個眼神非常打動我,讓我覺得很揪心——這個孩子就是小雙。
在小雙出生之前,爸爸突發腦出血去世,媽媽生下他和雙胞胎哥哥之后就走了。家里人原本想把小雙送人,但因為他生下來太小了,腦袋只有大人的拳頭那么大,在保溫箱里待了好幾個月,就把他哥哥送走了。小雙先是被他大伯養著,大伯去世后被送到了姑姑家,幾年后,姑姑也去世了,他又被送到二伯家。2015年,孫嶺峰去接他的時候,他抱著電線桿哭鬧著不愿意走,還踹孫嶺峰,當時,他以為是二伯不要他了。
到基地后,小雙很長時間都不吃不喝,也不跟人交流,可以說這個孩子在10歲以前,就經歷了很多人要用七八十年才能經歷的事情。
家
孩子們每天早上大概7點起床,8點去上文化課。基地離學校很近,走路就幾分鐘。中午回來,下午訓練,訓練完晚上寫作業。
平時,負責孩子們訓練的是張錦新,他是孫嶺峰的教練,孩子們都叫他師爺。師爺以前是北京市豐臺棒壘球運動學校的校長,教了40多年棒球,曾經4次帶領中國少年棒球隊獲得世界冠軍,50%的國家棒球隊隊員都跟著他學過棒球。
在基地里做飯的是李師傅,孩子們每頓飯至少有3個菜,每天都有肉。基地還有一位李阿姨,主要負責洗衣服,天天洗,因為小朋友訓練的衣服很容易臟,得一天一換。
郭忠健老師是基地的志愿者,他是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主管孩子們的生活和學習,每天吃完晚飯把孩子們集中起來一起寫作業,然后給孩子們補課,抽查作業。他有自己的公司,是做環保設備的。
我問過他,你來這兒家人有什么想法?他說,他爸爸有點不太理解,覺得搞公益是政府或者相關部門的事。但郭老師做這些更多的是緣于一種情結,他原來是清華大學棒壘球隊的隊長,從小就學,他想要把有限的生命消耗到愿意消耗的地方。
我們拍攝的時間很長,每個月都會去一次,一次待15天。
除了小雙,很多小朋友都令我印象深刻。比如李海鑫,他年齡最小,情商最高,跟師爺關系最好。
李海鑫的身世也很讓人心疼,他爸爸20歲的時候在一個私人金礦發生意外,掉進了30米深的礦井,全身很多部位粉碎性骨折。出院之后不能干太重的體力活,但他還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想支撐一家人的生活。
過年的時候,孩子們一般都會留在基地。有的小孩能被接回去,但有些小孩回不去,孫教練和師爺不想讓大家心理上有落差,就大家一起過完年再回老家——其實,來了北京之后,孩子們都把棒球基地當成了家。
闖入者
最開始我們是按照群像的方式拍攝的,大范圍地拍攝人物。但是跟拍了很多孩子之后,我們發現,缺少一個類似于闖入者的可以串起所有人的角色。
等到我們在基地見到馬虎時,就覺得這樣一個主要人物終于出現了。
剛到基地一兩天,馬虎就把基地搞得雞飛狗跳。所有人都圍著他轉,不拍攝他他也過來找我們,拽著你問這問那,展示自己的各種技能,倒立、翻跟頭,拿著我們拍攝用的挑桿蹭鼻涕,一會兒和小朋友打起來了,一會兒又把人家弄哭了。
馬虎來自寧夏的西海固,他告訴我們,在寧夏老家的時候,他的外號叫“游俠”。他3個月大的時候,媽媽跟爸爸打架之后就離家出走了,爸爸常年在外靠賣烤羊肉串為生,很少回家,他跟著奶奶長大。
他跟我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年,他爸爸突然帶回來一個女人和小男孩,第二天,這3個人騎著摩托車出去玩了,留馬虎自己在家里餓了一天。爸爸回來后跟馬虎說,下次也帶你去。但馬虎說他不去。后來,爸爸又外出打工,那個女人有一天帶著小男孩走了。當時,奶奶在新疆的姑姑家,馬虎一個人在家里餓了3天,直到奶奶回來之后才吃上飯。
所以,馬虎很能吃。剛到基地的時候,他一頓能吃3碗米飯,甚至會把自己吃吐。我們經常看到他挺著一個圓圓的肚子在訓練場上跑。
他喜歡當老大,享受那種被別人尊敬也保護別人的感覺。在基地,只有球打得好的人才能當老大。他不好好訓練,其他隊員都不服他。他當不了老大就很失落,還跟我說,這里的社會太大了。
其實,馬虎是一個很善良、內心很柔軟的小孩,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達。有一次,他跟小雙鬧矛盾,對小雙說,“你爸爸掛在那兒了”,被小雙打了。他跑去跟郭老師告狀,被郭老師教訓了一頓。郭老師跟他說了小雙家里的事,他的神色就變了,覺得自己做錯了。
有一次,別的小朋友去上海參加活動了,他留在基地。他就在那兒跟兩個小朋友玩鬧,追著追著突然返回來,自己對著攝像機表演,還說了一句話:“我叫馬虎,來自十字路口,走丟了,被愛心棒球基金會的人撿到了。”
在西海固,我們見到了馬虎的爸爸。他十七八歲就有了馬虎,年輕時愛流浪,很少回家。作為留守兒童的父輩,這些爸爸也都有自己的困境。他們不得不出去打工,解決一家人的生計問題,又要考慮小孩的教育和陪伴問題。
馬虎內心其實會怨自己的爸爸,他會說,我不恨我媽,我恨我爸,這些都是他造成的。但當他爸爸打開短視頻軟件放音樂的時候,他又很開心地跑過去跳《摩托搖》。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攻擊性很強,另一方面又很脆弱和柔軟。
有一天下午,我們讓他留下來。那天太陽很好,能夠照到臉上,在場邊坐著聊完之后,他又開始各種表演,跳舞,翻跟頭。天黑了,他邊玩邊往回走,從場地回宿舍,邊走邊唱歌,那天,他唱的是:“媽媽呀,媽媽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著雨……”
來處與歸處
在整個拍攝的過程中,我哭過兩次,這在過去的拍攝中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其中一次哭是拍攝小雙,聽他講身世的時候。
“我剛出生的時候,媽媽跑了。我有一個雙胞胎哥哥,家里養不起我們倆,就想把我送走,但是我生下來太小了,別人都不要我,后來就換走了我哥哥,留下了我。本來家里人說要把我埋了,我大伯不讓。我差點兒被埋了。”
還有一次是小朋友們去美國參加比賽。
去美國比賽之前,基地面臨拆遷,小朋友們都很難受,馬虎一直在抹眼淚。師爺就安慰他們說,去美國之后好好比賽,拿一個名次回來比什么都重要。雖然是安慰,但實際上孩子們的壓力都很大。
在美國正式比賽的時候,隊長大寶、馬虎,還有好幾個隊員都超齡了,胳膊受傷的小雙成了主力。孩子們前3局的表現都非常好,一直1比0領先。到第4局的時候,小雙的投球失誤讓對方連續回本壘得分,孩子們盡了全力,但還是輸了。
比賽結束之后,小雙在場邊大哭。馬虎捧著一盒漢堡和薯條安慰他。他一邊哭一邊喊著說,沒有機會了,機會只有一次!
當時,我也在攝像機后面哭。
從美國回來之后,拍攝基本就結束了,我開始做剪輯。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消息,小雙離開基地回家了,因為他二伯得了胃癌。小雙不想讓別人說他是白眼狼,也不想失去二伯,他想回去照顧二伯。
之前在拍攝的時候,我見過小雙的二伯。他有一個養女,是在火車站的垃圾堆里撿到的一個女嬰。二伯需要打工為女兒賺學費。
孫嶺峰教練很想把小雙接回來,但他突發心梗住院做了手術。等他出院休養了一段時間后,我就又跟著他去了一次小雙家。
那一次,小雙的態度非常堅決,不肯回基地,還對他二伯發了很大的脾氣。老實講,當時的我并不是特別能夠理解小雙為什么要不顧一切地放棄棒球回家。但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想通了這件事。
在開始拍《棒!少年》的時候,我兒子3歲,現在,他已經快6歲了。因為我經常出差,所以很少陪他,我覺得他不太需要我,只需要媽媽。2020年疫情期間,他一直待在家里,我和我愛人只好輪流照顧他。照顧了一段時間之后,我們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他變得需要我了,我也有了做父親的感覺。
我更加理解了一件事,小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親人的陪伴。馬虎和小雙,他們的問題,根源都是親情的缺失造成的極度的不安全感。小雙之所以堅定地留在老家,是因為他從小經歷了太多的變故,看著親人一個個離去,親情是他內心最需要的。
感覺自己理解了小雙之后,我也調整了片子的結尾。原本,我是用馬虎唱張震岳的《再見》作為結尾的,但后來,我把小雙在村里那棵大樹下跟二伯招手,說“你不要丟下我”的畫面放在了全片的結尾。
在片子里面,那棵樹出現了3次。那是一棵高大的松柏,它長得很慢,已經有幾百年樹齡了。其實,很多北方農村都有這樣一棵樹,一棵神奇的樹,這棵樹讓你跟家鄉有一種牽連。我覺得它是家庭、家鄉在人的心里生成的坐標系一樣的東西,標注著你的來處。
這和棒球很像。棒球的本壘也叫“家壘”,小孩子訓練的時候,會一直喊回家壘,因為根據規則,跑一圈,回家壘一次,就得一分,因此,最終都需要回本壘,都需要回家。
其實拍紀錄片更多的是解決我自身的問題。我怎么去理解自己的過往,去理解我的祖輩,去理解我走出去的那個地方。但最終需要解決的都是一個心靈歸處的問題——我們的家到底在哪里。
小雙的家鄉跟那棵樹是聯系在一起的。不管他出生的哪個地方,或者他的親人能夠給他帶來什么,那都是他可以自由呼吸、大聲吶喊的地方,那都是屬于他的世界。
成長
《棒!少年》的后期,我們做了差不多一年半。那段時間,我每天從上午10點開始,一直工作到晚上12點。影片剪了至少40個版本,其中有兩個鏡頭是始終保留的,一個是馬虎唱《摩托搖》的片段,另一個是小雙插松枝的片段。
那次是我們跟著小雙回老家,在一個山頭,他圍著一棵大樹一圈圈地轉,過了一會兒不知從哪兒找出一簇松枝,試圖插進大樹的孔里。插的過程中掉了好幾次,但我們一直在拍,拍到他把那簇松枝放進去為止。
最初拍攝時,我曾經希望能把孩子們拍成一個傳奇,就是他們很厲害、很牛,最后拿到了世界第一或第二,這讓我們一度很著急。我們天天盼著馬虎能學會控制自己,但他總是說得比做得好。我們也希望小雙能堅強勇敢一些,但他還是動不動就鬧情緒哭鼻子。我們也想讓李海鑫不要那么貪玩,但他每天都在玩。
其實在成長這件事上,心急是不行的。我們長大了,就變得不單純了。成年人認為所有的事情都得有結果,付出就是為了收獲,訓練了就得贏,我們給了孩子太多的期待。
師爺有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他說,教育小孩不能急,而是要將一件事一盯到底,一直盯著,一些改變就會慢慢發生。事實也的確如此,在美國輸球小雙大哭那次,我就能感覺到他們一下子長大了。

這些年,基地幾經輾轉,最后搬到了通州,新的場地很大,訓練不成問題。孩子們的人數從15人增加到了60人,其中還有25個從大涼山接來的女孩子。
馬虎變高變瘦,也更能吃了,一頓能吃100多個水餃。他身上那種野性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他知道在不同的時間段、不同的場合應該做什么,能把自己控制住,跟別人溝通時用語也從“你”改成“您”了。在西寧FIRST影展跟觀眾互動的時候,他看著影片里的自己說,我現在已經變了。但后來他又很羨慕小時候的自己。
小雙前不久也歸隊了。
我非常希望能把他們拍攝到18歲,繼續記錄他們的成長。在“一席”演講時,我引用了導演赫爾佐格的一句話:你帶來一個雞蛋的故事,那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事實,但你帶來一個小雞破殼而出的故事,這就是關于生命的故事。
我想呈現希望,因為,大家都太需要希望了。我也真心地希望棒球可以帶給他們快樂,彌補他們內心的缺失,讓他們獲得生存的能力和尊嚴,希望有更多的人幫助和關照他們成長。
(云 婷摘自微信公眾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