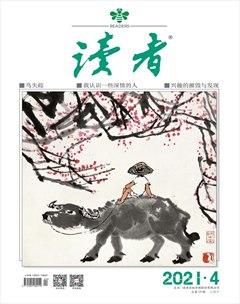我們離婚了
李察

一段婚姻在走向消亡時,能有多殘酷、多令人窒息,無數(shù)優(yōu)秀的文學、影視作品都有過刻畫描寫。電影《革命之路》里,凱特·溫斯萊特飾演的妻子對丈夫凄厲尖叫,明白地宣示“我恨你”。《婚姻故事》里,亞當·德萊弗飾演的丈夫向妻子怒吼,咬牙切齒地詛咒“我希望你死”。曾經(jīng)相愛的兩個人歇斯底里地爭吵、痛哭,互相指責,用最惡毒的語言撕開對方心底最軟弱的傷口。更別說還有爭搶孩子撫養(yǎng)權(quán)、爭執(zhí)彼此父母對錯、爭奪家產(chǎn)的各種不堪。是的,許多人都聽過身邊離異朋友的傾訴,多少有所了解:當一段婚姻走向深淵,其摧枯拉朽的破壞力宛若戰(zhàn)爭。
但我們從未見過,戰(zhàn)爭結(jié)束后,走下戰(zhàn)場的兩個人能坐下來一起平靜地回顧戰(zhàn)爭。打開韓國綜藝節(jié)目《我們離婚了》的那一刻,我一度誤以為能看到這樣的奇觀。畢竟是如此稀奇的設定:已離婚的前任夫妻單獨相處三天兩夜,一室二人三餐,在72小時里回顧過去、打開心結(jié)。而第一期參加的夫妻又是如此獨特:一對已離婚13年的老人,均年過六旬,到了耳順之年,能以更平和寬容的心態(tài)相對;另一對年輕人則剛離婚不過7個月,卻能和睦相處、合力育兒,做到“分手仍是朋友”。這樣的組合應該能碰撞出一些對破裂婚姻的全新體察。
然而奇特的設定和選人似乎并沒有帶來太多不同。離婚13年組,前妻鮮于恩淑的質(zhì)疑如連珠炮般不肯停歇:“為什么新婚旅行時全程丟下我,和朋友狂歡?”“當年被我撞見牽別的女人的手是怎么回事?”“為何非要和對我不友善的人來往?”以及“我曾經(jīng)多么痛苦委屈,你知道嗎?”這些本該在婚姻中說清楚的問題,離婚13年后她還在苦苦等待一個答案。而前夫李英河依然顧左右而言他:“喝杯咖啡吧!”“今天有點冷!”“我給你念首詩!”對于所有質(zhì)疑,他都矢口否認:“不是這樣的。”“沒這回事。”“我不記得了。”他還連連擺手,叫前妻不要再問。結(jié)果,這三天兩夜相處下來,不過是26年婚姻生活的重演:男方還是沒能體會到女方的心情,照舊呼朋喚友、喝酒彈琴;女方依然沒能表達真實感受,仍困在賢妻的角色里,壓抑內(nèi)心的不滿,做飯清掃,強撐笑臉待客。
反倒是離婚7個月組更平和地談到了婚姻中的問題和感受,但也不過是浮皮潦草的反思。前夫崔烤肉認可前妻在婚姻中的辛苦和委屈,但主要目的還是為求復合,提到核心的家庭矛盾,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句“父親年紀大了,他的意思我不能違抗”。也就難怪他的前妻劉紫蘇不愿過多吐露心跡,談及過去種種只是皺眉不語。當仍在挑剔前兒媳的男方父親突然出現(xiàn)時,女方依舊躲起來不敢露面,男方也依然沒有承擔責任、協(xié)調(diào)關系的自覺。
即便如此,《我們離婚了》還是讓經(jīng)歷過婚姻和正在婚姻中的人們邊看邊嘆息。崔烤肉字斟句酌、反復試探前妻是否能改變心意,劉紫蘇決絕之下一次次別開頭去、強忍淚水。鮮于恩淑對前夫感慨:“你不覺得過去的時間好可惜嗎?”一直左躲右閃的李英河也感嘆:“26年的婚姻生活,我又怎會沒有遺憾?就這樣后悔著、反省著,年歲漸長,歲月流逝……”視頻上方,一條條彈幕時不時飄過:看哭了。
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理查德·拉索在小說《格里芬教授的煩惱》中有一個關于婚姻生活的絕妙比喻。工匠們蓋房時,每隔一會兒就要確認:“垂直嗎?”回答經(jīng)常是:“一分鐘之前是的,現(xiàn)在還算垂直。”不過,“只要不是在蓋摩天大樓,偏離地基半個氣泡也沒什么大不了”。然而婚姻偏偏就是一棟30層的高樓,往往蓋到十幾層時才發(fā)現(xiàn)底層偏離了基準線,如果手邊的工具又沒法夠到,就只能忘了它,另起爐灶。于是,那棟蓋了一半的破屋也就永遠留在了那里。《我們離婚了》之所以引發(fā)關注,就是因為它把曾經(jīng)的兩名工匠重新帶回到那棟破屋前。追究當初是誰搭偏地基已無意義,如果雙方都沒有拿到新的工具,重新添磚加瓦蓋下去也不過是屋毀樓塌。最理想的結(jié)局,是站在樓前憑吊一番,然后互相拍拍肩膀,一起動手拆了這棟爛尾樓,讓內(nèi)心的這塊領地重歸平整。
只是談何容易。華盛頓醫(yī)科大學的壓力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在人一生承受的壓力中,排在前10位的:第一是配偶的死亡,第二是離婚,第七是結(jié)婚,第九是與配偶和解。10件事竟有4件與婚姻相關,難怪有人感嘆“不婚保平安”。但也由此可見,婚姻在我們的人生中占據(jù)了何等重要的地位。我們由之組建家庭、誕育子女,為之全心投入、全力以赴。要一磚一瓦地把曾經(jīng)滿懷憧憬和期待、辛苦搭建起來的建筑拆除,再共同把曾經(jīng)合力深挖的地基填平——《我們離婚了》試圖引領離婚夫妻做出這樣的嘗試,卻似乎遠未成功。
但即便只是看著離婚夫妻扒開荒草,短暫地回到舊屋前并肩憑吊,已經(jīng)意義非凡。人們被這檔節(jié)目打動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每對夫妻在搭建婚姻大廈的途中,都曾付出心意和努力,一次次地確認垂直,卻難免敵不過時間和生活的消磨。回頭看時,發(fā)現(xiàn)不知在哪個瞬間變成了“還算垂直”。如果還來得及,多確認審視幾次,確保大廈垂直下去;就算來不及,只能放棄,也不能任由破屋荒蕪坍塌,留下一片狼藉。
畢竟,我們過去人生中最好的以及最糟的事情都發(fā)生在那里。
(停 云摘自《中國青年報》2020年12月14日,小黑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