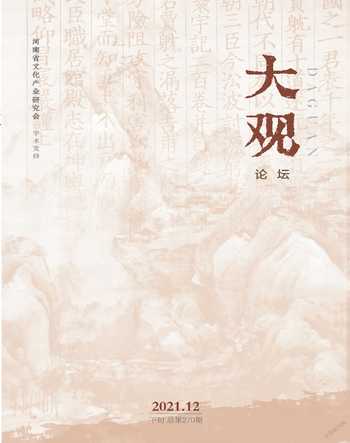書寫內容對書法創作的影響
陳宜佳
摘 要:創作一幅書法作品,無論其表現方式是簡潔還是豐富,所需要展示出的內涵都是尤為重要的。書法作品離不開漢字本身的含義,究其內容并擴展至整個作品的呈現則理解得更為完整,這樣勢必會對書法創作產生影響。因此,從書法創作的文字內容來探討其對書法作品整體性的影響十分有研究價值。
關鍵詞:書法創作;書寫詩文;《黃州寒食詩》;《自敘帖》
一、書法與書法創作內容的定義
(一)書法
什么是書法?若僅從字義上看,書法就是一種書寫的方式,只是其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要求。有人說書法是一門單純的藝術。2008年薛宣林更是提議將“書法”改名為“書藝”,認為其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的一種藝術形式。陳振濂在《書法美學》一書中說:“真正的‘書法’,是包含著作者抒情、泄意、在形式中融入有個性的審美意念的一種絕對強調主體精神的藝術。”這些理論解釋,幫助當代人更好地理解了書法。書法是以漢字為載體,融入書寫者的技巧、學養與審美情趣,通過視覺形式來展現的藝術形式。
對現在的我們而言,日常書寫工具已經顛覆,書寫方式已經改變。在文字形成之初,書法在人們眼里就是文字的載體。所以說書法是慢慢地才轉換為藝術,是一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
(二)創作內容
從宏觀上來說,書法是藝術性的,但從創作的內容來看,實用性實則占據半壁江山。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是用來記錄占卜結果的卜辭。民間瓦當、陶器上的文字是為了表明所屬人的信息。另外,摩崖石刻、歌頌帝王的石碑以及人去世之后的墓志,為了祈禱平安匠人們在佛像背后刻下的造像記,文人喜時、怒時、哀時、樂時所寫下的詩詞歌賦,友人之間來往的書信,等等,都可以作為書法創作的內容。
中國古代書法家大多都是文人出身,寫詩賦文乃文人立身之本。古代三大行書都是書文并茂,所以古代經典書作大都出自文人之手。當代書壇也不乏能獨自作文賦詩的書家,啟功就著有《啟功論書絕句百首》。但現代詩因為種種原因并不被現代書家所喜愛,更多的是用古詩、古詞、古曲、古籍來作為創作內容。
二、書法與創作內容的關系
書文相生,只要書法它寫的是字,我們就無法避免去義的問題。對于書文相生,唐代著名書論家張懷瓘指出“文章發揮,書道尚矣……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書議》),“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書斷》),“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為用,相須而成”(《文字論》)。
這說明書法的誕生離不開文字,因此也離不開有序字群所表達的內容。張懷瓘認為與文是相交而用的:一方面,文需要書來發揮,有了優美的書寫,文就能大為增色,廣為流傳;另一方面,書又需要文表達某種思想以增添作品的審美意趣。因此,從中國書法美學的角度來看,書和文的結合“在一切可能的結合之中,無疑是最完善的”。
(一)實用性
中國書法的實用性是其他任何藝術門類都難以比肩的,從甲骨文到金文到秦篆到漢隸,實用性都是第一位的。在書法還沒有上升到藝術抒情的高度時,官方文書、墓志、好友的書信等就是書法存在的環境。原始時期書寫的文字還遠遠達不到抒情寫意的欣賞標準,但是我們從文字的整齊、均勻、貫行、橫平豎直中發現這一切都是在為文字的可變性作鋪墊。當這一切趨于成熟時,人們不再滿足于當下,書法的審美開始慢慢轉變,特別是漢隸的出現,可以說已經突破了實用性。如今書法的實用性已經減退,它變為純藝術欣賞的對象之后,對字義的苛求并沒有消失。人們在長期的審美積累中,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慣性,無法去欣賞一幅文意不通、白字連篇的作品。
(二)思想性
書法作為一種外現形式,它的背后隱藏著創作者的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會有藝術。裝飾或一般意義上美的追求,談不上藝術思想的不同范圍的表現。文人介入書法后,書法的格調上升,使書法思想染上明顯的修養色彩。文人介入書法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書法實用的傳統觀念,把書法從用作記錄的工具變成抒發自我感情的媒介,這對于書法而言是一個劇烈的轉變。文人筆下,書法開始變得風花雪月,從嚴謹的碑銘抄錄中解脫出來,帶上了一定的浪漫氣息。這樣的轉變讓我們更加注意文字的內容。
(三)識讀性
書法當然不是以字意為主體,人們欣賞書法作品時,也不會只看書寫了什么內容,如果真是這樣,書法就會變成一張文書或者一份抄件,這是書法的藝術表現所不允許的。書法作為一種視覺藝術,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藝術形式的美,而不是文義上的美。后者是文學家們所要做的事。在現代社會,書家跟文人已經變成了兩類人。當我們不認識或不明白意思的甲骨文、狂草作品或殘碑殘簡出現在我們面前時,并不影響我們欣賞它們,它們作為藝術品,所具有的書法特征是不可否認的。
我們無法否認一個事實:書法中的字具有可識性,在我們欣賞文人書卷尺牘等完整的書法作品的時候,字義和形式都將被列入思考的范圍,摒棄其中任何一項都是不可能的。
三、作品分析
(一)懷素《自敘貼》
懷素是唐代的書法家,雖為佛門弟子,卻不守清規,酒肉不禁。佛門戒律與懷素狂放個性的沖突,使書家必然尋求一種宣泄。《自敘帖》按內容分的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記錄自己的生平。第二部分是節錄顏真卿《懷素上人草書歌序》,借顏魯公之口,展示“草圣”氣象。第三部分將張謂、戴叔倫等人的贈詩,按“述形似”“敘機格”“語疾迅”“目愚劣”進行分錄,列舉諸家的評贊。全文字體大小交錯,虛實互見。狂草強調制造矛盾又能解決矛盾,對比極為夸張。隨著感情的起伏,有些字寫得很大而有些字卻很小。帖的前半段較舒緩飄逸,從容不迫,寫到別人對他的贊詞時就狂態畢現了。如后面的“顛”“來”“戴”“翻”“目”“愚”“劣”“辭”“奧”“固”“非”“虛”“蕩”等字,寫得很大。一開始是豎有行橫無列,寫到后來非常激動,就既無行又無列了。從這些字就可以看出,懷素對于別人對他的評價是非常滿意的。這些字都寫得非常精彩,寫到滿意處,他就開始放縱自己的筆頭。
(二)蘇軾《黃州寒食詩帖》
蘇軾作為宋代的大文豪,其作為詩人的名氣遠大于書家。《黃州寒食詩》是在蘇軾由于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寫下的。當時蘇軾過得并不好,惆悵、孤獨等情緒一擁而上,才讓這個文字文本和書法相結合的作品誕生。這篇詩作是蘇軾“書出無意于佳乃佳爾”“書必有神、氣、骨、血、肉,五者缺一,不為成書也”書學思想的完美體現。
《黃州寒食詩帖》有詩兩首。第一首,詩人感慨因病而錯失花期,雖已是生機盎然,但“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至詩結尾詩意都較平常,感情是有節制的,書法也未見太大的跌宕起伏。第二首開篇便發身世之感,筆勢隨之搖曳奔放起來,字形變大。看到烏鴉銜紙才記起是寒食節,為自己受到了無謂的猜忌而傷心、難過、悲憤,深感報國無望,有一種生死不由人的無奈。“哭途窮”三字,給出了重點,情緒起起落落,字或大或小,用筆或重或輕,正是因為這種情緒的宣泄,字里行間仿佛注入了詩人的無限哀傷。然而線條的凝重、寬博,依然傳達出詩人不折不撓的頑強生命力量。正是由于這種強烈的“隨心感”,我們才能看到這樣的曠世之作。從《黃州寒食詩帖》中可以看出,從文的“義”去剖析這件作品的必要性。
四、結語
書文相生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書文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直相互依存,并不能摒棄其中之一把它們獨立出來。現代的某些新興的創作形式只側重書法帶給我們的視覺沖擊力。但是一幅成熟的書法作品,應該集結了書寫者自身對于作品形式和內容的諸多考慮和思量,而不單是為了追求一種“筆走龍蛇”之視覺體驗或者只是為抄錄記述而做單方面的功課。
參考文獻:
[1]陳振濂.書法美學[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
[2]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3]上海書畫出版社.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4]由興波.詩法與書法[D].上海:復旦大學,2006.
[5]鄧寶劍.從蘇軾《黃州寒食詩》墨跡看詩文與書法之關系[J].文史知識,2014(10):87-93.
[6]姚山晨.飛鳥出林驚蛇入草:論懷素《自敘帖》的書法藝術[J].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3):87-89.
作者單位:
香港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