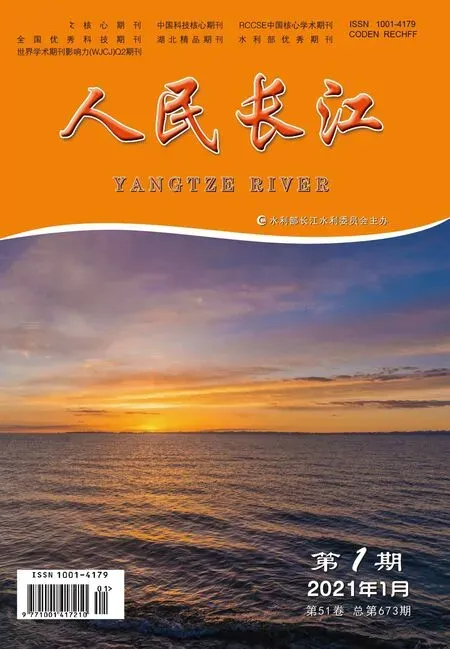長江口臺風影響能力研究
周 才 揚,殷 成 團,章 衛 勝,張 金 善
(1.長江水利委員會水文局 長江口水文水資源勘測局,上海 200136; 2.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29)
近年來,強臺風和超強臺風登陸我國的頻數明顯增多[1],其誘發的風暴潮在河口海岸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2017年臺風“天鴿”在珠海登陸,最大風速達45 m/s,中心氣壓950 hPa,造成最大增水2.79 m,直接經濟損失51.54億元[2];2018年“山竹”在廣東省臺山市登陸,最大風速達48 m/s,中心氣壓955 hPa,造成最大增水3.39 m,直接經濟損失24.57億元[3];2019年臺風“利奇馬”橫掃我國南北沿海地區,帶來大范圍降雨,直接經濟損失超過500億元。長江口作為我國第一大河口屢受臺風暴潮襲擾,造成嚴重經濟損失。近70 a共計160場臺風影響長江口地區,年均2.3場,而2018年臺風數多達6.0場。
以往對熱帶氣旋活動變化趨勢的研究多集中在臺風頻數及登陸頻數[4-6],臺風對區域的影響程度與臺風強度、距離、最大風速半徑、持續時間及登陸位置等密切相關,頻數只能反映熱帶氣旋對近岸影響能力的一部分,綜合評價仍需其他指標予以補充。Emanuel采用氣旋能量指數PDI(Power Dissipation Index)研究了西太平洋熱帶氣旋與海表溫度的相關關系[7],Bell等采用熱帶氣旋累計能量ACE(Accumulated Cyclone Energy)統計分析了1950~1999年熱帶風暴和颶風逐季變化特征[8],Yu等在2009年將熱帶氣旋累積能力進行了改進(the Revised Accumulated Cyclone Energy Index)[9],Lin等采用熱帶氣旋潛在影響指數PI(the Potential Intensity Index)建立了熱帶氣旋和海表溫度、拖曳力等變量之間的聯系[10],Haig等采用氣旋活動指數(Cyclone Activity Indices)對熱帶氣旋活動特征變化進行了評估[11]。上述指標從臺風內部主要構造特征參數對臺風影響能力進行了刻畫,其描述對象為大范圍區域如大洋乃至全球。 而臺風在小范圍地區影響能力評估指標尚不多見。影響長江口的熱帶氣旋活動特征尚不明晰,本文旨在從風暴潮防災減災的角度對影響該地區的臺風活動特征進行長周期統計研究。
1 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假定
目前,評價熱帶氣旋對小區域的影響能力尚無較好的指標。本文根據以往對風暴潮的模擬研究和7級風圈半徑大小,提出了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假定。即假定以長江口概化點(122°E,31.5°N)為中心,8倍最大風速半徑Rmax為半徑(約400 km)的圓形區域為長江口臺風影響圓。當臺風路徑與長江口臺風影響圓相交或相切時,則認為該臺風對長江口造成影響。影響長江口的臺風路徑概況及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如圖1所示,圖中灰色線為未對長江口造成影響的臺風路徑。

圖1 1949~2018年影響長江口的臺風路徑Fig.1 Tracks of typhoons affecting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from 1949 to 2018
2 長江口臺風影響能力分析
2.1 長江口臺風影響頻數分析
基于最近70 a來(1949~2018年)的熱帶氣旋最佳路徑資料,本節從統計學角度對影響我國各類熱帶氣旋尤其是近10 a的變化規律進行分析。1949~2018年影響長江口地區臺風共計160.0場,平均每年登陸2.3場,占西太平洋海區發生臺風數的8.92%。影響長江口臺風按路徑的不同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登陸北上型”臺風,共計92場,占總數的57.86%;第二類為“外海活動北上型”臺風,占總數的42.14%。“登陸北上型”臺風中登陸點離長江口較近的“長江口直接登陸型臺風”危害最大,按其風向變化過程又可分為長江口南側登陸(87%)和北側登陸(13%)兩類。還有少數奇怪路徑的臺風,因數量較少本文不做分析。
圖2為1949~2018年長江口及全國臺風生成時間分布圖。由圖2可以看出:不同于全國統計情況,影響長江口的臺風只發生在汛期,即每年的5~11月份;其中7~8月份最多,占臺風總數的64.8%,同時7~8月份也是我國中東部地區雨量比較集中的月份,暴雨和上游洪水加劇了長江口河口風暴增水過程。從生成日方面看(餅圖),臺風產生的時間為中旬(39%)>下旬(32%)>上旬(28%),月內差別較小。

圖2 1949~2018年影響中國臺風生成時間分布Fig.2 Formation time of typhoons affecting China from 1949 to 2018
2.2 長江口氣旋活動強度指數分析
為量化臺風給長江口造成影響,采用熱帶氣旋活躍指數(Cyclone Activity Index)、區域累計氣旋能量(Regional Accumulated Cyclone Energy)、年影響臺風最大風速Vmax和年影響臺風頻數C四個指標對長江口的氣旋影響強度進行綜合評估。
Cyclone Activity Index(CAI)是Haig[11]等基于NOAA和其他氣象專家對氣旋強度和尺度研究進行改進,提出的一個新的氣旋活動指數。CAI從風暴數量、強度、大小和壽命等方面描述了年均臺風破壞性大小。其公式為
(1)

當臺風距長江口尚遠如仍在西太平洋面活動時,除從大洋傳到近岸的先兆波外,臺風氣旋對近岸水體影響很小。為描述長江口地區臺風破壞能力影響能力,本節基于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假定定義一個新的指標——區域累積氣旋能量(Regional Accumulated Cyclone Energy,RACE)。該指標認為只有臺風眼進入長江口影響圓范圍內的臺風,才會在河口地區造成較為嚴重的災害,此類臺風路徑在影響圓內的部分便被計入RACE指標。同時,RACE在風速權重方面的考慮取了平方,更貼合能量的概念,其公式為
(2)
式中:i為每年進入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內臺風路徑點數;V為最大風速半徑處風速,m/s;di為第i個路徑點到長江口的距離,km。
臺風是一類中尺度天氣事件,其范圍遠遠大于河口等研究區域。CAI和RACE都是評估小研究區域的指標,但是其側重點不同。CAI空間計算范圍是西太平洋所有發生的熱帶氣旋,時間計算范圍是熱帶氣旋從生成到消亡的整個生命周期。其側重點在于氣旋對區域的影響能力。但有些臺風距離目標地區較遠,風速不大,卻依然被計如參數計算范圍。而指標RACE基于“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假設提出,更強調研究地區的臺風能量及災害。2個指標各有側重,計算結果可作相互補充。
年影響臺風最大風速Vmax為長江口影響圓內出現過的年海表最大風速,單位m/s,這個指標主要是對臺風強度進行刻畫,尤其是強臺風和超強臺風。年影響臺風頻數C為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內出現過的臺風個數,主要從年臺風頻數方面進行描述。
從氣旋活動指數(CAI)看,近70 a熱帶氣旋按其活躍度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1949~1985年,CAI指數在平均線上下波動劇烈,表明熱帶氣旋影響能力極不穩定,處于活躍期;第二部分1986~2018年,除2015年外,其余CAI指數在平均線以下小幅波動,表明該階段內熱帶氣旋對長江口地區的影響能力較為穩定。
區域累積氣旋能量(RACE)結果表明,長江口的臺風影響年際變化較大。1976~1991年的5 a移動平均值(虛線)均超過多年平均,表明這15 a中氣旋影響能力較強;1991~2018年氣旋影響能力較為穩定,僅部分年份大于均值。
年影響臺風最大風速Vmax歷史最值達到84 m/s(5 907超強臺風Sarah )。2010年之后最大風速都一般在50 m/s左右,稍高于平均,但未出現異常值。從本文指標來看,近年登陸我國的強臺風和超強臺風雖然有所增多[1],但是因為距離長江口較遠,影響有限。年影響臺風頻數C沒有比較明顯的長期規律,從短期角度看,自2009年之后一直高于歷年平均值,且保持上升趨勢,并在2018年達到歷史極值6場。
CAI,RACE和Vmax三個指標的5 a滑動平均線均表明:近30 a來臺風對長江口的影響程度并不算高(略低于均值),但自2009年之后長江口臺風影響能力一直保持增長趨勢,且近年臺風影響頻數較大(見圖3)。

圖3 1949~2018年長江口臺風影響能力年際變化Fig.3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typhoon impact capacity in the Yangtze Estuary from 1949 to 2018
3 結 論
利用1949~2018年最佳臺風路徑資料,在長江口臺風影響圓假定的前提下,提出了臺風對小區域影響能力的評估指標,并采用多個指標對長江口臺風影響能力進行了長周期的統計和研究,結果如下:
(1) 本文提出的指標區域累積氣旋能量(RACE),可以較好地評估臺風對小區域的影響能力。
(2) 1949~1985年熱帶氣旋影響能力極不穩定,處于活躍期;1986~2018年表明熱帶氣旋影響能力較低且強度穩定,影響長江口的強臺風和超強臺風有所減少。
(3) 1991~2018年的近30 a來臺風對長江口的影響程度并不算高(略低于均值),但自2009年之后臺風影響指數一直保持增長趨勢,且近年臺風影響頻數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