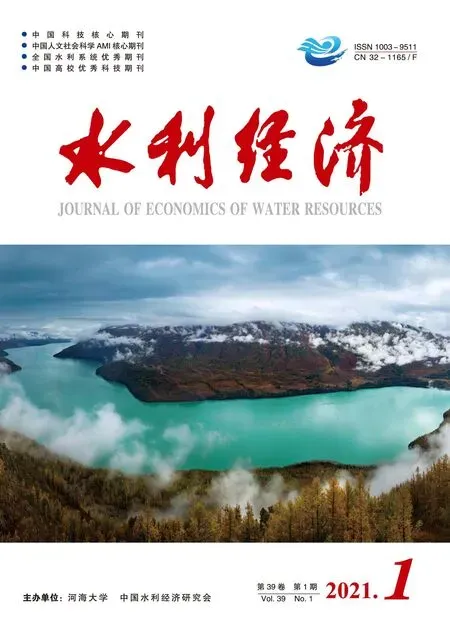江西省水資源生態足跡時空格局
谷文林,劉 楓,井沛然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隨著人口增長和社會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的地位日趨重要。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水資源作為人類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資源,其可持續利用狀況關系到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但是在當前階段,我國的水資源狀況并不樂觀,人均水資源量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僅62.8%的水資源和22.2%的湖泊水質可飲用,約 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資源短缺[1]。江西省地處中國東南部,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較多,省內河網密布,區域內有著名的鄱陽湖自然保護區。由于季風氣候的不穩定性,臺風、旱澇等災害頻發,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隨著江西省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資源開發利用效率以及水資源環境污染等問題亟須解決。
1992年Rees[2]首次提出生態足跡理論,為區域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評價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水資源生態足跡可以表述為:在特定人口和經濟狀況下,為了維持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水資源消費以及消納水污染所必須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3-5]。水資源生態足跡核算基于兩個假設條件:第一,能夠對人們所消費及浪費的大部分水資源進行跟蹤;第二,人們消費及浪費的水資源能夠被轉化為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6]。在國內研究中,徐中民等[7]首次將生態足跡法引入中國,并使用該方法對甘肅省生態足跡進行了測算;同年,張志強等[8]對生態足跡法的理論概念與計算模型進行了系統介紹,將生態足跡法完整地引入了國內;龍愛華等[9]將生態足跡法應用于水資源領域,對西北四省(區)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狀況進行了評價;黃林楠等[10]以生態足跡模型為基礎,提出產量因子和均衡因子模型,并用該模型對江蘇省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狀況進行了評價;張義等[11]建立了水污染生態足跡模型,并將該模型引入水資源生態足跡的計算中;陶倩君等[12]運用時空分析和相關分析等方法對廣東省2000—2014年的水資源生態足跡進行評價。參考近幾年國內研究文獻,研究對象以干旱省份和經濟區域為主[13-16],對南方水資源充沛的省份研究較少。由于各省對地級市的水資源數據披露情況不盡相同,水資源生態足跡空間研究也相對匱乏。
本文以江西省為研究對象,對其2010—2018年水資源生態足跡時空格局進行系統評價,以期為該地區水資源可持續利用以及水資源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鑒。
1 模型構建與指標計算
1.1 模型構建
1.1.1一級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
現階段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發展較為完善,根據陸硯池等[17]的研究,一級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可以描述為
Ew=Nfw=Rw(W/P)
(1)
其中
P=Q/S
式中:Ew為水資源生態足跡,hm2;N為區域內總人口數;fw為人均水資源生態足跡;Rw為水資源全球均衡因子;W為區域內消耗的水資源總量,m3;P為區域水資源生產能力,m3/hm2;Q為區域內水資源總量,m3;S為區域面積,hm2。
參照世界自然基金會核算的各類土地均衡因子,Rw取值為5.19。使用水文學中產水模數這一概念來衡量區域水資源生產能力P,產水模數為區域內水資源總量與區域面積的比值,表示區域內每公頃土地所分配的水資源量:
1.1.2二級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
《江西省水資源公報》將年用水總量指標細分為六類:農田灌溉用水量、林牧漁畜用水量、工業用水量、城鎮公共用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和生態環境用水量。按照用水特性可以將這六類劃歸為生活用水量、生產用水量和生態用水量三大類綜合用水指標,賬戶劃分情況見表1。根據一級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建立生活用水生態足跡模型、生產用水生態足跡模型和生態用水生態足跡模型3個二級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生活用水生態足跡模型為
Edw=Nfdw=Rw(Wd/P)=RwWd/(Q/S)
(2)
式中:Edw為生活用水生態足跡,hm2;fdw為人均生活用水生態足跡;Wd為區域內生活用水總量,m3。將Wd換成生產用水量和生態用水量,可以得到生產用水生態足跡模型Eiw和生態用水生態足跡模型Eew。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可以表示為

Ew=Edw+Eiw+Eew (3) 表1 水資源生態足跡賬戶劃分
1.1.3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模型
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是指在一定區域和時間內,水資源能夠滿足該區域社會發展和人口增長的最大供給量[18]。為實現可持續發展,區域的水資源開發利用率應不超過40%[19],因此在水資源生態承載力的計算中要扣除60%用于維持當地生態環境。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模型構建如下:
Cw=Ncw=(1-60%)ψRw(Q/P)
(4)
其中
ψ=P/Pw
式中:Cw為水資源生態承載力,hm2;cw為人均水資源生態承載力;ψ為區域水資源產量因子,該變量可以對不同地區同類生態生產能力進行比較;Pw為全球單位面積產水量,參考方偉成等[20]的研究,Pw取值為3 140 m3/hm2。
區域水資源生態承載力也可以用“區域地表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與地下水資源生態承載力之和”來表示:
Cw=Csw+Clw
(5)
式中:Csw為地表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其計算方法是將式(5)的區域水資源總量Q換成區域地表水資源總量;Clw為地下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計算方法同Csw。
1.2 指標計算
1.2.1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
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是用來衡量區域內水資源是否滿足該區域生產、生活以及生態用水的需求[21],其表達式為
Dw=(Cw-Ew)/N
(6)
式中:Dw為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當Dw>0時,表示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區域內水資源可以滿足各方面的用水需求;當Dw<0時,表示人均水資源生態赤字,區域內水資源不能滿足用水需求。
1.2.2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
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水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安全程度[22],用水資源生態足跡與水資源生態承載力的比值表示。根據王先慶等[23]的研究,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可分成不同區間: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大于1,水資源供給不足,水資源安全性較差;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等于1,水資源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水資源安全性有待提高;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在0.5~1的區間內,水資源供給較為充足,水資源安全性較高;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小于0.5,水資源供給充足,水資源安全性高。
1.2.3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
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反映的是水資源的利用效率[24],用區域水資源生態足跡與該區域相應年份GDP的比值表示。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與水資源利用效率之間具有負相關性,即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越低,水資源利用效率越高。
本文的水資源指標數據來自2010—2018年各年度《江西省水資源公報》,人口、土地面積和GDP數據來自2010—2018年各年度《江西省統計年鑒》。
2 計算結果與分析
2.1 區域水資源生產能力
在水資源生態足跡模型中,用產水模數來衡量區域水資源生產能力。由于江西省年降水量差異較大,各年度產水模數會有較大不同,最終計算出的歷年水資源生態足跡會出現大幅度變動。為了排除歷年降水量對水資源生態足跡的影響,參考趙春芳等[25]的研究,將樣本年度內各地級市的產水模數取平均值作為各自的水資源生產能力,見表2。

表2 江西省及各地級市水資源生產能力
2.2 江西省水資源生態足跡與水資源生態承載力
2010—2018江西省年水資源生態足跡賬戶相關指標的計算結果見表3。研究期內,水資源生態足跡呈現波動上升的變化趨勢,生產用水生態足跡所占比重最大,每年均超過87%,且歷年變化較小;生活用水生態足跡每年穩定上升,這與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等因素都有密切關系;生態用水生態足跡呈現逐年上升的變化軌跡,說明江西省在生態方面的用水量逐年增加,這與其所倡導的綠色發展模式相吻合。

表3 2010—2018年江西省水資源生態足跡賬戶
江西省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波動較大。由式(4)可知,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與水資源總量具有正相關性,影響水資源總量的最主要因素是降水量。江西省屬季風氣候,季風的不穩定性易造成各年度降水量出現較大差異,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會隨著降水量的差異而波動變化。受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波動的影響,各年度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也出現同向變動。此外,江西省人口數量每年穩定上升,但對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的變化沒有顯著影響。
2.3 江西省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足跡
江西省各地級市2010—2018年水資源生態足跡整體上較為平穩(圖1)。根據水資源生態足跡計算結果,可將11個市分成3組:第一組包括贛州和宜春兩市,水資源生態足跡常年保持在較高水平;第二組包括吉安、南昌、九江、上饒和撫州5市,水資源生態足跡保持在中等水平;第三組包括新余、萍鄉、景德鎮和鷹潭4市,水資源生態足跡處于較低水平。以2018年各地級市用水情況(表4)為例,對江西省水資源生態足跡空間分布狀況進行解釋。

圖1 江西省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足跡
a. 第一組。在用水總量方面,2018年宜春市和贛州市用水總量分別為42.81億m3和34.04億m3,位居全省第一、二位。在具體用水指標方面,宜春市工業用水量為14.59億m3,占全省工業用水總量的24.83%,所占比重最大。宜春市第二產業中以鋰電能源、紡織和建筑等水資源消耗極高的行業為主,該市的鋰電新能源、豐城再生鋁、奉新棉紡織等產業被列為省級重點產業集群,產生了極大的用水需求。贛州市居民生活用水量位居全省第一,達4.1億m3。在2018年江西省各市人口排名中,贛州市以常住人口850.75萬人高居全省第一,生活用水量需求巨大。較高的用水量是宜春市和贛州市水資源生態足跡高的主要原因。
b. 第二組、第三組。各市用水總量第二組均超過20億m3,第三組均低于10億m3。在具體用水指標方面,農田灌溉用水量和居民生活用水量是兩組用水總量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第三組中4個市的農田灌溉用水量合計為16.28億m3,僅與第二組中南昌市的農田灌溉用水量大致相當。在居民生活用水量方面,第三組最高的萍鄉市僅為0.97億m3,第二組中最低的撫州市已達到1.85億m3,其他各市均超過2億m3。較高的農田灌溉用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和用水總量是第二組水資源生態足跡高于第三組的主要原因。
對研究時段內其他各年度江西省各市用水量進行統計,其他各年度狀況與2018年大致相同,驗證了結論的準確性。

表4 2018年江西省各地級市用水量 億m3
2.4 江西省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
江西省11個地級市各年度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呈現較大的波動(圖2)。江西省氣候濕潤,降水偏多,受梅雨、強降雨以及“早春汛”的影響,2010年全省降水量達到3 482.89億m3,較多年均值高于23.7億m3;2012年全省降水量3 614.53億m3,較多年均值高于32.2億m3。這兩年均屬于豐水年份,各市的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均達到了較高水平。2011年和2018年江西省梅雨持續時間短,整體降水較少,部分地區出現夏秋連旱,2011年降水量為2 176.4億m3,低于多年均值20.4億m3;2018年降水量2 483.6億m3,低于多年均值9.2億m3。這兩年屬于枯水年份,各市的水資源生態承載力都處于較低水平。
從空間分布來看(圖2),11個地級市大致可分成3組:第一組為贛州市,各年份水資源生態承載力都高居全省第一位;第二組包括吉安、撫州、上饒、宜春和九江5個市,各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處于全省中等水平;第三組包括南昌、景德鎮、鷹潭、萍鄉和新余5個市,各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長期處于全省較低水平。對于江西省水資源生態承載力空間分布狀況,以2018年為例,結合表5從降水量、水庫蓄水量以及地表水總量3個角度進行解釋。

圖2 江西省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
a. 第一組。在降水量方面,贛州市地處江西省最南部,梅雨季節開始時間早于其他各市,結束時間相對較晚,全市受梅雨影響時間長。2018年降水量達546.89億m3,占全省降水總量的22.02%,高居全省第一。在水庫蓄水量方面,贛州市擁有大中型水庫共計49座,水庫數量全省第一,蓄水量為12.81億m3,位居全省第四。在地表水方面,2018年贛州市地表水資源總量達到222.92億m3,占全省地表水資源總量的19.73%,位居全省第一。降水多、地表水量豐沛,水庫蓄水充足,這是贛州市水資源生態足跡全省最高的主要原因。
b. 第二組與第三組。在降水量方面,由于江西省降水量呈現出從東南向西北遞減的變化軌跡,位于東南部的吉安、撫州和上饒3個市降水量均超過300億m3,宜春市和九江市降水量也在250億m3之上,對比而言,第三組5個市的降水量均未超過100億m3。在蓄水量方面,第二組的九江市水庫蓄水量達到47.81億m3,占全省水庫蓄水總量的38.91%,高居全省第一。吉安市和宜春市水庫蓄水量分別為21.37億m3和19.23億m3,位居全省第二、三位。

表5 2018年江西省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影響因素 億m3
上饒市和撫州市水庫蓄水量分別為8.89億m3和7.03億m3,處于全省中等水平。第三組中,新余市水庫蓄水量最高,為2.78億m3,其次是萍鄉市,蓄水量為1.09億m3,景德鎮、鷹潭和南昌3個市的水庫蓄水量均未超過1億m3,處于全省末端水平。在地表水方面,第二組上饒市地表水資源總量為204.88億m3,居全省第二,吉安、撫州和宜春各市的地表水資源總量均超過100億m3,九江市為98.77億m3,位居全省第六。第三組各市地表水資源總量明顯低于第二組,該組中地表水資源總量最豐富的是南昌市,僅為59.33億m3,與第二組末端的九江市有較大的差距,其余4個市的狀況則更加不容樂觀。

表6 江西省各地級市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

表7 2010—2018年江西省及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
綜上所述,第二組各市在降水量、水庫蓄水量和地表水資源總量3個方面全部高于第三組,這是第二組各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高于第三組各市的主要原因。
對研究時段內其他年度的降水量、水庫蓄水量和地表水資源總量進行了相同的對比分析,各年度結果與2018年基本一致,驗證了結論的準確性。
2.5 江西省各地級市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
通過式(6)計算各地級市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結果見表6,其值為正表示水資源盈余,為負則表示水資源短缺。對比圖2與表6,可以確定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赤字)與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變化軌跡基本相同。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排名第一的贛州市在2010年、2012年和2016年的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均超過1,水資源充足。2011年、2013年和2018年南昌市人均水資源生態盈余均出現生態赤字,其余年份盈余都較為接近0。南昌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排在第三組,整體水資源較為匱乏是南昌市出現人均水資源生態赤字的主要原因;此外,南昌市人口較多,人均分配量較低,這是南昌市出現人均水資源生態赤字的另一重要原因。
2.6 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
2010—2018年江西省各年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均低于0.5(表7),表明江西省水資源安全程度高,水資源供給能夠滿足各方面的用水需求。從空間上來看,2011年、2013年和2018年南昌市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均超過1,水資源安全狀況差,供給嚴重不足;其他年份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均在0.5~1之間,水資源安全狀況有所緩解,處于相對安全狀態。景德鎮、鷹潭、贛州、上饒和撫州5個市在2010—2018年各年的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均低于0.5,水資源安全程度高,供給充足。萍鄉、九江、新余、宜春和吉安5市較早年份部分值大于0.5,但在近4年中,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均小于0.5,且呈現出逐年減小的趨勢,水資源安全程度不斷改善。
2.7 江西省及各地級市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
2010—2018年江西省及各地級市的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均呈現逐年下降的變化趨勢(表8),水資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這與江西省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以及技術進步、工業轉型都有一定關系。從空間分布來看,吉安市和宜春市各年度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明顯高于其他地級市,用水效率顯著低于其他地級市;從2010—2018年9年的時間對比來看,吉安市用水效率提高了66.67%,漲幅位列全省第一,宜春市增長51.30%,漲幅位于全省中等水平,兩市用水效率顯著提高。南昌市的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處于全省末位,用水效率高于其他地級市;2010—2018年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值漲幅達53.85%,處于全省中上水平,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速度較快。分析其原因可知,一方面南昌市水資源生態足跡處于中等水平,但該市GDP產值巨大,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顯著低于其他各市;另一方面,南昌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水平低、人均水資源生態赤字以及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大,可利用水資源短缺是南昌市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值較低的原因之一。

表8 2010—2018年江西省及各地級市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 hm2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文基于江西省2010—2018年水資源相關數據,構建江西省及11個地級市的水資源生態足跡賬戶,并從水資源的盈余狀況、安全性和用水效率3個方面對江西省及各地級市的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水平進行了評價。
a. 2010—2018年江西省水資源生態足跡與全省用水量逐年增多正向關系顯著,整體呈現穩步上升的變化趨勢。生產用水生態足跡變化較為穩定,各年生產用水量均保持在總用水量的87%以上,生活用水生態足跡和生態用水生態足跡則逐年上升。在空間分布方面,各地級市生態足跡差異較大,根據生態足跡高低將11個地級市分成3組,第一組宜春市工業用水消耗巨大,贛州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居高不下,水資源生態足跡分別居于全省第一、二位。第三組的鷹潭、景德鎮、新余和萍鄉4個市在農田灌溉用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和用水總量方面與其他地級市差距較大,水資源生態足跡處于全省后四位水平。
b. 2010—2018年江西省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出現較大波動,這與江西省各年度降水量的不穩定有關。在空間分布方面,各地級市歷年水資源生態承載力與江西省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基本保持同步變動,依據各地級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的高低將11個市分成3組,贛州市降水豐沛、地表水充足、水庫蓄水量較高,水資源生態承載力全省最高,位居第一組;南昌、景德鎮、鷹潭、萍鄉和新余5個市同屬第三組,降水量相對較少,水庫蓄水量和地表水總量都處于全省末位,水資源生態承載力位居全省末端。
c. 從人均水資源盈余(赤字)來看,南昌市水資源較為匱乏,個別年份出現赤字,其他各市水資源均較為充足。從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來看,南昌市多個年份的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大于1,水資源供需存在不平衡;景德鎮、鷹潭、贛州、上饒和撫州5個地級市歷年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均小于0.5,水資源安全程度非常高;其余各市歷年值雖有波動,但近4年呈現出逐年減小的變化趨勢,水資源安全程度逐步提高。從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來看,南昌市歷年值較小,用水效率高;吉安市和宜春市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偏大,水資源利用效率較低,但研究時段內漲幅較大,用水效率提高較快。
3.2 對策建議
a. 宜春市工業用水量大、水資源生態足跡高,建議對現有的鋰電能源、紡織和建筑等高耗水行業進行技術創新或者有規劃地逐步淘汰,優先發展高新技術企業,解決工業用水過高的問題;對于生態足跡較低的新余、萍鄉、景德鎮和鷹潭4個市,可以鼓勵利用現有資源,合理發展農業生產,適當增加工業規模,增加GDP產值。此外,江西省各市應該繼續增大生態用水投入,并根據實際狀況調整產業結構,優先發展低耗水的第三產業[26]。
b. 南昌、景德鎮、鷹潭、萍鄉和新余5個市水資源生態承載力過低,建議通過興修水庫、大壩等水利工程措施提高地表水資源儲備。江西省過境水資源較為豐富,應充分利用過境水資源與本地水資源互補[27],保證水資源總量充足,提高水資源生態承載力。
c. 要解決南昌市人均水資源生態赤字和水資源生態壓力指數過大的問題,重點在于“節流”。南昌市要加大研發投入,發展節水灌溉帶等節水農業,同時通過改進技術等方式提高工業用水效率,實現污水處理回用資源化;日常生活中應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居民的節水意識。對于宜春市和吉安市萬元GDP水資源生態足跡偏大的問題,可以充分利用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加強技術交流與合作,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