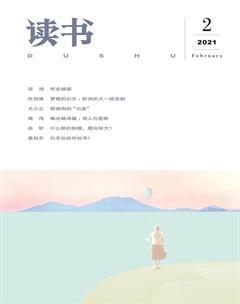收藏、作偽與鑒定
2021-02-06 10:18:37劉濤
讀書 2021年2期
劉濤
世有收藏而后有作偽,有偽作而后有鑒定。書跡的收藏、作偽與鑒定,皆早于繪畫。
收藏名人書跡, 起于仰慕, 因于學書,漢代已見。《漢書》 載:西漢晚期,嘉威侯陳遵(孟公)“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杰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陳遵“略涉傳記,贍于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游俠·陳遵傳》)。東漢,帝王也收藏書跡。《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云:“(劉)睦能屬文,作《春秋旨意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病寢,(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魏晉時,收藏名家書跡蔚為風氣,藏品以當代為主,也有前代名家書跡,卻少。
最初的作偽,為獲利,發生在收藏“二王”書跡正盛的南朝前期。劉宋虞龢《論書表》說:宗室新渝侯劉義宗雅愛二王遺跡,“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
虞龢是整理劉宋內府藏品的主持人,《論書表》是他整理工作的報告書。虞龢不僅記錄了當時偽造二王書跡的手段,還提到“字之美惡,書之真偽”,他整理藏品,已注意到鑒別偽跡。
南朝人鑒定書法的具體情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有所記錄。他鑒定的藏品主要是內府收藏的大量王羲之書跡,還涉及鐘繇之跡。陶弘景熟悉東晉士人尤其二王父子書法,憑經驗性的眼力判斷真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