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孕前BMI和孕期增重與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的相關性研究
魯旭文,陸 菲
(1.余姚市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浙江 余姚 315400;2.余姚市人民醫院兒科,浙江 余姚 315400)
兒童超重肥胖已逐漸成為全球熱議的公共性衛生問題,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兒童肥胖的發病年齡逐漸前移,不僅影響到兒童本身的身心健康,還會使得兒童到達成人期后患代謝性疾病的風險增加[1]。隨著對兒童肥胖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諸多研究發現,母親孕期營養過剩與子代的肥胖和代謝性問題有關,會對子代造成嚴重的影響[2-3]。目前研究較多的方向為母親孕前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和孕期增重對子代的影響,主要目標人群集中于新生兒,對于學齡前兒童的研究報道較少。學齡前兒童是生長發育過程中脂肪堆積的時期,故極易引發兒童肥胖,也是預防后期超重肥胖的關鍵時期[4]。本次研究通過對本市學齡前兒童進行相關調查分析,旨在于探討母親孕前BMI以及孕期增重對學齡前兒童的影響,為兒童肥胖問題的預防提供理論依據,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于余姚市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進行兒童保健咨詢的3~5歲兒童共300例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母親孕前BMI和孕期增重信息完整;②年齡<7歲。排除標準:①母親孕前BMI和孕期增重等信息不完整;②病理性肥胖,如甲狀腺功能減退、腦垂體病等;③繼發性肥胖,如服用激素藥物后肥胖者。兒童超重肥胖的診斷參照2007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推薦的生長發育標準進行,當不同性別的兒童生長發育BMI高于P85則為超重,高于P95則為肥胖[5]。本研究300例兒童中超重肥胖人數為35例(11.67%)。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所有研究對象家屬均對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自愿參與研究。
1.2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研究對象母親的個人信息調查通過問卷形式收集,由一名通過標準化培訓的調查員進行問卷調查,主要內容包括:一般情況、個人史以及母親孕期情況、生活習慣、家庭情況等;另外由母親代為回答兒童的一般情況。體格檢測:所有研究對象母親孕期均進行過體格檢測,標準為:脫鞋帽,著輕便衣服進行測量,體重讀數精確到0.1kg,身高讀數精確到0.1cm,均測量2次后取其平均值,而后進行BMI的計算,BMI=體重(kg)/身高(m2);同時測量生產前產婦的體重,計算孕期增重;兒童的體格測量方法同母親。
判斷標準:①母親BMI劃分參考Goldstein等[6]2017年發表的文獻進行,主要分為3個等級:BMI<18.5kg/m2為低體重、18.5~23.9kg/m2為正常體重、>23.9kg/m2為超重肥胖;②母親孕期增重劃分參照美國醫學研究所2009年推薦的增重標準進行,具體標準為:孕前低體重孕婦增重范圍為12.5~18.0kg、孕前正常體重孕婦增重范圍為11.5~16.0kg、孕前體重孕婦增重范圍為11.5~16.0kg、孕前肥胖孕婦增重范圍為5.0~9.0kg。根據以上標準將孕期增重情況劃分為不足、正常以及過度3個等級。
1.3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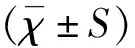
2結果
2.1一般情況分析
本研究300例兒童中,平均年齡為(4.31±0.78)歲,其中男童174例,女童126例;超重肥胖患兒35例,占比11.67%(35/300),其中男童超重肥胖24例,占比13.79%(24/174),女童超重肥胖11例,占比8.73%(11/126);母親孕前BMI平均為(20.58±2.81)kg/m2,母親孕前低體重69人,占比23.00%,正常體重199人,占比66.33%,超重肥胖32人,占比10.67%;母親孕期增重不足121人,占比40.33%,增重正常101人,占比33.67%,增重過度78人,占比26.00%。同孕前正常體重母親相比,孕前低體重母親孕期增重過度者比例較低,孕前超重肥胖母親孕期增重過度者比例較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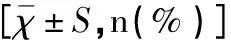
表1 一般情況比較結果
2.2母親孕前BMI以及孕期增重與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間的相關性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校正性別、年齡等混雜情況后,同母親孕前BMI正常組相比較,母親孕前低體重的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降低,母親孕前超重肥胖的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增加,其OR值及95%CI分別為0.602(0.413~0.755)、1.822(1.370~2.424),均P<0.05。同母親孕期增重正常組相比較,母親孕期增重過度的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增加,其OR值及95%CI為1.298(1.009~1.669),P<0.05,但是母親孕期增重不足并不會降低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P>0.05),見表2。

表2 孕前BMI及孕期增重與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關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2.3母親孕前BMI合并孕期增重與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的相關性
根據母親孕前BMI分層分析,結果顯示與母親孕期增重正常組相比較,母親孕期增重不足或過度均不增加兒童超重肥胖的風險,見表3。而后將兩者進行合并,同母親孕期BMI正常且母親孕期增重正常組相比較,母親孕前超重肥胖且孕期增重過度的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顯著增加,母親孕前低體重且孕期增重不足或孕期增重正常的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顯著降低,其OR值及95%CI分別為1.575(1.031~2.411)、0.556(0.343~0.872)、0.411(0.233~0.719),P<0.05,見表4。

表3 按孕前BMI分層后,母親孕期增重與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關系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表4 母親孕前BMI合并孕期増重與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關系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討論
3.1母親孕前超重肥胖及孕期增重過度均會不同程度增加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的風險
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已成為全國性的公共衛生問題,兒童生長發育期超重肥胖會增加成年后患其他疾病的風險。本次研究結果表明,母親孕前超重肥胖以及孕期增重過度均會不同程度增加子代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與既往研究結果基本保持一致[7-8]。但既往也有研究發現,母親孕期增重過度與子代早期超重有關,與子代晚期超重無相關性,母親孕期增重過度與兒童出生時機體脂肪含量有一定相關性,但到4歲后則無明顯相關性,6歲后出現弱相關性[9-10],分析其中原因在于孕期增重可能主要通過出生體重間接性影響到兒童的體重。
本次研究在分析孕前BMI以及孕期增重時,校正混雜因素后結果仍表明母親孕前BMI以及孕期增重會對學齡前兒童超重肥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分析原因在于胎兒在宮內發育時,宮內營養起著關鍵的作用,而宮內營養與兒童超重肥胖密切相關。當宮內出現營養過剩的情況時,極易造成胎兒生長發育過度,增加巨大兒及兒童超重肥胖的發生風險。同時宮內營養過剩還會進一步影響到胎兒下丘腦中食欲控制中樞的生長發育、脂肪細胞的代謝以及胰島素分泌,使得胎兒能量平衡系統遭到破壞,更易出現超重肥胖[11-12]。在兒童生長發育過程中,遺傳因素以及家庭環境同樣起著一定的作用。第一,兒童在遺傳了母親的肥胖基因后,更易在后天的發育過程中出現超重肥胖;第二,超重肥胖的母親在生活方式方面或多或少均存在高能量飲食和低體力勞動等不健康生活方式,導致兒童生長發育的生活環境出現偏差,進一步增加超重肥胖的風險[13-14]。本次研究結果還顯示,將母親孕前BMI正常且孕期增重正常作為對照組,發現母親孕前超重且孕期增重過度的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最高。但是將母親孕前BMI分成3個等級進行分層分析時發現,母親孕期增重不足或過度并不會增加兒童出現超重肥胖的風險,提示母親孕前超重肥胖較孕期增重對兒童超重肥胖的影響更嚴重。
3.2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研究雖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首先,本次研究的樣本量偏小,加之收集的產前產后信息均為回顧性信息,使得結果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倚;其次,本次研究中并未將兒童生長發育過程中的飲食以及體力活動等生活情況納入到研究中,無法避免其對結果產生的影響,但家庭的生活方式與兒童的超重肥胖是存在一定相關性的;最后,本次研究的對象均來源于本市城區,農村和城市的差異依然存在,無法將結果推廣到更多地區,需要進一步多中心、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
綜上所述,母親孕前BMI超重和孕期增重過度均是學齡前兒童發生超重肥胖的影響因素,并且母親孕前BMI的影響更加嚴重。隨著國家二胎政策的出臺,高齡超重肥胖的孕婦逐漸增多,同時也增加了子代發生超重肥胖的風險,故應加強孕婦的健康教育和體重管理,減少對子代的不良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