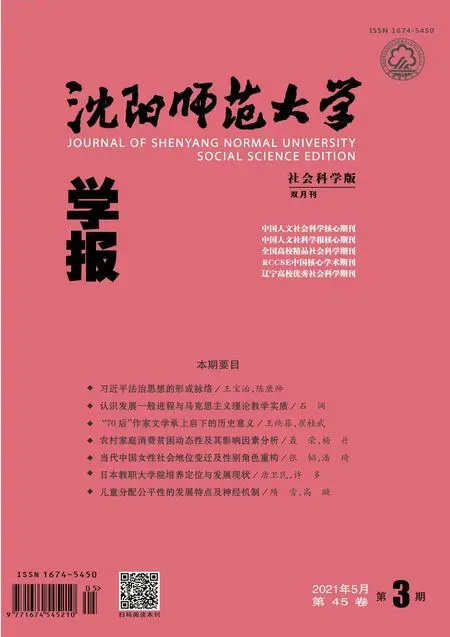阿特伍德《強盜新娘》中的“局外人”互文敘事
佟艷光,付筱娜
(遼寧大學 公共基礎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素有加拿大“文學女王”之稱,多年來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在她的第六部小說、反烏托邦經典力作《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中,阿特伍德描繪了一幅神權專治國家女性完全喪失人身自由而淪為生育工具的可怕圖景。之后發表的兩部小說,即略帶自傳性質的第七部小說《貓眼》(The Cat’s Eye,1988)和第八部后現代哥特式小說《強盜新娘》(The Robber Bride,1993),都是以中年女主人公之口講述主人公如何由毫無反抗能力的受害者成長為生活強者。這兩部風格迥異卻在內容上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作品,體現了阿特伍德繼《使女的故事》對女性未來命運做出可怕預言之后,對女性如何擺脫生存困境、完成自我重建進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
《強盜新娘》是一個取消了二元對立的模糊地帶,展現了一個后現代社會荒唐的生存狀態。小說文本打破了男權至上的神話,完全采用女性視角審視歷史、戰爭、家庭、婚姻、兩性關系、友誼、當今多元化社會乃至時事政治,充斥著對傳統童話、民間文學的顛覆性改寫和戲仿。《強盜新娘》存在大量“局外人”文學形象,該作品在主人公人物形象、內容、情節、結構與主旨上都與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大師阿爾貝·加繆的代表作《局外人》存在著明顯的互文關系。二者的互文關系為文本解讀提供了一個新的闡釋空間。
一、女性生存困境與“局外人”形象
阿爾貝·加繆的代表作、中篇小說《局外人》(法文原名 L’étranger,英譯名The Stranger),塑造了一個二戰前夕在孤獨中抗爭荒唐世界的“局外人”形象,使得“局外人”作為一個時代名詞和文學概念走入人們的視野。時隔半個世紀,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小說《強盜新娘》中塑造了一系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的女性“局外人”形象,她們生活經歷不同,性格秉性各異,然而女性生存的傳統與當代荒唐困境卻把她們共同推到了社會與人生的邊緣地帶。
《局外人》塑造了一個思想性格與二元對立的父權社會格格不入、因誤殺他人被判處死刑的青年職員形象——默爾索。荒唐而艱辛的現實生活使默爾索由雄心勃勃的大學生變成了心灰意冷的小職員。在母親的葬禮上,他拒絕看母親最后一眼,沒掉一滴眼淚。“無所謂”是他生活中的口頭禪。無論是老板想提拔他到巴黎辦事處工作,還是拉皮條的提出與他做朋友、女友瑪麗提出與他結婚,他都同樣表示無所謂。在監獄里,囚徒基本是由阿拉伯人和摩爾人構成的,他作為法國人是個特殊的存在。在法庭上,他根本插不上話,自己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最終淪為荒唐社會的無辜受害者。
在《局外人》這部小說中,“局外人”有著多重涵義:一是家庭里的“陌生人”,雖然有著直系的血緣關系,但是感情淡漠;二是一定社會范圍內的“邊緣人”,其所作所為不被世俗所接受;三是在生活、工作、情感等各個方面,一向置身事外,漠然對待一切事物,不想和外界發生任何聯系的人;四是在某種意義上處于劣勢的族裔或外國人;五是無力反抗而只能任人宰割的“受害者”。可見,“局外人”最核心的涵義是孤獨的人,不被社會所理解或被社會所排斥的人,有著超然人生態度的人,無辜的受害者①關于“局外人”基本內涵,筆者是在對加繆《局外人》作品中的“局外人”形象的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進行梳理總結的。國內外學術界對加繆《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形象內涵也有過一些比較深入中肯的研究,如段曉琳的論文《“局外人”與“例外狀態”“不正常的人”》:由阿甘本、福柯介入加繆《局外人》,指出默爾索嚴重觸犯法律、違背倫理、威脅社會共同體,是令正常社會秩序所懼怕的反常,但實際上,被法庭判定為冷漠殘忍的默爾索,是一個對生活充滿激情和真摯的熱愛、敢于直面存在與荒謬的真正的人;再如馬小朝的《覺悟到荒謬的局外人態度:加繆文學作品人物形象論》指出,覺悟到荒誕的局外人態度,表現為對常規生存狀態的疑問,延伸為超越眾生的孤獨感。。
阿特伍德小說《強盜新娘》中的三位女主人公托尼、查麗絲、洛茲,都有著與“局外人”涵義相符的身份和背景,也同樣是“局外人”多重涵義的集中體現。
首先,三位女主人公都是孤獨的人,她們的孤獨都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她們出生在二戰期間,戰爭給她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托尼的父母在戰爭年代倉促結合,沒有感情基礎,因而托尼從小生活在沒有愛的家庭,感覺自己是個外來者和陌生人[1]。母親來自英國,厭惡托尼的加拿大口音,忽視她的存在,很早就拋棄了托尼;而父親與她口音相同,卻因她不是男孩子同樣常常忽視她的存在。在母親與人私奔后,父親常常醉酒發狂,托尼倍感孤獨落寞。在大學時代,她醉心于戰爭史研究,變得更加冷漠,不和任何人往來。查麗絲原名凱倫,父親死在戰爭中[1]302,八歲就成為孤兒,寄人籬下生活在姨母家里,成為外來者和“陌生人”。查麗絲的姨母表面關心,實則冷淡;面對姨父肆無忌憚的性騷擾,小凱倫內心痛苦,卻無處傾訴[1]289。在遭姨父強奸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的靈魂與肉體一分為二[1]290。她沉默寡言,目光冰冷,等待著時機,永遠擺脫這個魔鬼般的家庭[1]293。在大學時代,她形單影只,不與任何人聯系。洛茲的母親是天主教徒,父親是德裔猶太人。洛茲黑色的頭發和并不白皙的皮膚,以及父親曾經的“難民”身份,使得她不被周圍的人所接受;從小跟著母親生活的她,也無法真正融入猶太人的社會。她一度缺乏歸屬感[1]360。父親在戰爭中走私,戰后一夜暴富,但財富來歷不明,洛茲總有歉疚之感和暴發戶的自卑感[1]379。
其次,三位女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加劇了她們的生存困境,迫使她們成為不被男權社會所理解或被社會所排斥的人。在托尼工作的歷史系,女同事不能夠理解托尼對戰爭史研究的興趣,將她視作另類;男同事把她視為不會構成任何威脅的存在,不論她的學術報告如何精彩,她也不過是一介女流,永遠被排除在同行決策層之外[1]121。童年遭受強奸的經歷,使得查麗絲靈與肉處于分裂狀態,成為一個不被人所理解的怪人。洛茲身為商界女強人,一方面感到自己在女權主義運動中往往被其他女性視為“局外人”[1]387,一方面感到自己被女下屬所排斥[1]97。
再次,三位女主人公在孤獨面對人生痛苦的過程中各自形成了超然的人生態度。托尼有從右往左讀的習慣,她的名字反著讀就是“Ynot”(為什么不)[1]153。她在研究戰爭史時,從不會站在戰爭的任何一方。查麗絲持一種極其超然的宇宙觀,認為每個人都是任何一個人的一部分。洛茲超乎于宗教、種族差異之外,將自己視為各種信仰、種族觀念的“大拼盤”[1]383。
最后,三位女主人公在婚戀生活中均在第三者澤妮婭出現時遭到丈夫或男友的無情拋棄,淪為男權社會的無辜受害者。
小說作者阿特伍德生于193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對二戰后的精神廢墟,對二戰后女權運動的興起與衰落、對戰爭給婦女兒童帶來的痛苦和災難有著深刻的體會。無論是加繆還是阿特伍德,他們筆下的“局外人”都是對社會問題的揭露和批評。阿特伍德一向非常關心政治問題,2013年,她參加了加拿大杰出女性倡議國歌中性化的運動。她指出,很久以來,一半的加拿大人——即加拿大女性,都被排除在男權社會話語之外,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加拿大“局外人”[2]。她在《強盜新娘》中對“局外人”形象的塑造則以文學手段深刻地表達了對女性生存困境的關切。
二、畸形婚戀和情感失衡的荒唐世界
在《強盜新娘》中,阿特伍德再現了傳統父權社會思想支配下的荒誕現實世界婚戀家庭生活,現代女性成為婚戀生活忍耐退讓的“局外人”,進而在婚戀家庭危機中淪為“受害者”。
如果說加繆的《局外人》尤為側重展現荒唐世界的司法暴力和來自宗教的精神暴力[3],那么阿特伍德的《強盜新娘》則更側重于表現荒唐世界中畸形婚戀和情感失衡的家庭生活。韋斯特在大學時代被同居女友澤妮婭拋棄。但是在同托尼結婚后,韋斯特在內心深處依然保存著對澤妮婭的執著愛戀,雖然敬重妻子托尼,卻只把她視作朋友。比利從美國逃到加拿大,一方面為了拒絕服兵役赴越南作戰;另一方面,還為了逃脫縱火犯的罪責,得到查麗絲的收留并一起同居。然而比利心安理得地過著寄生的生活,靠毫無積蓄的查麗絲獨立負擔全部開銷。比利和查麗絲還達成共識,“一切都是為了比利的快樂”[1]231。洛茲清楚,對于丈夫米奇來說,家就像是他的旅館,他的心并不屬于這個家,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他會不斷地出軌,而自己只是他窮途末路時的救命稻草[1]332。
在這樣荒唐的情感失衡的家庭生活中,三位女主人公以無言隱忍和退讓成為婚戀生活中的“局外人”。她們義無反顧地愛自己的男人,默默承受內心的痛苦,竭力在生活中充當著溫柔善良、勤勞賢惠的“家庭天使”。雖然身心俱疲,但也心甘情愿地延續幾千年來父權社會的傳統家庭悲劇,正如希臘史詩《奧德賽》中的珀涅羅佩那樣,永遠守候在靈魂的家園等待浪子的回歸。
《強盜新娘》的三位女主人公在荒唐世界的無言忍耐和退讓,使她們從婚戀生活中的“局外人”進一步淪為婚戀風暴中的無辜“受害者”,先后被所愛的人拋棄。澤妮婭像古希臘的海倫一樣能輕易俘獲所有男人的心,她一經出現,三位女主人公的家庭就瞬間土崩瓦解,三個男人無一例外地成了她的戰利品。韋斯特在澤妮婭重新出現后,不顧妻子托尼的苦苦哀求,搬去與澤妮婭同居。比利和澤妮婭雙雙不辭而別,拋棄了查麗絲和她腹中未出世的孩子。洛茲的花心丈夫米奇一反常態,不再偷偷摸摸地與美女幽會,而是公然與澤妮婭正式同居。
在古希臘史詩里,英雄憑借智慧、勇氣和力量對抗自然界的艱難險阻,對抗各種各樣的誘惑,對抗外來入侵者,保護自己的家園和女人[4]。在《強盜新娘》里,傳統的男人保護家園的英雄形象被徹底顛覆,他們不但無法保護自己的家園和女人,自己還做了對方的戰利品。
歸根結底,三位女主人公在男權社會中從小所承繼的傳統性別觀念和男女性別定位[1]368,使她們在荒唐的現實世界婚戀家庭生活中處于被動地位,一味付出和忍讓,終歸淪為受害者[5]。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三位女性一致把自己在婚戀生活中的不幸,完全歸咎于一位被她們妖魔化的女性澤妮婭,正如在古希臘悲劇《特洛伊婦女》中,以特洛伊王后赫卡柏、王子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瑪克和卡珊德拉公主為首的特洛伊婦女,眾口一詞地將海倫視為給她們的城邦、家族和個人命運帶來毀滅的紅顏禍水[6]。“所有的父權制,包括語言、資本主義、神論,只表達了一個性別,只是男性利比多機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權制中是缺席和緘默的”[7]。在父權制社會,女性常常成為“邪惡”的代名詞。男權社會“厭女”意識從小就折磨著三位女主人公,使她們感受到自身是社會的“他者”,同時這種意識與男權社會的其他話語一道逐漸滲透到她們的意識中,成為她們主體意識的一部分,在思想上也打上了“厭女”的烙印。洛茲為米奇之死氣勢洶洶地向澤妮婭興師問罪,澤妮婭對她說,難到米奇本人就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嗎?洛茲若有所思地沉默了[1]486。
荒唐世界中畸形婚戀和情感失衡的家庭生活的實質,是男權社會傳統性別觀念在現代家庭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失語并喪失了自我。
三、尋找自我之旅的引路人
《強盜新娘》三位女主人公同《局外人》中的男主人公默爾索一樣,因與被社會所唾棄的人物即澤妮婭、雷蒙結交而進一步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由“局外人”發展為“受害者”(反英雄),進而涅槃重生,成長為英雄。可以說,與被社會邊緣化的人結交,是這兩部作品中主人公開啟尋找自我之旅的前兆性因素,帶有“邪惡”標簽的邊緣人是主人公升華為英雄的引路人①本文利用美國著名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的理論來對《局外人》和《強盜新娘》中的主人公走上尋求真理的自我發現道路和自我成長道路進行神話學互文解讀。約瑟夫·坎貝爾(1904—1987年),美國著名作家、神話研究的大師級學者。他創作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神話學巨作,跨越人類學、生物學、文學、哲學、心理學、宗教學、藝術史等領域,包括《千面英雄》《追隨直覺之路》《指引生命的神話》《神話的力量》《坎貝爾生活美學》等。。
美國比較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指出,“童話故事里被人厭棄的青蛙、蛇、被拒絕的東西代表著潛意識的深處,在那里貯藏著所有被拒絕的、不被承認的、未知的或不成熟的因素、原則和存在要素,因此歷險的預言者或引路人往往被塵世認定為是兇惡、可怕、令人厭惡或邪惡的”[8]。在童話故事《青蛙王子》中,隨著小公主酷愛的金球落入泉水中,青蛙出現了,預示著個體與未知的力量發生了聯系。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人們通過吸收并整合新的力量,體驗到一種幾乎超人類的自我意識和控制力,而成為超越個人和當地的歷史局限性的男人或女人,即實現個人成長或者成為英雄[8]54。
《局外人》和《強盜新娘》中主人公在善意地完成雷蒙和澤妮婭交給他們的一系列“任務”后,并沒有成為英雄而是成為“受害者”,即人的存在價值和意義被無情“證偽”的“反英雄”人物[9],從而在遭到人生慘敗的絕境中,獲得了新的力量,重建自我,實現自我超越。
雷蒙是個人人不屑于理睬的拉皮條的,脾氣暴躁,是警察局的常客。默爾索在無奈之下答應與他做朋友,出于善意給他幫了好幾次忙——替他給情婦寫信、到警察局作證、在海灘與他情婦的弟弟打架,后因誤殺雷蒙情婦的弟弟成為殺人兇手而被捕,為生活所拋棄,淪為階下囚,從而深刻體會到個人與刻板教條的傳統父權社會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認清生活的荒唐本質。
在阿特伍德的筆下,《強盜新娘》的標題主人公澤妮婭神秘而復雜,既是為人所拒絕的,又是不可知的、可怕的。她的身世神秘莫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她出生于二戰期間,作為二戰的歐洲難民來到加拿大,曾經生活在滑鐵盧的孤兒院里,一度作為加拿大社會的邊緣人,受到社會的排斥與侮辱[1]402。她聰明貌美,會充分利用所有與她交好的人(不論男人還是女人),并讓他們付出慘痛的代價。“澤妮婭像迷藥、毒品、炸彈,迷惑了男人的心智,粉碎了女性幸福的美夢,以破壞性的力量對抗這個冷酷的男權世界。”[5]
三位女主人公不顧世俗偏見和他人勸阻,各自與澤妮婭有過一段密切交往的日子,在一次次幫助澤妮婭后淪為其“受害者”,成為“反英雄”人物,從而開啟了她們各自的自我發現之旅。“女性的身份構建過程并非個體孤立的,而是女性在與生存困境的沖突、協調與抗爭的過程中呈現。”[10]正是這樣新的生存困境沖突,引發了女性精神危機,開始了尋找自我與重建自我之旅。在大學時代,托尼我行我素地與人人敬而遠之的澤妮婭結交,常常借錢給澤妮婭,替她抄寫課堂筆記,撰寫學期論文,最后卻默默咽下因代筆撰寫論文反遭對方無情敲詐的苦果[1]192。幾年后,澤妮婭再次出現,搶走了托尼的丈夫,使托尼再次遭受沉重打擊[1]206。生活拮據的查麗絲毅然收留了謊稱身患絕癥、無路可走的澤妮婭,竭盡全力為其調治,但是男友比利卻與澤妮婭雙雙不辭而別,拋棄了查麗絲和她腹中未出世的孩子[1]310。洛茲不顧托尼和查麗絲的警告,盡力幫助澤妮婭,并請她出任女性雜志社的主編,然而不久,澤妮婭與洛茲的丈夫米奇開始正式同居,洛茲追悔莫及[1]410。
三位女主人公在絕望的痛苦中成為互相慰藉的好友,澤妮婭成了她們共同的“敵人”。她們每個人都曾經竭盡所能地給予澤妮婭善意的幫助,但澤妮婭卻恩將仇報,給她們各自的家庭帶來滅頂之災。澤妮婭成了“邪惡”的代名詞,她們認為澤妮婭是一個“強盜新娘,隱藏在幽暗森林中的豪宅里,專門捕殺那些無辜者,誘惑年輕人殞命于她邪惡的大鍋之中”[1]327。但與此同時,澤尼婭還是唯一一個了解她們最關心的事情真相的人。
比較而言,阿特伍德筆下的澤妮婭比加繆筆下的雷蒙更加復雜,更加耐人尋味,而且她與三位女主人公的關系也更為復雜。她們每個人都在澤妮婭的身上看到了另一個分裂的自我的“影子”[11],把她看作自己“未出世的雙胞胎姐妹”[1]210。也正因如此,她們無視她的異己個性,容忍她,縱容她,甚至在內心深處甘心情愿做她的受害者[1]204。
正如默爾索成為“階下囚”,并非雷蒙主觀原因造成,三位女主人公淪為“受害者”,與澤妮婭的闖入亦并無必然關系,她只是激化矛盾的外在因素。三位女主人公在澤妮婭闖入她們正常生活之前,就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本人在婚戀關系中所處的“受害者”地位,但卻安于現狀,聽憑命運擺布。在與澤妮婭的交往過程中,三位女主人公逐漸認識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從而完成了從反英雄人物到英雄人物的涅槃重生。
四、自我之死對荒誕世界的抗爭
在結構與主旨方面,《強盜新娘》和《局外人》都是以自我之死主題貫穿小說,表達了對荒誕世界進行抗爭的創作主旨。兩篇小說均以一個葬禮為敘事開端,以一個死亡達到敘事的高潮,又以一個死亡收場。《局外人》以默爾索母親的葬禮(預示自我之死)為開端,以默爾索在海灘失手開槍打死阿拉伯人(他者之死)為敘事高潮,以默爾索被判死刑(自我之死))而終結。《強盜新娘》以澤妮婭為自己安排的假“葬禮”(預示自我之死)為敘事開端,以洛茲的丈夫米奇以為澤妮婭已死,心灰意冷自溺而亡(他者之死)為敘事高潮,以澤妮婭從陽臺墜亡,三位女主人公為她舉行葬禮(自我之死)而告終。對于死者本人,是自我之死;對于他們所在的社會,則恰恰是“他者”之死。從邏輯上說,他者之死,意味著自我之新生。加繆和阿特伍德在這兩部作品中以“自我之死”母題表達了主人公對荒誕世界進行抗爭的強烈訴求。
《局外人》采用第一人稱,以主人公默爾索的口吻來敘述,默爾索因對社會價值觀的淡漠,而成為社會的“他者”,淪為社會的犧牲品。默爾索以“自我之死”與荒唐的社會抗爭到底,為求不再孤獨,只希望在他行刑之日,觀看的人山人海“向我發出憎恨的吼聲”[12]。加繆在《局外人》中的一個觀點就是,人孤獨地生活在冷漠的世界,此生之外再無來世。因而默爾索之慷慨赴死,顯得尤為悲壯。加繆在創作中一直在尋找著一條走出人生困境的道路——它通常是平庸之人在非理性世界憑借著本能與理性而非“希望”或“上帝”尋求到的并非有效的道路[13]。
《強盜新娘》采用第三人稱,分別以三位女主人公托尼、查麗絲和洛茲的視角來敘述。這樣,這三位女主人公既是“自我”,同時又是“他者”,而澤妮婭雖然是她們敘述中的“他者”,但她作為標題主人公,同時又是小說中的“自我”。“澤妮婭之死”主題在小說中被多次反復暗示,足可見其意義的重大。小說最主要的敘述者托尼在與澤妮婭初次見面時,只見到處涂成黑漆的房間,裝點著白色的菊花,所有的女孩都身著黑衣融入漆黑一片的背景,唯一的例外是穿著白色開衫的澤妮婭,她像夜空中皎潔的月亮,又像葬禮的中心人物[1]139。具備超自然預知能力的查麗絲,小時候外祖母曾經多次用圣經給她預測未來,但每一次預測的結果都驚人地一致[1]281,都是關于“大淫婦墜亡”,即“澤妮婭之死”。此外,查麗絲自己進行的圣經預測[1]463、她的少數族裔女老板的紙牌占卜[1]64及澤妮婭本人的紙牌占卜[1]302也反復預示了“澤妮婭之死”。另外,在三位女主人公分別單獨去酒店與澤妮婭會晤之前,她們每個人的夢都以不同的形式預示出“澤妮婭之死”,而且她們各自同澤妮婭合二為一。在托尼的夢中,澤妮婭的脖子上有一個大而深的切口,似乎喉嚨被割開了,她還看見澤妮婭有鰓(托尼是早產兒,剛出生時放在保溫箱里,像魚一樣嘴一開一合地呼吸,托尼的母親因此給她取個昵稱“孔雀魚”)[1]439。查麗絲在夢中看到,澤妮婭穿著一件跟自己那件很相似的睡袍,正對鏡梳頭。她的頭發像火焰一樣扭曲,像暗黑的柏樹枝條一般直指蒼穹[1]440。查麗絲走過去,同她肩并肩,融為一體……在洛茲的夢境中,一個男人擋住她,不讓她去找米奇,橙色的光(洛茲的睡袍是橙色的)從他的嘴巴和鼻孔中傾瀉而出,他打開自己的外套,里面是他圣潔的心(暗合洛茲幼年時的天主教信仰),在突然而起的風中閃爍著橙色的光,洛茲意識到這個男人一定是澤妮婭[1]442。
“他者”之死,意味著“自我”之重生。在種種預示澤妮婭之死的暗示中,都一再表明澤妮婭是三個女主人公“自我”的一部分。托尼將澤妮婭的骨灰帶回家,悄悄放在閣樓,沒有告訴丈夫韋斯特,因為這是女人間的事情[1]505。查麗絲相信,每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的一部分[1]499。澤妮婭之死,也是三位女友的“自我”之死。澤妮婭這個名字不再是之前假死時被大家諱莫如深,不愿提及了,她們要在講述她的故事中重啟自我的新生之旅[1]520。
《強盜新娘》是對《格林童話》中《強盜新郎》的改寫。《強盜新郎》中有一伙強盜每娶一名新娘,就要在婚禮之日將新娘殺害吃掉。小說的標題主人公則反其道而行之,引誘小說中三位女主人公的丈夫或男友,并讓他們付出慘痛的代價。她曾對查麗絲說,男人是沒有感情的,必須讓他們付出代價[1]254。雖然澤妮婭有著憤世嫉俗的一面,但是她也表現了維護自身尊嚴和權力的勇氣和智慧。相較于三位女主人公在婚姻戀愛生活中,冷漠地將自己置身事外,任人擺布,澤妮婭的針鋒相對,表現出與荒誕世界抗爭的勇氣。
阿特伍德在接受一次訪談中講到,加拿大的女性缺乏生存所需要的強大勇氣[14]。她在這部小說里塑造了澤妮婭這一在荒誕的孤軍奮戰的形象,目的就是希望女性在荒唐世界中遭遇自我毀滅之后可以從“澤妮婭之死”中獲得新的生命啟示——即與荒誕世界抗爭的勇氣,獲得超越自我的超道德價值,從而開始自我的新生,重建自我,改變“局外人”的身份和命運。
五、結語
加繆的《局外人》與阿特伍德的《強盜新娘》存在多層次的互文關系。通過這樣的敘事策略,阿特伍德含蓄委婉地表達了對后現代社會女性生存的深切關注。加繆《局外人》的橫空出世,表達了一個黑暗時代人的麻木、冷漠與孤獨絕望,他筆下的“局外人”懷抱著渺茫的希望準備走向犧牲的祭壇。然而阿特伍德的《強盜新娘》卻在塑造后現代女性“局外人”的同時,努力探尋她們未來的出路、重獲新生的路徑,盡管澤妮婭所代表的自我之死,暗示了重獲新生之途的黑暗與曲折,但無論如何作者還是在冷峻晦暗的世界里投下一縷淡淡的光亮,讓它照耀著人們不斷求索前行。阿特伍德寫道:“像扮演其他角色一樣,一個人一旦披上作家的外衣,便會獲得某種權力。”[15]她正是在充分運用作家的權力來履行藝術家的道德和社會責任,在嚴肅冷靜地觀察社會、解剖社會的同時,為社會的良性發展開出一劑藥方,讓身心疲憊的“局外人”看到前方若隱若現的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