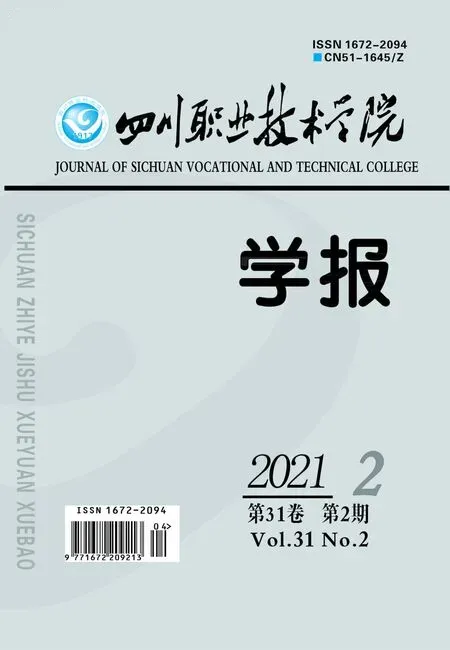《廣韻聲系》校正十則
王雪
(西南大學 漢語言文獻研究所,重慶 400715)
《廣韻聲系》(以下簡稱《聲系》)是沈兼士主編的一部研究漢字諧聲系統的工具書,其中的諧聲關系和諧聲層級對于漢語語音的研究有特別重要的作用。但沈兼士在敘例中指出:“本書諧聲字之排列既依據《說文》而作,而許氏之言亦有訛謬,案之殷周古文,往往不合……雖欲廣加判定,慮有未周,而近人新解,亦不盡可信。故仍本許氏之說,不便輒加更易。”[1]顯然,沈兼士已注意到《說文》中的諧聲分析多與古文字不合的情況,但因編纂時有限的古文字材料和研究成果,尚不能判定正確的諧聲關系,故大多仍從《說文》。隨著古文字材料的不斷涌現以及研究水平的逐漸提升,當時一些不能確定的諧聲分析,現據新材料和新成果已可認定,所以我們對《聲系》中的部分錯誤進行了校正,希望對諧聲系統和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有所幫助。
一、“尹”“聿”“君”“伊”聲 系
《聲系》將“尹”“聿”“君”“伊”分為四個聲系,其實應當合并為一個聲系。
《說文》:“尹,治也,從又丿,握事者也。”《聲系》沿用之,將“尹”列為第一主諧字。“尹”甲骨文作(《甲骨文合集》27011何組)[2]333(2以下簡稱《合集》)、(《合集》3480正 賓組)[2]587,金文作(《新金文編》10175史墻盤)(以下簡稱《新金》)、(《新金》2829頌鼎)[3]333。
《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從一聲,凡聿之屬皆從聿。”《聲系》沿用之,將“聿”歸為“一”聲系。“聿”甲骨文作(《合集》28169無名 組)[2]3471、(《合集》22063組)[2]2827,金文作(《新金》5391.1執卣)、(《新金》6040.2聿觶)[3]358。
裘錫圭認同王國維、葉玉森和李孝定等學者關于“尹”所從之“丨”象筆形的觀點,并進一步指出:“‘尹’、‘聿’二字不但字形上同出一源,且聲母皆屬喻母四等,韻部文、物對轉,古音相近。”[4]我們認為,其說可從,從“聿”“尹”之古文字看,二字在形音義三方面都有密切聯系,“聿”不應從“一”,而從“尹”,當歸為“尹”聲系。
《說文》:“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聲系》沿用之,將“君”列為第一主諧字。段玉裁、王筠和宋保等學者指出:君,從口從尹,尹亦聲[5]581。陳英杰認為:“君,形聲兼會意字,從口、從尹,尹亦聲。‘君’由‘尹’字分化而出。”[6]82我們認為,“君”屬見紐文部①,“尹”屬喻紐文部,二字讀音相近,“君”實由“尹”增加“口”形分化演變而來,且從“尹”得聲,故“君”也應歸為“尹”聲系。
《說文》:“伊,殷圣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聲系》沿用之,將“伊”列為第一主諧字。朱駿聲、王筠、徐灝等學者均指出:伊為形聲字,從人,尹聲[5]3489。我們認為,“伊”屬影紐脂部,“尹”為喻紐文部,二者聲紐同屬喉音,韻部文、脂旁對轉,語音相近,可通。“伊”應從“尹”聲,也當歸于“尹”聲系。
二、“云”“旬”“勻”“軍”聲 系
《聲系》將“云”“旬”“勻”“軍”分為四個聲系,其實應當合并為一個聲系。
三、“奸”聲系
《說文》:“奻,訟也,從二女。”“奸,私也,從三女。”《聲系》沿用之,將“奻”歸為泥類意符字之不為主諧字者,將“奸”視為見類第一主諧字。
我們認為,諸家均從《說文》《釋名》等傳世文獻出發,指出“奸”應從“奻”聲。但據目前所見出土文獻材料來看,并沒有充分的辭例證據證明“奸”“奻”存在音義等方面的聯系,諸家的觀點還需更多的材料作為補充,故“奸”從“奻”聲之說,當存疑待考。
四、“今”“琴”聲系
《聲系》將“今”“琴”分為兩個聲系,其實應當合并為一個聲系。
《說文》:“今,是時也,從亼從乁,乁古文及。”《聲系》沿用之,將其視為第一主諧字。“今”甲骨文作(《合集》649賓組)[2]156、(《合集》6426賓組)[2]944,金文作(《新金》2809師旂鼎)、(《新金》2820善鼎)[3]656。
于省吾認為:“今”系由“亼”下附加一橫劃作指事區別標志,以別于“亼”,而仍因“亼”以為聲,是附劃因聲指事字[12]456。季旭升指出:“今為見類侵部開口三等,亼為從類緝部開口三等,二字形音皆近。”[9]448何琳儀認為:“今,甲骨文從亼,右下加短橫分化為今,亼亦聲。今從亼聲為入陽對轉,今為亼之準聲首。”[11]1389我們認為,從字形、字音上分析,諸說皆有理,可從。“今”乃由“亼”分化而來,且依“亼”為聲,故“亼”當列為從類第一主諧字,“今”則應歸于“亼”之第二主諧字。
《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凡珡之屬皆從珡。,古文珡從金。”《聲系》沿用之,將其列為第一主諧字。
五、“豦”聲系
《說文》:“豦,鬬相丮不解也。從豕、虍。豕、虍之鬬,不解也。”《聲系》沿用之,將其視為第一主諧字。“豦”金文作(《新金》4167豦簋),(《新金》6011.2盠駒尊)[3]1365。朱駿聲認為:“豦,虎食豕不相斗,當從虍聲。”[15]馬敘倫指出:“豦,則從豕虍聲亦可也,依司馬相如說,亦當虍聲。”[16]何琳儀指出:“豦,從豕,從虎省,會野豬與虎相斗之意,虍亦聲。”[11]447孟蓬生師認為:“豦,形聲字,從豕,虍聲。本義為一種體型較大的豬。”[6]846劉釗則指出:“‘虍’字來源于‘虎’,聲音也藉用了‘虎’的讀音。‘虍’字在文字系統中從不單獨使用,而是作為一個構形因素與其他構形因素組合成復合形體,‘虍’字在復合形體中大都作為聲符使用。”[17]我們認為,字形上,“豦”本從“虍”;字音上,虍,曉紐魚部;豦,見紐魚部,二者聲紐相近,韻部相同,可通,“豦”當為“虍”之第二主諧字,故“豦”及從“豦”得聲之諧聲字皆應歸于曉類“虍”聲系。
六、“繼”聲系
《說文》:“檵,枸杞也,從木,繼省聲。一曰,監木也。”《聲系》沿用之,將其列為“繼”之第二主諧字。
關于《說文》中形聲字的省聲分析,大部分學者認為應以辯證的眼光看待,不可盡信。陳夢家就指出:“《說文》中的省聲和亦聲,歷來的傳寫本都有偽易增奪,必須經過一番校勘的工夫。”[19]裘錫圭也認為:“雖然省聲是一種并不罕見的現象,我們對《說文》里關于省聲的說法卻不能相信。”[20]何九盈也認同段玉裁、丁山、王力及姚孝遂等學者關于《說文》省聲不盡可信的觀點,并進一步指出:因《說文》在傳寫過程中失“?”之篆形,乃將“檵”視為“繼”之省聲,此實乃因傳抄奪字而造成的省聲,“檵”應本從“?”聲[21]4-17。另,段玉裁、王筠、苗夔等人均指出“檵”當本從“?”聲[5]2430。我們認為,諸說可信,檵,應本從木?聲,不必從“繼”省聲,應歸為“?”之第二主諧字。
七、“麥”“棗”二字與“來”“棘”聲系
《聲系》將“麥”“棗”二字歸于意符字之不為主諧字者,將“來”“棘”分為兩個聲系,其實“麥”“棗”“來”“棘”應當合并為一個聲系。
蘇建洲從“來”“棗”“棘”三字的形音義等各方面進行了分析,指出“棗”“棘”確有可能本從“來”,而后訛變為從“朿”[22]118。孟蓬生師從字形、假借、聲訓及同源詞等多方面考察了“來”字古音,指出:“來”“麥”音義相通是沒有問題的,“棘(?)”字本從并來,而不從并朿。來,古人稱為芒谷,是有刺兒的植物,“棗()”字從重來,也是有刺兒的植物,來棘(?)棗()應看作是一組同源詞,音義俱近②。那么,據目前可見材料及相關研究分析可知,“來”“麥”“棘(?)”“棗()”當系同源分化,皆均應歸于“來”聲系。
八、“亟”聲系
《說文》:“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聲系》沿用之,將“亟”列為見類第一主諧字。
九、“庸”聲系
《說文》:“庸,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聲系》沿用之,將“庸”視為會意字,歸為喻類第一主諧字。宋保、苗夔[5]1392、于省吾[12]317及何琳儀[11]422-423等學者均認為:庸,從用從庚,用亦聲。我們認為,諸說可從,字形上,“庸”本從“用”;字音上,“庸”“用”同屬喻紐東部,古音相同。故“庸”無疑當從“用”聲,“庸”應歸為喻類“用”之第二主諧字。
十、“幼”聲系
《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凡幺之屬皆從幺。”“幼,少也,從幺從力。”《聲系》沿用之,將“幺”列為影類意符字之不為主諧字者,將“幼”列為影類第一主諧字。段玉裁、苗夔[5]1067及何琳儀[11]160等學者均指出:幼是會意兼形聲字,從幺從力,幺亦聲。我們認為:“幺”屬影紐宵部,“幼”屬影紐幽部,二者聲紐相同,宵、幽旁轉,讀音相近,可通,故“幺”應列為影類第一主諧字,而“幼”當是“幺”之第二主諧字。
以上是對《聲系》中十處存疑的諧聲層級的重新分析、歸類,通過利用新材料和新成果對其進行校訂,能幫助我們正確地劃分諧聲層級,厘清諧聲關系,也有利于漢語語音的進一步研究。
注釋:
①文中上古音聲韻歸類均參照唐作藩編著的《上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下文不更注。
②轉引自孟蓬生師之未刊稿《“來”字古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