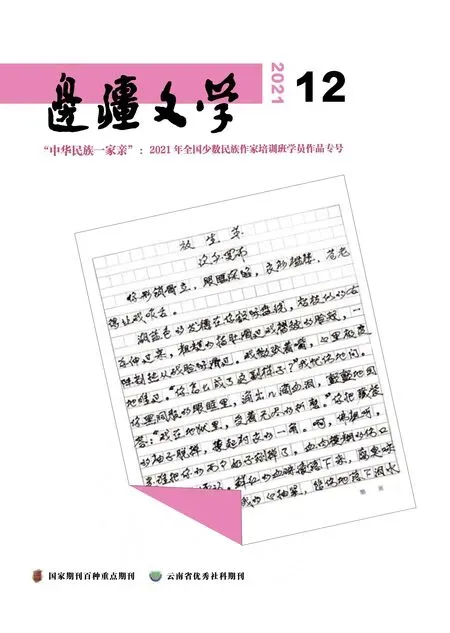少即是多
田馮太(土家族)
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和同學們的各抒己見猶在耳畔,就像下關的風輕柔地拂過洱海平靜的水面,激起陣陣漣漪,回蕩在大理古城的青瓦白墻之間。
2021年6月25日至30日,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主辦、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承辦、云南省作家協會協辦的“‘中華民族一家親’:2021年全國少數民族作家培訓班”在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舉辦。很榮幸,我以作家和編輯的雙重身份參加了本次學習。在這座素有風花雪月之稱的美麗小城,我們不談風月,只談文學。談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談新時代文學的現狀與發展;談文學創作的內涵與技法;還談我們的少數民族身份與各自民族文學的特色,展望少數民族文學不可限量的未來。
編輯這一期專號,絕不是我一時的心血來潮或突發奇想。事實上,《邊疆文學》自創刊以來,就時刻密切關注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情況。除了云南本土的25個少數民族,其他兄弟民族的作家作品也一直在我們的視野范圍之內。“邊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學家園”,這是我們一以貫之的辦刊理念。
6月25日晚上,我將編輯一期專號的想法向總編輯潘靈先生匯報,他欣然應允并給予了極大的肯定。說干就干。我找家在大理的白族作家李達偉同學借了一臺筆記本電腦,白天學習,晚上上百度搜索和中國知網(CNKI)查閱與會作家及其作品的情況。參加本次培訓班之前,與會的119 名少數民族作家我大概知道三分之一,在某些文學場合見過面或者讀過、編發過他們的作品,另外的三分之二則稍顯陌生。要在短短的五天時間內了解他們過去的創作情況,網絡無疑是最便捷的方式之一。
從119 名優秀少數民族作家的優秀作品中挑出一二十人,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不過現在回想起來,似乎也挺輕松,把握好三個原則就好。一、先來后到,誰的稿子先來就先讀誰的,先送審,這跟正常編稿沒什么兩樣;二、質量為先,這也跟正常編稿別無二致;三、每位作家每年在我刊發表作品小于等于一次,這也是很多期刊不成文的規定。最終,我選出了15 個少數民族的20 名作家的作品。
編完這期的所有稿件后,我突然有了一個策劃之外的發現。這20 名少數民族作家涵蓋了60 后、70 后、80 后和90 后,形成了一個梯隊。按照出生年代給作家劃分代際,這是批評家們常用的便捷方法,但通過這一期的編稿情況我發現,這也不無道理,不同代際的作家在題材和表達方式上,還真存在差異。就本期的20 名少數民族作家而言,60 后作家的尋根意識更強,題材方面更傾向于向民族地域文化與歷史的縱深處延伸;70 后作家處于一個過渡階段,各種風格并存,更多姿;80 后大都像我這樣聽著港臺流行音樂、讀著中西方文學經典,在各種文化的碰撞中長大的,本民族文化的遺傳密碼還在血管里流淌,但筆下更重視我們身邊的物非人亦非;至于90 后,本期雖然只有兩名作家,卻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種后現代語境下解構中的建構,我喜歡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銳氣。
綜觀這20 名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不難發現,大多數都是本次培訓班結束后的新作。這說明,本次培訓確確實實對大家的寫作起到了指導作用。云南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李勇先生是第一位授課教師,他講的是“黨的民族政策與民族工作”,其中,對改土歸流以來的民族識別與民族政策做了系統梳理,有著學者式的嚴謹,本期就有作家受到他的影響,對本民族的文化展開知識考古的同時,進行了詩意的表達;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關仁山先生的講座題名為“文學的社會廣度、人性深度與精神高度”,側重于文藝學的理論指導,進一步堅定了作家們追求真善美的決心;沈陽師范大學賀紹俊教授和贛州文學院卜利民院長分別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闡明了紅色文學的重要意義和創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項,在他們的啟發下,本期有作家對以錢創作的紅色文學作品進行了修改與完善;云南省作家協會秘書長、著名作家胡性能先生從敘事學的角度對經典文本進行了解剖,提升了大家的小說創作技法。小說要怎么寫才更具現代性?在這一期專號中,80、90 后作家也在極力探索這一問題。期間,大家還觀看了張桂梅的事跡報告,有一位詩人看完后深受感動與鼓舞,據此創作了作品,寫得情真意切,就發在這一期專號里。
著名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先生曾說,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本。編完這期專號,我對這句話的認同度又加深了一層。如果單論人口數量,少數民族確實是少,但從文化多元的角度來看,少即是多。毫無疑問,無論是題材還是話語方式,少數民族文學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的視野,形成了百花叢中爭奇斗艷的繁榮局面。
由于版面有限,我們無法將55 個少數民族的優秀作品一一呈現。我希望這一期專號能起到窺斑見豹的效果,讓讀者朋友們領略到少數民族文學的獨特魅力。

麥場上的男子 紅河瀘西 2014.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