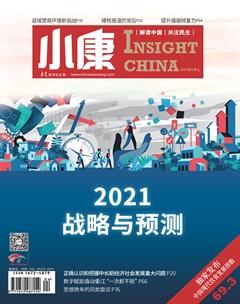分級診療,從制度建設走向體系建設
劉建華

組合拳“ 分級診療”要取得成效,實際是需要以地方政府為主導、醫療機構相配合,共同來完成一套“組合拳”。
分級診療制度是現代醫療服務體系中一項基礎性、關鍵性的重大制度。“充分利用現有的醫療資源”是分級診療制度的終極目標,其核心要義是,根據不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比較優勢,對不同種類的疾病進行分類診療,將有限的醫療資源轉化為最大的健康產出的醫療服務分工合作的最佳制度模式。
事實上,分級診療在我國醫療體系推行多年,但長期以來,仍處于“有分級”“無分診”的狀態,并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分級診療。分級診療制度的缺失,無疑是醫療服務供給側的一大缺陷、一大短板、一大弊端。醫衛、醫藥、醫保領域中產生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諸如資源配置失衡、制度性浪費嚴重、運行效率低下、就醫盲目無序、“看病難、看病貴”等等,幾乎都與此有關。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繼續重點關注分級診療,并提出要加快體系化建設,這是對該制度運行效果給予肯定的同時,對其發展目標的推進時間提出了明確要求。另外,從制度升級到體系化,也是對我國醫療服務供給由粗放規模走向高質量發展方向的有力引導。
北京分級診療已顯成效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部署加快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形成科學有序就醫格局,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通過推行分級診療制度,將大中型醫院承擔的一般門診、康復和護理等分流到基層醫療機構。
形成“健康進家庭、小病在基層、大病到醫院、康復回基層”的新格局是醫改的一項重要任務。但就全國總體情況來看,效果一直不太盡如人意。
對此,廣東省衛建委巡視員廖新波表示,“分級診療是一個好東西,一直以來都在推行,但是為什么在中國就實行不起來,甚至導致居民對醫生有如此多的微詞與抵觸,關鍵就是政府的引導與市場的推動沒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甚至兩者是對抗的。”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錢學明多年來一直在關注基層醫療的發展,他多次在接受《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記者采訪時反映,基層醫療機構留不住醫學人才。在他的主導下,5年前便在南寧市的上林縣推行一體化改革,將鄉鎮衛生院一并納入縣人民醫院,以此阻止人才的流失和吸引優秀的醫護人員,通過多年的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廖新波分析稱,“基層醫院沒有人才”,造成這種尷尬的局面是因為分級診療沒有做好,而實際上是因為沒有分級診療實施辦法,現在只是一種“鼓勵”。“分級診療說白了不是醫院干活,而是機制干活。”2009年,他在參加國務院組織的醫改新方案論證會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把“鼓勵”醫生到基層改為“吸引”醫生到基層。
“分級診療”要取得成效,實際是需要以地方政府為主導、醫療機構相配合,共同來完成一套“組合拳”。
北京是全國醫改的風向標。
2017年4月,北京實施醫藥分開綜合改革,取消醫療機構藥品加成,實行零差率銷售,設立醫事服務費,取消掛號費、診療費,實施藥品陽光采購,規范調整435項醫療服務項目價格,實施改善醫療服務等綜合改革措施。
2019年6月,北京實施醫耗聯動綜合改革,取消醫用耗材加成,規范調整6621項醫療服務項目價格,開展京津冀醫用耗材聯合采購,穩妥實施國家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試點,改善醫療服務和加大醫療保障改革力度。醫藥分開和醫耗聯動綜合改革使參改醫療機構告別了以藥品和耗材補償運行成本的歷史,技術勞動補償發揮更大作用,新的補償機制有效支持了醫療機構平穩運行發展。
截至2020年10月,北京基層醫療機構門診量增幅連續43個月高于二級和三級醫院,呈現門診服務向基層機構分流的態勢,分級診療效果持續向好。2020年1月至10月,基層診療量占比較2015年同期上升了約8個百分點。不含來京的就診患者,基層診療量占比達到51.2%,創近年來歷史新高;住院服務則向三級醫院集中,三級醫院住院日縮短,效率提升。
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相關負責人在2020年12月23日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北京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成效顯現。北京穩步推進醫聯體建設,組建了覆蓋全市16區的60個綜合醫聯體和37個緊密型醫聯體,基本形成了醫聯體為主體的分級診療格局;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新建和改擴建525個村衛生室,實現全市基本醫療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全覆蓋;提升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擴大簽約服務隊伍,加強重點人群服務,優化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內涵,提供個性化簽約服務,已組建家庭醫生團隊5158個,重點人群簽約率保持在90%以上。
找準突破口,抓實著力點
“按照現行政策,存在收費標準、報銷比例不同。以闌尾炎手術為例,在縣醫院看病,個人承擔的費用是鄉鎮衛生院的5倍,市醫院增加到7倍,省醫院約10倍。一旦衛生院治不好,農民被迫去上級醫院看病,將會造成嚴重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錢學明說,現實狀況是,由于縣、鄉、村三級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并不一體,性質不一、編制不同、相互獨立,導致縣鄉之間存在著利益上的不一致甚至矛盾。檢查結果無法互認,分級診療、雙向轉診難以實現。
分級診療要得到順利實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設計是否精細、具有可操作性。雖然國家在相關文件中多次提到要加快形成分級診療體系的步伐,但是醫聯體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作為實施分級診療的重要載體,需要從制度層面明確相應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并細化相關操作流程,以確保各級醫療機構在實施分級診療時能夠明確相互間的責、權、利,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相對完善的操作細則。
目前,基層醫療機構大多基礎設施差,沒有足夠的業務用房面積,且多數機構沒有房屋產權,是租房經營;設備簡陋,就醫環境差,難以滿足城鄉居民的就醫需要。加上基層醫務人員的工資待遇、培訓體系、職稱晉升等制度不完善,首診激勵不足,積極性不高,以至于優秀醫師不愿到基層醫療機構行醫。
患者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信任度也不高。按理來說,患者的就診路徑應該是“金字塔”形的,即一般常見病、多發病在基層診治,疑難雜癥等在大醫院診治,但是現階段的就診路徑卻呈現出“倒金字塔”形。居民一旦患病,無論大病小病,首先選擇大醫院,以致出現大醫院人滿為患、基層醫療機構門可羅雀的怪現象。這些都源于居民對基層醫療機構的不信任、對大醫院有慣性的依賴心理。
下一步怎么走,南通大學校長施衛東認為,推進多類型醫聯體建設,是進一步完善分級診療制度、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他建議,進一步完善醫聯體運行機制,推動各級各類醫聯體實質性運作,積極采取專科共建、臨床帶教、專家坐診、業務指導、開設聯合病房等緊密合作方式,全面加強下級機構薄弱專科建設,提升其服務能力和水平,提高基層就診率。
此外,他還建議推動落實藥品傾斜政策,為基層就診、轉至基層治療患者提供必要的藥品供應保障;全面開展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形成長期契約關系,促進基層首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