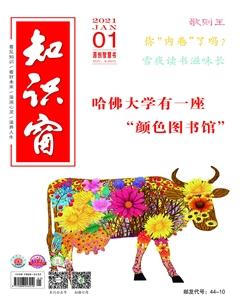我們開始了自己的故事
卡拉·德魯斯 孫開元
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小時候,我每個星期都會去幾次圖書館,拿著手電筒看到很晚。每次,我都會借走好多喜歡的書,過幾天就送回來。一次,圖書館管理員問我:“你要是看不過來,就不要一次借走那么多。”
“但是我都看完了。”我說。
我在大學里主修英語,接著攻讀文學碩士。填寫網絡交友資料時,我在“最喜歡的書”一欄填得滿滿的:《百年孤獨》《流動的饗宴》《白牙》《同名同姓》《已知世界》《微物之神》《誰解風之語》。
其實當時我心里知道,這幾本書當中的大部分我只看了書名。我加入過幾個讀書俱樂部,但從沒去過。我從圖書館借了一本大家都在看的網紅書,一個星期后還了回去,交了借書費,一頁沒看。
一想到看書,我依然會歡喜,也依然珍視書和書店。每次找到一個書店,我都會在一排排書架間逗留幾個小時,如同老友相逢,看幾頁,然后買幾本。問題是,書依然是紙質書,我已不是原先的我。
大衛是我在網上結識的初戀,我看他的個人說明上寫著喜歡讀書,于是我問他最近看什么書。他的眼睛一亮,如數家珍般地說起來。他看的書比我看得多,一個星期能看一兩本。我倆似乎不可能結合,因為地位不同。但是我們相識后,書籍給我們架上了一道心橋。
我們喜歡的書各不相同,大衛喜歡歷史和人文,我喜歡看小說。第七次約會時,大衛和我第一次逛了圖書館。
“我們做個游戲吧,”大衛說著,從挎包中拿出了兩支鋼筆和兩本任意貼,“我們找幾本讀過的書,給其他讀者寫幾句留言。”
我們在書架前看了一個小時,最后在詩歌類書架前的地板上坐了下來,他先選了一本。
那一年春天,一次外出野餐時我告訴他:“我今年只看了一本書。”
“現在剛到六月,而且你喜歡書,喜歡書店,喜歡圖書館。”他說。
“那我應該看很多書嗎?”我反問。
“不是,可你今年仍然應該再看一本。”他說。
現在網購盛行,但我仍然看重書店的文化氣息,每次逛書店我都會買幾本書,只是幾乎不看。我家里的椅子上、沙發扶手上都擺著書,如同我的衣服,棄之可惜,留之不用。
我的每個書架都有兩排書,書架旁邊還分門別類地堆著幾堆書:我看過的書、我想看的書、不大喜歡所以沒看完的書、有猶豫是否繼續看的書。
后來,在一家一美元書店,我給自己買了五本書,給大衛買了兩本書。他的“看一本書”的建議一直縈繞在我耳邊。一天下午,我拿起一本書,我買這本書只是喜歡詩情畫意的書名。
書名雖好,卻難以看進去。書中主人公是一位老先生,作者似乎是以一個女性角度描寫他的言行。可每次當我打算放棄看下去時,就會想起大衛。
我看了前兩章,第三章時人物換了一種敘述方式,我喜歡這個轉換。我把這本書帶到公司,吃午飯和走路回家時都要看,偶爾抬起頭看看路。
“你今天過得怎樣?”大衛發短信問我。
“還好,有點兒累。”我回答,“我夜里很晚才睡,看完了這本書。”我上一次徹夜看書還是在12歲的時候,那次我看的是《小婦人》。
在大衛的帶動下,我越來越接近真正的自己,成為我喜歡的自己。他有時和我談起他看的書里的硅谷或者環保,我給他講我看的小說里的故事:一個人藏在一個盒子里離開故鄉,爬出來變成了一只小鳥飛上藍天。我讓他知道,有時候說清這個世界的唯一辦法就是虛構。
有一次我問大衛,他喜歡我什么。他想了想,說:“你讓我少了些憤世嫉俗,和你在一起,我看這個世界更可愛了。”
大衛建議我們再逛一回第七次約會時去過的書店,到了那里,他從一個書架上拿過一本書,翻開了它。扉頁的任意貼上寫著:“卡拉,我的心里只有你。嫁給我,好嗎?”
大衛的求婚寫在《叛逆公主》這本書的扉頁上,已經有一年多了。
“好,我愿意嫁給你。”我說。
我們站在好多排小說中間,別人的故事圍繞在身旁,現在,我們開始了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