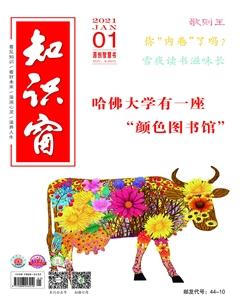黎明,橫跨長夜的等候
紙袋
云靄低沉,遠空廣闊。重重交疊的烏云像是被一筆濃墨浸漬,又被時而吹來的微風揉亂、弄散。明月躲在城市和天空的交界處,只留下一圈淡淡的光影。群星茫然地徘徊在天際,如同迷途中驚恐不定的孩童,找不到回家的路。
雨已經停了。
公交車隨著遲緩剎車聲的響起而停下,車頂的照明燈撲進伸展出水泥路面的綠枝丫里,嘩啦落下一地積雨。水滴沾濕了站臺的欄桿和長木椅,氤氳了跳動著字幕的玻璃站牌,牌里隱約倒映著暮色中的城市模樣。
我摘下耳機,耳邊的音樂聲在頃刻間被切斷。隨著前排的人群漫步下車,我收起深藍色的雨傘,目送末班車的遠去。朦朧的睡意被冷風吹醒,我嗅到空氣中混雜著的泥土與塵埃的氣味,世界都濕透了。
街邊的店鋪有些關了門,有些剛剛開始營業,不遠處的體育場內已經亮起了燈光,放眼望去,能看到吃過晚飯的人們正在兜圈散步。車流并不算擁擠,晚高峰已經過去了,偶有小車經過稍顯凹陷的路面,壓起水花將車輪又漿洗了一番。
歲數較小的孩子們躲在書店的一角看著饒有趣味的漫畫書,全然不知已是日暮將晚時分。巷子口叫賣吃食的小販騎著三輪車從我面前經過,香味飄散了一路。我坐在站臺的長木椅上,放下手里用來打發時間的雜志,抬起頭發現月亮已經出來了。
你還沒來,我還在等。
道路兩旁的燈光幾乎在同一時間熄滅,尖銳的鳴笛聲、零碎的細語聲都漸漸消失在深夜的靜謐里。我望著石橋下的流水,水過木筏流聲簌簌,像是緩緩淌過城市的側影。腦海里回響著不知是哪一年的歌曲,向不知名處道一聲晚安,與風共枕,和光同眠,我倚靠在木椅上陷入了夢境。世界轉到零點,悄無聲息。
你還沒來,我還在等。
夢醒時,城市已踏上新一天的軌跡,深夜在輕薄的晨霧里褪去舊衣。大貨車笨重的輪胎刮擦過瀝青路面,帶走了昨晚堆積未干的洼水。將清冷的空氣吸入鼻腔,我空有一身疲倦,想把與你有關的世界都悄然掩藏。
等待好像是一件說來稀松平常的事,我們短暫的人生旅途中不知為多少人和事駐足等待過。
小時候,我們經常等,站在家門口等下班回來的父母,拿著木頭棍子在地板上一橫一豎地劃,感覺時間過得特別慢,慢到明明數了幾百下,還沒有在視線的盡頭看見父母所騎的摩托車燈光。
長大后,我們反而不愿意等待,時間成了別人的東西,不再被我們任意揮霍。我們活得很急,為眼前的事焦頭爛額,為以前的事懊惱不已,為以后的事愁眉苦臉。好像不單單是不能停下來等待,似乎要用跑,跑著過完一生才算是對得起別人的期待、自己的本心。
成長往往是一晃而過的事情,我不知道成長以后的我還能否這樣等。
其實,有時候你等的是誰并不重要,那人來不來也不重要,因為等候本身就可以成為一次面向自己的朝圣。就像生命長線是一場未知的際遇,讓那些未曾經歷過的人為之憧憬,為之動情。
想把每一次空守長夜的等待都換成不期而遇的邂逅。那是一段美好的塵緣,我們用雨水洗盡鉛華,把所有煩愁都給抹殺,將生命定格在最初的悸動里,宛如山間的漫野繁花,爛漫卻不失風雅。
誰會在意你來時的一身塵土,我只記得你笑時燦爛如霞。拋去這樣那樣的過往,我們依舊可以如沐微陽,希冀遠方。只是有時我們需要等待,就像是等待黎明,它終歸會出現。
那個女孩,不知道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她站在站臺的扶手邊,如同一支娉婷盛放的白蓮。晨風吹起她的長發,潔白的裙邊綴滿了花朵。她優雅地立在那兒,仿佛整個世界都要為之傾覆。
可是那又怎樣,你依然沒來,我仍舊在等。
我試探著向女孩靠近,心跳驟然加速,咯噔地敲擊著胸腔。我想發聲問候,嗓子卻突然干涸。她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清脆的、銀鈴般的聲音在我的耳畔回響著。
“你呢,也等車嗎?”她反問道。
“我嗎?我在等風,等黎明,等一場不期而遇。”我的聲音逐漸微弱下去。
“那一定很有趣吧。”女孩笑著說道。
“應該是吧。”我尷尬的笑容凝結在晨霜微露中。
晨光透過云層散射下來,像是密網中漏出的游魚。我整個人沐浴在城市的日光中,天快要破曉了。
或許你還沒來,我一直在等。
輕簡的車身遮擋了眼前的一片光亮。女孩緩緩地走上車,扭頭向我揮別。我目送她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目送著微風吹起她的長發,一路向前。
人生有時就像是一次漫長的車程,我們在旅途中遇見,在旅途中揮別,在旅途中失去,然后重新遇見。莫要帶走一絲一毫的悲傷,我想把剩下的時光都留給那個姍姍來遲的你。
你是“黎明”。
你還沒來,我還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