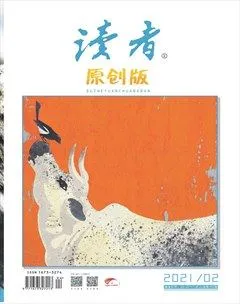做你的降落傘
阿寧
一
2020年1月,我帶著抑郁癥診斷單坐上了回家的高鐵。
盡管幾個月前已經同父母坦白了這一切,我仍然心懷忐忑。離家遠游,報喜不報憂早已成為游子的習慣。
然而,沒等我沉溺于傷感的情緒中太久,一踏進家門,5歲的弟弟鹿鹿就像一枚小炮彈一樣沖上來,樹袋熊似的掛在我身上,一口一個姐姐地喊。這小朋友,數月不見,我還以為他會把我忘了。
“你不在的時候,他天天問你什么時候回來呢。”媽媽拿來他的小日歷給我看,在每一個日期的下邊兒都有一個數字,那是在為我歸家做倒計時。
坦白地說,在鹿鹿出生之前,我對他的到來其實并沒有太多期待,畢竟我們相差了14歲。可他實在擁有太多愛的天賦,高中時我每次回家,小朋友都第一個跑出來用滿眼的歡喜迎接我,一如現在。
二
回到家,緊繃的狀態一松懈下來,身體里困住的“黑狗”又開始蠢蠢欲動。崩潰是悄無聲息的,當抑郁的潮水漲上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把自己蜷縮起來,像一團漂在水面上的藻類,任憑它漫過頭頂。

我蜷在沙發上,臉朝里,把傷口隱藏在洞穴的深處。
“姐姐你怎么啦?”
在房間里看動畫片的鹿鹿不知道什么時候跑了過來,拿小手撥拉我的頭,想讓我轉過去。他爬上沙發,跪坐在我身邊,伸手給我抹眼淚,抹得我滿臉都是。
見我沒有回應,他的小手一下一下地在我的背上輕輕地拍:“不哭,姐姐不哭。”
他還小的時候我就是這么哄他的—小小的男孩兒,睫毛上掛著兩滴淚珠,委屈巴巴地跑到我懷里來,我就輕輕地拍著他,給他唱歌。
現在居然輪到他哄我了。
聽著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唱著動畫片的主題曲,很神奇地,分明眼淚還在眼眶里,我竟然笑了。
洗了把臉,我抱著鹿鹿坐在沙發上:“姐姐剛剛是不是嚇到你了?”
小孩兒伸出兩只手捧著我的臉,很認真地說:“沒有嚇到,我心疼。”他滿臉嚴肅,“姐姐,誰讓你傷心了嗎?”
“沒有人讓我傷心,鹿鹿,姐姐只是被不好的心情困住了。”
鹿鹿眨眨眼睛,有些疑惑:“怎么會困住呢?”
我思考了一下,說:“姐姐就像從很高很高的地方摔下來,一直在往下掉。”
“你是蜘蛛俠嗎?可以從樓上飛下來!”
“不是蜘蛛俠,我太弱了。”我把腦袋輕輕靠在他肩上,“姐姐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螞蟻,一直在空中飄啊飄,還沒有落地。”
鹿鹿看著我想了好一會兒,我以為他會說些無厘頭的童言童語,可是他說:“那我做你的降落傘!”
那一瞬間,我的心被觸動了。一直以來,我孤身在無助的空氣里飄蕩,不知其所止。很多時候我甚至覺得,也許我這輩子都將在漩渦里孑然沉浮,沒有落地之時。
可現在,這個5歲的小朋友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說,他要做我的降落傘,就像在說,你可以依靠我。
那天晚上,媽媽領著穿著睡衣的鹿鹿站在我的房門口。
“這個黏人精,非要和姐姐一起睡。”
鹿鹿已經帶著他的枕頭爬上床,往我身邊一躺,把肩膀一聳:“姐姐靠著我!”
見我沒有行動,小朋友又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一臉的男子漢氣概。盛情難卻,我只好靠了過去。
依偎著他稚嫩的肩膀,恍惚間我好像回到幼時。我記得那時候最喜歡聽夜雨,在昏黃的燈光里,依在媽媽懷中,在連綿的雨聲中沉沉睡去。
那一夜是沒有雨的,可我難得地睡安穩了。
三
寒假結束后,我開始在家上網課,爸媽照常上班,剩下我和鹿鹿被困在家里,大眼瞪大眼。于是,他被迫品嘗了我炒煳的土豆絲和發苦的青椒肉絲,以及干硬的米飯。
最后,我倆愉快地達成一致:上泡面,加兩根香腸。
在泡面的氤氳水汽里,幸福感包裹了我。一個人在外頭,太多孤獨的時刻,有時寫論文到半夜,回到宿舍悄悄開一盞小燈,就在昏暗的燈光下吃點兒麥片果腹。黑暗靜悄悄地圍在四周,寂寞就無聲地漫上來。
我忽然發現,重要的原來是人。一個人即便享盡天下海味山珍,也不如和家人一塊兒吃一碗泡面。
吃著吃著,鹿鹿悶悶地說:“姐姐,要是你一直在家就好了。”
“嗯?”
“姐姐,告訴你一個秘密。”他湊上來,在我耳邊拉長了聲音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忽然感到,心里某一處空洞好像被填滿了棉花糖,柔軟、甜蜜得不像話。
四
白天通常只有我和鹿鹿在家。有一天鹿鹿忽然發起高燒,正是非常時期,我的神經瞬間緊張到了極點,一個人火急火燎地抱著他往醫院趕。
還沒到醫院,我就在出租車上掉了眼淚。鹿鹿燒得迷迷糊糊,還伸出燙乎乎的小手夠我的臉,想給我擦眼淚,他聲音嘶啞地說:“姐姐不哭。”
做檢查之前,我告訴鹿鹿不要怕,他還沖我笑:“你會保護我的!”
我愣了一下,想起來,那天下午,我接鹿鹿放學回家,鹿鹿蹦蹦跳跳地走在我前面,突然有兩只大狗躥到鹿鹿面前,沖著他厲聲吠叫,我的心臟狂跳。我從小就怕狗,可我至今都不知道當時究竟是哪里來的勇氣,幾乎是下意識地沖了上去,把鹿鹿擋在身后。狗抻著身子,我趕緊從路邊抄起一塊石頭,作勢要扔過去。兩只大狗這才后退幾步,離開了。
抱住鹿鹿,我的心臟幾乎要掙出胸膛:“鹿鹿不怕,沒事了……”我的聲音都在抖。
那天我告訴鹿鹿:“姐姐會一直保護你的。”
而我的鹿鹿,他一直毫無保留地信任著我,信任著這個脆弱甚至是怯懦的姐姐。
我死命把眼淚逼了回去,咬著牙想,我絕對不會讓他有事。
萬幸的是,一番檢查下來,鹿鹿只是普通感冒引起的發燒。我幾乎又要落淚。媽媽已經趕來陪床,我便拿著蜘蛛俠手辦和我小時候玩過的芭比娃娃,給他表演“蜘蛛俠救美”。鹿鹿咯咯地笑,酡色的小臉活泛起來。
看著他臉上明亮的笑容,我也無聲地笑起來。我的鹿鹿,我將盡我所能,讓你可以永遠笑得這樣開懷。
五
開學的日子還是到了。我離家的那天,小朋友幾乎是寸步不離我身邊,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我會很想很想姐姐的。”
我又怎么舍得他呢?坐上高鐵的時候我還在悵惘之中,打開背包,想拿手機給鹿鹿打個電話,露出來的卻是蜘蛛俠手辦的腦袋。
在手辦的后背上還貼著一張小紙條,歪歪扭扭地寫著“開心”,還畫了一個笑臉。
我把蜘蛛俠手辦揣進懷里,像擁抱鹿鹿那樣擁抱它。
開學后,抑郁的潮水仍不時漲起。有一天,在冰冷的情緒漩渦中,我發了一條宣泄式的“朋友圈”消息,內容只有一張全黑的圖片,就像籠罩著我的漫長黑夜。
點下發送,還沒過一分鐘,媽媽的視頻電話就打了過來,屏幕里,鹿鹿做著鬼臉湊上來:“姐姐!”
一旁,媽媽無奈地解釋:“鹿鹿說想你了,非要我現在打。”
“姐姐不要不開心,我明天給你買果凍。”
我失笑,果凍是他最愛的零食,現在卻要割愛于我了。我逗他:“你拿誰的錢給我買呀?”
“我的!”我本以為他要管媽媽要他的壓歲錢,誰知道小朋友吭哧吭哧從口袋里翻出兩張皺巴巴的五元鈔票,驕傲地在鏡頭前晃:“是我自己賺的!我幫林奶奶掃樓梯賺的!”
他揚起臉:“以后我每個星期都要去掃樓梯,這樣我就可以一直給你買果凍!”
我的眼睛忽然就酸澀起來。我的鹿鹿,這個和我相差14歲的小朋友,已經在不知不覺間,長成這樣一個溫暖的、可以依靠的小男子漢了。
他給我的明亮、坦率的愛,載我渡過這灰暗的潮水。
我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來,一個雨夜,我們一塊兒走路回家,他在前面一蹦一跳地踩著水,我視力不好,慢吞吞地跟在后面。走了兩步,鹿鹿忽然跑回來,把我的手拉起來,說:“姐姐,你拉著我走。”
隔著900多公里,我的身體漸漸回暖。
螞蟻不再飄在天上無法落地,一把小小的傘給了它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