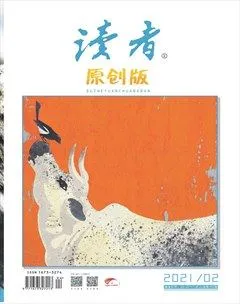父母的有求必應,孩子的欲哭無淚
葉傾城
平凡人的悲傷,像一滴流不出來的眼淚,是眼眶里永遠的澀與脹。
她從小是爺爺奶奶帶大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年見不到一次。小學三年級,父母買了房子安頓下來,才把她接到身邊。當母親第一次拉她手的時候,她全身都不自在,像被靜電刺痛一般。
那靜電一直在。她與父母,像超市貨架上兩盒綁在一起的豆腐,明明同根同源,卻被一層又一層的保鮮膜阻擋,不能同聲同氣。
她漸漸發現,父母對她有求必應。
四年級時,她是班上第一個擁有手機的人。用了半年,她又想要個iPad。她真的只開了一次口—心情是惴惴不安的,但iPad第二天就來了。
此后,她又發現,無論她怎么玩游戲,父母都不會說什么。到了初中、高中,她要的東西越來越多,無論是多么無理荒唐的—比如她有段時間聽了《風居住的街道》想買個二胡;她曾經想報個拳擊班;她癡迷于游戲,買過游戲皮膚……任何東西,她只要開口,父母全都二話不說答應。
同學們都羨慕她有有求必應的父母,但她并不快樂。她也希望父母能嚴厲、堅定地拒絕自己,像其他同學的家長一樣批評自己。
有時候很難受,她會更加放肆地要一堆東西,而當父母真給她買回來,她又想失聲大叫:“拿走,我要的不是這些!”
怎么說呢?有些傷的彌合需要時間,即使是看不見的傷。有些隔膜的打破需要契機,即使是父母和子女。
我得承認,她的故事會讓所有的父母落淚。她也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兒,但全世界每一位父母都明白,這一方面出于想要證明愛與被愛的急切,而另一方面是出于內疚。
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一些父母不得不去遠方謀生。當下與未來相沖突,要給孩子更好的明天,可能就得犧牲此刻能給孩子的陪伴。
這樣的內疚,讓他們想竭盡全力補償孩子,這種補償時常會過火,讓他們忘記了教育和愛應該并重,他們小心翼翼不想讓孩子受任何傷,想用物質和實際行動表達愛意。
而有些事孩子表面上忘了,卻可能烙進了他的潛意識。在孩子幼時,一定被父母拒絕過很多次—當孩子哇哇大哭希望父母留下來,他們頭也沒回;當孩子在黑夜被噩夢驚醒,身邊卻空無一人。拒絕是一個詛咒,孩子必須借用“永不被拒絕”來破解它們。所以,當孩子索取,多半索取的不是物質本身,而是“你們不會拒絕我”。
雙方的心結都同樣痛楚,但卡在這里不能解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孩子越不被拒絕,越知道這里面只是家長的補償心理,和自己想要的“愛”相去甚遠;家長給予越多,越懷疑自己已經永遠失去了孩子的愛,孩子只是把他們當提款機。
年輕的兒女,可以試試主動地去愛父母,以打開他們的心結。
試試想象一下父母多年奔忙、千里風霜的不容易,說一句:你們辛苦了;媽媽的手因為勞作而粗糙,給她買一支平價手霜吧;爸爸是否積攢了一肚子委屈無處訴說,問問他,告訴他:我永遠與你同在。
愛給人以力量,讓人知道:我不是苦海孤雛,我是一個強大的、有能力給予愛的人。我能大大方方表達我的感激,也能半開玩笑說出自己的心傷。
而我,甚至強大到,可以與我的父母共同組成愛的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