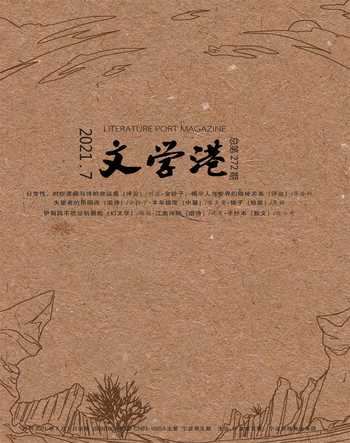藝術之于人生的況味
林馥娜

在這個信息和娛樂方式空前多元的時代,人們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填補閑暇的空隙,卻沒辦法用任何外在的事物代替精神的空虛,因為精神的充實倚仗的是能使心靈安妥的追求。而在生活中尋覓詩意,是使我們心靈豐盈的蹊徑,緣徑而達的,便是內心安寧的桃花源。好的電影是具有詩性的,它可以令人在觀影中體會到靈魂的景深。
當遠洋客輪在暴風雨的推來搡去中顛簸:當解開輪鎖的鋼琴前后左右滑動在船廳里的每個角落,1900卻揮灑自如地隨著鋼琴的傾斜和旋轉進行著他的演奏,仿佛整個大海是一個廣場,而輪船是一個旋轉舞臺般氣定神閑。鋼琴和他已融為一體,共同演繹著舒展流逸的華爾茲,那是藝術與生命共同達到的極致。甚至連無法站穩(wěn)而趴在鋼琴上的麥克斯也成為舞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個場景充滿著詩意的舒暢,令人過目不忘。這是意大利著名導演朱塞佩·托納托雷的電影《海上鋼琴師》中的一個場景,1900是其中的主人公,一個被遺棄在弗吉尼亞號頭等客艙,被客輪燒煤工收養(yǎng),而又沒有任何合法身份證明的人。
由于天賦異秉與心無旁騖,1900從一個孤兒成長為一個杰出的鋼琴師,他在上等艙給旅客們彈奏舞曲,也到下等艙為窮人們送去音樂的歡樂。作為一個具有藝術家敏感天性的旁觀者,他能從船上任何一個旅客的舉手投足中解讀出他們的生活狀況與內心世界。從權貴人物、謀殺者、投機者到平民走卒:從夜夜笙歌、衣香鬢影的上等艙到擁擠嘈雜、酸臭難聞的下等艙,客輪就是一個濃縮的社會,各個地方、各個階層的人帶著他們各自的氣味和烙印,絡繹不絕地在1900的眼前新舊交替。他雖足不下船,卻已洞知世上的一切。
他與知交麥克斯談起新奧爾良時的描述——三月,大霧像一把白劍,讓街上的人沒了腦袋。在杰克遜廣場上,只能看到一具具無頭尸體走來走去。撞到一起,他們就問候說“家里人都好嗎?”——何曾不是對行尸走肉的世相的一種深刻認識。
對于庸庸碌碌地追逐別人所認為的成功與快樂,永遠不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的世人,他說“你們岸上的人,總是在尋找不屬于你的四季如夏的世外桃源,我想這并不適合我”,對于有自我追求的人,過好一種適合自己的生活,這就夠了。面對發(fā)行唱片、巡回演出的名利誘惑,他沒有動搖,唯一一次下船的沖動是因為愛情。那天,他和船上的人一一告別,沿著下船梯往下走,走到一半時,他停了下來。如果說之前他對外面的世界因為麥克斯的勸說和對那份一見鐘情的愛情還有憧憬,那么此刻,他已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對于什么都不缺,道路千萬條,沒有盡頭的城市,他意識到那是他無法控制的生活,那種隨時會在熙熙攘攘中迷失自我而無法聽從內心追求的生活。
弗吉尼亞號就是他此心安處的故鄉(xiāng),因為心安,故能在洞悉一切之后葆有一顆童稚的善待一切之心。他的一生隨著弗吉尼亞號從客輪到因戰(zhàn)爭爆發(fā)而成為醫(yī)用船,直至最后廢棄并炸毀,他都用他的琴音給旅客、給傷員、給靈魂帶去安撫和寧靜。甚至面對上船來向他挑戰(zhàn)的對手,他也并無敵對之心。當他選擇與輪船一起灰飛煙滅時,他的內心是安寧的,甚至還給來勸他下船的唯一知己麥克斯講了個笑話。1900走了,在世俗的意義上,他甚至沒有存在過,但他的音樂和故事留了下來,留在懂他的人心中。正如凡·高死了,他的藝術卻流傳了下來。
將藝術融入生命者,必擁有一顆自絕于平庸的孤獨之心。比如凡·高、高更……比如就在我們身邊的女詩人安琪。為了追尋語言藝術的極地之境,安琪不惜北漂十幾年,舍棄了世俗常態(tài)的安好生活。雖然最終安琪還是回歸家庭生活的常態(tài),但這個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同一個不懂她的人勉強過下去與同一個懂她的人身心相伴是有天壤之別的。心靈的歸宿才是真正的歸宿。當他(她)在藝術中體味到深刻的愉悅之后,浮淺的世俗之歡、身外之利已激不起內心的波瀾。正如安琪的詩《我本質是個孤絕的人》所言:“畫地為牢,或自甘困頓。我本質是個/孤絕的人我自絕于/元旦五一,自絕于/中秋國慶,自絕于/除夕元宵。一切與歡樂有關/的事物全部與我無關我自絕/于歡樂并獨自享用/這份自絕——∥我的孤獨之心/我秘密養(yǎng)育它已有40年。”他們耽于孤獨,乃至刻意保持自己的孤獨,自絕于庸常的侵襲,這是一種純粹靈魂所擁有的自由。
人們往往在做了某些錯事之后,悔恨地說:早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就不會做了。但是我們如何能夠“早知道”呢?電影《恐怖游輪》里的杰西就因為獨自撫養(yǎng)有孤獨癥的孩子,生活壓力過大,總是為一些小事打罵兒子,乃至于在焦躁中造成車禍,與兒子雙雙喪命。杰西的靈魂不愿接受這個事實,一心想恢復失去的愛,彌補自己曾經(jīng)帶給兒子的傷害,因而一再選擇進入三維時空的殘酷循環(huán)中,一次次地陷入同樣的輪回中,唯一支撐著她走下去的是她對兒子那絕望的愛。雖然這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藝術的力量就在于它能給我們以各種各樣的啟迪。在生活中,我們也會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像杰西一樣產生焦慮,也不乏無意之中傷害親人的實例。我們不能擁有先知的預感能力,但我們還是可以盡量避免,我甚至認為,如果杰西有寫日記的習慣,她將會在記錄的過程中反思自己,發(fā)現(xiàn)自己的問題,生活的辛酸便不至于蒙蔽她的心靈。
由此而聯(lián)想起詩人杜朗朗的日記體詩歌集《傾聽花開的祝福》,詩集的獨特之處是作者在每一首詩的后面都做了自注,把觸發(fā)詩意的來由和生活線索貫穿其中,有家史的性質,也有為心靈立檔的意味。他的詩歌有比較分明的兩條線,一是情義: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鄉(xiāng)情到親情、從分離到聚合,無不記錄著他與故鄉(xiāng)、父母、姊妹、妻兒的濃濃深情:二是勵志:從立志改變命運到奮斗拼搏、從遭遇磨難到堅定志向,“堅持使命在上命運在下/堅持青春在左奮斗在右”(《我并不拒絕生活的困苦》)。他在書寫中反思、在反思中領悟,從而在生活中更堅定地前進。我固執(zhí)地一再想到杰西的悲哀,如果她能夠靜下心來想一想,哪怕只是記錄一下自己和孩子的日常,也許生活的樂趣就來到了她的面前。同時,杜朗朗的詩也讓我們看到——珍惜現(xiàn)有的一切,生活的路會走得更加踏實。
杜朗朗寫詩的指導思想,也即審美理想是:“以記日記的思路寫詩,寫下生活、情感、處世的點點滴滴,記錄真實的情形,抒發(fā)真實的情感。”故即便在結集后他陸續(xù)抒寫的其他詩歌中,也都具有相同的品性。這種注重真實記錄的方式使他的詩歌呈現(xiàn)了“真誠”的高貴品質,但同時也難免因為側重“建檔”這種求實的寫作意圖而輕慢了“技藝”元素,忽略了詩是語言的藝術。詩歌不同于報告文學,如果過于注重真實過程的描畫,而不注重凝練與留白,則會使本來可以濃郁飽滿的詩意被過多的文字羅列所稀釋。在我們將心中的詩意付諸文本的時候,不妨想一想,是否還存在另一種或另幾種的表達方式,可以在準確表達主題的情況下,使文本更趨于“詩”這種體裁所應有的簡潔和飽滿,而不至于讀到最后倒是涉了詩氣,可惜了一個好題材和心中的詩意。竊以為,藝術評論的最佳狀態(tài)是能通過作品的橋梁使作者與評者之間達成一種創(chuàng)作交流,起到互為觸發(fā)、促進的作用。而欣賞不同的藝術,會給我們帶來多維的經(jīng)驗與視角,從而在寫作與生活中避免走“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的彎路。
電影就是人生之濃縮,人生是電影的肥皂劇。《海上鋼琴師》以1900這個角色為串線,把肥皂劇一樣的各種真實人生,包括非常態(tài)的戰(zhàn)爭,由各種各樣的旅客和線索集中呈現(xiàn)在輪船這個舞臺上。而《恐怖游輪》通過杰西一次次返場的歷程來告訴我們,人生沒法倒帶重來,腳下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選擇的結果。這兩部同樣以輪船作為敘事舞臺的電影,讓我在折服于藝術的感人魅力之余,不由品咂起藝術之于人生的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