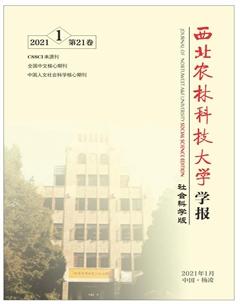風險感知、制度信任與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摘 要: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受內在風險感知和外部制度環境的雙重影響。基于四川瀘縣和寧夏平羅803戶農戶的調研數據,實證研究了風險感知、制度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風險感知抑制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且存在區位異質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為信任)促進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且能減輕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負面影響,從邊際效應看,行政行為信任的緩解作用強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審視宅基地區位級差效應,建立差別化的宅地基退出權益保障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注重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通過改善個體對政府行政的情感態度以提高人們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議。
關鍵詞:風險感知;制度信任;宅基地退出;行政理念信任;行政行為信任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民大量涌入城市,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18年的59.58%,農村正在經歷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歷史性變革[1]。然而,進城農民由于未能在住房、教育、養老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而無法真正融入城鎮,他們留在農村的住房幾乎長期處于閑置狀態[2],導致農村空心化和農村社會空殼化加劇。《農村綠皮書》指出:截至2018年,中國農村宅基地閑置率達10.7%。農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與優化直接影響著我國城鄉土地資源配置、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等[3],而農戶是否選擇退出宅基地受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響[4]。內部因素方面,農村宅基地承擔生產、生活及資產增值等多種功能[5],農戶退出宅基地面臨農村土地處置、城鎮住房購置及城鎮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未知變化,使得農戶在宅基地退出中存在不同的風險感知。同時,由于農村并非均質空間,不同區位宅基地功能差異巨大[6],使得不同區位農戶在宅基地退出中的風險感知也存在差異性。外部因素方面,盡管國家先后出臺了大量宅基地退出文件,并先后在33個縣(市、區)試點,但截至2018年6月,試點區共騰退零星、閑置宅基地9.7萬戶共計7.2萬畝,退出比例為0.63%。宅基地退出比例偏低,其原因包括農戶資源稟賦特征[7]、宅基地特征[5]、市場特征[8]等多個方面,但也與當前宅基地制度改革仍有較大彈性空間以及農戶對宅基地退出制度期望值偏高密切相關,進而造成農戶對現有宅基地制度改革產生不信任,可見,制度信任影響農戶的宅基地退出行為。那么,風險感知、制度信任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影響機理是什么?影響程度如何?制度信任是否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起調節作用?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促進農戶宅基地退出、盤活農村閑置宅基地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近年來,隨著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穩慎推進,關于農戶宅基地退出的研究日益增長,研究的著力點主要集中在影響因素、機制設計及案例分析[1,9]等方面。在影響因素的探究中,學者們逐漸關注到農戶宅基地退出的風險問題。已有研究指出,農戶對退出宅基地有著生活成本、生產收入、環境狀況等方面的風險認知與預期[10],不確定性成為阻礙農戶退出宅基地的關鍵因素之一,對此,學者們試圖通過提高農戶自身的抗風險能力[11]、加強社會網絡的非正式保險作用[12]等途徑來弱化風險,促進農戶退出宅基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主要靠政府推動,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在退出范圍受到嚴格限制的條件下,市場在農戶宅基地退出過程中發揮作用非常有限,退出后農戶獲得的相應補償與其心理預期差距較大,進而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決策。基于此,本文擬將風險感知和制度信任同時納入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分析框架,利用四川瀘縣和寧夏平羅803戶農戶的調研數據,實證檢驗風險感知、制度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風險感知與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Slovic將人們依靠直覺對未知事物進行風險判斷和評估的過程定義為“風險感知”[13]。風險感知常伴隨決策的產生[4],因此農戶對退出宅基地的風險感知直接影響農戶的宅基地退出決策。農戶對宅基地退出的風險感知依托于宅基地承擔的功能,已有研究指出,農村宅基地承擔著居者有其屋的居住功能、保障農業收益的生產功能、應付市場風險的社會保障功能以及增加財產性收入的資產功能[14]。農戶退出宅基地意味著這些功能權益的喪失。但由于農村土地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農戶對宅基地的資產功能感知較弱,因此,本文將農戶退出宅基地面臨的風險感知劃分為“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具體而言,在居住方面,農戶退出宅基地后沒有了住房以及可建造住房的地,農戶要面臨住房搬遷的問題[5],而現有宅基地退出補償標準較低,不足以彌補退宅農戶的搬遷成本、新房建造和購置成本[15],進而抑制農戶做出宅基地退出的行為。在生產方面,農村土地系統是由農地、宅基地等多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宅基地服務于農業生產。宅基地退出實現的是人的流動,而農地具有不可移動性,人地分離,田園經濟成本增加,農地處置機制與農地功能價值的不對等致使農戶不愿退出農地承包權,進而抑制了農戶的宅基地退出行為。在保障方面,進城定居的農戶雖然在空間位置上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但卻未能完全實現農民向市民的身份轉變,他們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很難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始終擔心有朝一日在城里無法持續生活而可能會再次退居鄉村,進而抑制了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宅基地的功能價值因區位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根據區位理論和宅基地的地理分布特征,并借鑒已有研究[6],本文將農村宅基地劃分為城中村宅基地、郊區村宅基地和純農區村宅基地。其中,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建成區范圍內仍然實行村民自治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村莊,受城市化的強烈影響,城中村耕地已基本消失,但由于經濟地理區位好,農戶擁有較多的非農就業機會,非農收入占比高,因而農戶對退宅后的各類風險感知相對弱化;郊區村是指毗鄰城市的近郊農村,受城鎮輻射相對較強,農戶非農就業較為方便,對農業生產依賴較小,宅基地的農業生產輔助功能弱化;純農區村是指遠離城鎮,農戶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村落,由于純農區經濟地理位置較差,宅地基仍然用于滿足農戶日常生產生活需要,因而農戶對退宅后的各類風險感知較強。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1:居住風險感知負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H2:生產風險感知負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H3:保障風險感知負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H4: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存在區位異質性。
(二)制度信任與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制度通常可以理解為權威機構制定和頒布的正式規范或條款,而制度的存在依賴于制定制度的人或機構,因此制度信任可以理解為個體對相應政府機構公平執政的合理期待[16]。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產生是基于農戶利益與政府執政合作的結果,這種合作依賴于準確的信息和可靠的執行,本質上是個體對政府的主觀情感及對政府的行政反應[17],因此,借鑒張郁等的研究[18],將制度信任劃分為政府行政理念信任和政府行政行為信任兩個維度。行政理念信任側重個體對政府機構日常公共決策中理念和價值取向的認可度,行政行為信任則側重在公共決策執行時個體對政府對待群眾意見的行為方式的信任度。具體而言,中國社會長期處于“政府依賴型”狀態,宅基地退出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其順利進行離不開政府的助推作用,要求政府不僅要在執政理念上以公眾利益為優先考慮要素,充分考慮退宅農戶的權益補償,在執政行為上更應該做到信息透明化、公眾參與化。農戶在參與中積累信任經驗,進而通過制度環境形成穩定的情感態度和行為傾向。依據社會交換理論,在此印象的驅動之下,農戶會更多地從政府的角度思考問題,政府的付出會得到農戶的積極響應,積極配合政府工作[19],即農戶對政府行政理念和行政行為信任度越高,越容易配合政府完成宅基地退出工作。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5:制度信任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H6:行政理念信任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H7:行政行為信任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三)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
足夠的制度信任存量能促使公眾對政府及政策存在較強的心理認同而帶動其行動積極性[20],因此,制度信任除直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外,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調節作用。如前文所述,由于農村宅基地具有多種功能,農戶退出宅基地意味著這些功能權益的消失,因而退宅農戶存在各個層面的風險感知,究其根本,在于宅基地退出政策實施處于初始階段,相關政策不完善。Aven和Renn在對民眾災難應對行為策略研究中發現,民眾對政府等官方機構的信任能夠彌補其負面的風險感知,使其采取積極的應對行為[21]。對于宅基地退出行為而言,無論農戶存在哪些層面的風險感知,無論對這些風險感知程度如何,只要政府始終以農民利益為主,盡一切可能為退宅農戶爭取權益補償,并在服務過程中能夠做到公開、公正、公平,農戶對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政行為就會維持在一個較高的信任水平,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行為的不利影響就可能會降低。而現實中,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為信任對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緩解強度可能存在差異,這是因為:“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直以來是黨和政府執政的根本宗旨,農戶在行政理念上是充分信任政府的,但具體到事件上,農戶對政府的信任更多來自政府的實際行動。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說:
H8:制度信任對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具有緩解作用;
H9:不同維度制度信任對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緩解強度存在差異。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9年9-10月對四川瀘縣、寧夏平羅農戶開展的抽樣調查。四川瀘縣是西部丘陵區農業大縣,全縣共有26.88萬戶1.62萬公頃宅基地,其中閑置宅基地8.2萬戶0.49萬公頃。目前正面臨村落衰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管理不善等問題。自2015年瀘縣被列入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縣以來,政府依托改革政策,鼓勵農戶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截至2019年,全縣共退出宅基地2.86萬戶0.12萬公頃。寧夏平羅位于銀川平原北部,村莊布局分散,空心化現象嚴重,村莊房屋平均閑置率42%,部分村莊高達70%以上。自2015年平羅縣被列入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縣以來,抓住改革機遇,積極引導農戶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截至2019年,全縣累計清理騰退閑置建設用地790宗87公頃。因此,本文選取四川瀘縣、寧夏平羅兩個地貌環境不同的試點縣作為研究區域,分析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考慮宅基地的區位不同可能導致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存在差異,課題組按照城中村、郊區村和純農區村隨機選擇樣本鎮,并采用分層逐級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式選取樣本農戶。本次調研共發放問卷812份,獲取有效樣本803份,問卷有效率為98.89%。其中城中村樣本共197個,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34%,包括四川瀘縣玉蟾村等村莊的100個農戶(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30%)和寧夏平羅星火村等村莊的97個農戶(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34%);郊區村樣本共278個,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55%,包括四川瀘縣新聯村等村莊的189個農戶(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60%)和寧夏平羅周城村等村莊的89個農戶(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46%);純農區村樣本共328個,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43%,包括四川瀘縣馬溪河村等村莊的214個農戶(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43%)和寧夏平羅北長渠村等村莊的114個農戶(農戶宅基地退出率為33%)。
(二)變量選擇
1.因變量。本文因變量為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由問卷題項“您家宅基地是否退出”直接獲取相關數據,答案有“是=1;否=0”兩種情況。
2.核心自變量。本文核心自變量包括農戶對宅基地退出的風險感知和制度信任。基于上文理論假設,本文對農戶風險感知的測度主要從農戶對退出宅基地后在居住、生產和保障上的預期及不確定性的評價展開。對農戶制度信任變量的測度主要從農戶對政府機構公平執政的信任程度展開,運用SPSS19.0軟件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兩個公因子,公因子1命名為行政理念信任,公因子2命名為行政行為信任。最終,根據各因子得分及其方差貢獻率,通過公式“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45.761%+行政行為信任×35.861%)/81.622%”計算農戶制度信任的綜合指標,具體結果見表1。
3.控制變量。借鑒相關研究[4,10],本文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戶主特征、家庭特征、宅基地特征、宅基地區位特征及地區虛擬變量。戶主特征選取戶主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變量;家庭特征選取耕地面積、家庭年收入(取對數)、非農收入占比等變量;宅基地特征選取宅基地距中心城鎮的距離、宅基地新舊程度等變量;宅基地的區位特征以純農區村為參照,對比城中村、郊區村、純農區村農戶退出宅基地的差異。各變量定義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2。
(三)模型設定
1.Probit模型。農戶是否退出宅基地屬于典型的二元選擇問題,因此,本文選用二元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yi為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即農戶是否退出宅基地;RR為農戶風險感知變量;TP為制度信任變量;RR×TP為農戶風險感知與制度信任的交互項,以檢驗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Xij為第i個農戶的第j個控制變量;β、γ為待估系數;εi為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的擾動項。
2.分組回歸模型。為進一步檢驗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本文借鑒Aiken等的研究,將制度信任分為高制度信任和低制度信任兩組分別進行回歸,其中低制度信任是指其均值減去一個標準差,高制度信任是指其均值加上一個標準差[22]。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風險感知與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表3中,基準方程回歸結果顯示,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及保障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農戶對宅基地退出后的住房問題、農地經濟功能的實現問題以及未來城鎮生活的社會保障問題的風險感知越高,越不利于農戶做出退出農村宅基地的決策,H1、H2、H3得到驗證;此外,調節效應方程3~5估計結果顯示,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負向顯著影響,與基準方程估計結果一致,表明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負向影響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宅基地區位不同,宅基地的功能會存在顯著差異,這會直接導致農戶對風險的敏感度和退出宅基地的行為響應不同[23]。因此,本文分別在城中村、郊區村和純農區村樣本下進一步分析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見表4),在城中村居住、生產、保障等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影響均不顯著,可能的原因為城中村受城市化的影響最為強烈,無論在地理區位還是經濟區位均占優勢,宅基地的居住、生產和保障功能相對弱化。在郊區村,居住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從邊際效應系數看,保障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抑制作用大于居住風險感知,可能的原因:一方面,近郊村毗鄰城市,農戶以非農就業為主,對農業生產的依賴性小,因而宅基地的生產功能相對弱化;另一方面,郊區村農戶收入狀況較好,比起遷移成本問題,他們更關心農民轉市民的待遇問題。在純農區村,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從邊際效應系數看,各類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抑制作用表現為保障風險感知gt;生產風險感知gt;居住風險感知,可能的原因為純農區村遠離城鎮,伴隨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純農區人口老齡化嚴重,在相關政策不明晰的情況下,退出宅基地后的養老、醫療等保障問題是留守老人首要關心的問題;另外,相關研究表明,區位越偏,老年群體依靠自己勞作獲取收入的比例越高[24],因此純農區宅基地除居住功能外,服務田園經濟的生產功能占重要地位,H4得以驗證。
(二)制度信任與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
表3中的基準方程1回歸結果顯示,制度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農戶的制度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農戶做出退出農村宅基地的決策,H5得到驗證。基準方程2回歸結果顯示,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為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農戶對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政行為信任度越高,越有利于農戶做出退出農村宅基地的決策,H6、H7得到驗證。此外,表5中方程7、9、11估計結果顯示,行政理念信任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方程6、8、10估計結果顯示,行政行為信任顯著正向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與基準方程估計結果一致,表明制度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正向影響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三)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
表3中,方程3~5估計結果顯示,居住風險感知與制度信任的交互項、生產風險感知與制度信任的交互項以及保障風險感知與制度信任的交互項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制度信任能減輕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負面影響。
分維度將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分析(見表5),方程6、8、10估計結果顯示,行政理念信任與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的交互項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行政理念信任能減輕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負面影響;方程7、9、11估計結果顯示,行政行為信任與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的交互項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行政行為信任能減輕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負面影響。以上結果證實不同維度的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均具有調節作用,也進一步表明制度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正向影響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為更為直觀地說明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繪制制度信任調節效應圖(見圖1)。圖1顯示,從縱向看,無論是行政理念信任還是行政行為信任,在較高的制度信任條件下,三種風險感知與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關系的回歸線斜率均較大,表明制度信任度高的農戶風險感知對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抑制作用越弱,制度信任度低的農戶風險感知對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抑制作用越強;從橫向看,不同層面風險感知下,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為信任的斜率值存在差異,即不同維度制度信任對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緩解強度存在差異,H9初步得到驗證。
(四)控制變量的影響
家庭特征中,家庭年收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農戶家庭年收入越高,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宅基地退出補償標準低,難以對家庭年收入高的農戶形成吸引力;另一方面,對于家庭年收入高的農戶來說,物質生活滿足的情況下更注重精神層面的享受,鄉愁情懷使得他們對農村有著較強的情感依戀。宅基地特征中,宅基地距中心城鎮的距離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宅基地價值遵循空間分布上的距離衰減法則,宅基地距中心城鎮的距離越遠,農戶退出宅基地可能性就越大;房屋新舊程度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房屋越新,農戶的折舊成本越高,農戶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宅基地區位特征中,與純農區相比,郊區村農戶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更大,這與郊區村在自然環境、地理區位、經濟區位等資源稟賦上的比較優勢密不可分。
(五)穩健性檢驗
由表3模型估計結果及圖1調節效應圖可知,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起到調節作用,且不同維度制度信任對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緩解強度存在差異,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分組回歸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做法為:借鑒Aiken等的研究,將行政理念信任分為低行政理念信任(低于均值一個標準差)和高行政理念信任(高于均值一個標準差),將行政行為信任分為低行政行為信任(低于均值一個標準差)和高行政行為信任(高于均值一個標準差),對比不同程度制度信任下,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影響的差異。表6結果顯示,相比高制度信任組,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不利影響在低制度信任組中更大,表明制度信任確實能減輕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的負面影響。同時,從邊際效應絕對值差值上看,行政行為信任組的差值高于行政理念信任組,表明行政行為信任的緩解作用強于行政理念信任。以上結論證實前述回歸結果是穩健的,且H9得以驗證。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四川瀘縣和寧夏平羅803戶農戶的調研數據,實證檢驗了風險感知、制度信任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風險感知影響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中的調節作用。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風險感知抑制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且存在區位異質性。對城中村而言,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影響不明顯;對郊區村而言,抑制農戶退出宅基地的風險感知主要是居住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且從邊際效應看,保障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抑制作用大于居住風險感知;對純農區村而言,抑制農戶退出宅基地的風險感知主要是居住風險感知、生產風險感知和保障風險感知,且從邊際效應看,各類風險感知對農戶退出宅基地的抑制作用表現為保障風險感知gt;生產風險感知gt;居住風險感知。第二,制度信任能夠促進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且無論是行政理念信任還是行政行為信任的提升均能促使農戶退出宅基地。第三,制度信任能減輕風險感知對農戶宅基地退出行為的負面影響,且從邊際效應上看,行政行為信任的緩解作用強于行政理念信任。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審視宅基地區位級差效應,建立差別化的宅地基退出權益保障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切實回應農戶的差異化政策需求,弱化退宅農戶的風險感知。城中村宅基地區位優勢明顯,農戶各類風險感知相對弱化,應充分發揮政策信息宣傳和個人示范效應,實現農民主觀能動性與政策工具的雙向互動;郊區村和純農區村應重點解決的是退宅進城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建議廢除農民工身份,所有的產業工人都享有工作的全部權益,包括社會保障權益,對于老年農民,可借鑒國外經驗,實行“職業農民退休制度”,消除退宅農民的后顧之憂。第二,提升農戶制度信任水平。注重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規范宅基地退出政策制定、運行過程中的行政程序及監督機制,加強政策實施信息透明度,充分保障農民關于宅基地退出政策實施的話語權與參與感,進而通過改善個體對政府行政的情感態度以提高人們的制度信任水平。
參考文獻:
[1] 劉守英,熊雪鋒.經濟結構變革、村莊轉型與宅基地制度變遷——四川省瀘縣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18(6):2-20.
[2] 張勇.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內在邏輯、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基于農民市民化與鄉村振興協同視角[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118-127.
[3] 范輝,李曉珍,余向洋,等.基于交互決定論的農村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以河南省為例[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0(2):22-28.
[4] 劉峰,張飛.江蘇省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20(1):250-252.
[5] 胡銀根,張曼,魏西云,等.農村宅基地退出的補償測算——以商丘市農村地區為例[J].中國土地科學,2013(3):29-35.
[6] 楊麗霞,李勝男,苑韶峰,等.宅基地多功能識別及其空間分異研究——基于嘉興、義烏、泰順的典型村域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19(2):49-56.
[7] 韓文龍,劉璐.權屬意識、資源稟賦與宅基地退出意愿[J].農業經濟問題,2020(3):31-39.
[8] 楊玉珍.農戶閑置宅基地退出的影響因素及政策銜接——行為經濟學視角[J].經濟地理,2015(7):140-147.
[9] 李榮耀,葉興慶.退出與流轉:農民宅基地處置選擇及影響因素[J].農村經濟,2019(4):10-20.
[10] 新華,陸思璇.風險認知、抗險能力與農戶宅基地退出[J].資源科學,2018(4):698-706.
[11] 王兆林,楊慶媛,李斌.農戶農村土地退出風險認知及其影響因素分析:重慶的實證[J].中國土地科學,2015(7):81-88.
[12] MUNSHI K,ROSENZWEIG M.Why Is Mobility in India so Low? Social Insurance, Inequality and Growth[Z].Nber Working Papers,2009.
[13] SLOVIC P.The Perception of Risk[J].Science,1987(4799):280-285.
[14] 龔宏齡.農戶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基于宅基地不同持有情況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7(11):89-99.
[15] 孟祥仲,辛寶海.明晰使用產權:解決農村宅基地荒廢問題的途徑選擇[J].農村經濟,2006(10):15-17.
[16] 魏東,劉鴻淵,孫玉平.制度信任對農民參與環境治理決策意愿影響研究[J].軟科學,2019(7):111-115.
[17] 張冰超,史達,劉睿寧.風險感知、政府信任與在地居民參與特色小鎮建設意愿關系的研究[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103-111.
[18] 張郁.公眾風險感知、政府信任與環境類鄰避設施沖突參與意向[J].行政論壇,2019(4):122-128.
[19] CROPANZANO R.Social Exchange Theory: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6):874-900.
[20] MUSSO J A,WEARE C.From Participatory Reform to Social Capital:Micromotives and the Macrostructure of Civil Society Network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5(1):150-164.
[21] AVEN T,RENN O .On Risk Defined as An Event Where the Outcome is Uncertain[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09(1):1-11.
[22] AIKEN L S ,WEST S G.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M].Lonclon:Sage,1991:9-27
[23] 吳郁玲,石匯,王梅,等.農村異質性資源稟賦、宅基地使用權確權與農戶宅基地流轉:理論與來自湖北省的經驗[J].中國農村經濟,2018(5):52-67.
[24] 趙渺希,王慧芹,劉明欣.集體土地養老支持的區位差異及政策啟示——基于廣州和佛山地區的實證[J].農業經濟問題,2018(3):1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