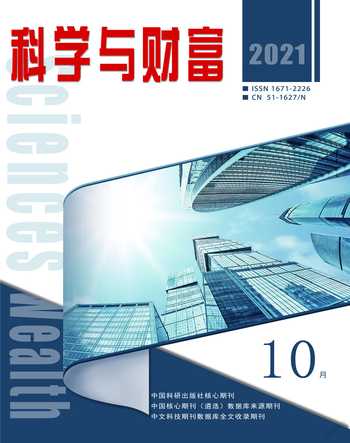微議手語的一個新的屬性
彭正星
摘 要:構成手語的兩大部分之一——手控信息,不僅僅是五個屬性(即手形、動作、朝向、位置、運動),也需要一個新的屬性作為補充性元素來組成這一門語言——它是“速度”。為什么要有速度這個屬性呢?因為一個聾人的理解準確度,能夠映射出手語本身的速度。本文以手語的速度為基本點,以聾人群體為特定對象,展開相關的理論論證與調查論證兩種方法,支撐速度作為手語的一個新的屬性,并探索其相關問題及其一般性答案。
關鍵詞:速度;手語;聾人;屬性體系
1引言
通過細致觀察、調查研究等方法,發現了構成手語的屬性體系的確需要一個新的屬性:速度,以完善手語這門語言。
如果拋開速度的這一屬性,手語的屬性構成體系貌似不完整,則不能更好地綜合調研聾人群體的手語有關的一系列問題。假若手語的屬性體系接納速度這個不可或缺的新支點,那么手語研究者就能以一種新的視角去研究手語這門語言,甚至還可能會以速度作為特定調查對象去研究聾人對自己的母語的認知及其能力情況(這一調查法并非片面,即在綜合全面的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對象性調研),從中或許會發現新的問題,比如聾人之間語言溝通上的“互知”、聾人的認知思維結構(亦或是理解角度)、手語速度對聾人思維速度的影響及其程度等。
2手語特點
手語速度大小對聾人理解的影響主要有兩種:
有些聾人手語水平極高,手語速度也很大,能夠看得懂其他聾人打手語所表達的意思,不管他/她手語有多快(這種速度的前提必須是系統的、規范的)。也有些聾人手語水平不太高,手語速度也不大,一般來說很難看懂聾人打得快的手語,造成不能理解或者不全理解其意思的現象。
當然還有其它(亦或是個別的)情形如下:
2.1手語打得又好又快的聾人,也有看不懂聾人同學或者聽人老師打的手語,特別是不全看懂漢語手語的這一種方式。比如,習慣并非常熟悉自然手語的聾人碰到傾向于打漢語手語且速度大的聾人,雙方在溝通交流過程中肯定存在互相看不懂對方所表達的意思,哪怕對方把手語速度調小也還有這樣的情況。
2.2雖然某一聾人手語打得不怎么樣,但他/她卻能夠看得懂打得快的手語(指自然手語或者漢語手語,又或者都能看懂兩種手語)。例如,聾人A和聾人B,前者的自然手語打得很好也快,后者漢語手語打得很好但也能看得懂自然手語。A和B在溝通交流過程中,A非常熟悉地打起自然手語,打得很快而流暢,而B在一旁點頭稱是,稍微插話以應答——這個情況說明了一個客觀存在性:有些聾人自己打自然手語并不怎么樣,不過可以看懂他人的自然手語。
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復雜的特點,如:某一類手語不怎么樣,也看不懂這類手語;自己會的某一類手語,也有不全看明白另一類手語;會好幾類手語的,不代表能明白其他聾人的手語(主要是因為每一個地區的手語有自己的特色);等等。但是無論手語是什么樣子,都存在著:速度的屬性。
總的來說,手語作為聾人之間交流溝通的互動性媒介,其本身本來內含著一個新的屬性:速度,這個屬性對聾人群體或者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交際溝通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作用,即會影響聾人所進行的互動信息的理解準確度。
3觀察推理
很多聾人在使用手語的時候,總習慣于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把握著手語的速度。“就像”、“比如”、“好吧”、“還有”、“不過”、“但是”、“如果”等雙音節都體現了手語的速度屬性,具體來講是與其相對應的手語的速度要大一些。這和聽人亦是如此,說話都有停頓的普遍性語言現象。所以這也是速度的一種體現。不管是手語的還是口語的都有速度屬性的語言恒性。
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現象:一個聾人打某一類型手語(譬如純自然手語、中國手語、漢語手勢等),而且速度較大的時候,另外一個聾人在“聽”的過程之中碰到不理解或者看不清的部分手語時,眼睛則自然會看向他/她的手語(手勢)本身,欲求理解對方的意思。所以說影響聾人理解的因素里面,同樣地包括了手語的速度這一屬性。
例如,名為“黑川手說”的公眾號發布的很多視頻中,這位聾人主播手語打得流暢無阻而輕快。每次打手語時,他都會調整不同的手語速度來打,打得順暢無阻(也有沒有停頓而連貫的時候)。某一條視頻中他和印度聾友(在中國生活)交流過程中,他的眼睛并沒有發生看向聾友手語的上述情況,而是自如地看著聾友,無論聾友打手語是快的還是慢的。這是手語速度和思維速度之間聯系著的“近同步性”的一種體現。要怎么樣才可以自如地不靠看部分手語而能夠做到整體地看著聾人+手語的全貌以獲取信息?這個問題本來因人而異,因為每一個聾人成長環境、生活經驗、理解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
這個情況印證了一個事實:手語速度大還是小的,都會直接地或者間接地影響著聾人思維速度,即聾人對手語速度存在著自己的感知思維和理解視角。這跟聽人口語速度同樣是一個道理,口語速度有大小之分,不同程度地影響聽人的思維速度。
4調查驗證
為了進一步證明手語存在速度的屬性而采訪數名聾人,了解其在手語快、慢的主要兩種不同情況下的理解情況,并進行了相應的實驗。他們一致認為,手語速度不大不小是能夠看懂手勢表達的意思的重要條件。有個別人說手語太慢是會影響理解的,因為認知是需要一定速度(一般以毫秒為單位)的,即合適的思維速度。這個同樣地證明了合適的手語速度是聾人準確理解意思的一個重要條件。
一名志愿者(以下簡稱甲方)和一名志愿者(以下簡稱乙方)共同參與手語速度對理解的影響程度的實驗。經調查發現,不管打文法手語還是打自然手語,且在不知道故事內容的情況下,都有甲方對于乙方的手語的不同理解的狀況。從這場實驗當中可以發現,手語有速度的屬性,而且是客觀存在的。
針對不同對象(特指本次實驗的甲方)思維速度在不同手語速度影響的情況下分為兩場實驗,如下:
4.1甲方的手語水平一般,理解水平不高,乙方據此按從大到小的手語速度來跟他介紹一則小故事:《農夫的故事》。
4.1.1在本次實驗中乙方先將手語速度調整為大的時候,甲方臉上顯出茫然表情,隨即把雙手置于胸前交叉,干巴巴地看著乙方。結果,這位甲方表示乙方手語打得很快,不能明白其表達的意思,很難理解故事主要的內容。
4.1.2乙方適當調小速度(即不快不慢),還是按照同一故事復述。正是這種合適的速度,令甲方表示愿意繼續看打手語者。結果是其稱可以看懂乙方手勢的意思,因這得益于手語速度處于中間值(注:該中間值未作進一步的調查)。
4.1.3乙方再次調小打手語的速度。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了:在乙方手語打得慢的過程中,甲方眉頭稍微緊鎖,過程中發生從忍俊不禁逐漸至不耐煩的心理狀態變化。乙方因為打手語之慢,提出的問題好像沙子般的散開不齊,影響了甲方的思維速度。到了最后,后者直接提出:“別這樣打了,我能明白故事,但這太慢了,我不想看了……”
4.2甲方和乙方互換身份。甲方的手語水平既高,理解水平也很高,乙方據此按從大到小的手語速度來跟他介紹一則小故事:《小豬搬西瓜》。
4.2.1乙方根據該寓言故事內容來打手語,速度很大,甲方同樣能看得懂大部分手語,也能大致地清楚故事的主要內容。
4.2.2乙方手語速度調整至適當程度跟甲方復述故事。乙方的這種速度明顯比第一場實驗(指4.1.2)乙方打的手語慢一些,但整體上看還是徘徊于正常速度的區位之中(正常速度一般為150字左右/min,聽人語速一般為200字左右/min。此參數為估算)。結果是,甲方知道故事內容的信息數量比4.1.2的結果還多一些。
4.2.3甲方心里有些別扭,不習慣乙方打得慢的手語,其隨后撓撓頭,有些安耐不住笑意,但耐心直到乙方打完了手語為止。結果是,甲方雖然能看懂乙方的手勢所表達的意思,但這種速度過小了。
綜合以上兩場實驗,不管結果怎么樣,那只有一個事實——那就是手語本身存在速度屬性,是手語屬性體系的一個支撐點,又是影響理解的一個重要因素。
5速度和運動
作為手語屬性體系里面的兩個:運動和速度,看似同為一個概念,亦或是一對相似的意思,然而從邏輯學角度或是釋詞學視角來看,卻不是同一個概念,就像速率和速度這兩種也是不一樣的概念。
一般來說,運動是物質或者物體在外部或者內部一定條件(刺激物)之下自發/被動地以某種可見/不可見的方式出現于相應的空間環境當中。
《邏輯學辭典》指出,“物質的存在形式及其固有屬性,也是思維、概念的基本特性。它包括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簡單的位置變動起直到復雜的思維活動止”[1]。
速度在物理學中的概念是指:“速度來表示物體運動的快慢和方向”[2]。
由此可知,運動與速度是不一樣的概念,并不能劃上等同號。但又如若從辯證法立場去考量,此兩者也是一對相輔相成的內在聯系——沒有速度的運動是不存在的,沒有運動的速度亦是不存在的。當然,它們也可以組合起來為“運動速度”。手語的運動、速度的這兩個屬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互相離不開對方(它們亦有自己相對的獨立性)。
再從一個相反的角度來講,不承認速度屬性屬于手語的屬性體系,那么生活中的手語為什么會影響到看手語者的理解或者理解角度呢?為什么看手語者在沒有明白打手語者的時候會看他/她的手勢(其條件為打手語者手上沒有影響手語表達的干擾因素)呢?為什么有很多聾人打手語有的快、有的慢(姑且不論影響手語表達的思維能力的因素,也不論手語慢而思維快的情況)呢?所以,這個不承認的觀點將不符合速度屬性作為人類社會語言發展進程的客觀性質——手語的屬性體系之一的客觀事實,即接受手語有速度這一客觀屬性的不可改變的事實。這樣便可讓手語的屬性體系進一步完善,并為手語作為一門社會語言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6申明結論
速度這個屬性應作為手語屬性體系之一部分,即“5+1”:手形、朝向、動作、運動、位置加上速度等六個要素構成的屬性體系。無論聾人個體還是個體和個體之間,又或聾人群體之間,他們在表現手語的時候,便有六個要素的交叉式運用、互相作用,構成聾人可以看得見、感知到帶有速度性的完整手勢的外在表現。這個“5+1”新概念的出現,或許能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手語研究門路(方法)提供進一步的想法與新穎的研究視角。
7手語研究一般性思路
對于手語有沒有速度屬性的這個現實理論問題,首先應該進行必要的實踐,然后據此恰當調整(改變)原有認識并升華新的認識,再進行與原有實踐相互聯系而又有自己的特色的、嶄新的實踐,最后再得出新的認識,并下符合客觀規律的新的結論。這是對于證明手語是否有速度屬性、影響理解所應有的方法論的研究思維的一種體現,即“實踐——認識——實踐”[3]。這種方法是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新延伸出來的一條“子方法論”,也可以適用于手語研究這個領域。
當然這種方法論不是教條,而是基于符合客觀世界和客觀社會兩大物質形態及其一般規律而形成的動態的、辯證的、發展著的“辯證方法”,這種方法能夠為手語在將來發展變化整體過程中發生了新變化、新情況的時候,能夠提供一套與時俱進的、近乎客觀規律的一般性闡釋(論證)。這是對手語作為一個物質過程而存在所引發的相關問題、亦包括對屬性體系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的一條“應走的路”。
研究手語,必須要有歷史的、唯物的、發展的研究眼光和研究思維,這樣便可得出正確性大于錯誤性的結論,比較好地實現推動整個手語研究事業發展起來,取得比較好的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
在研究手語的時候,能否正確發揮主觀能動性所引起的可能性結果,會決定是否可以引導手語進入接軌于整個人類社會語言發展軌道上來。現在正處于新時代最好的歷史方位,也是最為關鍵的階段,應當且必須抓住時代機遇來推動展開一場“手語運動”,甚至“手語革命”——這是一種手段,而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社會、世界對手語的公眾知曉率以及提升聾人在社會甚至世界的應得之地位,形成比現在還要進步、全面一些的聾健群體融合之協調性格局,這本身就是手語研究、發展的客觀要求。
參考文獻:
[1] 編輯委員會 編:《邏輯學辭典》,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頁。
[2] 參見百度:https://baike.baidu.com/。
[3]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作者注:“實踐——認識——實踐”為對該文之總結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