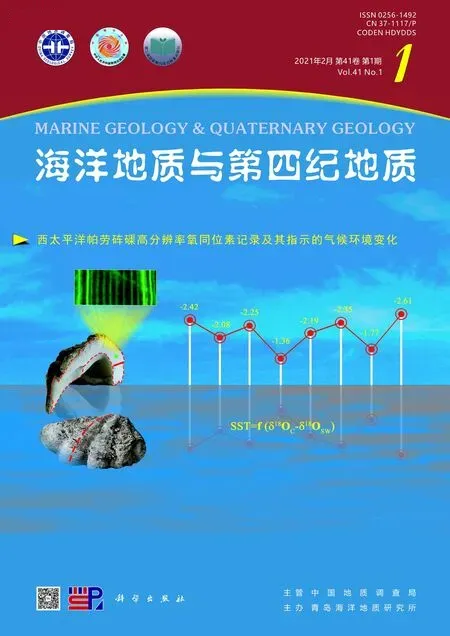全球變暖和海洋酸化背景下珊瑚礁生態響應的研究進展
李言達,易亮
1.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北京 100871
2.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南京 210008
3. 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92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所排放的大量CO2及其他溫室氣體進入大氣圈后,對全球變暖產生了重大影響;就海洋而言,伴隨海水溫度和大氣CO2濃度的升高,極端事件更加頻繁且劇烈,海水水體也逐漸酸化[1]。作為海洋系統的重要組成,珊瑚礁具有巨大生態和經濟價值,也是海洋生態系統中最脆弱的一環,不可避免的遭受到全球變暖和海洋酸化的全面影響[2-3]。近年來,大量學者從全球增溫和海洋酸化背景下的珊瑚礁生態響應過程與機制等方面開展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認識。例如,有研究預示,受全球變暖和海洋酸化的嚴重干擾,21世紀生物礁生態系統中的珊瑚含量將大幅下降[4];雖然,應對這一不可逆過程并維持珊瑚礁的生態功能需要借助科學、社會和政府多方面的全力合作[5],但由于在過去珊瑚礁響應全球變化等重要細節不清晰,目前預測珊瑚礁的發展仍有許多不確定性[6]。這些認識不但為珊瑚礁的保護和預測提供了理論支持,也為揭示過去全球變化中珊瑚礁記錄的古環境過程及其可能反饋奠定了基礎。因此,本文將從全球變暖和海水酸化兩個主要方面,對近年來獲得的這些研究進行總結,嘗試為珊瑚礁古環境研究中“將今論古”這一方法論提供支撐。
1 珊瑚對全球變暖的響應
伴隨全球增溫的顯著,海洋極端高溫事件(marine heatwaves, MHWs)也更加頻繁和劇烈[7-8]。這一熱脅迫可能會使造礁珊瑚的共生藻遺失,即珊瑚白化現象。近三十年以來,全球大多數地區的珊瑚礁均受到了較為嚴重的白化威脅[9];但不同地區的白化歷史也有所不同:其中,大西洋的白化風險最高,太平洋其次,印度洋和澳大利亞周邊則風險較低;不過在澳大利亞周邊及中東地區,白化風險已經迅速增加(圖1)。倘若熱脅迫持續存在,白化的珊瑚最終將面臨死亡,對珊瑚礁生態系統造成毀滅性打擊[4-6]。因此,研究珊瑚白化對全球增溫、海水變暖的響應特征與機制是預測未來珊瑚生存狀況的基礎。
1.1 高溫脅迫引發珊瑚白化的生物學機制
對于熱脅迫而言,珊瑚白化在分子及細胞層面的機制,目前研究還很不充分。一些研究認為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可能在珊瑚白化中有重要影響[10-11]。根據這一活性氧假說,高溫及強光導致共生藻葉綠體吸收更多能量,累積過量電子,生成更多氧氣;高濃度的氧氣產生活性氧,并向珊瑚細胞中擴散;珊瑚自身的線粒體也可在高溫脅迫下產生活性氧。共生藻以及珊瑚中的活性氧在細胞層面造成的氧化損傷,可以最終誘導珊瑚白化。高溫或強光脅迫下,共生藻主要是通過胞吐或類似機制被珊瑚宿主完整地排到珊瑚細胞外[12],其他可能還包括藻類的原位降解、藻類被珊瑚宿主釋放到胞外、含有藻類的宿主細胞脫離珊瑚體,以及含有藻類的宿主細胞凋亡或自噬等[11]。不過,單細胞層面上的研究卻表明活性氧可能并不是引發珊瑚白化的初始因素[13],當高溫脅迫已經引起一定程度白化時,珊瑚內的活性氧濃度并無顯著上升,且無明顯的氧化損傷。

圖1 2015—2016年白化事件中全球珊瑚礁的白化程度統計[9]Fig.1 Global coral bleaching in 2015 and 2016[9]
1.2 珊瑚對溫度上升的適應性
按照適應白化假說,不同的共生藻類群對溫度(或其他環境因子)有不同的適應能力,珊瑚也能調節其共生藻群落組成(如Tong等[14]):為適應環境,珊瑚通過白化失去共生藻,隨后從外界獲得新的共生藻。Baker[15]的移植實驗中,從深水向淺水移植的珊瑚,在這種應激策略下,雖然短期白化率較高,但共生藻類隨后發生的轉變,促使珊瑚長期存活率也有提高;相反,從淺水向深水移植的珊瑚,雖然短期內沒有經歷白化,但其長期存活率較低。這些結果支持了珊瑚白化現象本身是一種高風險的適應機制。同時,野外觀測也表明,在高溫導致的嚴重白化和死亡事件后,珊瑚中耐熱的共生藻更為豐富[16-17];并且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珊瑚白化后的耐熱性增加是由共生藻群落組成的變化所導致,而不僅僅由于熱脅迫引起的珊瑚自身變化[18]。
此外,珊瑚還可通過其他機制適應環境。例如,生活在溫度更高且變率更大的潟湖環境中的風信子鹿角珊瑚(Acropora hyacinthus)對熱應激白化的耐受能力更強[19],1~2年內就可獲得對熱應激的耐受能力,可能與其基因表達的變化有關[20]。通過短期熱馴化(7~11天),細枝鹿角珊瑚(Acropora nana)表現出廣泛的基因表達變化,表明這類珊瑚可能具有多級適應機制[21]。形態學方面也可觀察到類似的熱適應特征,如熱馴化后的鹿角杯形珊瑚(Pocillopora damicornis)的胃層增厚,可能有利于保護共生藻[22]。
另一方面,全球變暖也可使一些珊瑚的抗白化機制失效。例如,Ainsworth等[23]發現過去30年間大堡礁75%的熱應激事件都可歸入“保護軌跡”:先有一個低于珊瑚白化閾值的亞高溫,約10天的回落期后,溫度再升高到白化閾值以上;這種情況下,前一個亞高溫有助于珊瑚獲得耐熱性,降低珊瑚細胞的死亡及共生藻的損失。但0.5 ℃的全球變暖可能就足以使得“保護軌跡”轉變為“單一/重復白化”軌跡[23]:亞高溫的缺失導致抗白化機制的失效,造成珊瑚直接白化或死亡。
1.3 全球變暖抑制珊瑚的自我恢復
盡管小幅變暖可能會促使珊瑚鈣化率升高,但安達曼海[24]和紅海[25-26]的珊瑚鈣化率下降可能與溫度上升直接相關。這是因為珊瑚鈣化中的pH調節過程通常依賴于共生藻的代謝活動,當溫度超過閾值并疊加海水酸化的影響時,珊瑚的鈣化過程將被抑制[27]。
同時,珊瑚幼蟲的再定殖對于珊瑚白化后的恢復非常關鍵:白化事件后,成年珊瑚的死亡將直接導致新生珊瑚幼蟲的數量減少;如果連續發生熱脅迫,下一年珊瑚幼蟲的存活率也會降低[28]。例如,2016年和2017年連續2次白化事件后,大堡礁的珊瑚幼蟲定殖量僅為過去20年平均水平的11.3%,一些耐熱性較差的種群下降幅度更大[29];倘若這種惡性循環得不到實質性緩解,整個珊瑚礁系統將最終崩潰。
1.4 溫度上升改變珊瑚礁的群落結構
海水增溫也將改變珊瑚礁的群落結構:某些珊瑚種類占比大為降低[30-31],這類以分支狀珊瑚為主,如鹿角珊瑚(Acropora gemmifera、A. digitifera)、萼柱珊瑚(Stylophora pistillata)等;另一類以團塊狀及皮殼狀珊瑚為主,種群占比相對增加,如橫小星珊瑚 (Leptastrea transversa)、 澄 黃 濱 珊 瑚 (Porites lutea)、琉球扁腦珊瑚(Platygyra ryukyuensis)、海孔角蜂巢珊瑚(Favites halicora)等。同時,熱脅迫下的珊瑚白化也會促使微生物群落發生改變[32]。如,有益細菌可能會減少,而珊瑚致病菌(pathogen)或機會致病菌(opportunistic pathogen)則可能增加[33]。此外,珊瑚群落結構的變化也可影響與珊瑚相關的其他動物的種群、多樣性與行為模式等[34-36]。
例如,大堡礁2015—2016年白化事件中,珊瑚群落改變的程度與熱脅迫呈正相關,嚴重白化(>60%)的珊瑚礁群落明顯改變,未受白化影響的珊瑚礁則變化較小[37]。同時,珊瑚礁白化后,藻類覆蓋率大幅增加,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的空間分布格局也隨之改變[38](圖2)。從長期來看(10年以上),海水溫度恢復正常后,雖然珊瑚礁群落的物種豐度可恢復到白化前的水平,但主要構成已轉變為耐熱種、能快速生長的本地殘余種,及從附近遷移進入的新種[39]。在長期的生態系統修復中,塞舌爾的案例表明一部分嚴重白化(>90%)的珊瑚礁可以恢復到了由珊瑚主導的狀態,另一部分則轉變為了由肉質大型藻類主導的生態系統,Graham等[40]認為這種差異可能與珊瑚礁的群落復雜性或水深等要素有關。
2 珊瑚對海洋酸化的響應
珊瑚的鈣化率由珊瑚的骨骼密度與生長速率兩項參數決定。生長模擬[41]和野外觀測[42-44]表明不同pH值影響下的珊瑚文石晶體結構沒有明顯區別,也沒有溶解的跡象,因此,海水酸化并不會顯著影響珊瑚骨骼的生長速率;但其形態結構卻發生改變,即骨骼變薄、骨骼孔隙度增加、骨骼密度降低(圖3)。此外,珊瑚幼體在酸化條件下的骨骼形態結構不但發生了變化,骨骼表面也出現溶解跡象,可能說明珊瑚幼體更加脆弱[45]。因此,海水酸化影響下珊瑚鈣化率的變化并非只是簡單的物理化學溶解過程,還與珊瑚發育機制有著密切聯系。

圖2 海表溫度上升對珊瑚礁群落的影響[3]Fig.2 Effects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creases on coral reefs[3]

圖3 海洋酸化對珊瑚礁的影響[3]Fig.3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 on coral reefs[3]
2.1 珊瑚鈣化對海水酸化的抵抗力
珊瑚骨骼鈣化過程并非直接發生在海水中,而是在珊瑚體內的胞外鈣化流體(extracellular calcifying fluid)與腔腸中的海水被反口面內胚層、中膠層和外胚層分隔開[46]。多種實驗結果均表明,珊瑚鈣化流體中的pH值要高于環境海水,原位微電極和pH敏感染料測得的pH值較日間瞬時鈣化流體高約0.6~1.2[47-48],而硼同位素測得的pH值較長期平均值高約0.3~0.6[49]。當海水pH值下降時,鈣化流體中的pH值下降幅度要小于環境海水[15],使得骨骼鈣化實際發生處的文石飽和度維持在相對較高水平。珊瑚細胞膜上由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驅動的Ca2+/H+反向轉運泵應當參與了pH值的調節過程[46]。
McCulloch等[49]在考慮珊瑚的pH自我調節功能的基礎上,建立了IpHRAC模型用以模擬不同要素影響下的珊瑚鈣化響應。結果表明:假定溫度恒定,CO2增加引起的海水酸化將導致珊瑚鈣化率下降,但下降程度比其他沒有pH調節能力的鈣化生物低一半以上;若同時考慮水溫和CO2的增加,珊瑚鈣化率基本保持不變,對于部分珊瑚種類還可有小幅上升。同時,CO2增加可以促進珊瑚共生體的光合作用,協助抵消海水酸化的影響[50]。此外,澳大利亞西部珊瑚礁的野外研究表明,20世紀期間的濱珊瑚(Porites)鈣化率非但沒有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還升高了,表現為鈣化率和海表溫度距平的正相關關系[51]。
這些研究強調了當溫度增加不太多時,珊瑚自身pH值調節功能在全球變暖背景下可以部分抵消海水酸化對珊瑚鈣化率的影響。
2.2 海洋酸化抑制珊瑚幼蟲發育
實驗研究表明,珊瑚的精子活動[52-53]、受精過程[54-55]、幼蟲代謝[56-57]、變態[57]、定殖與其后生長[54,56],特別是側向生長[57],都受海水酸化的控制。野外觀察證實酸化條件下的珊瑚幼蟲定殖效率較低[58]。作為珊瑚幼蟲的主要附著基質[59],殼狀珊瑚藻因為高鎂方解石含量較高而對海水pH值的變化非常敏感[60-64]。珊瑚生長的模擬實驗也觀察到海水酸化將導致的殼狀珊瑚藻相關的微生物群落改變,并抑制珊瑚幼蟲的附著[65-66];表明海洋酸化可能會對受損珊瑚礁的恢復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盡管成年珊瑚的頂端生長和整體的鈣化率對海水酸化的響應并不顯著,但其生活史的早期過程對酸化程度卻十分敏感[67];在評估海洋酸化對珊瑚生長的影響時,不僅需要考慮珊瑚的整體鈣化率,還需特別注意生長階段的差異性。
2.3 海洋酸化引發珊瑚礁的溶解
雖然活體珊瑚對海水酸化有較強的抵抗力,但自然條件下,疏松的珊瑚骨骼將對溶蝕作用更為敏感[68]。礁相沉積也是珊瑚礁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死亡珊瑚的骨骼、其他生物殘體及各類碎屑組分。雖然活體珊瑚為應對海水酸化可以主動調節自身pH值,但珊瑚礁中沒有生命的部分顯然不具有此類功能;因而海水酸化對珊瑚礁的影響不僅反映在活珊瑚鈣化率的變化上,也表現為礁相沉積的溶解過程[69]。
研究表明,對于活體珊瑚,即使在酸化水體中生長7個月至一年以上,文石晶體的形態也無明顯變化[41,70];但死亡珊瑚的骨骼在酸化水體中僅放置3個月,其文石晶體就已經發生明顯溶解[70]。模擬實驗的結果也表明珊瑚礁中的活體珊瑚比例越低,礁體對于海水酸化越敏感[68]。
Eyre等[71]、Cyronak和 Eyre[72]分別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多個珊瑚礁中,向礁相沉積放置的有機玻璃腔通入CO2,通過控制局部海水pH值,獲得了碳酸鹽巖溶解程度與海水文石飽和度的負相關關系。按照這一認識,目前珊瑚礁沉積總量已比工業革命前有所下降,并在21世紀中期可能轉為凈溶解,由此導致整個珊瑚礁系統的徹底破壞[71-72]。
此外,Albright等[73]通過潟湖海水的CO2注入實驗,進一步驗證了海洋酸化會降低珊瑚礁系統的總體凈鈣化率。相反的,若加入NaOH使海水pH值恢復至工業革命前的水平,整個珊瑚礁系統的凈鈣化率顯著升高[74]。這或許表明增加珊瑚礁周圍海水的堿度是一種珊瑚礁保護的有效措施。
2.4 海洋酸化改變珊瑚礁的群落結構
總體而言,生長較快的珊瑚更容易受到海水酸化的影響[75-77],而在對海洋酸化有較強抵抗力的物種中,抵抗酸化的機制也不盡相同[78];因而,珊瑚對酸化的響應具有顯著的物種特異性。在海洋酸化的背景下,珊瑚礁中對酸化敏感的物種會相對減少,抗酸性強的物種則會相對增多,生態系統內的多樣性隨之降低[79],而多樣性的下降則可能進一步抑制珊瑚的生存和生長,形成惡性正反饋[80]。與珊瑚共生的微生物群落結構在這一過程中也可能發生改變,從而影響珊瑚的生理或健康狀況[81]。
同時,通過研究與海底火山活動相關的CO2噴口或滲漏點附近的天然珊瑚礁群落特征(圖4),人們發現隨著海水pH值的降低,珊瑚礁生態系統將由珊瑚主導轉變為大型藻類主導[82],珊瑚群落構成由造礁珊瑚轉變為非造礁珊瑚[83],珊瑚的多樣性顯著降低[84],礁體發育停滯[84]、侵蝕增強[85]。此外,與珊瑚礁相關的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86-87]以及下層浮游動物[88]的數量以及多樣性總體上也有減少。盡管這些研究反映的是與海水的空間pH值變化相關的群落差異,而非珊瑚礁群落在時間上的變化,但這一結果仍強烈暗示了全球海洋酸化可能導致珊瑚礁系統發生類似的群落結構變化。
3 珊瑚礁演變預測
珊瑚礁的預測主要基于耦合不同要素的環流模型(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GCMs)[89-90],或基于詳細觀測的局地數值計算[91-92]。在這些預測中,早期通常簡單地使用周熱度指數衡量珊瑚的白化閾值[89-90],而未能考慮極端高溫事件的頻率、局地的水動力條件、海洋酸化的協同效應,以及珊瑚自身演化和適應。新近研究指出,局地的水動力條件復雜多變[93];海水酸化影響下的珊瑚更易受到生物侵蝕[68];珊瑚種群的恢復速率并非一成不變,也會受到白化影響[29]。與全球平均溫度逐漸升高的趨勢相比,珊瑚種群對極端高溫事件的反應更為強烈,在極端高溫事件頻發的 RCP(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溫室氣體排放情景)8.5情景下,珊瑚不太可能從白化事件中恢復過來[91]。不過,Woesik等提出RCP 6.0情景下珊瑚覆蓋率或許足以維持在可觀水平[91];但Kubicek等[92]堅持認為只有能快速適應的珊瑚群落才能在RCP 6.0或更高情景下生存,適應慢的珊瑚群落即使在RCP 2.6情景下也令人堪憂。因此,對珊瑚礁未來變化的預測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5],未來需要獲得更多、更精確的約束條件等關鍵數據,具體包括珊瑚礁演化對過去全球變化的響應過程、珊瑚生態系統對現在全球變化響應的深層機制、珊瑚及其他藻礁生物的進化特性等。
4 結論與展望
伴隨著海洋水體的增溫和酸化,全球珊瑚礁系統均遭受較為嚴重的威脅。其中,對于高溫強迫而言,海水溫度上升誘發珊瑚白化、抑制珊瑚的自我修復,影響珊瑚礁的群落結構;另一方面,海洋酸化可以顯著降低珊瑚鈣化率、抑制珊瑚幼蟲發育、引發珊瑚礁的溶解,也可改變珊瑚礁的群落結構。在這些過程中,珊瑚自身可以通過調控共生藻的種群轉換與基因表達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高溫脅迫,但對于高溫誘導珊瑚白化的生物學機制目前還不清楚。此外,較低程度的升溫也有助于提高珊瑚對酸化的抵抗能力,并最終影響珊瑚白化后的恢復。

圖4 海底火山通風口處CO2排放量對生物礁群落的影響[82]Fig.4 The influence of CO2 released from submarine volcanic vent on coral reef taxa[82]
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目前已經建立了珊瑚白化事件與海洋變暖之間的半定量關系,并意識到隨著全球變暖,珊瑚白化的頻率與嚴重程度也在逐漸升高。根據模型結果推測,倘若溫室氣體的排放不受控制(RCP 8.5),絕大多數珊瑚礁到21世紀末都將遭受災難性打擊。為更好地應對珊瑚礁保護,構建未來不同場景下的珊瑚礁預測模型,闡明不同類別珊瑚礁對高溫、酸化等關鍵因子的響應機制是此間要點之一。
然而,現代觀測僅能覆蓋過去數十年至一百年的區間,這些數據在有效約束模型方面仍存在極大的局限性。例如,過去數億年間,海洋的水化學特征可能控制了珊瑚的骨架特征與種群進化[94];另一方面,中中新世(16.0~11.6 Ma)是全球氣候的溫暖期[95],但也是西太平洋珊瑚礁發育的極盛期[96-97]。由此推測不同地史時期內的珊瑚礁對全球變暖和海洋酸化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響應特征和機制。因此,加強珊瑚礁的長序列研究可以為珊瑚礁演化預測提供有益的關鍵補充,特別是在彌補現代觀測的不足、刻畫珊瑚礁長周期演化特征、揭示珊瑚礁響應全球變化的長期機制等方面展示更為精準的邊界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