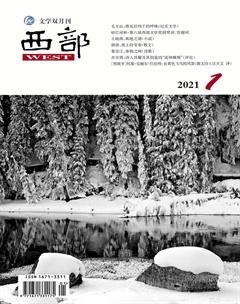它們追求的愛遠大于愛本身
張勇敢
東部施工時間
我把這種生活當作
抵達孤獨的必經之路:
催熟的柿子,澀味在齒間蔓延
畢業后,我們開始各自的生活
新鮮的、枯燥的、偉大的、渺小的
在今夜統統卸下了它們的面具
成為我們飯后閑聊的談資
回首過去的幾年,我們也是這口中
催熟的柿子,在城市的枝頭
被生活無情地搖晃著
阿楚,窗外西禪寺的輪廓
在夜色中依舊清晰可辨
這多像此刻的我們
不愿融入無盡的黑暗中
阿楚,今夜兩座在海上相遇的孤島
它們追求的愛遠大于愛本身
火,以及詞語
南下,在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地點,我們帶著某些溫暖的詞
南下。帶著它們
以備在冬天這樣的季節,顯得從容
很多年前,祖先教會我們如何生火、如何
建造房屋,以及用糧食釀酒
將肉煮熟,就著酒水痛快地吞下
誰能在冬天吃飽穿暖,誰就是英雄
野蠻的年代,火是我們的武器
是慈悲又暴躁的母親,甚至宗教
一把火,熊熊燃燒
順著群山的眉頭越過千年
無數的原野,在野火燒盡之際
詞語,橫飛
同時又具備了火的某種屬性
代替太陽,在寒冷時將我們一一縫合
那些詞
踏著古老祖國的軀體走來
落在紙上成了喂養精神的食糧
刻上石頭便是永垂不朽的豐碑
冬天,我們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
比如從肩膀,進入一棵樹
仔細觀察,它的年輪變老的過程
比如致敬一條河流,最好在下雨天
讓泥沙成就歷史,帶來山和高原
再比如,到夕陽最接近夜晚的部分
扎進去,去熬、去摘星
冬天,有些人選擇成為柵欄
以陪伴湖水的方式紀念森林里的雨露
風起時,便揚起了身子,放生一只飛鳥
有些則涌成浪,一層蓋過一層
用白的、輕的色彩
將老而舊的骨頭堆成——另一個母親
或者把自己染成黑色,為黎明
揭竿而起,賭上金錢、房屋、性命
連同自由和浩瀚的宇宙
這,便是冬天
冬天,我們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
成為了眼前的飄雪
成為了遠處的冰川
宋荔*短章
它古老的根須
尚存對宋朝土壤的敬意
在西禪寺內筑塔、修廟
立地成佛
同樣古老的雨,從它
鏤空的腹部穿過
辨認一場前世的巨大寒潮
此刻立于天地間,唯有我
如此年輕
也唯有我如此渺小,轉瞬
即逝
*宋荔,位于福州西禪寺的一棵古荔枝樹,
傳說種植于北宋天圣年間。
小春詩
春天到了
寫桃花如何盛開
寫春江水暖與鴨的先知
春天到了
寫我們的戀愛
吻和失眠
愛與恨都不加任何修辭
春天,對事物的如實陳述
已是一種贊美
春月夜,與眾兄飲
或飲茶,或飲酒,飲一年之計
在于春。飲竹林外桃花三三兩兩
飲它們初登枝頭時攜來的新鮮感
春月夜,客居山城,與眾兄飲
我們有在信中相逢的喜悅
此刻,醉與不醉
僅是兩個詞的爭論
“老板,再給我們上一壺春色
三兩月光”
對鼓浪嶼的近距離觀察
秋,一只溫度偏高的虎
在祖國南部被流放
島是它暫時的王國
它的低吼頻頻軋過我的耳膜
一年之中,唯有此時的海灘才能擁有
最柔軟的沙子,供它行走
我們在最高處圍觀、夜飲
說一些適宜的話
你酒杯中的海岸線悄然蔓延
秋天,在鼓浪嶼
一些遠的風吹著一些近的風
大片礁石在海風中交出了
自己柔軟的部分
十二月的黃昏短章
這是世界上的,第四個黃昏
前三個已從神壇退下,變成了
春天、夏天和秋天
這是人類歷史上僅剩的一個
坐在海邊,看一場謝幕表演
黃昏與我,成為彼此最忠實的觀眾
風偶爾吹一吹,云偶爾走下松木梯子
來到人間
十二月了,在海風均勻地吹拂中
萬物開始染上冰冷的秩序
重慶回憶錄
其一
出了后門,往右走
是鴻林老火鍋
往年冬天我們常聚在這里
擺龍門陣,喝山城啤
一座座小火山在舌尖相繼爆發
此刻,無人關心世界的秩序:
毛肚、鴨腸、耗兒魚
被隨意地擺放
它們構成夜晚最自由的姿態
重慶在紅湯鍋底中肆意翻滾著
你我也從不刻意隱藏
滿臉通紅,醉意醺醺
飯后從店里出來,不規則的天空
你說,若要下雪
便三三兩兩飄些雪花吧
若不下,我們在山城夜景中晃著
也無妨
其二
生活中唯有這樣的時刻
才完全屬于我們:
霧鎖山城
清白的霧浮于我們的掌紋
嘉陵江卻深陷其中
在生命線跌落懸崖之際
一條江在另一條江的體內
完成了自己的謝幕
這多美啊,無數被稱之為鳥的橋
在大霧中飛著
只要飛著,時間和方向
就是無關緊要的事
有時候,我們在重慶相愛
但更多時候,我們
在重慶的大霧中散步
什么話也不說
其三
沿著南濱路,我們開始奔跑
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
此時,我們是長江遺落在
陸地上的兩滴水
被重慶小心翼翼地捧著
在重慶,夕陽落在誰的身上
誰就被愛著
我們時而停下來
看江上的船,順流而下
江上的船時而停下來
看我們成為長江的第三岸
但始終,萬物都有
彼此無言的默契
在巨大的無邊的沉默中
我們突然就愛完了這一生
我愛你
我愛你,以及一切以“玫瑰”來命名的風
他們總是無理由地吹起,又散開
我愛你,愛這個世界在冬天的時候
把自己覆蓋成雕像的整個過程
我愛你,如同在夜里反復咀嚼糧食,咀嚼
具有相同屬性的形容詞
我愛你,因此,一首詩涉及的所有意象
都必須承擔超過自身重量近百倍的意義
一首詩里,一部分的美好被稱之為太陽
另一部分,則由你和春天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