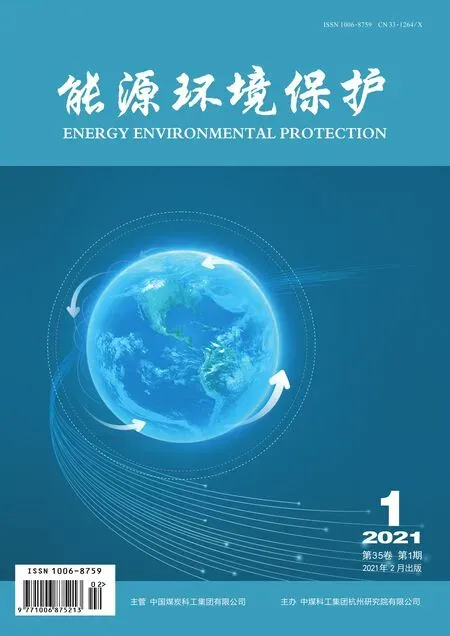淺析安徽省工業能源消費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
馬建中,王 琨,2,朱 虹,2,黃 和,胡槐生,2,徐 波,2,溫 泉,2,賈 利,朱宇軍
(1.中國能源建設集團安徽省電力設計院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省能源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
0 引言
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消費總量呈逐年增加的趨勢,造成了相關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也表示中國將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這意味著我國在為減緩氣候變暖影響的貢獻上,加快了“減碳”的快進鍵。隨著我國82個省市開展低碳建設,制定各省市的行業碳排放清單和企業碳排放核查成為當前“減碳”工作的重點。現有研究認為90%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于工業活動化石燃料的燃燒,工業能源消費是當前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
安徽省作為我國中部能源消費大省自2004年以來工業能源消費快速增長。根據安徽省統計年鑒顯示,全省能源總消費從2004年的6 209萬噸標準煤增加到2018年的13 228萬噸,平均增長率約為6%。截止2018年,工業能源消費占比為63%。安徽省《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方案》提出,2020年安徽省碳排放單位總值需比2015年下降18%。在此背景下,建立適合安徽省地區尺度的工業能源消費與碳排放的關聯模型對于制定能源政策和“十四五”規劃十分重要。
目前影響碳排放的因素主要研究方法為因素分解和計量經濟學方法。本文通過環境庫爾茨曲線及因素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Index,LMDI)對不同產業和經濟指標與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強度關聯進行了分析。發現碳排放量與人均產值(GDP)、產業結構、能源消費結構及基礎研發投入存在較強的關聯,且安徽省接近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拐點。本文的研究結果對實現安徽省低碳綠色發展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 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1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美國經濟學家G.Grossman 和A.Kureger通過研究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的倒U型的關系提出的函數方法。本文中為環境質量隨著經濟增長的積累呈現的變化趨勢,其表達式如下所示:
污染物=α1+α2GDP +α3GDP2+β
(1)
1.2 因素分解法
根據Grossman和Krueger對污染物排放因素的公式分解,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分解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如下式(2)表示:
CO2=Y×S×T
(2)
本文沿襲Crossman和Kureger研究思路將經濟社會發展對CO2的排放拆分為若干因素且遵循上述模型。
1.3 CO2排放量估算
工業能源消耗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由兩部分組成。一類是化石燃料的燃燒和消耗的逸散過程,本文中統計的為主要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類。另一方面為熱力和電力供應企業消耗隱含的電力生產時二氧化碳排放。公式3可估算出安徽省工業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CFEC=∑EFi×CEFi
(3)
式中,CFEC為工業能源消耗的CO2排放量,單位tCO2;EFi為碳排放系數,tCO2/t;CEF為工業能源消費量。根據《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能源消費的CO2排放系數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系數
1.4 數據來源
本文2004~2018年安徽省工業能源消費及經濟社會指標(GDP等)相關數據來源于《安徽統計年鑒》。在核算過程中采用煤炭、原油等13類能源消費。碳排放系數來源于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
2 結果與分析
2.1 安徽省能源消費及CO2排放量分析
通過安徽省2004~2018年能源消費相關數據估算出安徽省歷年來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量變化情況,結果如圖1所示。安徽省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量從2004年的2.26億噸增加到2018年的5.35億噸。從圖中可以看出,2004至2013年間,安徽省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加,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0%。這階段安徽省工業GDP也從2004年的1 736億元增長到2013年8 928億元,工業產值占比也從31.3%大幅增長到46.2%。可以得出,安徽省在2004~2013年間的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加是由于工業產值的急速增長引起的。
能源消費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13年出現拐點。此后五年內,CO2排放量的平均增長率下降至1%。此階段,安徽省工業產值占比46.2%下降至38.9%。通過對化石能源種類的貢獻分析,煤炭類能源CO2排放貢獻從2004年的66.2%增加至2013年的77.8%后又緩慢下降至2018年的77.3%。

圖1 安徽省2004~2018年度不同能源消費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貢獻Fig.1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energy consumption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18

圖2 2004~2018年度安徽省煤炭類消費對二氧化碳排放的貢獻及能源結構碳強度Fig.2 Contribution of coal consumption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nd carbon intensity of energy structure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18
上述結果過可以得出安徽省CO2排放主要來源于煤炭類能源的消費。如圖2所示,能源結構中碳強度(即碳消費量能源占比)與煤炭對CO2排放的貢獻的比例走勢基本一致,煤炭消費比例上升帶動了能源結構碳強度從而導致了CO2的大量排放。
2.2 CO2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分析
通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一步分析安徽省碳排放與產業增長之間的關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描述了人均GDP與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聯,其模型表達如下所述:
CO2=a+b×GDP+c×GDP2
(4)
CO2=b×GDP+c×GDP2
(5)
式中,GDP為人均GDP,單位為萬元,CO2為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單位為噸。根據庫茲涅茨模型,上述方程中系數項c<0,此時庫茲涅茨曲線形狀為倒“U”型,出現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拐點,如圖3所示。我省人均CO2排放量拐點(ε)可由式6計算而得:
ε=-b/2c
(6)

圖3 安徽省二氧化碳排放庫茲涅茨曲線Fig.3 Kuznets curv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in Anhui Province
由式6分別計算出兩種模型下的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為3.25和3.59萬元。上述結果表明,當人均產值小于3.6萬元,人均CO2排放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當人均產值大于3.6萬元時,人均CO2排放會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開始降低。截止2018年我省人均GDP為4.23萬元,已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右側,未來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人均CO2排放量會進一步走低。這一結果對于認識和了解安徽省碳排放情況十分重要。但是隨著近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及中央對未來幾年我國經濟將處于低速增長的判斷,3.6萬元的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拐點需要進一步驗證,下文將從多個分解因素來分析安徽省二氧化碳排放趨勢與關聯。
2.3 研發投入對CO2排放量的影響
圖4展示了安徽省2004~2018年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的變化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安徽省的碳排放量逐年增加從2.26億噸增加到5.35億噸,同時碳排放強度持續走低,從2004年的4.76噸CO2/萬元降低至2018年的1.78噸CO2/萬元。
這一結果表明隨著產業的快速發展,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會逐漸降低,其原因是由于產業經濟的發展,工業技術得到提高,在投入相同數量的原材料下,工業經濟提升的同時碳排放量有所下降。為了進一步考察這一關聯,圖5展示了研發投入(R&D)與單位能耗與碳排放強度的負相關性,其表達式如下方程:

圖4 安徽省2004~2018年度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變化Fig.4 Change of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18
碳排放強度=-200.6×R&D+6.15
(7)
單位能耗=-66.7×R&D+1.63
(8)
由圖可得,R&D投入每增加1億元單位能耗和CO2排放強度將分別下降66.7噸標準煤/萬元和200.6噸CO2/萬元。試驗研發投入顯著影響碳能耗和碳排放強度,因此加大研發投入促進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實現低碳經濟。
2.4 CO2排放量因素模型分析
根據本文的上述研究成果,在規模方面考察了人均GDP,將結構因素分解為工業產值占比和能源結構碳強度,而技術要素考察了研發投入(R&D)的關聯。因此,本文中關于碳排放強度與規模、結構及結構效應的函數為:

圖5 2004~2018年度安徽省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強度與碳排放強度和單位能耗之間的線性擬合Fig.5 Linear fitting between R&D expenditure intensity,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unit energy consumption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18
lnCO2=α0+α1lnYi+α2lnSi+α3lnSt+α4lnTi+ε
(9)
式中,CO2表示二氧化碳排放強度,α0是截距項,ε是隨機項,Y是安徽省人均GDP表示規模效應,S是產業結構分別由工業產值占比(Si)和能源結構碳強度(St),T表示我省R&D投入強度。X變化量的殘差范圍見圖6。

圖6 多元線性回歸變量(人均GDP、工業產值占比、能源結構碳強度、R&D強度)殘差圖Fig.6 Residual diagram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variables(per capita GDP,industrial output value ratio,carbon intensity of energy structure, R&D intensity)
對上述變化量做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預測法(線性回歸預測)。根據表2協整檢驗結果,本文所選取的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面板協整實驗,可以選擇線性回歸進行預測分析。

表2 協整檢驗結果
圖6展示了X變化量的殘差范圍,可以發現預測范圍較好,誤差較小。結合偏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預測法,得出2019~2022年碳排放強度變化趨勢,如表3所示。2019年碳排放強度為0.497 tCO2/萬元,比2018年下降14.9%。而到2022年我省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至0.283 tCO2/萬元,比2018年下降51.5%。安徽省在未來4年中由于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和改變能源結構碳強度將會有效降低工業能源消費碳排放。雖然總體上碳排放強度降低,但是由于產業經濟的發展,GDP會繼續增加這使得安徽省在工業碳排放總量控制上依然需要加大碳減排力度,爭取實現“十四五”減碳目標。

表3 2019~2022年安徽省碳排放強度預測結果
3 結論
本文按不同工業化石能源種類的消費量計算了安徽省2004~2018年間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分析了其變化趨勢。根據本文研究結果可以得出安徽省工業能源消費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但在2013年出現拐點后增長趨勢顯著下降。這一現象是安徽省在2013年后煤炭類占能源消費總量比例下降引起,能源結構碳強度是安徽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環境庫爾涅茨曲線簡單模型分析得出安徽省二氧化碳排放拐點在人均GDP產值3.25~3.59萬元之間。碳排放因素分解結果表明,規模效應-人均GDP、結構效應(能源結構碳強度及工業產值占比)和技術效應(R&D投入)是影響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預測結果表明安徽省的碳排放強度在未來4年內會進一步降低。根據以上結論,為實現安徽省的低碳經濟發展和實現碳中和遠景目標提出如下建議:
(1)產業結構方面,工業能源消費碳排放量與工業產值占比存在緊密的關聯,雖然截止2018年,工業產值比重已經降到38.9%,但是依然高于第三產業。因此需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利用經濟結構轉型機遇提高科技型制造業和第三產業比例,降低傳統高能耗產業比重,從而在總量上控制碳排放。
(2)根據本文研究結果可知,煤炭類消費比例在安徽省能源消費結構中依然過高,2018年能源結構碳強度為56.3%,未來我省在能源結構方面可以通過政策引導,因地制宜提高新能源(如風能、太陽能)比例。尤其是繼續加大基礎試驗投入,改進工藝技術,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促進低碳經濟發展。
(3)環境經濟學分析結果表明安徽省經濟增長存在碳排放和能源消費的剛性需求,強制化的碳減排工作必然會以阻礙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為代價。因此在保持人均GDP增長的同時,減緩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通過降低能源強度和煤炭消費比例而實現的。由于安徽省重工業對煤炭的依賴性使得技術改進尤其是提高化石燃料效率應該是未來我省科技發展規劃的重要方向。